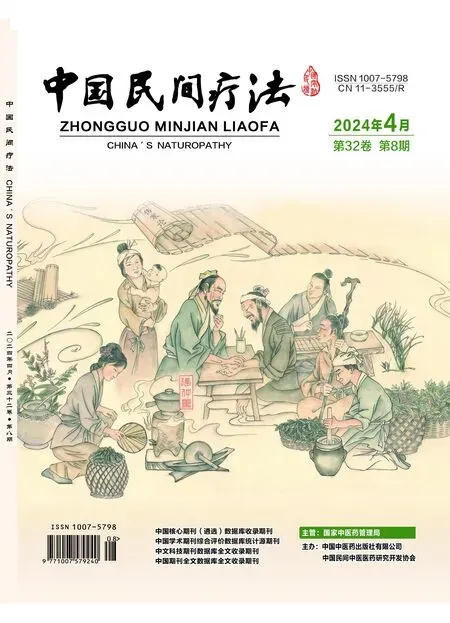王燦暉治療哮喘慢性持續期常用藥對的經驗總結
陳凌昊,劉玉瀅,殷立平
(1.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2.南京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17)
王燦暉教授是全國著名中醫溫病及中醫內科專家,投身中醫藥事業60余載,對中醫理論有精辟獨到的見解,臨證重視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方式,在遵循傳統配伍的基礎上靈活參考現代藥學理論,圓法施治,在治療肺系疾病方面收效顯著,經驗頗豐。
1 哮喘慢性持續期概述
哮喘慢性持續期是哮喘急性發作期常見的轉歸,是評估哮喘預后的關鍵時期,具體表現為患者雖沒有哮喘急性發作,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有不同頻次和不同程度的喘息、氣急、胸悶、咳嗽等癥狀,并伴有通氣功能下降[1]。
王燦暉教授認為哮喘慢性持續期可歸于中醫“哮病”“喘證”“咳嗽”等范疇。哮喘發病是由外邪犯肺、引動伏痰、肺氣郁閉、肺失宣肅所致。哮喘慢性持續期病因為肺脾腎虛損,宿痰內伏,表現為不同程度的咳嗽、喘息、氣急、胸悶,勞累、飲食不當、氣候變化、情緒波動等因素均可誘發。對于哮喘慢性持續期的治療,王燦暉教授遵循未發當以扶正氣為主、治本不離標的原則,以益氣清肺、化痰祛風為治法,在臨床用藥過程中結合藥物的傳統功效和現代藥理作用,兩兩配伍,協同增效,療效顯著,茲將王燦暉教授治療哮喘慢性持續期的常用藥對介紹如下,以窺一斑。
2 藥對舉隅
2.1 益氣
(1)生黃芪-太子參 生黃芪,味甘,性微溫,歸脾、肺經,能補脾益肺,固表止汗,《藥性賦》曰:“(黃芪)溫分肉而實腠理,益元氣而補三焦……外固表虛之盜汗。”太子參,味甘、微苦,性平,歸脾、肺經,功擅補氣健脾,生津潤肺,《飲片新參》謂其能“補脾肺元氣,止汗生津,定虛悸”。
王燦暉教授指出,哮喘慢性持續期患者雖仍以咳嗽、喘息、胸悶等肺臟虛損表現為主,但發病與脾腎密切相關,“脾為生痰之源”,脾臟虛損,水液停滯,化為痰濕,腎攝納失常,則氣無所主,肺失宣肅。多數醫家認為黃芪主補肺脾之氣,太子參養肺脾之陰。與人參不同,黃芪補氣力道綿柔而穩健,得土之正味,在補中之余能兼顧余下四臟,《藥性論》提及黃芪“內補,主虛喘,腎衰,耳聾”,可見其補益元氣之效。《本草從新》言:“太子參,雖甚細如參條,短緊結實,而有蘆紋,其力不下大參。”兩藥合用,調補肺脾腎三臟,補肺氣,固肌表,健脾胃,益腎元,為治療哮喘慢性持續期經典藥對。藥理研究結果顯示,黃芪皂苷Ⅱ能夠減少血清中炎癥因子的表達,從而減輕氣道炎癥,減少肺組織病理損傷[2]。實驗研究表明太子參參須提取物包含多糖、皂苷等活性成分,不僅可以改善體液免疫功能,還能增強小鼠抗氧化功能[3]。臨床上哮喘慢性持續期患者多有肺脾腎虛損表現,凡此類氣虛證候者均可使用生黃芪及太子參,常用劑量為生黃芪15~20 g,太子參20 g。
(2)菟絲子-五味子 菟絲子,味辛、甘,性平,歸肝、腎、脾經,能補益肝腎,固精縮尿,《本草蒙筌》言其“氣平,無毒,益氣強力,補髓添精”。五味子,味酸、甘,性溫,歸心、肺、腎經,具收斂固澀、益氣生津、補腎寧心之效,《神農本草經》將其列為上品,言其“主益氣,咳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男子精”。
王燦暉教授強調,宿痰內伏為哮喘發病之本,但其根源在于腎氣虧虛,腎陽不足。因此,哮喘慢性持續期治療的關鍵在于改善患者的腎虛體質。菟絲子主入腎經,于滋補之中,又有溫運陽和之意。五味子主收耗散之氣,哮病者,本虛而標實,腎氣虧虛,不足以固攝一身之氣,而“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本草備要》言其“斂肺氣而滋腎水”。此藥對取自五子衍宗丸,王燦暉教授在臨床運用時將兩藥配伍,肺腎同治,澀中寓補,以補助澀,適用于虛咳虛喘患者,常用劑量為菟絲子10~15 g,五味子6 g。
2.2 清肺 金銀花-酒黃芩。金銀花,味甘,性寒,歸肺、心、胃經,具有清熱解毒、疏散風熱的作用,《本草正》言其“善于化毒,故治癰疽、腫毒、瘡癬、楊梅、風濕諸毒,誠為要藥”。黃芩,味苦,性寒,歸肺、膽、脾、大腸、小腸經,具有清熱燥濕、瀉火解毒之效,《藥類法象》言其“治肺中濕熱,療上熱、目中赤腫、瘀肉壅盛必用之藥”。
王燦暉教授指出,哮喘臨床多為陽熱表現,且伏痰日久,易趨化熱,故清肺之法當貫穿哮喘治療始終。金銀花,質輕上浮,性寒而潤,被譽為“清熱解毒第一花”,在《神農本草經》中被列為上品,甘潤清涼而不傷正。黃芩苦寒,能解諸多熱毒,《本草蒙筌》言:“枯飄者名宿芩,入手太陰,上膈酒炒為宜”,酒黃芩借酒力上行,主入肺經。兩藥合用,協同清肺,瀉上焦伏火。藥理研究結果顯示,金銀花乙醇提取物能降低哮喘模型小鼠炎癥因子水平,同時能使小鼠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的嗜酸性粒細胞趨化因子水平顯著下降至接近正常水平[4]。黃芩提取物黃芩苷作為一種苦味受體激動劑,可激活苦味信號傳導系統,促進呼吸道炎性細胞凋亡,減輕肺部炎癥和損傷,緩解哮喘發作[5]。臨床上凡見哮喘慢性持續期患者復感風熱之邪或熱郁于肺,均可使用金銀花-酒黃芩,常用劑量為金銀花10~15 g,酒黃芩10 g。
2.3 化痰
(1)枇杷葉-款冬花 枇杷葉,味苦,性微寒,歸肺、胃經,能夠清肺止咳,降逆止嘔。《滇南本草》言其“止咳嗽,消痰定喘,能斷痰絲,化頑痰,散吼喘,止氣促”。款冬花,味辛、微苦,性溫,歸肺經,長于潤肺下氣,止咳化痰,《本草蒙筌》用之以“潤肺瀉火邪,下氣定喘促”。
王燦暉教授認為,治肺宜潤,“肺為嬌臟,喜潤而惡燥”,同時哮喘慢性持續期患者表虛而易受風邪侵襲,風為陽邪,易化熱化燥。枇杷葉與款冬花同為涼潤之品,擅清肺潤肺,《本草綱目》記載枇杷葉“和胃降氣,清熱解暑毒”,同時兼具降氣之效,能夠順應肺臟宣發肅降的特性。款冬花化痰止咳,潤而不寒,藥性平和,順應肺臟多種特性。葉廣億等[6]研究發現枇杷葉水提物能夠延長咳嗽潛伏期和引喘潛伏期,從而發揮鎮咳和平喘作用,同時其通過酚紅實驗驗證枇杷葉具有祛痰的功效。款冬花有效成分總倍半萜能夠阻斷促炎因子信號向胞內的傳遞,減少炎癥細胞的過度激活,從而抑制炎癥因子分泌,使哮喘炎癥進一步緩解[7]。哮喘慢性持續期或咳或喘者,均可酌情加用,常用劑量為枇杷葉10 g,款冬花10 g。
(2)魚腥草-金蕎麥 魚腥草,味辛,性微寒,歸肺經,具有清熱解毒、消癰排膿的作用,《滇南本草》言其“治肺癰咳嗽帶膿血,痰有腥臭”。金蕎麥,味微辛、澀,性涼,歸肺經,功專清熱解毒,排膿祛瘀,《本草拾遺》稱其“主癰疽惡瘡毒腫”。
王燦暉教授指出,除了肺脾腎三臟虛損,痰邪上犯也是哮喘發病機制之一,若調護不當,常可復發,如《諸病源候論》言:“肺病令人上氣,兼胸膈痰滿,氣機壅滯,喘息不調,致咽喉有聲,如水雞之鳴也。”故化痰為治療哮喘慢性持續期另一重要的原則。魚腥草與金蕎麥均為治肺癰要藥,擅清熱排痰,兩藥相須為用,協同增效。藥理研究結果顯示,鮮魚腥草揮發油能降低炎癥介質釋放,減輕氣道慢性炎癥,能抑制白細胞三烯D4,推測其可能通過緩解呼吸道平滑肌痙攣,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減少呼吸道黏液分泌和抑制呼吸道平滑肌增殖等作用,從而降低氣道高反應性[8]。動物實驗研究表明,金蕎麥能發揮鎮咳、祛痰作用[9]。臨床上見咳喘兼痰熱未清者,可予適當加減,常用劑量為魚腥草20 g,金蕎麥20~25 g。
2.4 祛風 炙地龍-蟬蛻。地龍,味咸,性寒,歸肝、脾、膀胱經,長于清熱定驚,平喘,《本草綱目》謂之“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故其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諸熱疾,下行故能利小便”。蟬蛻,味甘,性寒,歸肺、肝經,具有疏散風熱、利咽開音之功效,《本草備要》言其“蟬乃土木余氣所化,飲風露而不食。其氣清虛而味甘寒,故除風熱”。
王燦暉教授認為,哮喘慢性持續期患者體虛而伏痰未清,外風時而襲肺,引內風,聚痰飲,《證治匯補》記載“內有壅塞之氣,外有非時之感,膈有膠固之痰”,內有風邪與肝關系密切,故在補益肺脾腎的同時,適當兼顧肝氣升散的特性,使補中有散。蟲類藥物是中醫藥學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具有辛散走竄、搜風通絡等特點,常被用于治療慢性病證。地龍性寒下行,利尿瀉肺平喘,蟬蛻質輕,其氣上浮,又為土木余氣所化,能散肝經風熱。兩藥合用,平肝疏肝,祛風化痰平喘,能有效防止哮喘再發。藥理研究結果顯示,地龍有顯著的舒張支氣管作用,并能對抗組胺及毛果蕓香堿引起的支氣管收縮,地龍提取液能有效抑制哮喘小鼠氣道炎癥,阻礙氣道重塑發生[10-11]。蟬蛻水提物具有明顯的鎮咳、祛痰作用,同時推測其平喘作用機制可能是通過抑制過敏介質的釋放來發揮效應[12]。臨床上凡見氣急而喘、痰多色黃,無論處于發作期還是緩解期,均可使用,常用劑量為炙地龍10 g,蟬蛻10 g。
3 驗案舉隅
患者,女,39歲,2022年6月20日初診。主訴:咳嗽氣喘間歇發作2年余。患者2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咳嗽、咳痰、胸悶、氣喘,伴有喉間哮鳴音,于外院診斷為支氣管哮喘,經特布他林擴張支氣管,甲潑尼龍抗炎平喘,配合化痰、抗感染等治療好轉后出院,其間規律使用孟魯司特鈉片和糖皮質吸入制劑,2年來咳嗽氣喘間歇發作。刻診:咳嗽,咳痰,痰少色黃,質黏,偶有胸悶氣喘,夜間無憋醒,咽癢,怕熱,平素易感冒,舌質紅,苔薄黃膩,脈弦細。既往體健。查胸部X 線片:雙肺紋理增多。西醫診斷:支氣管哮喘慢性持續期。中醫診斷:哮病(緩解期),證屬表虛內熱。治則:益氣清肺定喘。方藥組成:太子參20 g,五味子6 g,魚腥草20 g,金蕎麥20 g,矮地茶20 g,枇杷葉10 g,款冬花10 g,炙百部10 g,炙地龍10 g,蟬蛻10 g,酒黃芩10 g,木蝴蝶6 g。14劑,水煎,每日1劑,早晚分服。
2022年7月5日二診:患者服藥后咳嗽、氣喘等癥較前明顯好轉,咳痰量少質黏,痰液黃白相間,平素汗多,易感冒,倦怠乏力,舌質紅,苔薄黃膩,脈弦細,在初診方基礎上稍做調整。方藥組成:生黃芪15 g,太子參20 g,五味子6 g,麥冬10 g,荊芥10 g,防風10 g,炙地龍10 g,蟬蛻10 g,金銀花15 g,酒黃芩10 g,款冬花10 g,生百部10 g,金蕎麥20 g。21劑,煎服法同前。門診隨訪3個月,患者經服藥后,咳嗽、咳痰、氣喘等癥不顯,哮喘控制良好,效不更方,守方繼進,另囑患者清淡飲食,忌魚蝦,避風寒,慎起居,暢情志。
按語:哮喘反復發作,日久則正虛與邪實互為因果,相互為病,虛中有實,實中夾虛,痰邪內阻,郁而生熱,熱邪煉液成痰,痰熱膠著,且哮喘患者容易合并肺部感染,或因上呼吸道反復感染而致哮喘反復。本案患者系體虛易感,哮病反復發作,日久可由實轉虛,肺虛則腠理不實,表邪乘虛而入,脾虛則積濕生痰,上貯于肺,中焦樞機不利,氣機升降失常則氣喘,且又值夏日,外邪入里,濕困久蘊化熱,郁熱征象明顯,故治療時以生黃芪、太子參補脾益肺,五味子、防風固護肌表,魚腥草、金蕎麥、枇杷葉、款冬花清肺潤肺,化痰平喘,酒黃芩、金銀花肅清郁熱,同時慢性持續期內咳嗽氣喘間歇發作,有哮喘發作之征,故以炙地龍、蟬蛻平肝疏肝,祛風化痰利咽。諸藥合用,標本兼治。
4 小結
哮喘慢性持續期,虛實夾雜,虛多實少。王燦暉教授治療哮喘慢性持續期,首重肺脾,兼顧肝腎。“五臟皆令人咳,非獨肺也”,肺臟嬌嫩,易受侵襲,余臟不安,肺氣亦難順暢。王燦暉教授指出,以上6組藥對遵循益氣清肺、化痰祛風治療原則,不僅能夠順應肺臟特性,還能健脾、益腎、柔肝,為調暢肺氣奠定基礎,在補益正氣的基礎上輔以化痰祛風,標本同治,提高哮喘控制水平。筆者有幸跟隨王燦暉教授學習,根據其臨床治病用藥特點,將其藥對分類梳理,但臨證還需系統辨證論治,由于各證表現及患者體質不同,強調一人一方,不可拘泥于藥對模板,還需整體審查,對證遣方用藥,加減化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