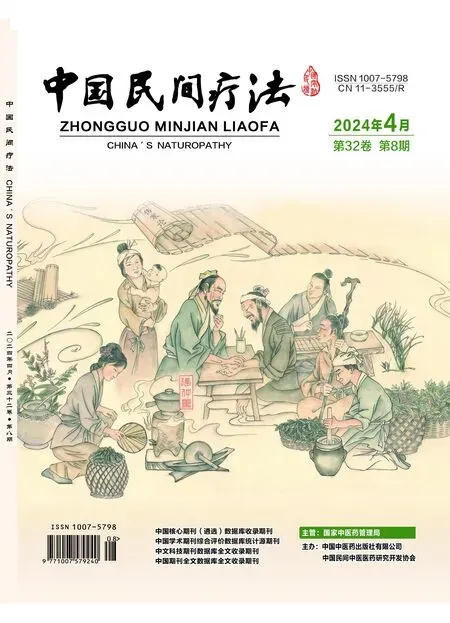刮痧對拔罐罐印的影響※
彭婉瑩,丁夢,吳端懿,蔣昕,甘沛艷,葉少劍,朱青艷
(江漢大學,湖北 武漢 430056)
刮痧療法是一種用特制的刮痧板刺激人體體表的經絡與腧穴,將阻滯于經絡的病邪從體表祛除,疏通局部經絡的氣血瘀滯,緩解疼痛的傳統中醫外治法。刮痧療法歷史悠久,使用簡便。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將刮痧作為養生康復的方法。現代醫學認為,刮痧對循環、呼吸中樞具有鎮靜作用,可直接刺激末梢神經,起到調節神經、內分泌系統的作用,此外,刮痧還能改善血管緊張度與黏膜通透性,降低血壓,但其確切機制尚不明確,實際應用也缺乏具體的指導[1]。本研究觀察刮痧對拔罐罐印的影響,從毛細血管脆性的角度研究刮痧的作用機制及拔罐罐印的形成原理,以期為刮痧防治相關疾病提供依據,也為臨床“辨痧診病”以罐印作為反映血管狀態的動態指征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2022年9—11月隨機招募江漢大學醫學院2019—2021 級學生21 名,其中男10 名,女11名,平均年齡(20.4±1.01)歲。本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中的相關倫理要求[2]。
1.2 納入標準 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關于人體健康的10條標準[3];血壓、體溫正常,一般檢查無明顯異常;無血小板異常及其他基礎疾病(高血壓病、糖尿病、高脂血癥或其他嚴重疾病);以右前臂肘窩下4 cm 處為中心,-5 kPa抽氣拔罐20 s,拔罐罐印出血點計數>10個。
1.3 排除標準 前臂拔罐、刮痧、血壓檢測處表面皮膚有皮損、瘢痕等異常者;皮膚過敏體質者。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過程 受試者首先進行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和拔罐罐印出血點檢測,然后實施刮痧。于刮痧后第7日,待局部皮膚反應消退,皮膚瘀斑消失后,接受第2次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和拔罐罐印出血點檢測。以上測試均在室內平均溫度25 ℃左右、受試者安靜放松的狀態下進行。
2.2 刮痧 分別消毒受試者左右前臂,將刮痧油均勻地涂抹于刮痧區域,用牛角刮痧板(8 cm×5 cm)較薄的長邊刮拭皮膚,刮痧板微微傾斜,以45°角最佳,調節刮痧力度,應盡量均勻,從肘窩向下至前臂中點處反復刮拭,直至局部皮膚出現細小的紅色結節瘀斑或簇集狀紅色斑點。
3 研究結果
3.1 觀察指標 ①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計數。將葉少劍等[4]的方法稍加改良,以受試者左前臂肘窩下4 cm 處為中心畫1個直徑為5 cm 的圓圈,仔細觀察圓圈內皮膚有無出血點,如發現有出血點則用標記筆標記。將水銀血壓計袖帶縛于左上臂,測量血壓,然后使血壓維持在收縮壓與舒張壓之間,時間為8 min,解除壓力5 min后計算圓圈內皮膚新出血點數量并記錄。②拔罐罐印出血點計數。拔罐罐印出血點個體差異較大。預實驗發現,初始拔罐罐印出血點較少時,刮痧后拔罐出血點變化不大,因此選擇初始拔罐罐印出血點>10個者作為受試對象。拔罐后局部皮膚迅速形成罐印,且發紅,有肉眼可見的出血點形成。以受試者右前臂肘窩下4 cm 處為中心用水彩筆畫1個直徑為5 cm 的圓圈,仔細觀察圓圈內皮膚有無出血點,如發現有出血點則用標記筆標記。根據葛泉希等[5]的研究,拔罐壓力值為(-5~-4)k Pa時,刺激量適度,可產生罐印,且患者可耐受。故本研究選取直徑為5 cm 的氣罐置于標記處,連接康健牌DGN-6多功能負壓電動拔罐器,調節負壓值穩定為-5 kPa。預實驗發現,拔罐時間過短,罐印出血點太少,不能反映變化趨勢,拔罐時間太長,出血點過多,不宜計數,故保持抽氣拔罐20 s,取罐后觀察5 min,計算圓圈內皮膚新出血點數量并記錄。
3.2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刮痧前后數據比較采用Willcoxon檢驗,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和拔罐罐印出血點采用Spearman相關性分析,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M(Q1,Q3)]描述,檢驗結果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3 結果
(1)刮痧對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的影響 受試者初始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為10.00(7.00,14.50)個,刮痧后降至8.00(4.00,12.50)個,刮痧前后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2.849,P<0.01)。
(2)刮痧對拔罐罐印出血點的影響 受試者初始拔罐罐印出血點為34.00(20.00,54.00)個,刮痧后降至10.00(4.50,16.50)個,刮痧前后拔罐罐印出血點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4.017,P<0.05)。
(3)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和拔罐罐印出血點的相關性分析 刮痧前,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與拔罐罐印出血點具有相關性(P<0.01),表明拔罐罐印出血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毛細血管脆性水平。刮痧后,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及拔罐罐印出血點均明顯減少,但二者的相關性不再顯著。這可能與刮痧療法的個體差異反應有關。
4 討論
4.1 刮痧的作用機制與毛細血管脆性的關系 歷代醫籍中有很多關于刮痧療法的記載。早在唐朝,人們就運用苧麻刮治痧癥,并稱為“戛”法。清代后刮痧療法治療的病證增加,并出版了《痧脹玉衡》《養生鏡》兩部刮痧專著。清·郭志邃在《痧脹玉衡》中曰:“刮痧法,背脊、頸骨上下及胸前脅肋、兩背肩臂痧,用銅錢蘸香油刮之。”刮痧療法借助刮痧工具對體表的特定部位反復進行刮、擠、揪、捏、刺等良性刺激,使皮膚表面呈瘀點、瘀斑狀態,達到解表祛邪、化瘀散結的目的[5]。
現代醫學認為,刮痧過程使血管擴張,毛細血管逐漸破裂,血液溢出,這種現象導致局部皮膚出現瘀血,而血栓迅速溶解和自溶,刺激局部的新陳代謝,產生新的具有抗炎和免疫調節功能的刺激物,從而起到消炎、免疫調節等作用[6]。刮痧引起的毛細血管出血與毛細血管脆性密切相關。毛細血管脆性主要反映皮膚微血管在應對血管內壓力增加時保持其結構和功能完整性的能力或彈性程度,并與血小板有關。當血管變得缺乏彈性或變脆,或血小板數量減少時,血管壁更易因血管內壓增加而破裂,表現為出血點。血管內皮是毛細血管壁的主要結構,所以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反映了內皮的結構和功能狀態[7]。
本研究結果顯示,刮痧后,受試者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顯著減少,表明刮痧的作用機制與改善血管內皮功能有關。這為臨床應用刮痧療法治療原發性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等疾病提供了實驗依據。作為一種簡便、價廉、無明顯不良反應的中醫外治法,刮痧療法用于防治心腦血管疾病的應用也值得期待。
4.2 拔罐罐印與毛細血管脆性的關系 拔罐罐印即起罐后吸拔部皮膚出現的點片狀紫紅色瘀點、瘀斑或水泡、血泡,可伴有不同程度的微熱痛感[8]。臨床多數醫家認為,拔罐罐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機體的不同狀態和疾病的治療效應[9-10]。
目前拔罐罐印的產生機制并不十分明確。火罐吸拔時產生的負壓可使局部毛細血管的通透性發生變化,毛細血管發生破裂,少量血液進入組織間隙,從而產生瘀血,這種拔罐引起的毛細血管出血被認為與罐印的形成密切相關[11]。也有學者認為,罐印的產生與罐內負壓、溫度、留罐時間長短及淺表毛細血管的分布、血管通透性、血管脆性和血小板數量有關,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2]。
本研究結果顯示,刮痧前,拔罐罐印出血點與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顯著相關。這與任天星等[7]對罐印實質上反映皮膚的毛細血管脆性的認識是一致的。該結果為臨床以拔罐罐印作為觀察指標,研判患者血管內皮的結構和功能狀況提供了依據。刮痧后,拔罐罐印出血點與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沒有明顯相關性,提示毛細血管脆性只能部分解釋罐印形成的原因,刮痧可能存在個體反應性的差異,其具體作用環節及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
4.3 刮痧對拔罐罐印出血點的影響 刮痧與拔罐均會產生局部瘀血和出血。刮痧主要通過機械刺激、熱效應擴張血管,漸至局部毛細血管破裂而產生組織瘀血。拔罐是利用負壓,使罐內皮膚表淺靜脈回流受阻,造成局部皮膚瘀血,微小血管管內壓增高,甚至使毛細血管破裂,產生出血點,即罐印。兩法均通過專門的操作主動使局部皮膚至瘀,又借由出血釋放局部壓力和瘀滯而“化瘀”,被認為是“以瘀治瘀”的典型中醫外治法的代表[13]。
本研究結果顯示,刮痧后,局部拔罐罐印出血點顯著減少,提示刮痧與拔罐在作用機制方面相關聯,對毛細血管脆性的影響可能是其共同的作用環節。筆者推測,通過刮痧刺激,可激活機體防御調節機制,使血管內皮適應性增強,毛細血管脆性降低,從而使拔罐罐印出血點減少,罐印變淺。
從中醫角度看,刮痧、拔罐均屬瀉法,皆作用于皮部,反應在血絡,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這類方法都包括化瘀、出血、溶血等作用環節,且迅速啟動一系列相關調節機制,起到對包括血管內皮功能在內的整體良性調節作用,體現“以瀉為補”“小瘀防大瘀”理論,也為臨床預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一種安全、方便的思路與方法[14-15]。
4.4 “痧診”與拔罐罐印出血點 “痧”有多重含義,現代多指“痧象”或“出痧”。2010年我國頒布的《針灸技術操作規范第22部分:刮痧》中“出痧”的定義為“刮痧后皮膚出現潮紅、紫紅色等顏色變化,或出現粟粒狀、丘疹樣斑點,或片狀、條索狀斑塊等形態變化,并伴有局部熱感或輕度疼痛”。張秀勤[16]認為,痧是滲出于血脈之外的離經之血,含有體內毒素。另有學者提出,刮痧可改變局部區域的皮膚顏色,“痧點”是由局部毛細血管的擴張或破裂,局部皮溫升高、血液灌注量增加所致,可促進局部血液循環和能量代謝[17]。從毛細血管出血點的角度看,刮痧、拔罐、毛細血管脆性試驗所產生的皮膚出血點均屬于“痧”的范疇。
痧象的診斷也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盧春霞等[18]認為,可通過出痧的部位結合經絡系統確定病位,通過痧象面積、形態、顏色辨別病性虛實、病情輕重、體質類型,通過板下手感、患者自感疼痛性質辨別病情。與之異曲同工的是,陳澤林[19]提出拔罐罐印“察痧辨病”的概念,根據拔罐施治后的痧象進一步判斷疾病的部位、性質等,可以為后續的治療方案及預后提供依據。“痧點”一旦形成,皮下血管充血、出血所產生的“痧”等作為刺激源,可激活不同的生物學通路,產生生物學效應,達到防病、治病的效果[20]。可見,“痧點”既是接受刺激后產生的體表反應點,又是激活機體進行整體調節的持續性刺激源,且因不同體質、疾病而有差異。這使得對痧象的觀察有著診斷、治療的雙重意義。
本研究結果顯示,刮痧前,拔罐罐印出血點與改良毛細血管脆性試驗出血點呈正相關,刮痧后,二者同步減少,提示拔罐罐印出血點變化可反映毛細血管脆性及血管內皮的結構與功能,直觀體現刮痧的療效。這與臨床常見的以罐印判別體質及觀察療效的經驗是相符合的。相較于刮痧后的痧象,罐印痧象簡單易得。從復雜痧象觀察中抽取的罐印出血點計數,能通過負壓和量化時間進行控制,可作為動態觀察血管內皮功能的指征,視為“痧診”的具體應用,而刮痧痧象、拔罐痧象的內涵及實質可能遠不止于此,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