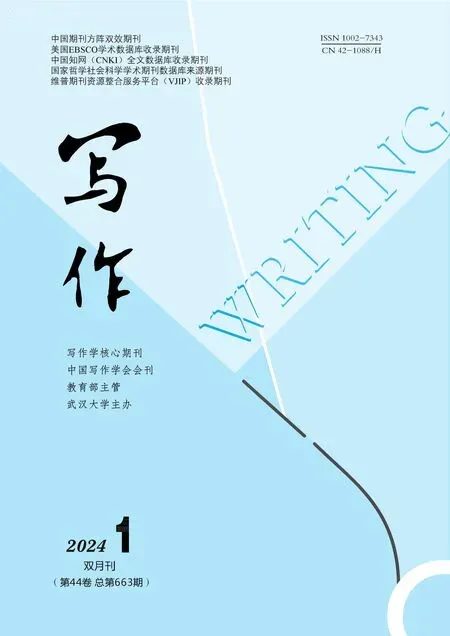解構與反抗:抗戰時期東北在地作家城市風景書寫
王 琪 王桂妹
21世紀以來,“風景學”逐漸成為國內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著名人類學家溫迪·J.達比認為風景是“文化權力的工具”,是一種“‘社會和主體身份賴以形成’,階級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實踐”①[美]溫迪·J.達比:《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張箭飛、趙紅英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因此,風景不再被簡單地當作視覺對象,而是被當作一種文化力量的工具,具有特定的文化意義。這也為我們從“權力—風景”的視角重新觀照抗戰時期的東北在地作家的城市風景書寫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論依據。抗戰時期,陷于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東北城市,由于特殊的社會歷史和地理環境,聚集了大量的日本、朝鮮和俄國人,形成了眾聲喧嘩、相互碰撞的多元復雜景觀。日本侵略者為了奴化東北民眾,不僅組織了一支軍國主義的“筆部隊”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還讓來到東北的日系文人為其殖民政策涂脂抹粉,對殖民侵略行徑進行美化書寫,刻意營造百姓安居樂業、經濟發展的欣欣向榮的“如畫風景”。這些宣揚殖民野心的作品描摹出一種表面的、外在的,同時也是虛假的摩登都市風景:歐式的建筑群,現代大廣場,有軌電車,散發著西洋味道的舞廳、咖啡館和悠閑自在的吃茶店等等,如日本作家竹內正一所描寫的,“新城大街的電車道旁,仍然有很多的大買賣開著板,綢緞莊呀,五金行呀的窗飾,在明亮的燈光里,緞子和銀鈿工物閃閃的放著光芒”②竹內正一:《馬家溝》,共鳴譯,《藝文志》1940年第3輯,第217頁。。這種城市風景是日本作家站在殖民者立場的一種畸形扭曲的描繪。一些受到殖民蠱惑與裹挾、迎合殖民政策的中國作家也在當時的期刊中發表了附和式風景,如《新京街頭》(《麒麟》1941年第1卷第2期)中“繁榮熱鬧”的城市風景。而居于東北的朝鮮、俄國等作家則以一種外在的欣賞眼光描繪著東北城市的異國情調:“仰到脖子酸痛才能隱約看到房頂的建筑鱗次櫛比,粗獷雄勁的建筑雕刻仿佛津津有味地講述過去帝俄時代的故事。路面一塵不染,即使食物掉在上面撿起來吃也無妨。”①[朝]嚴時雨:《哈爾濱的異國情調》,《偽滿洲國朝鮮作家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頁。俄國詩人阿列克桑德拉·巴爾考則在詩中描繪東北城市公園“別致的小橋躍躍欲飛,/曲折的人工池塘如溪流蜿蜒,/巴洛克式的涼亭裝飾精美,/人造小山上鮮花盛開”②[俄]阿列克桑德拉·巴爾考:《在都市花園里》,杜曉梅譯,《偽滿洲國俄羅斯作家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 年版,第216頁。。這些“外來者”的描繪無疑變相地迎合了殖民者營構的“如畫風景”。與這些侵略者、迎合者、外來者筆下的風景相反,深感殖民之痛和殖民之惡卻又無力逃離的東北作家,以“在地凝視”的切近與深刻,通過描摹真實而黑暗的殖民風景,解構了日偽營造的“如畫風景”,表達了自身的痛恨和隱形的反抗。
一、黯淡壓抑的生活空間:普通市民的生存困境
如果說,東北淪陷后流亡到關內的“東北流亡作家群”因為融入全國范圍內的抗戰熱潮,而能以一種昂揚的激情表達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以熱烈的懷鄉之情“遠觀”被侵略者踐踏的故鄉風光,那么更多未能離開東北的在地作家只能蟄伏在侵略者的暴政下,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反抗。他們以“在地”的便利“直視”被踐踏的城市“近景”,將目光集中于黑暗污濁、荒誕糜亂的復雜城市空間和不為人關注的暗陬里的悲慘風景,告訴人們這里不過是“罪惡的天堂”“死水的潭”和“吃人的怪獸”③山丁:《拓荒者》,《東北現代文學大系:1919-1949》第11集:詩歌卷(上),沈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頁。。于是,風景便具有了解構的力量和反抗的意涵。
抗戰時期,普通市民占據了殖民城市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生活在狹窄的街道、擁擠的大院、破敗的公寓和陰暗的房屋中,承受著被殖民的苦難現實。身處日本侵略者統治中的東北在地作家山丁、王秋螢等有意識地攝取了城市中這些勉強維持基本生活的普通市民生活景觀,描摹他們充滿沉重與憂郁、頹廢與感傷、絕望與無望色彩的家庭生存狀況。這些黯淡壓抑的風景與其說是一種背景,不如說更是一種隱喻,凸顯著普通市民在殖民壓迫中物質的匱乏與精神的頹唐,作家也借助對普通市民悲慘生活的憐憫表達著對殖民黑暗統治的控訴。古丁在《奮飛·自序》中曾直言書寫小市民的原因:
我是個平凡的小市民,不愁吃不缺穿,但我厭棄著自己以及和自己相仿的人們,這些人們卻又是我最能熟悉的,因為我自身就可以當做一個模特,所以寫的也較多;不過我不大愛這些人物,寫來寫去就流入油腔滑調,倒并非故意向讀者提供笑料的。我之所以寫這些不愁吃不缺穿的人物,目的并不在肯定如是的人生,是希望大約也是不愁吃不缺穿的讀者勾起反省,激起自新之念的,但也并非自居為人生的導師,只是想把文學和玩具分別開而已。④古丁:《奮飛·自序》,《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頁。
作家正是希望通過形形色色普通市民家庭及周遭黯淡壓抑的風景折射黑暗的殖民社會,而這一群體的生存空間風景也成為我們觀察抗戰時期東北普通民眾城市生活的一個重要窗口。石軍即寫道:“我暴露了一層層我認為黑暗的事象,也憫恤了一群群我認為可憐的人物。”⑤轉引自劉慧娟:《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頁。王秋螢《離散》中的主人公萍便處于“墳墓一般的暗室”風景中:“溫暖的陽光,已經填滿了整個的小室,但是這陽光卻抹不掉室內的污暗,一切都是破舊的,破舊的墻壁,破舊的雜物,樣樣都會使他生起一種難耐的焦躁。”①王秋螢:《離散》,《小工車》,益智書店1941年版,第4、5頁。外在黑暗的社會環境與人物親歷的家庭空間在這一刻似乎重疊,“污暗”“破舊”的室內風景與黑暗壓抑的外部社會構成呼應,加上主人公發出的感嘆“人生并不是痛苦的,可是只有我們這一伙人是始終摸不著幸福的邊沿呀!”②王秋螢:《離散》,《小工車》,益智書店1941年版,第4、5頁。這種無力感是那個高壓恐怖時代給予民眾的切身體驗,在那個艱難的時代里,即使是有工作的普通民眾,其生活也是壓抑黯淡的,幸福遙不可及。同樣在小說《滂沱雨》中落雨的街景與主人公徐先生借錢無果的陰郁心情相互映襯:“外面的雨,仍舊是落著,地上的積水,已經如同水池,那沉重的雨點飛擊到上面,便打起凌亂的水花。……他望一望天空,天上卻布滿了濃厚的灰云,這黑灰的天空,正像此時青士的心,簡直沒有一絲光亮。”“雨點的敲擊,似乎敲到他心上一般的焦躁。”③王秋螢:《滂沱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1919-1949》第3 集:短篇小說(中),沈陽出版社1996 年版,第887、890頁。歸家后的屋子:“陰沉的像是死寂的墓地,妻子臉色的冷淡更渲染著空氣的暗淡。……簡陋的家具,破敗的桌椅,灰暗而潮濕的墻壁……這里沒有花,沒有草,沒有陽光。”④王秋螢:《滂沱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1919-1949》第3 集:短篇小說(中),沈陽出版社1996 年版,第887、890頁。作家將主人公焦躁的情緒與風景的陰暗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強烈主觀感受性和體驗性的風景隱喻文本”⑤郭曉平:《隱喻機制:中國現代小說風景書寫的一種敘寫策略》,《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田瑯在小說《夏夜》中不止一次描寫吹口笛的青年工人趙興和老人吳慶豐兩個孤獨者的居住場景:“板筑的下層人住的公寓的樓舍,像一座黑色的、不太堅牢的城堡,寧靜地立在左側。仿佛它已經睡了,除掉二樓和一樓在一條垂直線上的兩扇窗子,宛如兩只黃色的、昏慵的眼睛,亮著燈光,把兩個長方形的光影,相錯疊地印在坎坷的碎石道上以外,所有的窗子都在黝黑里面沉默著。”⑥田瑯:《夏夜》,《東北現代文學大系:1919-1949》第2集:短篇小說(上),沈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頁。公寓這種被擠壓的現代化居住空間看似“現代”實則狹窄昏暗,普通民眾在這個由燈火晦暗的小屋、窄小的窗戶構成的空間中感受到的是無盡的孤寂與壓抑。在殖民社會歷史現實中的普通市民根本無法享受城市的“燦爛”,他們得到的只有生活的窘迫與悲痛的體驗。如小松《鐵檻》中的虎子,從城市返回故鄉,“懷著戰敗的心情,像是一個受了創傷抱著破碎了的夢從戰場歸來的勇士。他是缺了一件東西,都市給了他最大的污辱,而擄去了他壓在心胸最深處的寶藏。這失掉的悵惘,隨著身體的疲倦,像春潮一樣,向他吹卷過來”⑦小松:《鐵檻》,《東北現代文學大系:1919-1949》第5集:中篇小說卷,沈陽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頁。。在東北在地作家們看來,殖民控制下看似“文明”的城市實際充滿欺騙,城市中的普通民眾始終掙扎在貧困、衰敗和腐壞的環境中,丑陋與危險無處不在。
作為有著自覺思想藝術追求和反抗意識的作家,除了描寫逼仄、暗淡的家庭空間風景外,還將家庭空間周圍的風景與人物悲劇相勾連,不斷凸顯普通民眾生活的艱難,拓寬風景的意義空間。山丁的《狹街》就以普通工人劉大哥一家為中心,作家對擁擠污穢的狹街與小院風景進行剪裁拼接,風景中的“每一個場景都為接下來所產生的結果提供了原因”⑧[美]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頁。。伴隨著劉大哥大嫂一家悲劇的加深,“我”眼中的風景也為之變色,與這些普通民眾的卑微身份、悲劇命運融為一體:“世間有一批人們,痛苦的生入污泥里,然后仍悄然的從污泥中消逝掉生命。”⑨辛嘉:《評〈山風〉》,《滿洲作家論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頁。故事開頭“我”在前年夏天搬到了一條骯臟的街上:“這是一條彎曲得如一雙生滿霉瘡的蛇似的狹街。狹街上一間一間緊緊的擠著矮小的暗灰色的房屋,鑲在屋墻上的是狗洞似的窗子,墻根零落的長著幾叢水稗子和爬根草,毛廁的屎尿時時從院里流向污溝。”①山丁:《狹街》,《山丁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0、67、70頁。骯臟的街景成為普通市民悲慘生活的寫照,其中壓抑的風景與層出不窮的悲劇兩相交融,當劉大哥跟著招工的人離開家,留下懷孕的劉大嫂與孩子時:“太陽還不曾沉落,斜射的余輝,在小院的每個屋頂上輕輕的染了一層淺紫色的色彩,好像預防著有一個恐怖的夜色要降臨到這個宇宙似的。”②山丁:《狹街》,《山丁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0、67、70頁。風景似乎預示著災難的降臨,人物命運也與之相連,尤其在劉大嫂被房東謾罵以致流產,劉大哥在礦山病逝后,房屋“外面天上陰濃濃的,灰云鉛板一樣的壓著我的腦袋……”③山丁:《狹街》,《山丁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0、67、70頁。這些沉重壓抑的風景既不是孤立、靜止的畫面,也不僅僅是對氣候、建筑等的單純記錄,而是作家們利用風景符號連接起人物內心世界與社會外部空間形成的獨特景象,作家在書寫中引導著讀者找到風景的意義內核:對普通民眾的憐憫和對殖民者的深切控訴。
作家們城市日常生活的敘事空間及相關風景選擇,與日偽宣傳的現代城市建筑、便利的交通與繁華的購物中心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透過抗戰時期東北在地作家筆下普通市民的生活風景,我們看到的是一座毫無希望、黑黢黢、鬧哄哄、漫天籠罩著鉛灰色的無可救藥的城市,在黯淡壓抑的城市風景下容納著一張張令人無法釋懷的臉龐,他們滿目悲哀、步伐沉重,踽踽獨行于城市中,無法得到救贖。作家將自己的思想情感滲透于風景書寫中,如王秋螢在《去故集》中所說,創作“時時使我陷入與故事里的人物一樣痛苦的境界”④王秋螢:《去故集·序》,益智書店1941年版,第5頁。。這些黯淡壓抑的普通市民的生活風景,直接質疑了乃至解構了殖民鼓吹的“聳立云表的高樓大廈,幅員闊遠的道路區”⑤[日]日向伸夫:《從新京到哈爾濱》,《麒麟》1941年創刊號,第166頁。一類的“如畫”風景。
二、繁華迷亂的消費空間:“文明”城市的精神奴化
在殖民壓迫的境遇中,普通市民在黯淡壓抑的城市風景中艱難度日,有錢有閑的人們則迷失于城市繁華迷亂的消費空間中。隨著殖民侵略的加深,強行植入的殖民現代性使城市加速發展,逐漸形成了聲、色、光、影等交織的風景,不斷堆積、擠壓著現實中被殖民者的生存與生活,而其強烈腐蝕性也使人們在飛速膨脹的現代化進程中迷失、異化與墮落。對于在侵略者鐵蹄下只能做隱晦反抗的東北在地作家而言,被日寇占領的城市“象個魔鬼,在向他招手,讓他作罪”⑥石軍:《脫軌列車》,《燭心集》,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頁。。作家們對殖民城市的消費空間中絢麗的燈光、歇斯底里的音樂、絢爛的舞場等風景進行再現與編碼,鴉片館、舞廳、酒場、咖啡店、飯館和零賣所等消費空間在作品中不斷生成與呈現,進出于這些場所的男男女女,成為連接這些空間的鎖鏈。王秋螢《新聞風景》中的市街暮景便是由“具有狂放聲音的酒館,充滿色情氛圍的舞場,吞吐游人的影院,驚慌飛馳的汽車,高聳暗空中百貨公司的高大建筑”⑦王秋螢:《新聞風景》,《小工車》,益智書店1941年版,第153頁。組成。這些繁華的現代風景附上了一種迷亂的色彩,獲得了意義的賦值:殖民統治下的所謂“文明”城市根本無法為個體生命成長提供正常的環境,只會讓人落入精神與道德淪喪的陷阱。爵青就曾隱晦地諷刺道:“這所謂大都市的風景對我是如何的一種迫害,思維力和記憶力的減退伴著在我負不起的債務和病身……”⑧爵青:《談Standhol》,《爵青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16頁。正是在這些作家的風景透視中,殖民者營構的城市“文明”與“現代”實際是假象,繁華風景中的青年男女遭受著精神傷害才是當時真正的社會現實。
城市中汽車、燈光、廣告等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景觀只是日本殖民者為實現其殖民野心的矯飾,殖民造就的表層“文明”根本不可能帶來真正的現代與平等。古丁《平沙》中主人公白今虛(主人公的名字“白—今—虛”本身實際就構成了一個隱喻)調轉到新城,眼前的風景讓他驚奇:“夜飾光,柏油路……新型的汽車,新式的女發……新調的音樂,新味的咖啡……新樣的樓房,新案的廣告,……”①古丁:《平沙》,《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444頁。然而,這種由殖民者營造的“新奇熱鬧”風景帶給他的直觀感受卻是“大多的住民仍然在卑俗和低賤里”②古丁:《平沙》,《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444頁。。對此,主人公有著一種清醒的認知,喧囂繁華是城市風景的表層,城市中大多數人依舊困苦不堪。古丁運用高超的修辭手法將城市消費空間中令人眼花繚亂的風景描繪得淋漓盡致,引起讀者對風景的關注,思考風景的意義。《莫里》中新京(長春)的大街上“咖啡館的夜飾光里,透出來歇斯底里的音樂”“電燈把大街照耀的通亮。妓館里流動出胡琴聲,仿佛在秋夜雨里啜泣。飯館的鐵勺波波的響,震蕩著大氣。飯館的旁邊,就是零賣所。零賣所門前的紅燈綠燈在眨眼,金字匾晃得一明一暗”③古丁:《莫里》,《古丁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頁。。舞廳、咖啡店、飯館和零賣所等這些消費空間的出現應該是為現代生活服務,但是這種殖民主義裹挾而來的“現代化”,“無處不是淫媚、荒誕、黑暗、污穢”④轉引自[日]岡田英樹:《偽滿洲國文學·續》,鄧麗霞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頁。,恰恰在誘發著人性的墮落,城市中“多少丈夫坐在旅館的床沿上翻看電話簿,想給他的妻妹或另一個女人打電話去,而他的妻卻在電影院里把腰放在別人的臂間。金融交易所里走出在前五分鐘尚為巨富的商人,不留一個遺囑地跑到江沿去就自殺了。童貞女像游戲一樣,就把貞操交給另外一個男人,可是在妓館街拐角的露天飲食店里用餐的勞動者,卻是十年如一日……”⑤爵青:《哈爾濱》,《爵青代表作》,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這正是那個陰郁籠罩時代的城市民眾的精神面貌。繁華迷亂的風景達到一種反諷的效果,日偽宣揚的“文明”不過是空中樓閣,其中彌漫著混亂與不堪。
殖民者眼中的城市風景是消費空間中寬敞的街道、豪華的建筑和便利的交通,實際上伴隨著城市的急遽變化而來的是使人神經錯亂的生活、令人目眩的瘋狂城市風景。尤其是城市繁華迷亂的消費空間提供了欲望的渠道,脆弱的青年們“被引向自己所無法抵抗的物質欲望中”⑥[美]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頁。,烏煙瘴氣的迷亂風景給青年帶來的是可怕的精神迫害。古丁《莫里》的整個故事就發生在殖民控制的“文明”城市中,主人公莫里從壯懷激烈的革命青年變成令人可悲的權力走狗——“滿洲國”的警察,他像狗一樣分食著殖民者吃剩的骨頭,最終徹底淪落為梅毒纏身的鴉片吸食者。當“我”跟莫里走進鴉片館,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幅墮落污穢的風景:
屋里煙騰騰,一股似香非香的煙味撲進了我的鼻孔,樓下橫躺豎臥一群人,有的正在猛勁的抽,有的在閉著眼睛夢游著桃花源,有的西服革履,有的小商人模樣的長衫,有的穿著油泥麻花的像廚子,有的穿著短打像工人。我驚訝了,鴉片的浸蝕,竟遍及所有的階級層……莫里不是我們敬仰過的青年嗎?然而,他居然會走進了金字匾的下面,毫無慚色的走進了金字匾的下面。⑦古丁:《莫里》,《古丁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頁。
鴉片館中污糟的風景使“我”震驚,昔日那個慷慨激昂、催人奮進的青年莫里已經成為鴉片的俘虜,他百無聊賴、精神麻木,渾渾噩噩地沉溺于毒品世界,這是何等的諷刺!鴉片館中眾人沉淪的風景成為殖民壓迫下人們走向毀滅的寓言:殖民者宣傳的城市“文明現代”并沒有使處于其中的青年實現自身理想,相反繁華迷亂的風景不斷侵蝕著他們,最終讓一個被年輕人視作“思想上的恩師”的知識青年迷失于烏煙瘴氣、人際混雜的鴉片館,在“升官”與“發財”中沉淪。對此,作家發出了無奈的嘆息:“坦途走成死路,狂熱誘起幻滅。現實抹煞了空想,虛無吞蝕了銳志。”①古丁:《莫里》,《古丁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頁。殖民統治下的人們被囚禁在巨大的牢籠之中,他們被城市消費空間中的種種欲望引誘,變得精神萎靡、毫無生氣,陷入無法挽回的悲劇。文選派作家王秋螢《新聞風景》中的主人公林禹忱也逐漸淪落迷失在這種墮落的繁華中,他在“彩色的燈光,幽揚的夜曲,飄蕩的煙,濃味的酒,混合著男女的笑語”②王秋螢:《新聞風景》,《小工車》,益智書店1941年版,第155、163-164頁。的俄國風味酒場兼妓館中不由自主地沉淪、悲嘆:“我的生活已經完全走上毀滅的路上了。過去,我不是有著一種崇高的憧憬,一種拯救人類的偉大的企圖么?可是現在完了,連自己都不能自救,每天用鴉片與煙酒來麻醉自我的生之痛苦,這一種慢性的自殺啊!”③王秋螢:《新聞風景》,《小工車》,益智書店1941年版,第155、163-164頁。“文明”城市景觀讓人迷失其中無力脫逃,逐步喪失思考能力與自救意識。東北在地作家的風景書寫至此便具有了雙重意蘊:一方面隱晦地諷刺“文明”城市的精神奴化,另一方面滲透著作者濃重的憂郁。作者視野中城市的“繁華迷亂”與街上男女的嬉笑浪蕩相互交疊的背后是對“文明”城市的批判與知識青年在其中迷失沉淪的無奈。
滲透著現代與殖民雙重屬性的城市消費空間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獨特的現代圖景和殖民體驗,然而殖民侵略掠奪下的“現代”并非正常社會歷史進程中的“現代”,這種扭曲的“現代”使城市中的人們急速迷失,山丁曾說“新京的都市氣迫害了我而變成衰弱”④山丁:《否定是力》,《山丁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頁。。爵青也帶有批判性地指陳在哈爾濱這個開放的、具有濃厚異國情調的國際大都市“看不見美國的新文化,新俄的野性建設,或啟蒙民族的原始文化,而是黃金時代消失的落寞的頹廢美”⑤阿爵:《異國情調》,《哈爾濱五日畫報》1937年第9卷第31期。。由此可見,作家們清醒地認識到城市的“新奇”只是一種表象,實際帶來的是一種頹廢與陰郁。作家也不認同殖民侵略所帶來的“繁華”,他們將對殖民統治的憎惡隱藏在作品中。關沫南在《某夜書簡》直言道:
我們憎惡夠了一本萬利大腹賈的納妾藏嬌,妓館酒社小職員的進出呼哨;憎惡夠了街頭浪漢和摩登少女的淫聲穢語的眼飛舌戰,紳士淑女有錢有閑悠游經日的無所作為;憎惡夠了窮經之日胸猶壯志,等到走進現實卻只顧低下了腦袋來鬼混的青年,也憎惡夠了那些小心翼翼積金迎娶閉門繁殖的老實人!這些醉生夢死的小市民的形形色色,好象迷妄于造物之大夢,囚之鐵獄不知憂患,置之顛亂常自安然,佛前奉經,廟堂祈福,以肉身得失為歡樂,淪于極悲世界猶巧使銅臭冀求身入天國。⑥關沫南:《某夜書簡》,《關沫南研究專集》,北方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頁。
可見日偽鼓吹的“共榮”只是實現其侵略野心的借口,他們有意制造城市“繁榮”幻影達到蠱惑人心的目的,使民眾被“現代”腐蝕成“沒有思想的溫順羔羊”,心甘情愿為其殖民統治服務,作家們筆下城市消費空間中繁華迷亂的風景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日偽“精心制造”的騙局的揭露與嘲諷。
三、陰暗殘酷的幽暗之隅:城市底層游蕩者的慘境
抗戰時期的東北在地作家借助風景書寫表達了對殖民者的反抗和解構,這在他們對城市底層民眾陰暗生活的深描中得到進一步強化。抗戰時期,強占了東北地區的日本侵略者為了實現建造“世紀的偉業”①[日]日向伸夫:《從新京到哈爾濱》,《麒麟》1941年創刊號,第166頁。的野心,施行了一系列掠奪土地的措施,如兩次“產業五年計劃”“地籍整理”以及“百萬戶移民計劃”等,日偽利用漢奸實行土地收買工作,以“危險地”和“維持治安”的名義或把農民趕走,或沒收土地讓農民去做苦工。就是在這樣蠻橫的掠奪中,古老的農村勞動模式被改變,鄉村原住民無處容身,只能一批批涌進城市,變成了四處流浪居無定所的游蕩者。在這樣一個備受摧殘、極度壓抑的時期,古丁、袁犀、吳瑛、爵青等東北在地作家無法漠視底層民眾的悲慘遭遇,但嚴酷的監察環境又使他們無法直言,于是,狹街、暗巷、陋店等幽暗之隅以及回旋于其間的流浪漢、妓女和賣力氣的人所構成的風景,便成為無聲而強烈的抗議:“在街頭、在小巷里、在暗街、在垃圾上,隨處可以看到的人們……他們的生,是不知道在活著,死也隨便死在他們活著的地方。”②轉引自劉慧娟:《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頁。東北在地作家將這受奴役最深的一群人安置在一個由嘈雜擁擠的房屋、漆黑潮濕的道路、腐爛腥臭的氣味和微弱的燈光組成的風景體系中,充斥著貧窮、疾病和死亡的風景在其中不斷上演,如山丁《山風》后記中所說:“雖無長篇,但還有故事;雖非寫實,但還有風景。”③轉引自孟素:《〈山風〉及其作者》,《滿洲作家論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當風景與殖民的殘酷現實相遇,其背后的意義和內涵極大地超過了風景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不僅清晰直觀地呈現了日寇侵略下東北的底層慘境,而且隱晦地傳達出作家的抗爭意識。
為了將風景意義呈現出來,使其為更多的讀者所感知,東北在地作家將視線聚焦于城市底層民眾生活的擁擠雜亂的小店、賣力氣的工夫市和陰暗狹窄的暗巷,其中氣味、光線等多種風景元素的排列組合構成了民眾真實的生存處境。“陰暗、擁擠、嘈雜、濁臭”成為城市底層游蕩者混跡的小店風景的代名詞,人們如無頭蒼蠅般聚集在城市小店中,獲得片刻的停歇。吳瑛《望鄉》中擁擠嘈雜的小店里,每到晚上,“人像蟲子似的竄出去竄進來”,“炕上的小行李卷一個黑堆一個黑堆的”,“一盞十六度的電燈泡子讓灰塵給彌漫住照著暗的臉暗的屋子”④吳瑛:《望鄉》,《吳瑛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頁。。在這樣一個狹窄陰暗的鬧屋中,“抽煙,喝水,連放屁的聲音都擠在里頭。這里面跟市場是一個樣子,干什么的都有,算卦的,拾雀斑的,賣假煙袋嘴的,苦力,白天擠在市場里,晚上擠進小店里伸著腰”⑤吳瑛:《望鄉》,《吳瑛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頁。。被強占了土地、無產無資的農民只能匆匆涌進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獲得生存,蜷縮在城市陰暗的小店或流落街頭。古丁《變金》中進城做工的農民葛福、石軍《脫軌列車》中的蕭勁濤……無數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成了城市里的游蕩者,居住在骯臟惡臭的小店里:“屋壁的霜花閃耀著,紙窗的破窟窿處,風刮著爛紙呼打響”,“屋里一片片鼾聲,夾雜一股股燒酒大蒜的惡嗅。”⑥石軍:《脫軌列車》,《燭心集》,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400頁。小店混亂破敗的風景不僅是底層民眾生存的寫照,更是社會黑暗、人民苦難的隱喻:“濁臭的空氣里,流蕩著刺眼的煙。里面住著流浪的光棍,算命的瞎子,賣蒼繩拍子的行商,吹糖人的,花子,大多數是鏟地的工夫……”⑦古丁:《變金》,《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頁。殖民者宣揚城市中流淌的“誠懇愉快”⑧《大新京市的動態》,《麒麟》1942年第2卷第6期,第105頁。氣氛,正是在這樣隱晦的風景參照中被消解了。
因殖民侵略失去土地被迫進入“現代”城市的底層游蕩者夜晚短暫居住的小店只是城市幽暗之隅風景的一部分,他們白天為生計勞碌奔波,聚集在一個獨特的勞動場所——工夫市:“早晨的工夫市,只是一群灰暗的動物,浸在臟污的朝霧里。”⑨爵青:《大觀園》,《爵青代表作》,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頁。袁犀在《十天》中也著重描繪了工夫市這個聚集著無數等著賣力氣小工的空間風景:“那是太陽照不到的小巷里,堆滿了垃圾和人糞,道路永遠那樣泥濘著,陰暗低矮的小土屋”“這地方四周被沖天的臭氣和腐爛的泥土,人畜的便溺的氣味包圍著。”①袁犀:《十天》,《袁犀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頁。游蕩其間的人們掙扎求存,為了糊口終日蜷縮在“垃圾堆”里,根本感受不到所謂的“國際都市的風采”②《哈爾濱風光素描》,《麒麟》1942年第2卷第5期,第104頁。,工夫市中雜亂骯臟、臭氣熏天的風景無形地拆解了殖民者標榜的“現代”與“文明”。這種客觀真實的風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視覺上觀看底層民眾慘境的渠道,被強權控制的城市仿佛是一個外表光鮮、內部腐爛的蘋果,在骯臟與腐爛之下,居住著一個個渺小落魄的寄生者。
靠賣力氣生存的人居住在擁擠嘈雜的小店,游蕩于污濁的工夫市,他們的窮困可悲讓人憐憫,而生活在黑暗污濁、充滿呻吟碎語“地獄般”城市暗巷、貧民窟中的妓女、流浪漢,更讓人感到殖民掠奪的殘酷和人命的低賤。“潮濕的街道”“令人窒息的臭氣”“萎黃的燈光”等風景符號無不在昭示著人物身份與活動空間,在那里,“無論黑夜與白晝,似乎永遠也沒有陽光,如同一條條的陰溝,那些窮苦的流浪漢便常常游泳在其間”③王秋螢:《喪逝》,《小工車》,益智書店1941年版,第50頁。。如此陰森恐怖的風景不僅象征著底層民眾地獄般的生活,更是民族災難的隱喻。爵青的《巷》中被迫做了賣淫婦的素姝就生活在一個“發著綠霉的陰臭的幽谷”④爵青:《巷》,《爵青代表作》,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頁。中:
那是在黑暗中的垃圾堆那面的一個世界。濕泥、水沙和腐爛了的新聞紙所造成的垃圾堆上,滾動著發霉的食物,酸臭的湯水,鐵絲網,玻璃片和煙卷盒玩具類,就在這大都市的排泄物的垃圾堆那面存在著一個奇異的世界。在這夜里,這世界開展著,恰似一個頹廢的貴族的花園似的,開滿了被荼毒的肥料所培養出來的慘艷的植物;那里依然沒有光,更沒有一盞可以發光的微小的路燈。⑤爵青:《巷》,《爵青代表作》,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頁。
這種“有意味”的風景此時已不僅僅是為了表現主人公生存環境的可怖,而更像是一張電影屏幕再現著殖民陰云籠罩下城市的丑惡與恐怖,生存在這個殖民者“精心打造”的“先進”城市中的民眾實際承受著無法言喻的苦難。古丁《小巷》的格調與《巷》類似,同樣構建了一個異常“丑惡”的小巷風景,金花這個年近三十的野妓生活在“夜風飄蕩著令人嘔吐的惡嗅,夾雜著粗野的罵聲,淫浪的話聲”⑥古丁:《小巷》,《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6、226、225頁。的小巷中,當她因饑餓拖著笨重的腳步在小巷中前行時,發現一條剝得凈光的嗎啡鬼的死尸絆了她一腳,也只是輕輕地咒罵了一聲:“好喪氣!”物質的匱乏將人性的溫情消磨殆盡,暗巷中的人們變成了一具具情感麻木的行尸走肉。隨著人物視線的轉移,暗巷外的“亮晶晶的街燈,紅色和綠色的夜飾光,閃,晃,照”⑦古丁:《小巷》,《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6、226、225頁。,現代城市“繁華現代”的風景使她感到“仿佛在惡夢里被狗咬傷”⑧古丁:《小巷》,《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6、226、225頁。,她切身體會到的是“秋夜涼似古井的水。小巷上面的天空,像一張烏黑的布罩,在遮蓋著丑惡”⑨古丁:《小巷》,《東北淪陷時期作家:古丁作品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6、226、225頁。。作家有意識地將“五彩斑斕”的現代風景與黑暗的小巷風景并置,環境的惡劣與人物的苦難相互詮釋,風景與人物的情感相關聯,加深放大了個體生命與情感體驗,從而突出殖民統治下城市的丑惡。
抗戰時期東北在地作家城市幽暗之隅的風景書寫既是殘酷和冷漠情境的真實生發,又不乏作家內心情緒的投射,多重風景疊加交錯,呈現出被侵略、被壓榨、被剝削、被摧殘的種種掩蓋于浮華背后的黑暗與恐怖。這個無業游民、小商販、體力工人、妓女生活的城市幽暗之隅,反復出現的陰暗殘酷的城市風景,“超越了背景設置的需要而具有人物和情節的功能”⑩張箭飛:《風景與民族性的建構——以華特·司各特為例》,《外國文學研究》2004年第4期。,人與景共同構成了受難而非享樂的慘境,民眾在那個“已經死去了或將要死去的環境”①顧盈:《兩極》,《滿洲作家論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頁。里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混亂無序的城市不斷地吞噬著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而日偽宣揚的“人民得享王道樂土的幸福”②《謝恩特使一行感想錄》,《麒麟》1942年第2卷第5期,第46頁。與城市生活“如在天堂一般”③高作恒:《滿國誕生后的感想》,《盛京時報》1934年5月15日第7版。不過是一種謊言。這種風景書寫直接撕裂了殖民者宣揚的“王道樂土”和“如畫風景”的華麗面紗,正如王秋螢發出“我終久是要活的,我倒要看看社會會把我們這一些不幸者迫害到什么地步”④轉引自李春燕主編:《東北文學史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10頁。的呼喊,這不啻是一種“無形的抵抗”。
結語
西方學者W.J.T.米切爾把“風景”和“權力”相對接,認為風景不僅僅表示或者象征權力關系,而且是“文化權力的工具,也許甚至是權力的手段”⑤[美]W.J.T.米切爾:《風景與權力》,楊麗、萬信瓊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頁。。他借助這種“風景—權力”關系提示了解讀殖民風景的新視角:“對特定殖民風景的細讀不僅能幫我們看到通過帝國的再現而對一個地方的成功統治,還能讓我們看到從內部和外部抵抗帝國的跡象。”⑥[美]W.J.T.米切爾:《風景與權力》,楊麗、萬信瓊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頁。具有愛國情懷和反抗精神的東北在地作家,正是借助風景表達了對殖民統治的抵抗。小松曾說,他在塑造作品中的人物時會“抑止他們的喜怒,限制他們的哀樂。有時對我最喜歡的一個人物,在每次描繪他的時間,天總是落雨,結果我限制了他的呼喊,平息了他的血潮,冷息了他的熱情,使他成了一個既不會笑又不會哭的白癡”⑦轉引自李春燕主編:《東北文學史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10頁。。殖民者試圖以現代文明為誘餌讓東北民眾接受其種種安排,并試圖同化大眾最終實現其殖民統治的合法性,但是東北在地作家卻不斷勾勒出了一處處包含欲望與墮落、悲慘與痛苦的城市風景,不斷解構著日偽宣傳的“共榮”“和諧”“現代”“文明”的“如畫風景”,“如消除劑一般慢慢地消溶著偽滿洲國意識形態許諾的‘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美好生活’等,侵蝕著殖民地政權的統治根基”⑧劉曉麗:《反殖文學·抗日文學·解殖文學——以偽滿洲國文壇為例》,《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5年第2期。。這表明,在抗戰時期,擁有愛國情懷與民族意識的東北在地作家在殖民高壓的條件下依舊進行著抗爭,努力發出吶喊的聲音:“你看看我的瘋狂的眼睛,我的暴跳的肌肉。我的一切一切都在和你抗爭,和你鳴叫。”⑨吳瑛:《鳴》,《吳瑛作品集》,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頁。強權能制約作家的行動,卻不能約束作家的心靈,他們將反抗的意識隱藏于創作中,進行著隱形的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