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shí)期絲綢生產(chǎn)動(dòng)力研究
喬監(jiān)松(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 設(shè)計(jì)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3)
“栽桑、養(yǎng)蠶和利用蠶絲織造絲綢,是中國(guó)古代人民的偉大發(fā)明”,[1]1是“中華民族開創(chuàng)的歷史”,在華夏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受絲綢在我國(guó)民生領(lǐng)域的重要作用影響,長(zhǎng)期以來(lái)學(xué)界對(duì)我國(guó)古代蠶桑絲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織造技術(shù)演進(jìn)方面和經(jīng)濟(jì)價(jià)值領(lǐng)域,對(duì)絲綢生產(chǎn)的文化領(lǐng)域關(guān)注較少,更缺乏對(duì)流通方面的關(guān)注,在探究絲綢的早期生產(chǎn)領(lǐng)域更是如此,以至于長(zhǎng)期認(rèn)為絲綢的生產(chǎn)動(dòng)力來(lái)自經(jīng)濟(jì)交換價(jià)值和衣料所屬的實(shí)用層面。
在絲綢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與實(shí)用方面,胡厚宣引《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楚辭·天問》《荀子·解蔽》《呂氏春秋·勿躬》《世本·作篇》《易·系辭》《管子·輕重戊》以及《尚書·酒誥》等篇章,認(rèn)為殷人“立帛牢,服牛馬,引重致遠(yuǎn)”的目的是“以為民利”,而絲制成的帛是殷人在“以為民利”過程中的交易媒介和重要產(chǎn)品,強(qiáng)調(diào)絲綢在殷商時(shí)期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與實(shí)用屬性。并且,其還認(rèn)為“蠶桑絲織業(yè),在商朝已經(jīng)相當(dāng)普遍”“蠶桑之業(yè),在當(dāng)時(shí)必已為非常重要之一種生產(chǎn)”“蠶桑之業(yè),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一樣,亦為一年的重要收成”,[2]從經(jīng)濟(jì)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角度來(lái)看待蠶桑與絲織的生產(chǎn)活動(dòng)。這一觀點(diǎn)長(zhǎng)期占據(jù)中國(guó)的主流學(xué)界,致使諸多研究者在研究絲綢時(shí)傾向從絲綢織造的技術(shù)演進(jìn)和經(jīng)濟(jì)屬性等角度切入,試圖從絲綢織造的實(shí)用層面把握和理解絲綢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
但是,從我國(guó)古代絲綢生產(chǎn)和利用的實(shí)際以及發(fā)展脈絡(luò)看,絲綢生產(chǎn)在先秦時(shí)期并不以實(shí)用穿著和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為核心目的。相反,先秦時(shí)期的絲綢生產(chǎn)在相當(dāng)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具有顯著的精神訴求特點(diǎn),先秦時(shí)期絲綢的主要生產(chǎn)動(dòng)力既不來(lái)源于實(shí)用追求也不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而是源于人們對(duì)重生精神追求和祭祀的禮儀訴求,即文化訴求是先秦時(shí)期絲綢生產(chǎn)的主要?jiǎng)恿Α?/p>
一、絲的祭祀和禮儀本源
中國(guó)養(yǎng)蠶業(yè)的起源時(shí)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間,[3]73-89且華夏區(qū)域內(nèi)蠶桑的發(fā)展為多中心分布,主要集中在黃河中下游流域、[4]四川成都平原[5]以及長(zhǎng)江下游流域,[6]從發(fā)展進(jìn)程上看黃河中下游要較其他區(qū)域起步更早一些。
研究認(rèn)為在距今四千年前后,甘肅東部已有了養(yǎng)蠶和絲織技術(shù),[7]33甲骨文中有些“羌”字帶有繩索符號(hào),被認(rèn)為有從事絲織的羌人存在,[8]因此一些研究認(rèn)為甘、川、陜地區(qū)的古代氐羌先民是蠶桑絲織技術(shù)的共同發(fā)明者。[7]34《黃帝內(nèi)傳》記載:“黃帝斬蚩尤,蠶神獻(xiàn)絲,乃稱織纴之功。”蚩尤歷來(lái)被認(rèn)為是南方九黎族群的首領(lǐng),就此看南方的蠶桑制造應(yīng)不比中原和北方地區(qū)晚。[9]此外,與少數(shù)民族有關(guān)的文獻(xiàn)記載也顯示少數(shù)民族的蠶桑利用也不比中原地區(qū)晚。如《皇圖要覽》說“伏羲化蠶”,《通鑒外紀(jì)》載“太昊伏羲氏化蠶桑為繐帛”,《孝經(jīng)·援神契》說“神農(nóng)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太昊伏羲帶領(lǐng)東夷先民養(yǎng)蠶織造、神農(nóng)氏地處西方也耕桑養(yǎng)蠶,諸如此類記載雖不如考古發(fā)掘可靠,但說明中原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蠶桑利用的文化認(rèn)知在時(shí)間上非常久遠(yuǎn)。就此看,非中原地區(qū)、南方與中原和北方地區(qū)的蠶桑織造的利用歷史應(yīng)該同樣悠久,這些材料顯示絲綢織造在華夏區(qū)域內(nèi)不僅地域分布廣泛,而且利用時(shí)間久遠(yuǎn),說明蠶桑在華夏地域內(nèi)的發(fā)展應(yīng)有超越地域且較為一致的原始動(dòng)力。
關(guān)于養(yǎng)蠶繅絲的起源,食蛹說和衣料說最為典型。但趙豐認(rèn)為“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為人類提供了發(fā)現(xiàn)的偶然事件以及馴化的方便途徑的說法似乎并不可信,因?yàn)楫?dāng)時(shí)的糧食并未匱乏到要迫使人們?nèi)こ孕Q蛹,衣服的面料也并非匱乏到要迫使人們?nèi)ふ倚碌睦w維”,且“更為重要的作物粟并無(wú)粟神更為重要的家畜亦無(wú)豬神,更為重要的紡織原料麻亦無(wú)麻神。所以,蠶僅以其經(jīng)濟(jì)效益是無(wú)法被供作神靈的”,[10]進(jìn)而認(rèn)為絲綢的起源是基于人們?cè)谟^察蠶的過程中形成的蠶因變形態(tài)的特點(diǎn)被人認(rèn)為具有與生死、天地溝通的能力,從而將蠶視為通天的引路神;桑樹是通天的工具,致使人們產(chǎn)生了系列祭祀和崇拜行為,因此認(rèn)為人們利用蠶絲的最初目的是事鬼神。
趙豐認(rèn)為,新石器時(shí)代早期以來(lái)人們盡管物資并不充裕,但將蠶桑起源解釋為飲食和衣著需求并不符合邏輯和事實(shí),在蠶桑發(fā)展的同時(shí)期人們可以獲取到的飲食和衣料來(lái)源并沒有促使其開發(fā)蠶桑使之逐步成為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的動(dòng)力。考古材料顯示,西周至五代時(shí)期,很多地區(qū)人們的主要衣料是葛麻織品而并非絲制品,[7]300戰(zhàn)國(guó)以前絲的主要應(yīng)用反而在日常穿著之外的祭祀等禮儀場(chǎng)合。
1.絲的祭祀功用
在墓葬場(chǎng)景中,絲綢主要用以裝殮尸體、包裹隨葬禮器和用作荒帷、銘旌等,禮儀地位十分突出。
周以前尤其是殷商時(shí)期古人用絲織品包裹隨葬禮器較為普遍。河北藁城臺(tái)西商代遺址M38隨葬器物有銅戈、銅爵、銅觚、銅鏃等青銅器,除銅鏃外其他器物均有絲帛包裹;M112隨葬銅戈、矛、鐏、鼎、觚和銅泡等青銅器,銅觚上發(fā)現(xiàn)有經(jīng)緯密度較細(xì)的絲織物痕跡,說明當(dāng)時(shí)此批器物可能均由絹帛包裹或者覆蓋。河南殷墟婦好墓出土器物中,有50余件銅器器表黏附有織物殘片,鑒定顯示多數(shù)為絲織品,部分為麻織品。殷墟武官村殷墓出土三個(gè)銅戈,表面有絹帛痕跡。江西新干大洋洲發(fā)現(xiàn)的大量商代青銅器中,表面也發(fā)現(xiàn)有絲織品包裹的痕跡。[11]78-79
同時(shí),用以祭祀神靈祖先的祭祀器物上也多發(fā)現(xiàn)絲織物痕跡。考古顯示絲織品被用來(lái)包裹青銅器禮器與其他禮器進(jìn)行祭祀使用,如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銅鈴、銅牌飾上發(fā)現(xiàn)有絲織物包裹痕跡。后岡圓形祭祀坑中出土青銅鼎口沿部分發(fā)現(xiàn)絲織品殘跡,一件戈的援部發(fā)現(xiàn)有絲織品殘片,安陽(yáng)西北崗M1769出土銅爵上有絲織品印痕,[11]99說明夏商時(shí)期絲織品在墓葬禮儀場(chǎng)景中的應(yīng)用普遍。
不僅如此,在遠(yuǎn)離中原的西南地域內(nèi)絲織品用于祭祀或禮儀場(chǎng)合的情況也十分突出。近年來(lái)三星堆3-8號(hào)坑在發(fā)掘同步進(jìn)行了絲織品痕跡檢測(cè),結(jié)果顯示在三星堆的青銅蛇、青銅眼形器等40多件器物上均發(fā)現(xiàn)絲綢,且品種包含絹、綺和編織物等多種類型,在三星堆4號(hào)祭祀坑的灰燼層中亦檢測(cè)到非常強(qiáng)烈的絲素蛋白信號(hào),說明此處曾經(jīng)焚燒過大量絲綢。[12]
考古發(fā)現(xiàn)絲織品的祭祀通神作用很早就被人們認(rèn)識(shí)到。蠶的全變態(tài)性使先民在觀察蠶的過程中認(rèn)為蠶經(jīng)歷了死亡和重生兩個(gè)過程,使蠶及與蠶有關(guān)的形態(tài)都具有了神性。由于蠶繭象征著重生,因此絲織品很早就被運(yùn)用到喪葬禮儀中用來(lái)包裹尸體和作為隨葬禮器。[11]77在距今5500年的河南滎陽(yáng)青臺(tái)仰韶遺址發(fā)掘的W164和W486甕棺中,嬰兒尸骨被絲織物包裹。安陽(yáng)殷墟西區(qū)發(fā)掘的M1052商墓的人骨架上亦有絲織物包裹。福建武夷山白巖崖東的船棺中也發(fā)現(xiàn)有絲織品包裹死者遺體的情況。此類情況顯示以絲織物包裹尸體在上古時(shí)期十分常見,且可追溯時(shí)間都很久遠(yuǎn),說明絲織物在上古時(shí)期代表了重生的意義。
2.絲的禮儀化用途
蠶籽孵化到蠶生長(zhǎng)并進(jìn)行數(shù)次休眠,然后吐絲作繭自縛最終破繭成蝶,整個(gè)過程在上古時(shí)期為人所知曉,但對(duì)蠶數(shù)次“重生”并蛻化的變化則無(wú)法解釋。蠶的數(shù)次休眠、作繭自縛以及破繭成蝶的由生至死再由死而生的過程被理解為蠶的復(fù)生神力,因此先民認(rèn)為蠶具有重生能力,故對(duì)其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崇拜行為。絲織物是蠶吐絲之后紡織而來(lái),因此絲織品本身也繼承神性,成為溝通神靈的一部分。
從河南發(fā)現(xiàn)的甕棺看,兒童甕棺上都有人工開鑿的孔洞,甕棺內(nèi)的兒童尸骨則用絲織品包裹。這一現(xiàn)象可以理解為,兒童死后靈魂將升天,為避免升天時(shí)由于幼小無(wú)力無(wú)法穿出甕棺而提前開好通路,用以包裹兒童尸體的絲織物則類似蠶繭將包含靈魂的尸體包裹其中,形成一個(gè)可以通往上天的繭殼,其后經(jīng)過一系列法式或儀式引導(dǎo)兒童靈魂穿過蠶絲織成的裹尸布透過孔洞升天,喻示兒童靈魂完成轉(zhuǎn)世獲得重生。從一般的宗教意義而言,神性一旦具備,帶有神性的器物便成為神性的代表,即便器物被分解拆散其各部件也依然具有神性,[13]因此蠶繭以及由蠶絲織造的器物也具有重生的能力,使其成為祭祀和隨葬的重要組成部分。
絲織物在輔助溝通天地的儀式作用方面,不僅能夠幫助兒童靈魂升天,在幫助成年人方面也成為定式。周時(shí)在將死尸入殮前需要對(duì)尸體進(jìn)行裝扮,裝扮過程中的“掩”意指用帛巾將死者的頭裹起來(lái),以代替帽子。[11]84有的“掩”發(fā)展變長(zhǎng)趨于將整具尸體包裹,因而變成了“冒”。[14]《儀禮·士喪禮》說:“冒,緇質(zhì),長(zhǎng)與手齊。赪殺,掩足。”鄭玄注:“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zhì),下曰殺。”即說冒的功能是用來(lái)套裝尸體。[11]86《釋名·飾喪制》說:“以囊韜其形曰冒,覆冒其形使人勿惡也。”“冒的三邊縫,一邊不縫而用帶系,一則可能是為了套尸方便,另一方面亦可能帶有留出空隙、任其靈魂飛出的含義。”在喪禮中,無(wú)論是大殮還是小殮時(shí)用的衾和殮衣以及套裝尸體的冒等都使用絲織品,在統(tǒng)治集團(tuán)中成為定式。
絲織品用以喪禮不僅在統(tǒng)治階層內(nèi)被認(rèn)同和接受,在社會(huì)中也成為禮制,《禮記·喪大記》說:“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绤纻不入。”絺绤纻?cè)N分別為細(xì)葛布、粗葛布和苧麻布,按習(xí)俗不能作為殮衣使用,因此當(dāng)時(shí)已有的紡織物種類中中原地區(qū)只有絲織品可以用作喪禮。從喪禮細(xì)節(jié)來(lái)看,此種裝扮以及盛裝尸體的方式和禮儀被完整地延續(xù)下來(lái),成為喪禮中的一部分。絲織品用以喪禮,不僅出現(xiàn)在包裹尸體、盛放尸體等與尸體直接接觸的部分,還廣泛用于喪禮現(xiàn)場(chǎng)的銘旌、荒帷以及裝飾棺槨的布料,其使用范圍覆蓋到了與死亡有關(guān)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
這些現(xiàn)象都說明,先秦時(shí)期的絲綢使用可能并不在穿著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而是集中在祭祀和禮儀場(chǎng)合,即絲綢生產(chǎn)的原初動(dòng)力主要來(lái)源于與神靈溝通而并非實(shí)用和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價(jià)值。
二、先秦時(shí)期絲綢的生產(chǎn)動(dòng)力
敬德梳理了先秦時(shí)期絲織品在冠禮、婚禮、喪禮、祭禮以及朝聘等禮儀中的使用情況,認(rèn)為正是由于祭祀和巫術(shù)的使用促使巫師們發(fā)明了絲織技術(shù)。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的加快,絲織品由最初通神的巫用法器轉(zhuǎn)變?yōu)槎Y用物品,并成為王權(quán)的標(biāo)志、身份等級(jí)和權(quán)力的象征,成為社會(huì)組織結(jié)構(gòu)表征體系的一部分。[11]
在與青銅器、玉器以及漆器等禮器相比較的過程中,我們不免要問的是青銅器、玉器以及漆器等不斷通過器型、紋飾和制作工藝等方式建構(gòu)技術(shù)壁壘來(lái)表征禮制、體現(xiàn)用器者的身份和地位,絲織品是否也有這樣的需求?或者說,絲織品的發(fā)展動(dòng)力是否也因構(gòu)建符號(hào)區(qū)分的需求而不斷升級(jí)迭代?
1.基于區(qū)分的生產(chǎn)
從絲綢產(chǎn)地的分布來(lái)看,《尚書·禹貢》記載天下九州中六州有絲,說明至少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絲綢的生產(chǎn)已經(jīng)遍布華夏大地。盡管一般認(rèn)為《禹貢》成文于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但其呈現(xiàn)和理解的卻是戰(zhàn)國(guó)人對(duì)于大禹時(shí)代的印象。可以說《禹貢》中所展示的既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也是戰(zhàn)國(guó)人對(duì)大禹時(shí)期流傳下來(lái)信息的重構(gòu)和理解。
《禹貢》里的記載至少可以說明周代蠶絲的地理分布情況。[15]即:
袞州:桑土既蠶……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染織品);
青州:岱畎絲枲……厥篚檿絲(野蠶絲);
徐州:厥篚玄纖縞(黑色的細(xì)絲織品);
揚(yáng)州:厥篚織貝(染織品);
荊州:厥篚玄纁璣組(玄纁為黑色淺青色絲織品,璣組為穿珠的絲帶);
豫州:厥貢漆、枲,絺、纻,厥篚纖、纊(細(xì)的絲綿)。
上述《禹貢》中與絲綢有關(guān)的描述,其中絲可理解為未經(jīng)過加工和染織的絲原料,織文、織貝為經(jīng)過染織處理的成品,[1]9,[16]檿絲是與家蠶絲相對(duì)的野蠶絲,玄纖縞是染成黑色的絲織品,玄纁是被染成黑色淺青色的絲織制品,璣組為穿珠所用的絲帶,纖、纊為細(xì)的絲綿。在這份地方向中央納貢的“貢物需求表”中,產(chǎn)絲的六州均要向中央上貢,而且上繳的貢品還有所不同。如青州繳交野蠶絲,可被視為上繳的是原材料;揚(yáng)州只繳織成、染好的成品;袞州既繳絲的原材料又繳織成、染好的成品;徐州上繳黑色絲織品,可視為有特色的地方產(chǎn)品;豫州繳的產(chǎn)品類型豐富,有多種產(chǎn)品形式;荊州的產(chǎn)品既有特點(diǎn)還有專業(yè)細(xì)分。
就此來(lái)看,天下六州的絲織產(chǎn)品生產(chǎn)并不平衡,且已有部分地方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絲織業(yè),顯示西周時(shí)期的絲織業(yè)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明顯的分化,不同的地域在蠶桑方面可能已經(jīng)形成了不同的發(fā)展重點(diǎn)。地方貢納之物的最終去向一般是中央王畿直接消費(fèi)或中央王室作為賞賜物面向諸侯國(guó)進(jìn)行再分配,但無(wú)論以何種方式處置貢物,物品的最終使用者都將獲得與自身可輕易擁有之物具有差異化的產(chǎn)品,即通過器物的差異化實(shí)現(xiàn)貢納之物的稀缺性,進(jìn)而體現(xiàn)身份和地位。
從生產(chǎn)技術(shù)看,華夏地域內(nèi)的絲織技術(shù)無(wú)論是中原地區(qū)還是周邊區(qū)域都呈現(xiàn)出不斷提高且難分伯仲的發(fā)展脈絡(luò)。如發(fā)現(xiàn)于浙江錢三漾的絲帶采用的是斜邊法編織而成,而河南青臺(tái)的羅片則是由絞編法編織而成,二者所處時(shí)間較為接近、技術(shù)表現(xiàn)有所區(qū)別,但都顯示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有較為高超的織造技術(shù)。從技術(shù)演進(jìn)的角度看,商代前及商代出土絲織物與絲纖維的情況顯示南方與北方、中原與文化上的蠻夷之地沒有根本區(qū)別。高漢玉根據(jù)出土材料制作了《商代前及商代出土絲織物和絲纖維的鑒定表》,[3]84-87其中浙江錢三漾出土的平紋絲織品經(jīng)緯密度為經(jīng)絲20、緯絲28根/厘米,①朱新予《中國(guó)絲綢史(通論)》提供的數(shù)據(jù)為經(jīng)密52.7根/厘米,緯密48根/厘米,如果按照朱新予書公布的數(shù)據(jù)則錢三漾的絲織品經(jīng)緯線密度達(dá)到了高漢玉整理的殷墟晚期絲織物的較高水平,說明南方的絲織品水平并不比中原和北方的差。見朱新予,編.中國(guó)絲綢史(通論)[M].北京:紡織工業(yè)出版社,1992:11.河北藁城臺(tái)西遺址出土商代中期平紋絲織品經(jīng)絲24、緯絲21根/厘米,河南安陽(yáng)殷墟發(fā)現(xiàn)商代晚期平紋絲織品經(jīng)絲20、緯絲18根/厘米,福建崇安武夷山巖墓船棺葬發(fā)現(xiàn)商代晚期平紋絲織品經(jīng)絲32、緯絲19根/厘米,上述數(shù)據(jù)雖然不是所發(fā)現(xiàn)遺物的全部,如安陽(yáng)殷墟發(fā)現(xiàn)不少經(jīng)絲、緯絲明顯多于上述數(shù)據(jù)的絲織品,但可以說明在“低端技術(shù)”絲織品范圍內(nèi)華夏境內(nèi)諸多區(qū)域存在相似性或技術(shù)的根本差異并不顯著。至于其中的高技術(shù)產(chǎn)物,筆者認(rèn)為是中原集權(quán)政權(quán)在投入大量造物資源后所形成的高端產(chǎn)物,是因階層分化導(dǎo)致需求的差異化供應(yīng)而形成的技術(shù)高地。
在生產(chǎn)器具上,需求的擴(kuò)大也促使生產(chǎn)機(jī)具不斷提升并逐漸朝工業(yè)化的方向發(fā)展。河姆渡文化遺址和良渚文化遺址中均有原始腰機(jī)部件發(fā)現(xiàn),并可復(fù)原為一種已經(jīng)有經(jīng)軸、提綜桿、打緯刀和卷布軸等部件的原始織機(jī),[1]11說明當(dāng)時(shí)為了滿足需求已經(jīng)開始在向工業(yè)化提高產(chǎn)量的方向努力。河北藁城臺(tái)西商代遺址中出土的兩只紡輪經(jīng)鑒定認(rèn)為是紡絲用的紡錠,說明商朝手搖紡車已具有雛形。[1]231979年在江西貴溪崖墓出土一批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紡織工具,其中有3件I形繞絲器和1件X形繞絲器,[1]21顯示江西一帶已經(jīng)有較為成熟的織絲手工業(yè);該墓所出工具中還有三件殘斷的齒耙,研究者認(rèn)為可能是一套經(jīng)耙式整經(jīng)工具,[1]23說明當(dāng)時(shí)處于非中心區(qū)的織造工藝已經(jīng)進(jìn)入到專業(yè)化的狀態(tài)。
考古發(fā)掘顯示,在殷商、西周與春秋時(shí)期隨著“市場(chǎng)”需求的擴(kuò)大和滿足,工匠所能夠提供的絲織品種不斷增多,絲織品呈現(xiàn)出精致化和風(fēng)格多樣化的趨勢(shì)。到西周時(shí)期,華夏境內(nèi)的主要絲織品已形成了包括錦、綺、羅、締、紈、縞、榖、綃、紗等品種在內(nèi)的龐大產(chǎn)品體系,種類十分豐富。[1]33
生產(chǎn)技術(shù)的進(jìn)步,顯然得益于“市場(chǎng)”不斷提升的消費(fèi)需求。當(dāng)生產(chǎn)技術(shù)逐步進(jìn)步使生產(chǎn)業(yè)態(tài)整體得到進(jìn)步時(shí),貴族的需求便開始呈現(xiàn)出求異求精的趨勢(shì)。以色彩為例,貴族和禮制的需求極大程度推動(dòng)了染色技術(shù)的發(fā)展。《尚書·益稷》說:“以五色采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周代統(tǒng)治階級(jí)的禮制系統(tǒng)注重“九文、六采、五章”的服飾制度,強(qiáng)調(diào)以文彩進(jìn)行身份區(qū)分、顯示統(tǒng)治者等級(jí),[1]135因此逐漸造成了重文彩的社會(huì)風(fēng)氣,客觀上促進(jìn)了染色技術(shù)的發(fā)展,[1]26使染色技術(shù)在商周時(shí)期達(dá)到了相當(dāng)高的水平。[17]209市場(chǎng)的需求也促使絲織品生產(chǎn)和管理不斷完善和體系化提升,到周代時(shí)在官府作坊中,已開始設(shè)置掌染草、染人、繢、?等負(fù)責(zé)練染生產(chǎn)的專門管理機(jī)構(gòu),在集中人力和掌控生產(chǎn)的同時(shí)更促使生產(chǎn)技術(shù)得到加強(qiáng)和提高。
除此之外,在絲織品的紋飾方面,也隨著市場(chǎng)需求和技術(shù)本身的升級(jí)不斷得到提升。商、西周時(shí)期的絲織物圖案主要是幾何紋和小花紋,是平紋織造工藝生產(chǎn)的結(jié)果,無(wú)法對(duì)用器者的身份進(jìn)行區(qū)分。但是到春秋時(shí)期開始有少量的大花紋出現(xiàn),與春秋時(shí)期正值東周政權(quán)不穩(wěn)霸主漸顯的氛圍下諸侯、霸主對(duì)絲綢彰顯自身獨(dú)特身份的需求相吻合,說明市場(chǎng)的需求開始變得逐漸多樣化,需要生產(chǎn)和設(shè)計(jì)環(huán)節(jié)給予回應(yīng)。從紋飾的發(fā)展過程可見,商周時(shí)期絲織品的斜紋往往是在平紋地上用于顯示云雷紋、回紋以及菱紋等幾何紋,[1]34紋飾顯得較為簡(jiǎn)單。但是在西周和春秋時(shí)期出現(xiàn)了織錦等一些技術(shù)較為復(fù)雜的提花絲織物,開始在紋飾上出現(xiàn)大幅度升級(jí),既標(biāo)志著當(dāng)時(shí)不僅有專門用于織平素織物的素織機(jī)而且有提花機(jī)具,生產(chǎn)器具和技術(shù)得到了發(fā)展,也說明當(dāng)時(shí)的市場(chǎng)需求在織造技術(shù)和紋飾表現(xiàn)兩個(gè)方面的差異化塑造都有越來(lái)越高的需求。[1]24
從祭祀和禮儀的角度看,絲綢的主要作用是祭祀和通神,起著與神靈進(jìn)行溝通的橋梁作用,起作用的是蠶絲的重生神性,在色彩和紋飾方面并沒有“實(shí)用”訴求,按理說基于同樣通神和祭祀原始動(dòng)力發(fā)展的絲綢織造也應(yīng)以“素面”為發(fā)展方向,但隨著生產(chǎn)發(fā)展織造技術(shù)和紋飾的復(fù)雜化卻成為織造的演進(jìn)方向,說明區(qū)分性是禮儀性器物生產(chǎn)的核心價(jià)值。
在材料相同的情況下,織造機(jī)具的發(fā)展水平與紋飾復(fù)雜程度基本相吻合,說明來(lái)自用器者的需求要求生產(chǎn)和設(shè)計(jì)者不斷創(chuàng)新,以形成具有區(qū)分性的產(chǎn)品。最具代表性的是,齊桓公謀求稱霸時(shí)為了彰顯自己的獨(dú)特身份,不顧周室禮儀而喜愛穿紫袍,導(dǎo)致在齊國(guó)境內(nèi)一度流行紫色,使市場(chǎng)在短時(shí)間內(nèi)失衡,導(dǎo)致紫色絲織品價(jià)格猛漲十倍。[18]
這些現(xiàn)象說明,求新、求異以體現(xiàn)差異化身份的需求促使絲織機(jī)具和工藝不斷發(fā)展,禮制需求成為絲織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重要?jiǎng)恿Γ浣?jīng)濟(jì)屬性隨著生產(chǎn)能力的提升開始突出。
2.絲綢的定制特點(diǎn)與需求的擴(kuò)大
關(guān)于先秦時(shí)期絲綢生產(chǎn)的基本特點(diǎn),敬德認(rèn)為“春秋戰(zhàn)國(guó)之前,禮是蠶絲業(yè)發(fā)展的唯一動(dòng)力”“春秋戰(zhàn)國(guó)之后,禮與經(jīng)濟(jì)共同支撐著古代蠶絲業(yè)的發(fā)展”。[11]205-213筆者認(rèn)同這一觀點(diǎn),但這一觀點(diǎn)只能解釋絲綢生產(chǎn)的基本動(dòng)機(jī),不能解釋絲綢生產(chǎn)的核心動(dòng)力,即為何織造技術(shù)不斷提升的情況下絲綢依然長(zhǎng)期處于稀缺狀態(tài)?
在明確絲綢發(fā)展的禮儀動(dòng)力之后,我們需要進(jìn)一步明確的是,絲綢與同樣出現(xiàn)在祭祀禮儀場(chǎng)合的銅器、玉器乃至漆器的不同之處在于,屬于無(wú)機(jī)質(zhì)的銅器和玉器無(wú)論是通過地下埋藏、隨葬還是傳世其滅失難度均較大,即便如漆木器其自然毀滅的速度也較慢,但絲織品卻極易滅失,其難以生產(chǎn)又易于滅失的特性在產(chǎn)量不高的情況下需要蠶桑業(yè)始終保持較大的規(guī)模,否則無(wú)法給予“市場(chǎng)”穩(wěn)定的供應(yīng)。
更為重要的是,青銅器、玉器以及漆器等器類一旦成形之后就可以較長(zhǎng)時(shí)間傳承、轉(zhuǎn)手,即便銅器重熔之后也多是再鑄禮器,因此其器類本身?yè)碛休^好的傳承性。但是,絲織品一旦制成就無(wú)法傳承和轉(zhuǎn)手,在器用方面其具有更明顯的定制特征,即絲織品無(wú)論是作為包裹尸體的殮布、喪葬所用的荒帷和銘旌、逝者所穿的衣物、撰寫跟隨死者前往地府的“遣冊(cè)”、描繪往生引導(dǎo)死者升天的帛畫等,還是作為世俗服裝等用途一旦成形就無(wú)法進(jìn)行重構(gòu)和再利用,即便其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再高也無(wú)法更換使用者之后重復(fù)利用,因此絲織品在禮制用途中因人而造成為剛性需求,這一特性才是絲織品能夠保持長(zhǎng)期旺盛需求的重要原因。在唐代之前我國(guó)的絲綢生產(chǎn)始終處于供不應(yīng)求的狀態(tài)。筆者認(rèn)為,這與絲綢的使用方式和定制特點(diǎn)有直接關(guān)系。
從器用角度看,被廣泛用作禮器的青銅器、玉器和蠶絲織品都不具備實(shí)用性,由于生產(chǎn)耗費(fèi)大且普遍用于隨葬和祭祀通神,因此盡管其生產(chǎn)技術(shù)早已擴(kuò)散、產(chǎn)量不斷上升,但“市面”流通量始終不足、無(wú)法為世俗普遍所有,因此長(zhǎng)期處于稀有狀態(tài),導(dǎo)致經(jīng)濟(jì)價(jià)值逐漸凸顯。
在祭祀和通神體系中,絲綢的作用是充當(dāng)溝通神靈的媒介,因此其被擁有祭祀權(quán)的統(tǒng)治階級(jí)所壟斷。入周以后,政治上改變了商以軍事力量主導(dǎo)“國(guó)際”關(guān)系的模式,“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guó)十有五人,姬姓之國(guó)四十人,皆舉親也”[19]643“(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guó),姬姓獨(dú)居五十三人”,[20]在統(tǒng)一格局下采取分封宗子和政治同盟的形式確立了趨于統(tǒng)一的文化,極大程度地?cái)U(kuò)大了祭祀群體;同時(shí),宗子制度的施行,使統(tǒng)治者群體中擁有祭祀權(quán)的隊(duì)伍不斷擴(kuò)大,客觀上促使祭祀活動(dòng)或者禮儀活動(dòng)的范圍和頻率都大幅度增加,進(jìn)一步加劇了絲綢生產(chǎn)的不足。
西周施行以嫡長(zhǎng)子為代表的宗子制度,嫡長(zhǎng)子在宗族內(nèi)擁有極高的權(quán)力,也在祭祀權(quán)上擁有極強(qiáng)的控制能力,《禮記·曲禮》更是說“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但是,陳絜等人認(rèn)為“支子是指宗氏內(nèi)部的小子,不能將別族后的亞族涵蓋其中;并且宗氏祭祀權(quán)盡管為宗氏首領(lǐng)所獨(dú)享,但這種排他性的權(quán)力只體現(xiàn)在宗氏內(nèi)部,一旦有庶子另立宗氏,其祭祀行為就不再受母族掌控。當(dāng)小子獲得官職或足夠的土地后,便有可能分宗立氏,建立起自己的宗廟祭祀體系,成為舊宗氏的一個(gè)新分族,也即擁有了獨(dú)立的祭祀權(quán)”。[21]東周時(shí)期生產(chǎn)力得到發(fā)展、人口增長(zhǎng)幅度較大,國(guó)家間兼并現(xiàn)象常見,諸侯勢(shì)力的變動(dòng)較為頻繁,氏族內(nèi)部的分立較為普遍,因此祭祀權(quán)的擴(kuò)散也變得常見,用于祭祀的絲綢需求就更為龐大。
同時(shí),禮法針對(duì)嫡長(zhǎng)子缺失的情況也有立長(zhǎng)等多種“補(bǔ)充”方式,[19]474從而使分封的宗子理論上都具有成為統(tǒng)治者、掌控祭祀權(quán)的可能性。[22]事實(shí)上,西周時(shí)期“貴族之間爭(zhēng)權(quán)奪利,改立太子、宗子和爭(zhēng)立國(guó)君、卿大夫的事不斷發(fā)生,貴族內(nèi)部不斷因此發(fā)生內(nèi)亂”“君位改由少子繼承”等事并不少見。[19]174,560西周分封之后疆域內(nèi)部以及邊緣區(qū)域的諸侯國(guó)便通過生產(chǎn)力上升造成的實(shí)力擴(kuò)張以及軍事征伐等方式不斷兼并,奪取祭祀權(quán)和“僭越”行為便變得較為普遍,使祭祀權(quán)更傾向?yàn)閷?shí)力的象征。
在一系列政治與造物體系的變遷過程中,我們能夠觀察到絲綢發(fā)展的根本動(dòng)力在于由差別和身份識(shí)別引發(fā)的禮制需求,統(tǒng)治階層對(duì)自身與被統(tǒng)治者或其他統(tǒng)治者之間區(qū)分的追求促使絲綢逐步從代表祭祀權(quán)力轉(zhuǎn)向經(jīng)濟(jì)富有和實(shí)力方面,使本為祭祀服務(wù)的材料被用于世俗的服飾領(lǐng)域,使本為通神和往生者服務(wù)的材料被泛化為富貴的顯性代表,在絲綢供應(yīng)量增加的同時(shí)具有繼承權(quán)和祭祀權(quán)宗子數(shù)量也大幅增多,加之絲綢難以保存和無(wú)法繼承的定制式特點(diǎn)使其始終處于供不應(yīng)求的狀態(tài)。因此,盡管絲綢生產(chǎn)的分布范圍廣,但無(wú)法遺傳、繼承、轉(zhuǎn)換重構(gòu)等特點(diǎn)使絲綢具有明顯的定制特征,進(jìn)而使絲綢成為禮儀與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并重的產(chǎn)品。
在供不應(yīng)求的情況下,奢侈品乃至普通器物的享有亦可被視為一種權(quán)力,即稀有之物的分配、擁有以及使用本身就是權(quán)力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三代器主對(duì)器物最終采取的始終如一的隨葬、窖藏式擁有客觀上使在市面上存在、流通的能夠表征身份的奢侈品數(shù)量始終不夠充分,就此,我們可以說在三代時(shí)期絲綢制品始終沒有得到充分供應(yīng),相關(guān)的造物體系盡管不斷加大產(chǎn)量,但隨著貴族體量的增大和器物交換網(wǎng)絡(luò)的日益復(fù)雜,奢侈品的需求始終沒有回落。
三、趨向世俗的絲綢生產(chǎn)
文獻(xiàn)顯示,至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我國(guó)紡織業(yè)已經(jīng)比較發(fā)達(dá),齊魯?shù)葒?guó)表現(xiàn)尤為突出,不僅可以自給還可以大量對(duì)外輸出,達(dá)到冠帶遍天下的水平,其經(jīng)濟(jì)價(jià)值應(yīng)已十分突出。春秋早期,《左傳·成公二年》載楚侵魯,魯國(guó)派出孟孫賄賂楚國(guó),條件是“以執(zhí)斲、執(zhí)針、織纴皆百人,公衡為質(zhì),以請(qǐng)盟”,[19]276說明在當(dāng)時(shí)紡織織造產(chǎn)業(yè)不僅是魯國(guó)的特色產(chǎn)業(y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可以成為兩國(guó)罷兵結(jié)盟的條件,同時(shí)這一賄賂行為由于涉及的工序完整、工匠眾多,因此可以理解為魯國(guó)對(duì)楚國(guó)的產(chǎn)業(yè)輸出和技術(shù)擴(kuò)散,增強(qiáng)了楚國(guó)的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實(shí)力。
從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情況來(lái)看,這并非孤例。春秋中期,晉國(guó)伐鄭,鄭簡(jiǎn)公為求媾和,主動(dòng)贈(zèng)送女工妾三十人。戰(zhàn)國(guó)末期,秦滅巴蜀后移民入蜀,將昔日齊、魯、鄭、衛(wèi)等諸侯國(guó)富家旺族徙居蜀地,系統(tǒng)性地將工人、技術(shù)、審美和市場(chǎng)需求移入蜀地,[17]287與西周時(shí)期拆散殷商大族和瓜分工匠技術(shù)群體如出一轍,說明先秦時(shí)期存在多種形式的系統(tǒng)性工匠和技術(shù)擴(kuò)散模式,有效提升了絲織業(yè)的生產(chǎn)能力。
不僅如此,《韓非子·說林上》“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于越”的故事說明一是魯人的織造產(chǎn)業(yè)是家庭全員參與且各有擅長(zhǎng),二是當(dāng)時(shí)的技術(shù)人才流動(dòng)沒有受到明顯限制,三是“自由”市場(chǎng)似乎已有一定規(guī)模,工匠和商人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判斷而自行供應(yīng),也說明當(dāng)時(shí)技術(shù)的交互、輸出以及人才的流動(dòng)應(yīng)該較為常見,絲綢生產(chǎn)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開始超越文化價(jià)值成為主要特點(diǎn)。
關(guān)于絲織品的價(jià)格,盡管商周時(shí)期的物價(jià)研究并不完善,但西周銅器曶鼎“匹馬束絲”的銘文則為我們提供了參考,[23]這一以一匹馬和一束絲可以交換五名“奴隸”的故事顯然說明絲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很高,而詩(shī)經(jīng)“抱布貿(mào)絲”的詞句顯示絲織品的民間交易應(yīng)該已很常見,說明蠶桑織造產(chǎn)業(yè)的經(jīng)濟(jì)屬性開始凸顯。
相較青銅鑄造行業(yè)而言,絲織行業(yè)技術(shù)門檻較低但市場(chǎng)需求穩(wěn)定且屬于“奢侈品”的現(xiàn)實(shí)使絲織品的經(jīng)濟(jì)屬性逐步明顯,因此以往需要依靠商王室一類政權(quán)組織者親自養(yǎng)蠶織絲的生產(chǎn)模式在技術(shù)擴(kuò)散的背景下成為諸侯均有能力參與的產(chǎn)業(yè),并最終演變?yōu)椤睹献印ち夯萃跎稀分兴枥L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wú)失其時(shí),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美好生活期待和全民參與的事實(shí),說明絲織業(yè)已經(jīng)在國(guó)計(jì)民生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同時(shí),也逐漸內(nèi)化為一種與生活必需品類似的文化。
至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絲織品不僅成為一種商品,[1]94而且政府開始對(duì)蠶桑業(yè)開始進(jìn)行保護(hù)。云夢(mèng)睡虎地發(fā)掘出土《秦律·法律答問》,其中有律文“或盜采人桑葉,臧不盈一錢,何論?費(fèi)搖三旬”,另有律文“甲盜錢以買絲、寄乙,乙受,弗知盜,乙論何也?毋論”。[24]這些秦國(guó)法律條文的存在,說明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不僅絲織品的價(jià)格高,而且用以制造絲織品的原材料和蠶桑也很值錢,因此對(duì)盜竊絲織品與原材料的行為處罰很重,顯然蠶桑業(yè)已經(jīng)成為重要的生業(yè)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絲綢織造與青銅冶鑄不同,絲綢織造的技術(shù)門檻不如金屬冶鑄高,蠶桑養(yǎng)殖和生產(chǎn)所需要的物質(zhì)資源與人力資源遠(yuǎn)不如青銅冶鑄多和復(fù)雜,亦無(wú)須以國(guó)家軍事力量作為支撐,因此蠶桑織造容易進(jìn)入到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與玉、漆一道成為貴而不重的經(jīng)濟(jì)類產(chǎn)品,這可能是促使全域范圍內(nèi)絲織生產(chǎn)不斷全面升級(jí)以獲得市場(chǎng)的動(dòng)力之一。同時(shí),絲綢的祭祀、通神用途對(duì)紋飾的需求并不強(qiáng)烈,銅器冶鑄中頻頻出現(xiàn)的動(dòng)植物紋飾在絲織品中極少出現(xiàn),早期絲織品的紋飾極為簡(jiǎn)單,既受絲綢織造技術(shù)的限制,可能也是由使用需求導(dǎo)致。因此,在絲綢的技術(shù)升級(jí)進(jìn)程中絲織品紋樣的進(jìn)展較其他方面的進(jìn)展更為緩慢,也說明絲織品的用途逐步從祭祀、通神轉(zhuǎn)變?yōu)槭浪仔枨蟆H旧⒓y樣作為世俗的需求,逐漸疊加在絲綢織造工藝之上,成為再次進(jìn)行區(qū)分用戶的外在符號(hào),促進(jìn)了絲織業(yè)的發(fā)展,也顯示出精神文化領(lǐng)域的產(chǎn)品進(jìn)入世俗領(lǐng)域后的發(fā)展脈絡(luò)。
因此,筆者認(rèn)為絲綢至遲在西周后期已從祭祀通神、禮儀之用轉(zhuǎn)變?yōu)楸碚魃矸莸暮屯癸@經(jīng)濟(jì)地位的奢侈品,其標(biāo)志是宗子制度導(dǎo)致的祭祀權(quán)非正常轉(zhuǎn)移和不斷擴(kuò)大。祭祀權(quán)的擴(kuò)大、絲綢的定制化特點(diǎn)以及原本的禮儀性特征,都使絲綢的使用只能“個(gè)性化”生產(chǎn),而無(wú)法如銅器和玉器一般傳承使用,致使絲綢的生產(chǎn)和流通始終供應(yīng)不足,進(jìn)而使其不斷擴(kuò)大生產(chǎn)規(guī)模,最終在唐代時(shí)期實(shí)現(xiàn)供需平衡,而唐代作為中國(guó)古代造物水平最為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亦成為絲綢完成世俗化的一種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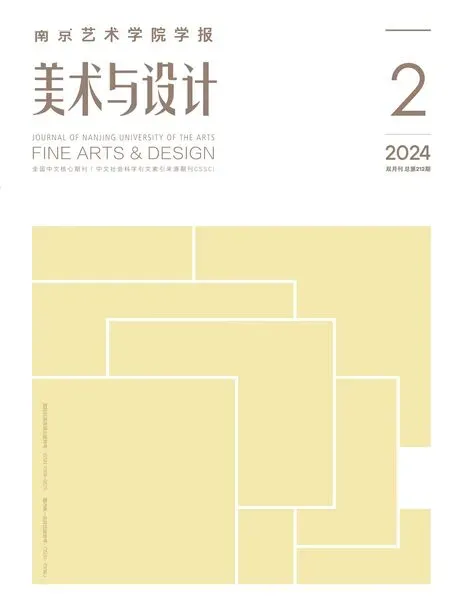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的其它文章
- 春 天
- 語(yǔ)言之思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切的雙重變奏
- 張杰創(chuàng)作中的社會(huì)學(xué)敘事與觀看之道
- 宗旨、體制與革命:高等美術(shù)教育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美術(shù)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三重維度①
- “以竹代塑”的審美倫理意蘊(yùn)
- 被身份重構(gòu)的晚明士人:主體覺醒與美學(xué)轉(zhuǎn)向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