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面性到平臺(tái)式畫面
—— 格林伯格與施坦伯格觀點(diǎn)的辨析
王晨林(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 藝術(shù)研究院,北京 100024)
一、格林伯格的“平面性”:現(xiàn)代繪畫基于媒介特性的自我觀照
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美國(guó)藝術(shù)評(píng)論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01.16—1994.05.07)的形式主義批評(píng)因?qū)ΜF(xiàn)代繪畫“平面性”的界說(shuō)而廣為人知,成為其中的主流。和多數(shù)評(píng)論家對(duì)于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論說(shuō)一致,格林伯格眼中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或者說(shuō)前衛(wèi)藝術(shù)首先是以反叛的形象出現(xiàn)在大家面前的。在寫作于1939年的《前衛(wèi)與庸俗》一文中,格林伯格指出,在西方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伴生著兩種文化現(xiàn)象:前衛(wèi)藝術(shù)和庸俗藝術(shù)。后者不僅指代工業(yè)社會(huì)所生產(chǎn)的千篇一律的大眾消費(fèi)品,也包括因循傳統(tǒng)的學(xué)院藝術(shù);前者則在格林伯格眼中具有深刻的否定性,既在藝術(shù)史的縱向維度上反叛傳統(tǒng),又在社會(huì)文化的橫向維度中區(qū)別于大眾文化。具體來(lái)說(shuō),這種否定性根植于前衛(wèi)藝術(shù)或現(xiàn)代繪畫內(nèi)部的自律性,現(xiàn)代繪畫通過(guò)一種自我觀照和自我批判的方式展示了這一點(diǎn)。
1960年,格林伯格發(fā)表了自己最具影響力的文章《現(xiàn)代主義繪畫》。在其中,格林伯格將康德式的自我批判視作現(xiàn)代主義的核心,認(rèn)為現(xiàn)代主義所展開(kāi)的自我批判是一種內(nèi)部批判。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式的批判建立在對(duì)于認(rèn)識(shí)能力明確分類、分工的基礎(chǔ)之上,內(nèi)部批判作用于這種條分縷析的框架內(nèi),在某一具體范圍中進(jìn)行闡釋與演繹,從而使得有限范圍的能力取得自己獨(dú)特而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04.22—1804.02.12)的書寫中,邏輯通過(guò)對(duì)于自身的觀照從舊有的管轄范圍內(nèi)撤銷了諸多職能,通過(guò)這種檢驗(yàn)而建基于更加堅(jiān)固的基礎(chǔ)之上。格林伯格將這套方法論運(yùn)用到了對(duì)于繪畫這一具體門類藝術(shù)的討論中,繪畫通過(guò)自我觀照所達(dá)到的基礎(chǔ)便是繪畫獨(dú)特的媒介屬性。格林伯格所追求的并非一般藝術(shù)中獨(dú)特且不可還原的東西,而是門類細(xì)分之下繪畫本身獨(dú)特的媒介特性,這一特性不能從別的藝術(shù)門類中借得,從而是純粹的。
早在發(fā)表于1940年的《走向更新的拉奧孔》一文中,格林伯格就展現(xiàn)了這種繪畫因其自律而走向純粹的思想,并貫徹在自己的批評(píng)生涯之中。具體來(lái)說(shuō),繪畫不僅要排除因模仿現(xiàn)實(shí)所體現(xiàn)的文學(xué)性,也要排除雕塑影響下所帶來(lái)的立體造型和明暗對(duì)比。純粹的媒介特性固然是具有局限性的,但卻是繪畫自身堅(jiān)實(shí)的根基。在《現(xiàn)代主義繪畫》中,格林伯格指出了繪畫的三種媒介特性,分別為扁平的表面、基底的形狀以及顏料的屬性。在這三種屬性中,格林伯格最為看重的是“平面性”,他認(rèn)為“正是對(duì)繪畫表面那不可回避的平面性的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現(xiàn)代主義繪畫藝術(shù)據(jù)以批判并界定自身的方法來(lái)說(shuō),比其他任何東西都來(lái)得更為根本。因?yàn)橹挥衅矫嫘允抢L畫藝術(shù)獨(dú)一無(wú)二的和專屬的特征”,[1]270而繪畫的封閉形狀與舞臺(tái)藝術(shù)所共享,繪畫的顏色則與雕塑所共享,從而“平面性”通過(guò)層層檢驗(yàn)成了繪畫藝術(shù)專屬的媒介特質(zhì)。
在格林伯格看來(lái),“平面性”不僅僅是繪畫藝術(shù)專屬的媒介特質(zhì),并且還作為繪畫自我觀照的指向,引導(dǎo)著繪畫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在《走向更新的拉奧孔》中,格林伯格認(rèn)為“前衛(wèi)繪畫的歷史是一部不斷向其媒介的抵制讓步的歷史”,[2]繪畫的自我觀照驅(qū)動(dòng)著繪畫媒介抵制其他門類媒介特性的運(yùn)動(dòng),而“平面性”便是這一純粹化的結(jié)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格林伯格看來(lái),“平面性”并非現(xiàn)代繪畫和傳統(tǒng)繪畫相決裂的媒介特征。相反,現(xiàn)代主義“也許意味著對(duì)傳統(tǒng)的一種轉(zhuǎn)移、一種闡明,但也意味著這一傳統(tǒng)的進(jìn)一步演化。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繼續(xù)著過(guò)去,沒(méi)有缺口,也沒(méi)有斷裂”。[1]274對(duì)于繪制傳統(tǒng)繪畫的老大師來(lái)說(shuō),“平面性”固然也是關(guān)鍵的,但基于模仿與敘事的要求,老大師作品的表面總是被充斥著視錯(cuò)覺(jué)的三維空間所覆蓋,同時(shí)其中的形象又任由敘事介入,從而觀眾在看到平面之前總是已經(jīng)被逼真的三維空間以及其中敘述的故事所吸引。換言之,在傳統(tǒng)藝術(shù)作品中,觀眾所看到的首先是繪畫中所畫的東西。然而,對(duì)于現(xiàn)代繪畫的觀看者來(lái)說(shuō),“觀眾在被迫注意到平面性所包含的東西之前,而不是之后,首先就注意到了繪畫的平面性……人們看到的現(xiàn)代主義繪畫首先就是一幅畫本身”。[1]271綜合來(lái)看,格林伯格認(rèn)為,無(wú)論是傳統(tǒng)繪畫或現(xiàn)代主義繪畫,在觀看中其實(shí)同時(shí)并存著對(duì)于一幅畫以及一幅畫內(nèi)容的體驗(yàn),只是老大師們隱藏了繪畫媒介,而現(xiàn)代主義繪畫則將繪畫媒介的凸顯強(qiáng)化為唯一和必然的觀看結(jié)果。在格林伯格看來(lái),馬奈(édouard Manet,1832.01.23—1883.04.30)的作品是第一批現(xiàn)代主義繪畫,在丟失了明暗對(duì)比與透視結(jié)構(gòu)的畫面中,平面成了作品首先呈現(xiàn)出來(lái)的東西。
綜合來(lái)看,格林伯格眼中現(xiàn)代主義繪畫的否定姿態(tài)背后存在著兩個(gè)相互關(guān)涉的邏輯。首先,現(xiàn)代主義繪畫展開(kāi)了一種自我批判,這種自我批判是一種自我觀照,一種自律性的體現(xiàn)。繪畫對(duì)于自己堅(jiān)實(shí)地基的檢驗(yàn),如同康德對(duì)于傳統(tǒng)邏輯形式的縮減一般,將繪畫獨(dú)有的、不可還原的地基通過(guò)檢驗(yàn)限定在了平面性之上,難怪邁克爾·弗雷德(Michael Fried,1939.04.12—)將格林伯格的現(xiàn)代主義繪畫觀稱作一種“還原”。[3]其次,是基于這種還原的結(jié)果來(lái)看,老大師的作品以充滿視錯(cuò)覺(jué)的三維空間掩蓋了繪畫的媒介特性,而現(xiàn)代主義繪畫則將“平面性”強(qiáng)化為觀看首要的體驗(yàn)。可以說(shuō),格林伯格將現(xiàn)代繪畫的自我觀照限定在了繪畫媒介特性的維度之上。
二、施坦伯格對(duì)格林伯格的批評(píng):形式主義中的減法原則
格林伯格對(duì)于現(xiàn)代繪畫“平面性”的界說(shuō)在當(dāng)時(shí)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在藝術(shù)批評(píng)的領(lǐng)域內(nèi)獲得了例如邁克爾·弗雷德等的簇?fù)恚谒囆g(shù)創(chuàng)作領(lǐng)域,海倫·弗蘭肯塔勒(Helen Frankenthaler,1928.12.12-2011.12.27)、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 Bernstein,1912.11.28—1962.09.07)、肯尼思·諾蘭(Kenneth Noland,1924.04.10-2010.01.05)和朱爾斯·奧利茨基(Jules Olitski,1922.03.27—2007.02.04)等藝術(shù)家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實(shí)踐了“平面性”。然而,批評(píng)的聲音也接踵而來(lái),如哈羅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1906.02.02—1978.07.11)、列奧·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07.09—2011.03.13)、T·J·克拉克(T.J.Clark,1943.04.12—)等也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發(fā)文闡述了自己的批評(píng)觀點(diǎn)。其中,施坦伯格的《另類準(zhǔn)則》頗具代表性。該文面世于施坦伯格1968年的演講中,并于1972年修訂后發(fā)表在《藝術(shù)論壇》中。文中,施坦伯格以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10.22—2008.05.12)的作品為例,指出了1950年前后繪畫中發(fā)生的某種巨大變化,并用“平臺(tái)式畫面”(the flatbed picture plane)概括了變化后作品的典型特征。“平臺(tái)式繪畫”這一概念明確指向的是1960年格林伯格在《現(xiàn)代主義繪畫》中所提出的“平面性”,前者可視作對(duì)后者的批判和發(fā)展。
在《另類準(zhǔn)則》中,施坦伯格首先明確表明的是自己反對(duì)形式主義批評(píng)的立場(chǎng):“我發(fā)現(xiàn)自己總是與被稱為形式主義的東西相對(duì)立……因?yàn)槲也恍湃嗡麄兊暮V定,他們的定量手段,以及他們那種自我陶醉式地漠視其工具無(wú)法測(cè)量的那部分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做法。”[4]84施坦伯格認(rèn)為形式主義批評(píng)本身具有一種禁止意味,其總是試圖在教導(dǎo)觀眾應(yīng)該看什么,應(yīng)該怎樣看,從而拒絕了不斷出現(xiàn)的創(chuàng)新性作品。施坦伯格總結(jié)了形式主義批評(píng)者在面對(duì)新藝術(shù)時(shí)候的態(tài)度,他們堅(jiān)守舊有的標(biāo)準(zhǔn),待在原地拒絕這些所謂偏離藝術(shù)“進(jìn)步”路徑的作品。而施坦伯格自己則偏向采取一種“同-情”(sym-pathetic)的方式來(lái)理解這些作品,通過(guò)懸置判斷,隨著作品一起感受,直到專屬于這件作品的體驗(yàn)與理解在觀看中出現(xiàn)。基于此,施坦伯格主要批評(píng)的是格林伯格將“平面性”視作現(xiàn)代繪畫的本質(zhì),且勾勒出一條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的進(jìn)步路線的觀點(diǎn)。在施坦伯格看來(lái),格林伯格通過(guò)“平面性”和“錯(cuò)覺(jué)”這一對(duì)非此即彼的概念,對(duì)現(xiàn)代繪畫和傳統(tǒng)繪畫做出了本質(zhì)性、界定性的區(qū)分,后者通過(guò)“錯(cuò)覺(jué)”掩蓋了繪畫媒介,而前者則通過(guò)媒介來(lái)凸顯繪畫本身,體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繪畫的自我觀照。然而,這一本質(zhì)區(qū)分卻并不牢靠,正如格林伯格在《現(xiàn)代主義繪畫》中自己承認(rèn)的,“老大師們已經(jīng)意識(shí)到保護(hù)被稱為圖畫平面的完整的必要性,也就是說(shuō),要在三維空間最生動(dòng)的錯(cuò)覺(jué)之下表示平面性的持久在場(chǎng)。”[1]271施坦伯格抓住了這一觀點(diǎn)并認(rèn)為,這一繪畫內(nèi)部本質(zhì)性的區(qū)別其實(shí)只是觀眾眼中的主觀傾向,也就是觀眾在觀看中傾向于先領(lǐng)會(huì)錯(cuò)覺(jué)或先注意到平面。其列舉了倫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07.15—1669.10.04)的速寫作品《讀書的女人》為例,并問(wèn)道:“要是其鋼筆的筆觸與深褐色的墨水先于,或與那位老太太的形象同時(shí)出現(xiàn),那么倫勃朗的素描就會(huì)變成一幅現(xiàn)代主義作品嗎?”[4]91施坦伯格又借雕塑家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1928.06.03—1994.02.12)的觀點(diǎn)指出20世紀(jì)50年代紐約畫派繪畫“平面性”中所包含的“虛空”以及“錯(cuò)覺(jué)主義空間”,但這些繪畫卻并不因此而歸于傳統(tǒng)。
不管是傳統(tǒng)繪畫還是現(xiàn)代繪畫,我們的觀看始終游移在平面和深度之間,這種二重性始終存在于我們的觀看之中,并能夠?yàn)槲覀兯刂啤J┨共窠鈽?gòu)式的批評(píng)指出了格林伯格“平面性”判斷中的含糊之處,格林伯格并非不能認(rèn)識(shí)到傳統(tǒng)繪畫中的“平面性”,而是基于自己的形式主義立場(chǎng),忽視了“平面性”在傳統(tǒng)繪畫中的展現(xiàn)。同樣受到格林伯格忽視的,是現(xiàn)代繪畫中出現(xiàn)的錯(cuò)覺(jué)深度,例如在其1959年的文章《論拼貼》中,格林伯格區(qū)分了“被刻畫的平面性(亦即諸截面)”以及“實(shí)際的平面(即畫布平面)”,在討論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05.13—1963.08.31)創(chuàng)作于1911年的作品《葡萄牙人》時(shí),格林伯格說(shuō)道:“被刻畫的立體主義平面與油畫表面的真實(shí)平面后,錯(cuò)覺(jué)獲得了更為明顯的在場(chǎng),但是,同時(shí)它也變得更加含混了……繪畫的物理表面本身在一瞬間竟成了錯(cuò)覺(jué)的一部分……其持久的效果就是不斷地在表面和深度之間來(lái)回穿梭。”[5]100可見(jiàn),在格林伯格看來(lái),“平面性”不僅指代繪畫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同樣也包括其繪畫構(gòu)型的形式屬性,后者通過(guò)在諸截面之間的穿梭中創(chuàng)造了深度。在這種持久的穿梭過(guò)程中,諸具體截面,包括被刻畫的平面與實(shí)際的平面,抽象成為一種“平面性”。然而,格林伯格最終還是將這兩種差異化截面的共同運(yùn)動(dòng)進(jìn)行了簡(jiǎn)化,其認(rèn)為“被刻畫的平面性受到了未加刻畫的平面性的‘感染’。與其說(shuō)眼睛被欺騙了,還不如說(shuō)被迷惑住了;它看到的不是空間中的對(duì)象,而是——并且僅僅是——一幅畫”。[5]100最終,“平面性”的形式屬性被物質(zhì)屬性所壓抑,現(xiàn)代繪畫在格林伯格看來(lái)丟失了本能通過(guò)差異化抽象運(yùn)動(dòng)所獲得的深度,而空白的、長(zhǎng)方形的畫布平面則成了賦予尺度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
在施坦伯格和格林伯格的論述中,觀看中均呈現(xiàn)了平面和錯(cuò)覺(jué)深度的兩重性。而對(duì)于格林伯格來(lái)說(shuō),媒介的物理屬性作為唯一賦予尺度的標(biāo)準(zhǔn)平息了平面和錯(cuò)覺(jué)的爭(zhēng)執(zhí),現(xiàn)代繪畫受限于這統(tǒng)一的尺度,從而進(jìn)行著自我觀照。這符合格林伯格還原式的批評(píng),媒介的物質(zhì)性作為現(xiàn)代繪畫自我觀照的指向,是通過(guò)檢驗(yàn),一種做減法的方式獲得的。施坦伯格則走向了相反的道路,其注重的是具體觀看中發(fā)生的多重性與復(fù)雜性,深度在主觀選擇的游移不定中被塑造,是一種做加法的方式。例如在分析喬托(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的繪畫時(shí),施坦伯格試圖將一直被孤立出來(lái)的圖像放回原本作為語(yǔ)境的整個(gè)墻壁系統(tǒng)之內(nèi),通過(guò)并置彼此矛盾的系統(tǒng),解釋在觀看中傳統(tǒng)繪畫的錯(cuò)覺(jué)是如何消失的。不僅如此,在觀看中,我們還能發(fā)現(xiàn)繪畫實(shí)現(xiàn)了其他藝術(shù)門類的特性。例如在分析楊·凡·艾克(Jan van Eyck,1390—1441)的作品時(shí),施坦伯格指出了繪畫自我觀照的擴(kuò)展路線,“任何人能做的任何東西,繪畫都能做得更好——而這對(duì)凡·艾克來(lái)說(shuō)就是繪畫自我實(shí)現(xiàn)的地方——正是在其不假外助的能力中,發(fā)現(xiàn)它的自主性”。[4]99在施坦伯格看來(lái),至少?gòu)?4世紀(jì)開(kāi)始的繪畫都是自我觀照的,而繪畫自我觀照的終點(diǎn)遠(yuǎn)不止格林伯格所指出的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這一種,繪畫無(wú)需排斥其他藝術(shù)門類,甚至可以在不假外助的情況下實(shí)現(xiàn)其他門類的媒介特性,更能夠容納本身非藝術(shù)的因素。
綜合來(lái)看,施坦伯格在《另類準(zhǔn)則》中對(duì)于格林伯格的批判主要發(fā)生在具體觀看的維度,其將格林伯格基于形式主義立場(chǎng)所說(shuō)的,作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錯(cuò)覺(jué)與平面的本質(zhì)性區(qū)別轉(zhuǎn)化為觀看中的主觀傾向,并否認(rèn)了格林伯格通過(guò)還原式的方法所歸結(jié)出的繪畫自我觀照的目標(biāo),即繪畫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
三、施坦伯格的“平臺(tái)式畫面”:觀看之維中的加法原則
優(yōu)秀的藝術(shù)總是自我觀照的,這是格林伯格與施坦伯格都不會(huì)否認(rèn)的觀點(diǎn)。如果說(shuō)格林伯格認(rèn)為現(xiàn)代繪畫的自我觀照路線是一條減法的形式主義路線,那么施坦伯格則通過(guò)“平臺(tái)式畫面”指出了在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觀看之維中所呈現(xiàn)的加法路線。施坦伯格的“平臺(tái)式畫面”描述的是“20世紀(jì)60年代那些典型的畫面——即對(duì)人類姿勢(shì)的極端顧慮成為其內(nèi)容變化的先決條件”。[4]105施坦伯格反對(duì)格林伯格用錯(cuò)覺(jué)和平面來(lái)區(qū)分傳統(tǒng)繪畫和現(xiàn)代主義繪畫,他認(rèn)為這些繪畫仍具有共同點(diǎn),即“繪畫再現(xiàn)一個(gè)世界的觀念,這是某種世界空間,它可以從畫面上讀出與人類的直立姿勢(shì)相一致的東西。畫作的上部對(duì)應(yīng)于我們頭部所在的空間,而其底邊則對(duì)應(yīng)于我們的雙腳所站的地方”。[4]105、107施坦伯格的“平臺(tái)式畫面”意欲取代格林伯格的“平面性”成為藝術(shù)史中的一個(gè)新節(jié)點(diǎn),其所依據(jù)的是我們觀看中的姿勢(shì)。施坦伯格認(rèn)為,不管是傳統(tǒng)繪畫,還是完全突破了傳統(tǒng)繪畫規(guī)則的立體派,乃至抽象表現(xiàn)主義的作品,都仍然共同對(duì)應(yīng)著一種觀看中的直立姿勢(shì),即觀眾以直立的姿勢(shì)在觀看直立的作品,這種直立的姿勢(shì)是一種受重力影響的自然狀態(tài)。即使如波洛克一般將畫布放置在地面上,然后往畫面上潑灑顏料,其后波洛克仍然會(huì)將畫布以直立的方式釘在墻上,從而觀察顏料的走向。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從傳統(tǒng)至當(dāng)代,哪怕先鋒如抽象表現(xiàn)主義的繪畫仍然是自然主義的。這些作品因?qū)?yīng)著直立姿勢(shì)的觀看,故仍然傾向于被理解為自然世界的再現(xiàn),正如我們往往會(huì)將波洛克的繪畫解讀為叢林。
施坦伯格認(rèn)為“平臺(tái)式畫面”的典型是美國(guó)藝術(shù)家羅伯特·勞森伯格的作品,其作品“不再模擬垂直區(qū)域,而是神秘的平臺(tái)水平面。跟一張報(bào)紙一樣,它們不再取決于與人類姿勢(shì)從頭到腳的對(duì)應(yīng)。平臺(tái)式畫面象征性地暗指諸如桌面、工作室地板、航海圖、公告板等堅(jiān)硬的表面”。[4]107“平臺(tái)式畫面”最直接、表面地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區(qū)別于垂直立面的水平面。勞森伯格的作品中經(jīng)常會(huì)出現(xiàn)一些水平面的象征物,如其1950年的作品《上帝之母》便是用地圖來(lái)打底的,又如其1953年的作品《為約翰·凱奇而作》便是用泥土制作的,報(bào)紙、各式的印刷物更是勞森伯格作品中的常用元素。在這一層面上,勞森伯格的作品還經(jīng)常以水平的方式進(jìn)行展示,既似平鋪在地面上的一堆雜物,又似佇立于地面上的一座雕像,其代表作《組字畫》便是如此。當(dāng)然,“平臺(tái)式畫面”所指的并非僅僅是物理意義上與垂直立面呈九十度角的水平面,其所帶來(lái)的觀看上的改變也并非簡(jiǎn)單從平視轉(zhuǎn)向俯視。施坦伯格所說(shuō)的“平臺(tái)式畫面”并非簡(jiǎn)單地只是物理平面的零曲率,其所反對(duì)的也并非只是將作品掛在墻上,“重要的并不是圖像實(shí)際的安置方式……我想到的是圖像的心理訴求,是在想象中面對(duì)的特殊模式,而我傾向于將畫面從垂直向水平方向的傾斜,視為藝術(shù)主題中最激進(jìn)的轉(zhuǎn)移,即從自然向文化的轉(zhuǎn)移”。[4]108
從自然向文化的轉(zhuǎn)移指示著“繪畫表面不再是自然的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的類推,而是操作過(guò)程的相似物”,[4]108“平臺(tái)式畫面”所帶來(lái)的觀看層面的轉(zhuǎn)變不只是觀看時(shí)物理視角的偏移,而是觀看不再受制于傳統(tǒng)透視法的理性視覺(jué),我們?cè)谟^看中還原、模擬了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勞森伯格不少作品都展示出了我們回溯其創(chuàng)作過(guò)程的可能性,如1950年所創(chuàng)作的《女性人體》,在藍(lán)色曬圖紙中,我們不難想象勞森伯格拿燈光照射躺在曬圖紙上女模特的過(guò)程。再如其著名的作品之一,創(chuàng)作于1953年的《汽車輪胎印》,順著作品橫向閱讀時(shí),仿佛用目光還原了行駛著的汽車,其染上顏料的輪胎壓過(guò)畫面的過(guò)程。施坦伯格十分重視“平臺(tái)式畫面”帶給觀者的變化,其稱“平臺(tái)式畫面”“暗示任何物體得以在其上分散開(kāi)來(lái)、材料得以進(jìn)入、信息得以收到、印刷、壓痕的接受體表面”,[4]107而在勞森伯格的作品中,這種接受體表面象征著觀看中我們心智層面自由聯(lián)想發(fā)揮的領(lǐng)地。觀看中接受的發(fā)生源于作品作為一種征兆向我們釋放吸引力,從而激活我們的感覺(jué)。文化所對(duì)應(yīng)的操作過(guò)程的相似物處在觀看的感覺(jué)之中,這種感覺(jué)擺脫了引力束縛之下的單一感覺(jué)模式,從而生產(chǎn)出了區(qū)別于自然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或者說(shuō)自然世界再現(xiàn)的復(fù)合的感覺(jué)。在格林伯格看來(lái),現(xiàn)代繪畫通過(guò)擺脫雕塑、文學(xué)等門類藝術(shù)而走向“平面性”,所伴生的是在觀看中感覺(jué)通過(guò)擺脫觸覺(jué)等因素而走向純粹視覺(jué),而施坦伯格所說(shuō)的“平臺(tái)式畫面”通過(guò)取消垂直平面,從而使得觀看從自然主義的傾向中解放出來(lái),感覺(jué)不再服從于自然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的再現(xiàn)秩序,而通過(guò)自由聯(lián)想表現(xiàn)出了更大的豐富性。
在50年代,勞森伯格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具有私人化特質(zhì)的組合作品,如1954年創(chuàng)作的《無(wú)題》,這是勞森伯格首批組合作品之一,有時(shí)也被稱為《普利茅斯巖石》。《無(wú)題》是一個(gè)下部半開(kāi)的長(zhǎng)方體柜子,在柜子上部外層的表面貼滿了勞森伯格家人、朋友的照片和信件等,而下部的圖像則多出現(xiàn)在內(nèi)部空間,一個(gè)男人的照片被垂直貼在柜子底部安裝的鏡子上,旁邊則放置著一只雞。《無(wú)題》是勞森伯格本人的象征物,在作品閉合和打開(kāi)、內(nèi)部和外部的交相呼應(yīng)中,我們仿佛體會(huì)著勞森伯格本人的本真與表演、誠(chéng)實(shí)與虛偽。《無(wú)題》要求一種區(qū)別于自然直立姿勢(shì)的觀看方式,我們至少需要圍繞作品一周,從不同的側(cè)面,才能將作品看完整,同時(shí)我們還需要俯身下來(lái)聚焦于某些細(xì)節(jié),或是蹲下身子再抬頭一探作品內(nèi)部的全貌。在觀看中,我們復(fù)現(xiàn)了日常生活中多樣的姿勢(shì)。不僅如此,作品所喚起的并非單一的視覺(jué)體驗(yàn),我們通過(guò)環(huán)繞一周來(lái)?yè)崦髌罚⒃谌缯掌⑿偶葞в谢貞泴傩缘奈锛畜w會(huì)更為豐富的感覺(jué)。
在格林伯格所描述的“平面性”中,繪畫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作為唯一的尺度規(guī)定著繪畫元素的準(zhǔn)入原則,而在施坦伯格看來(lái),勞森伯格的組合作品“成為一個(gè)任何可以想見(jiàn)、可以獲得的東西都可以依附于其上的表面……而且還進(jìn)一步被一切扁平與重做的東西所吸引”。[4]110勞森伯格的作品作為一個(gè)“平臺(tái)式畫面”呈現(xiàn)為一個(gè)永遠(yuǎn)開(kāi)放的平面,其不再似“平面性”守護(hù)著一個(gè)不可還原的內(nèi)部,而是不斷引入外部來(lái)豐富自身,平臺(tái)上已呈現(xiàn)的物品通過(guò)組合的方式表現(xiàn)出一種親和,并進(jìn)一步試圖與可能添加進(jìn)來(lái)的東西親近。觀看之維中所呈現(xiàn)出的豐富性離不開(kāi)“平臺(tái)式畫面”的加法原則,“平臺(tái)式畫面”作為一個(gè)接受的平面大大豐富了藝術(shù)材料媒介的種類,并使得唯一的尺度不再通過(guò)抽象的方式獲得。在我們所熟知的勞森伯格的《床》《峽谷》等作品中,現(xiàn)成品大量出現(xiàn),其中既包括日常生活物品直接或稍加處理后的使用,也包括其出場(chǎng)充滿偶然性的廢棄物。《床》似乎可以被看成勞森伯格躺在床上創(chuàng)作而顏料灑落在其表面的結(jié)果;《并存》則更像是隨機(jī)對(duì)某個(gè)垃圾堆偶然地截取。從60年代開(kāi)始,勞森伯格進(jìn)一步完善了自己組合的技術(shù),并從自我表達(dá)的絮語(yǔ)轉(zhuǎn)向了公眾的層面,其試圖通過(guò)自己的作品挑戰(zhàn)公眾的觀看結(jié)構(gòu),讓觀眾對(duì)于自身的感知模式進(jìn)行反思。勞森伯格往往通過(guò)引用為人熟知的大眾圖像介入公眾層面的表達(dá),如其1964年的作品《航線》中,就出現(xiàn)了作為大眾圖像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1961.01.20—1963.11.22)總統(tǒng)頭像,以及作為藝術(shù)史經(jīng)典作品的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06.28—1640.05.30)的《梳妝打扮的維納斯》。勞森伯格意在去除觀眾在觀看中這些圖像為人所熟知的意義的顯現(xiàn),通過(guò)并置高雅和世俗的圖像,私人絮語(yǔ)中內(nèi)在的親和轉(zhuǎn)變成為一種嚴(yán)厲的發(fā)問(wèn)。作品似勞森伯格本人一般,以《航線》中肯尼迪手指觀眾的姿勢(shì),向觀眾發(fā)問(wèn),我意味著什么?我想要什么?繪畫是什么?藝術(shù)是什么?這種發(fā)問(wèn)顯然是一種持續(xù)的發(fā)問(wèn),其基于永遠(yuǎn)開(kāi)放的“平臺(tái)式畫面”,通過(guò)不斷容納新的異質(zhì)物而持續(xù)著,區(qū)別于格林伯格通過(guò)繪畫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凝定了錯(cuò)覺(jué)與平面的不斷游移,異質(zhì)性的元素在“平臺(tái)式畫面”中持續(xù)地爭(zhēng)執(zhí)著,在尺度的不斷豐富中游戲著。
綜合來(lái)看,通過(guò)從形式主義立場(chǎng)向觀看之維的轉(zhuǎn)移,施坦伯格力圖通過(guò)“平臺(tái)式畫面”將觀看從自然主義的方法中解放出來(lái),使得觀看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過(guò)程相連接,從而觀看不僅關(guān)涉視覺(jué)而且蘊(yùn)含著豐富的感覺(jué)種類。勞森伯格的作品作為典型的“平臺(tái)式畫面”,不僅驅(qū)使著我們?cè)谟^看中采用多種多樣的姿勢(shì),更通過(guò)不斷容納異質(zhì)性的元素使得觀看持續(xù)以自由聯(lián)想的方式發(fā)生。在這一過(guò)程中,作品的意義無(wú)法根據(jù)某一尺度作為標(biāo)準(zhǔn)而確定,其始終保持著神秘從而激發(fā)觀者對(duì)于該作品乃至藝術(shù)概念意義的不斷追尋。
四、結(jié)語(yǔ)
施坦伯格的“平臺(tái)式畫面”是對(duì)于格林伯格現(xiàn)代繪畫“平面性”的批判與發(fā)展。通過(guò)這一概念的指出,施坦伯格否定了格林伯格對(duì)現(xiàn)代繪畫與傳統(tǒng)繪畫界限的劃定,并給出了“平臺(tái)式畫面”這一繪畫變革中的新節(jié)點(diǎn)。“平臺(tái)式畫面”具有一種不斷拓展自身的特質(zhì),使得觀看中展現(xiàn)出多種層次的豐富性,感覺(jué)通過(guò)與創(chuàng)作過(guò)程的嫁接而不僅限于視覺(jué),繪畫通過(guò)與其他門類藝術(shù)的并存而不受制于其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從媒介的角度來(lái)看,“平面性”象征著一種減法,其試圖通過(guò)還原繪畫絕對(duì)堅(jiān)實(shí)且自律的地基來(lái)為繪畫打底,將繪畫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作為唯一尺度。而“平臺(tái)式畫面”則做著加法,其通過(guò)這一永恒開(kāi)放、不加限制的平面,不斷容納傳統(tǒng)中非繪畫的內(nèi)容,每一次容納和拓展都是繪畫這一平臺(tái)通過(guò)膨脹自身來(lái)豐富其內(nèi)含的媒介尺度。
20世紀(jì)50年代中后期開(kāi)始的藝術(shù)實(shí)踐并未繼續(xù)走向“純媒介”的死胡同,相反卻走上了“跨媒介”的道路,“平臺(tái)式畫面”通過(guò)媒介尺度的不斷疊加,成了典型的跨媒介作品。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1938.03.15—1998.10.25)在《跨媒介》一文中表明:“現(xiàn)成品或拾得物都具有跨媒介的意義,因?yàn)樗鼈兌疾悔呄蛴诜霞兠浇椋⒂纱苏故境隽艘粋€(gè)在藝術(shù)媒介的一般領(lǐng)域與生活媒介的中間位置”。[6]跨媒介作品因其內(nèi)含豐富的媒介種類,從而使得作品整體上呈現(xiàn)為一種居間狀態(tài)。極簡(jiǎn)主義的作品便是極佳的案例,其典型作品所呈現(xiàn)的便是一種既是雕塑又是繪畫,或者說(shuō)既不是雕塑又不是繪畫的狀態(tài)。若按照格林伯格的思路,極簡(jiǎn)主義中那些空無(wú)一物,只剩一張白板或畫布的作品,因其對(duì)于繪畫物質(zhì)媒介的直接展現(xiàn),可視作現(xiàn)代繪畫的頂點(diǎn)而終結(jié)繪畫。然而這一“終結(jié)”并非現(xiàn)代繪畫的終點(diǎn),卻是“平面性”適用歷史范圍的終點(diǎn)。正如弗雷德在《藝術(shù)與物性》中為支持格林伯格的立場(chǎng),本意用于批判極簡(jiǎn)主義的“劇場(chǎng)性”恰恰成了極簡(jiǎn)主義的理論背書,各藝術(shù)門類未在自我觀照中相互隔絕,相反卻在劇場(chǎng)中相互召喚。
自20世紀(jì)初期以來(lái),不少歷史前衛(wèi)作品中就體現(xiàn)出了跨媒介的特性,作為歷史前衛(wèi)的重復(fù)與延遲,新前衛(wèi)藝術(shù)中也保留了媒介的疊加與相互關(guān)聯(lián)。“平臺(tái)式畫面”所呈現(xiàn)的居間效果不僅是其中異質(zhì)的媒介之間爭(zhēng)執(zhí)的結(jié)果,更在觀看中召喚了豐富的感覺(jué),使其以自由聯(lián)想的方式相互碰撞、不斷更新。居間作為一種既是又是,既不是又不是的狀態(tài),使得作品的意義遁隱于神秘之中,在觀看中對(duì)觀眾進(jìn)行發(fā)問(wèn)與質(zhì)詢,繪畫本身也得以在對(duì)“繪畫何謂”的不斷回答中,始終保持著更新與生成。
從“平面性”到“平臺(tái)式畫面”,是從形式主義走向觀看之維。繪畫的自我觀照方式,從做減法的還原走向做加法的爭(zhēng)執(zhí),從檢驗(yàn)堅(jiān)實(shí)的地基走向質(zhì)詢作品乃至繪畫及藝術(shù)本身的意義。“平臺(tái)式畫面”仍然保持著對(duì)于當(dāng)下藝術(shù)實(shí)踐的解釋力,于其上,仍有更多的內(nèi)涵等待被發(fā)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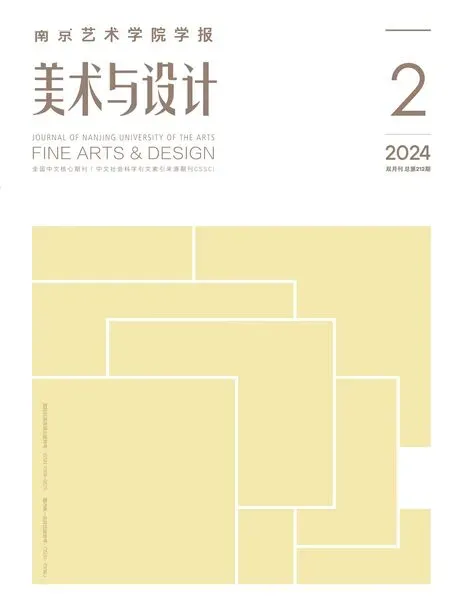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的其它文章
- 春 天
- 語(yǔ)言之思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切的雙重變奏
- 張杰創(chuàng)作中的社會(huì)學(xué)敘事與觀看之道
- 宗旨、體制與革命:高等美術(shù)教育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美術(shù)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三重維度①
- “以竹代塑”的審美倫理意蘊(yùn)
- 被身份重構(gòu)的晚明士人:主體覺(jué)醒與美學(xué)轉(zhuǎn)向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