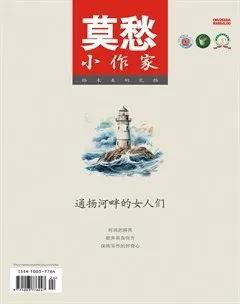立夏吃塊餅
今日立夏。
中國人時令節日,總要吃點什么,以示紀念。立夏,南方人吃立夏飯,五色或五谷糯米飯;北方人吃立夏餅,各式各樣的面餅。
江蘇沭陽有句老話,“立夏吃塊餅,夏季不打盹。”沭陽人過立夏,有吃糟面餅的習俗。據講,這一習俗來自一個傳說:說不清哪朝哪代,沭陽縣城有個看守城門的老兵,每逢夏季,耐不住炎暑漫長白晝,常常無精打采,邊站崗邊打瞌睡。一天午后,當他和另一個守門人迷迷糊糊、懨懨欲睡時,讓一群盜賊鉆了空子,偷偷溜進城里潛伏下來。當天夜間,這伙強盜把五爿大商店、三家金銀首飾店統統搶劫一空,揚長而去。老兵與他的伙伴被問罪,眾官兵一齊跪下求情,方從輕處置,被罰打五十大板,喊爹叫娘躺在床上兩個多月。為了記取這一沉痛教訓,他從每年立夏日起,天天值崗時帶上一塊辣椒粉和小麥面做成的糟面餅。每當兩眼發澀、上下眼皮打架時,他就狠狠咬上一口面餅,辣得滿頭冒汗,自然也就趕跑了困癮。慢慢地,立夏吃面餅這一習俗就流傳下來,說吃餅可以提神添勁增精力。沭陽也就留下了“立夏吃塊餅,夏季不打盹”這句老話。
立夏吃什么樣的餅,沒有規定。但南米北面,沭陽屬北方,沭陽人特別喜愛面食,面餅也就花樣繁多。
有發面餅,也有死面餅。先用小麥粉和水揣面,放在溫度適宜的地方使其發酵,冬天還會用棉被蓋起來保持溫度,俗叫起面、發面或長面。經發酵的面叫活面,做出來就是發面餅,也叫活面餅,比如大餅;沒有發酵的面叫死面,做出來就是死面餅,比如鍋貼。每次揣面發酵后,要留下一小塊面劑作為酵母菌種,俗叫糟引子。面發酵好后,有酸酸的味道,加適量的堿水中和,堿放少了有酸味,放多了黃而難食,就成了顏色發黃的大堿餅。胃不好的老人,偏愛這種黃色大堿餅,說吃了舒服。外公老年時在我們家生活,每次烙餅,母親都要專門烙幾塊這種大堿餅給他吃。
面發酵后加堿水,使勁揉搓成面團,用刀劃開,聞聞味道,若還有酸味,再放點堿水,繼續揉搓,直到沒有酸味為止。這個過程需要非常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驗老到的,劃開面團,看氣泡是否勻稱,就能知道適中與否。第一次做餅,很難成功,不是堿少酸了,就是堿多黃了,須反復摸索。今人多用發酵粉,按比例放入直接發酵就行,簡單易行。但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喜歡吃自然發酵放堿的面餅。面發好后,揉成一個個小團,再搟成小圓餅,在鐵鍋內翻覆烙熟,沭陽叫糟面餅,也就是發面餅。
有糊塌餅。小麥粉和水調成糊狀,比一般的糟面餅稀一些,發酵放堿水除酸后,用勺子搲一點,倒入烙餅鍋內,烙成軟軟的圓餅,叫糊塌餅,也叫水糊餅。有時發酵后故意少放些堿,保留一點酸味,叫酸糊餅;有的不經發酵直接烙成餅,叫死糊餅。
有鍋貼。面粉和水成糊狀,不發酵,貼在鍋邊上,俗叫鍋貼,因是死面,又叫死面鍋貼。過去做死面鍋貼,或鍋底少放些水,或鍋底燒菜鍋邊貼餅,燒的菜也都是家常菜,比如烀方瓜、烀豆角,都是可以烀時間長些的菜。今人做鍋貼,多是燒雜魚,鍋貼下端浸入魚汁,味道特別鮮美,成一道特色菜——雜魚鍋貼。不但有死面鍋貼,還有經過發酵的活面鍋貼,各有特色。
有大腳餅。名字有點難聽,但是很好吃。面發酵好,揉成長條形,貼在鍋邊,一面脆硬,一面暄軟。以其形似大腳,俗叫大腳餅,又叫大腳卷子。
有杠子餅。方言把硬叫作杠。死面,沒有經過發酵,不暄軟,烙成餅,就叫作杠子餅。小時候沒有面吃,多吃玉米餅,沭陽叫棒秫餅,玉米餅又柴又硬,貼在鍋邊,就叫棒秫餅;揉成小塊下到稀飯里,我們稱之為小杠子。小時候,早飯多是吃棒秫小杠子,再就點咸菜。
有單餅。面粉用開水燙熟后,制成很薄的圓餅,放在平底鍋內來回翻面烙熟,叫單餅,又叫薄餅。過去沭陽人夏季待客,多用單餅,既快又好吃。單餅可以直接吃,更多是卷著各種菜肴吃。單餅卷大椒炒小蝦,卷大椒炒小干魚,單餅卷馓子、卷油條、卷大蔥,都是沭陽的特色美食,百吃不厭。
有煎餅。用過去那種大鏊子烙出來的,有面煎餅、棒秫煎餅、沙干(山芋)煎餅、雜糧煎餅。放上餡料,就是咸煎餅,再打入雞蛋,就是雞蛋煎餅。小時很難吃到雞蛋,就用蔥花放點鹽,是一道印象深刻的咸煎餅,特別好吃。
有大餅。小時烙的面餅并不大,因使用的是尖底鍋。后來出現了平底鍋,就可以烙大餅,一兩寸厚,一鍋就烙一塊餅,兩面金黃,內部松軟,軟硬適度,香脆可口。沭陽把酥松叫作暄,又名大暄餅。如果大餅兩面受火,不用來回翻面,就成了吊爐餅。
有蔥油餅。和好面,搟成薄片,上面鋪上蔥、油、鹽,卷成團,再搟薄成圓形,烙成餅,就成蔥油餅,也叫千層餅、油暄餅。
烙餅里放餡料,就是各種餡餅:包糖的,就是糖餅,有白糖的、紅糖的,另外還會加芝麻,高級的會加桂花蜜。包菜的,就是菜餅,沭陽又叫咸餅,分韭菜餅、青菜餅、蘿卜絲餅、梅干菜餅、萵苣餅等。韭菜餅或是圓形的,或是半月形的,后者就叫韭菜盒子,韭菜里或放雞蛋皮或放粉條,沭陽人特別喜歡吃。現在還有小餅夾肉,相當于中國版漢堡,年輕人最喜歡。
記得小時候,母親什么樣的餅都會做,我們吃著母親做的各式各樣的面餅,慢慢長大。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母親做的餅是最好吃的。
“立夏吃塊餅”,我忽然想起母親用大鏊子做的蔥花煎餅,馬上上街買來現成的煎餅,放點蔥花和鹽,在鍋里炕炕,不香不酥不脆,一點都不好吃。
一眨眼,母親離開我們已一年多。
夏炳文: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做過中學教師,被評為“市級語文學科帶頭人”“全國優秀語文教師”。出版散文集《拈墨流年》。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