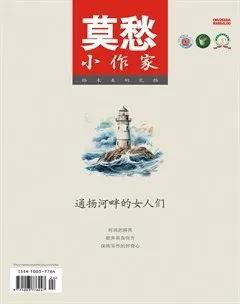有麥青青于野
我不由得停住了腳步。
道路左側,一溜坡地全被開墾出來,種上了麥子。麥苗青青,像絲滑的綢帶,軟軟系在春山的脖頸;又像溫潤的月牙,靜靜嵌于春日的額角。
很久沒有見過麥子了。城郊漫游,最常見的是菜花。平地坡上,金燦燦的,香噴噴的,不用睜開眼,便知道春已深。豌豆胡豆也能偶遇,喜相逢,唯有麥子,若少年舊識,被歲月的風吹散,很難再相見。
麥子,村莊不可或缺的底色,農人最堅實的依靠。層層疊疊的山野上,那些或大或小的土地曾經都是麥子的領地。把麥子種進地里,把麥子迎回家里,寒來暑往,曠日持久,大地為媒,日月作證,在曠野上,在風日里,在雞鳴狗吠的院落里,在酸甜苦辣具呈的餐桌上,我們與麥子相親相愛,不離不棄。
種麥子,割麥子,打麥子,每一個階段,付出的是真心,灑下的是汗水,收獲的是充實。數九天寒,農人一聲不響,默默蓄力;春暖花開,農人抬頭挺身,日夜兼程。麥子開花結籽,灌漿成實,結出飽滿的穗子,炸開金色的芒刺。隨后,在鐮刀的霍霍聲中,在連枷的嗒嗒聲里,麥子顆粒歸倉,然后走向餐桌,走向集市,走向四面八方。這是麥子的流年。
家鄉山坡上,曾經的麥地如今早已草木蔥蘢。而山腳下,農田依然豐茂,油料豆類,水稻玉米,輪番上陣,輪流出場。唯有麥子,曾經大片大片,如今不見蹤影。“阿公阿婆,割麥插禾”,年年春天,布谷鳥的歌聲依然會按時把寂靜的山野唱響。只是,鳥兒不厭其煩的提醒似乎再也找不到落點,“有麥青青于野”成為一種惆悵的回憶。
此刻,見到麥子,仿若故人重逢。麥稈亭亭,麥葉翩翩,麥穗短短,麥芒柔柔。白色的小花懸于莖節的小穗上,安安靜靜。少時,我們在山坡上放牛,在麥地里割草。麥子從不目空一切,唯我獨尊,麥麥草,鋸鋸藤,野豌豆,婆婆納,許多野草喜與麥子為鄰。傍著麥子攀緣而上的鋸鋸藤一扯一把,又嫩又干凈,牛的大舌頭一卷,帶有麥葉麥花香的草料一根不剩。在麥地里鉆來鉆去的我們,頭發上,衣衫上,落滿麥花。我們隨手一拍,撣掉麥花,卻撣不掉細細的香。麥花太小,我們似乎從未拿它當花看,從不會因為撞落了麥花而心生歉意。再說,麥花那么多,撞落一些又有什么關系呢。那時候,我們不知道麥花是開在瞬間的花,毫無惜花之意。
“麥子正揚花呢,不要亂竄!”母親的聲音穿過一壟壟麥子,清晰地落在我們的耳朵里。在麥地里挖預留行的母親總是非常小心,她高高舉起的鋤頭總是準確地落在麥子旁邊,卻不會碰觸到麥子。所謂預留行,就是麥壟與麥壟之間的空地,挖出來栽種玉米。這樣成行成列的布局,通風透氣,更利于麥子的生長。
收了麥子種玉米,太晚。種了麥子的土地沒法使用耕牛,預留行只能一鋤鋤挖出來,再將玉米苗一株株栽下去。栽在麥地里的玉米苗避免了太陽的直射,風雨的吹打,只管踏踏實實,安家落戶。在麥子的蔭庇之下,玉米苗慢慢坐根,靜靜長葉。待到麥子收割之后,玉米苗形容尚小,身量已高,緞帶樣的翠葉閃閃發亮,風在葉上跳舞,雨在葉上彈琴,要不了幾天,就扯起漫山遍野碧綠的青紗帳。春末夏初,母親總是待在麥地里,微醺的風怎么也吹不干她汗濕的衣裳,便將凋零的麥花,一朵朵灑在她的頭上身上。
麥花,二十四番花信風中最不起眼的花,花朵那么小,花色那么淡,是世界上花期最短暫的花,短到5分鐘,最長的也不過半小時。在短短的時間內,它靜靜地開,靜靜地謝,靜靜地孕育。孕育出風吹麥浪的壯觀,孕育出普濟天下的悲憫,孕育出大愛無疆,綿綿不絕的情懷。
一日三餐,有多少人的生活與麥子無關?生命的歷程,怎么少得了麥子的陪伴?小麥色,成熟而不刺眼,沉靜而明亮,自帶大地的深厚與天空的遼闊,也有時間的溫潤樸實,沉穩大氣。不蒼白不虛浮,這生命的本色,實在是一種動人的顏色。姹紫嫣紅開遍,踏春賞花路不斷。有沒有一個春天,有沒有一小段光陰,你專為麥花而去?因為一株麥子而駐足?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歷經顛沛流離,面對一片開花的麥子,詩圣的眼神,一定是喜悅的;詩人的內心,一定是寧靜的。那細細的莖稈,那小小的麥花,那脈脈的香氣,如此恬淡靜謐,令人陶然沉醉。小小的麥花,帶來的是豐收、篤定,鏈接的是家園、底氣,詮釋的是安居歡喜。
菜花黃過了,桃花艷過了,噴雪吐霞的櫻用一襲翠色替代了霓裳羽衣。在家鄉的山野上,走失的麥子也回來了吧?湛藍的天空下,寂靜的原野上,它們一定也是這樣,直起腰身,衣裙素素,芒針纖纖。微醺的風緩緩地吹,綠色的浪輕輕地搖,淡淡的花靜靜地香。
王優:四川省蓬安中學教師,作品散見于多家報刊。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