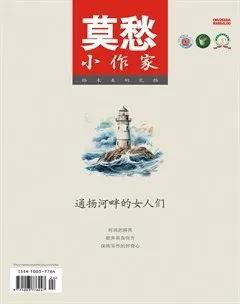永生的橋
進(jìn)入江西省瑞金市武陽鎮(zhèn)武陽村境內(nèi),迎面就是兩棵巨大的老樟樹。陽光從葉隙間鉆出來,輕手輕腳地灑在兩位歇晌的老人身上。老人一邊規(guī)整著腳邊的一堆樟樹寄生,一邊好奇地瞧著我,問:“你是來看橋的吧?”我點(diǎn)頭,她朝左手邊轉(zhuǎn)過臉去:“喏,就在那兒。”又意味深長(zhǎng)地補(bǔ)上一句:“八十多年了喲——”
是的,我要來看的武陽橋,是一座意義非凡的橋,一座被載入中國(guó)革命史的橋。1934年10月8日,中央紅軍第九軍團(tuán)進(jìn)行戰(zhàn)略轉(zhuǎn)移,作為首批出發(fā)部隊(duì)來到武陽村,在當(dāng)?shù)卮迕竦纳嵘硐嘀拢蛇^了二萬五千里長(zhǎng)征途中的第一座橋。1996年,原國(guó)家主席、曾任中國(guó)工農(nóng)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楊尚昆視察瑞金,再次來到武陽橋,回憶往昔崢嶸歲月,于萬千感慨中揮毫題寫下“長(zhǎng)征第一橋”五個(gè)大字。
武陽橋,是武陽村連接綿江河兩岸唯一的通道。只是,原來的那座橋已經(jīng)不見了,如今,一座鋼筋水泥雙曲拱橋雄壯地橫跨在河面上,橋墩結(jié)實(shí),兩車道的橋面寬闊平展。那是1988年,武陽鎮(zhèn)人民政府為改善沿河兩岸交通而修建的。橋頭立了一塊“紅軍長(zhǎng)征第一橋”紀(jì)念碑,永久地鐫刻下紅軍長(zhǎng)征的往事。
我望著滔滔奔流的河水,想象著從前那座橋、那些人,那樣一場(chǎng)義無反顧的前行。風(fēng)掠過草木,吹上身來。我的腦海中不由回蕩著《十送紅軍》的旋律和歌詞:“一送(里格)紅軍,(介支個(gè))下了山,秋風(fēng)(里格)細(xì)雨,(介支個(gè))纏綿綿……”沉浸于一種悲壯又哀痛的情緒中。
原來那座橋,我只在資料圖片上看過。那是一座簡(jiǎn)易的木板橋,全長(zhǎng)一百一十多米,寬不足一米。十三個(gè)木橋墩單薄地跨坐在河中央,二十多塊木板簡(jiǎn)陋地鋪在橋墩上,和寬闊的水面以及岸邊那棵巨大的老樟樹比起來,它顯得那樣輕飄,那樣脆弱。
故事來自老人的講述。那天半夜,從福建長(zhǎng)汀中復(fù)村趕過來的一萬多名紅軍來到這里,隊(duì)伍后面是隨時(shí)可能追上來的敵軍。僅憑小木橋那單薄的橋身,根本無法承受一支隊(duì)伍的急行軍。橋上的人多一些,行走得快一些,橋體便搖晃得厲害,隨時(shí)都會(huì)垮塌。可是分批過河,速度又太慢。
火把照亮了武陽村的夜空,紅軍戰(zhàn)士的說話聲、咳嗽聲,木橋板的吱嘎聲,驚動(dòng)了附近的村民。一些膽子大的村民循著火把和聲響,好奇地來到綿江河邊,不由大為驚訝:“這是紅軍,是我們的軍隊(duì)呀。”1930年8月,武陽區(qū)蘇維埃政府成立,區(qū)政府設(shè)立在武陽村,下轄石水、武陽、松山、新中、豐田、三壩、肖布、安富八個(gè)鄉(xiāng),全區(qū)人口兩萬一千余人,當(dāng)時(shí)僅武陽村便有九百多名青壯年參加紅軍。村民們送出了自己的親人,如今看到紅軍隊(duì)伍,就好像看到了親人一樣。
了解到紅軍面臨的困難后,地方干部曾光林和鄒光林分頭挨家挨戶進(jìn)行宣傳,動(dòng)員鄉(xiāng)親們拿出床板、木凳、布包、油桶等物品,用來拓寬加固橋面,幫助紅軍過河。
村民們沒有猶豫,紛紛從家里搬來門板、倉板和床板。一位姓鄒的老鄉(xiāng)二話不說將一張嶄新的婚床搬了出來。原來,他的兒子正準(zhǔn)備娶媳婦,按客家風(fēng)俗打制了婚床,剛剛搬進(jìn)家里沒幾天。住在不遠(yuǎn)處的一位老奶奶聽說后,顫巍巍地拉住紅軍戰(zhàn)士的手說:“我家還有木料。”等大家跟著老奶奶去搬木料,才發(fā)現(xiàn)是老人準(zhǔn)備后事的棺木。
村民們和紅軍戰(zhàn)士噙著淚水,將家家戶戶送出的木板運(yùn)到了河岸邊。就這樣,架橋物資很快備齊。老木匠來了,老鐵匠來了,老泥水匠也來了。他們一邊打著木樁,一邊低聲喊著號(hào)子:“心里不要慌,眼睛看木樁。搭好紅軍橋,一起上前方。”很快,一座寬約四米的臨時(shí)木板橋搭起來了。
紅軍隊(duì)伍要開拔了,村民們又急急地送來煮雞蛋、米果、炒豆、花生,塞進(jìn)戰(zhàn)士們的手上,還有的送來草鞋、斗笠和蓑衣,讓紅軍戰(zhàn)士們帶在身上。
可是,大部隊(duì)過河時(shí),橋身仍舊搖晃得厲害。村里上百名男人紛紛跳進(jìn)河中,站在橋身的兩側(cè),用身體頂著晃動(dòng)的橋墩,用肩膀扛著不穩(wěn)固的橋板,保障紅軍順利過橋。還有的,竟讓紅軍戰(zhàn)士踩著自己的肩膀渡河。
這是一座堅(jiān)定的人橋。十月的贛南,天氣微寒,凌晨的河水浸漫身軀,涼意從皮膚沁入骨髓。可是他們咬緊牙關(guān),一站就是幾個(gè)小時(shí)。腿站麻了,肩膀磨出泡了,有的人半個(gè)身體失去知覺,僵硬得不能挪動(dòng),但是沒有人喊累喊苦,沒有人退出人橋。他們只是深情地望著紅軍遠(yuǎn)去的方向,就像是送別自己的親人。
即便過去許多年,當(dāng)年的場(chǎng)景仍被親歷者一遍一遍地講述,他們講到有人當(dāng)完人橋后生病發(fā)燒,講到一處木樁突然折斷,把幾個(gè)撐橋人的腿砸傷了,有人落下了終身殘疾,但是,沒有人流露出一丁點(diǎn)的悔意。他們只是自豪,只是為自己曾經(jīng)拼了命的付出感到欣慰。據(jù)《瑞金縣志》記載,當(dāng)時(shí)全縣集中新谷五萬擔(dān),草鞋兩萬雙,被毯三千條,菜干兩萬多斤送給紅軍,組織群眾為紅軍運(yùn)輸谷子十七萬擔(dān)。每一份物資,每一組數(shù)據(jù)的背后,都是一顆顆跳動(dòng)著的火熱的心,都是一個(gè)個(gè)逃離舊社會(huì)奔向新生活的渴盼。
再后來,多數(shù)親歷者離開人世,但他們的故事經(jīng)由下一代人的口中流傳。他們是這一片土地上的人,他們忘不掉也不應(yīng)該忘掉祖輩的榮光。因?yàn)椋蝗f多名紅九軍團(tuán)的戰(zhàn)士,是在武陽人的幫助下,順利渡到了對(duì)岸,開始二萬五千里征途的。正是這樣的一群人,從武陽橋出發(fā),撥亮了新中國(guó)的燈火。
2017年夏天,一位空軍少將來到武陽橋邊,長(zhǎng)久地駐足凝望,默然不語。天空下著細(xì)雨,在綿江河上點(diǎn)出一個(gè)個(gè)細(xì)密的水波,像他此時(shí)的心緒,潮濕而傷感。少將是替父親回來看望老橋的。他的父親曾是紅軍第九軍團(tuán)的一位連長(zhǎng),當(dāng)年便是從這里渡河踏上了長(zhǎng)征之路。老父親的心中長(zhǎng)久地埋藏著一個(gè)秘密:渡河前夕,武陽村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年非要跟隨部隊(duì)當(dāng)紅軍,連長(zhǎng)便帶上了他。可是后來,在一次戰(zhàn)役的沖鋒中,少年為保護(hù)連長(zhǎng),用身體將他撲倒,自己卻被子彈擊中頭部而犧牲。他永遠(yuǎn)記得,少年?duì)奚按蠛暗哪且痪洌骸氨Wo(hù)連長(zhǎng)!”
這就是武陽的好兒郎,無畏,勇敢。當(dāng)年,就在渡過“長(zhǎng)征第一橋”的一萬多人的紅軍隊(duì)伍中,有七百多名是武陽的青壯年。他們,大多犧牲在湘江戰(zhàn)役中。
每年的清明和端午等節(jié)日,武陽鎮(zhèn)的中小學(xué)校都會(huì)領(lǐng)著孩子們來到渡橋舊址,追憶革命先烈。學(xué)校還將鄉(xiāng)親們幫助紅軍渡河的故事編成了校本教材,孩子們?nèi)级炷茉敗6宋绻?jié),武陽人會(huì)在這里舉行龍舟競(jìng)渡,在鑼鼓和吶喊聲中,用力量和速度重現(xiàn)當(dāng)年武陽男兒的英勇。
更多的人來到這里,尋覓著當(dāng)年紅軍渡河的蹤跡。人們一遍一遍地探究著,一座用血肉之軀筑成的人橋,曾怎樣見證著軍民魚水情?那些幾乎一無所有的鄉(xiāng)親,為何如此信任著這一支隊(duì)伍?如今,時(shí)間已奉上了所有的答案。現(xiàn)在,武陽鎮(zhèn)政府正計(jì)劃著在原址上進(jìn)行原貌修復(fù)。我想,無論它是否脫胎重現(xiàn),都已經(jīng)是一座永生的橋了。這座永生的橋,留下了太多值得深思,又無比樸素的真理。
我在老樟樹巨大的陰涼中久久地佇立,我望見了不遠(yuǎn)處的田園、村莊,一切都顯得安寧而平靜。一輛汽車從新橋上疾駛而過,那橋多么結(jié)實(shí)牢固,從前的搖晃、動(dòng)蕩和脆弱再不會(huì)有了。
朝顏:本名鐘秀華,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魯迅文學(xué)院第29屆高研班學(xué)員,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xué)》《散文》等刊,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麥菜嶺》《陪審員手記》。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