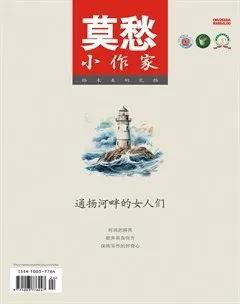一個人的平遙
這些年,我去過不少地方,論風景之秀麗,文化之昌盛,平遙并不顯得獨一無二。但是,當我把種種鏡像疊加在一起,很多時候,腦海中出現的畫面卻是平遙。
當我來到平遙縣衙門口,看到路中央矗立的高大市樓時,忽然挪不動步了。在保定、在淮安、在浮梁,我見過從總督衙門到府衙到縣衙的不同衙門,唯獨這回,我第一次感到氣象森嚴的官府衙門也能讓人感覺如此親近。
那座斑駁滄桑,綠黃兩色的琉璃瓦混融一體的建筑,讓我感到溫暖。我感到這里就是此行的歸宿,一個潛意識里苦苦追尋的家。當你見多了光怪陸離的霓虹閃爍,甫一接觸到這種沉靜的氣息時,你會覺得自己放下了一座無比沉重的山,那種由舊時的檐瓦和墻磚包裹的人間煙火會貼上脊背,輕輕擁著你走進心中的桃花源。
帶給我這種感覺的當然遠不止市樓。看完平遙縣衙,當我置身于有著典型北方氣息的一條商業街時,我有一種別樣的感覺。走進一家賣各種漆器盒的店鋪,一個個精巧漂亮的漆器盒打動了我,仿佛光陰的日歷在迅速回翻,最后定格在一頁上,而那一頁,正是我們在童年寫下的對五彩斑斕的世界的渴望。
為什么是平遙,而不是別的地方帶給我這種感覺?原因還在于山西這片土地。汽車行駛在山西高原上,我有一種奇怪的念想,這片干旱缺水,并不豐腴的土地,如何讓我神往?
公路兩側,莊稼大多已經收割,零星的玉米高粱搖曳在深秋的涼風之中;褐黃色的土地并不平坦,有的隆起,有的下沉,像通往大地深處的階梯。山西高原,這片誕生了堯舜禹等華夏文明先祖的神奇土地,所有能夠烙上文明印記的元素,都帶有一種樸素的泥土根性的光芒,那一層層通往大地深處的褐色泥土,猶如巨大的母體,容納著我們。
平遙之所以天下聞名,除了完整的城墻和布局,最響當當的是它的票號,當我走進日升昌留下的院落時,我驚奇地發現,這么一處原本以為沾染了太多“銅臭味”的所在,竟清幽得像一家書房。院子中間懸掛的“紫垣樞極”牌匾,怎么也聯想不到匯通天下、日進萬金的票號,倒更像一種弘道濟世的人生理想。
事實上,平遙就像一處巨大的天然博物館,有許多地方值得細細玩味,可惜我沒有時間。我跟在導游后面,又去了幾家票號、鏢局,還有博物館,仿佛把一本本應認真研讀的大書僅僅翻開了幾頁,便匆匆合上了。拐出一條巷道,一座高大的城樓出現眼前,前方已是歸程。
一瞬間,竟不知今夕何夕。我仿佛置身于原野之上,使勁地跑呀跑,待到目標終于接近,原來是一座山,上山玩了許久,心滿意足地下山,迎面撲來的是熱氣騰騰的小吃店,大人們帶著笑,犒勞我早已饑腸轆轆的辛勞。
這是小時候的一幅夢境。那座城樓就是山,兩邊的店鋪是滿足兒時愿望的天堂。雖然時間變了,地點變了,但氤氳著炊煙夕陽的情境沒變,古拙簡單的街市格局沒變,老鄉們古銅色的臉上質樸的笑容沒變。
一個人的平遙,一個人的原鄉。
?
張凌云: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多家報刊。出版散文集《高樹鳴蟬》《曉月馬蹄》等。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