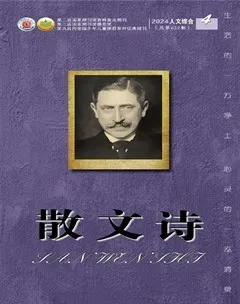清溪筆記·之四 曾記舊時溪
我的腳,甫一觸地,就進入了一個碩大廣場,那里有一座《山鄉巨變》人物群雕。除了周立波,我把所有的農人都看作是當代農民的樣子。我的腳步向西,沿村路下方草地往北走,即是有著1500米的清溪畫廊。石頭與石頭,以碑的形狀,匍匐河岸。石頭,西臨村路,東臨稻田菜地。人走路上,低頭即可覽讀部分小說細節。似從另一時空導引人們進入“曾經的”農耕歲月。有效進入一種語境。山鄉故事,從踏人第一步開始,慢慢閱讀,悉心傾聽。那是“過去時”的村莊,那是一個熱忱炙灼的時代。特別是人的精神、靈魂、情懷和理想。
雨水將麻石路濡得濕潤,又恍然看見,當年周立波先生披雨行走的鏡頭。他長得高大、瘦削,穿著雨衣,雖然肥了些,但仍挽了袖子,為了露出手,握拿鍬鋤。雨衣半遮半掩著臉龐,全身泛著雨水的柔亮光澤。肩膀聳起,略微彎腰。走近看:那“畫廊”一幅雕像側影。不是披著雨衣,而是敞著衣裳。遠處所見的,或是一株大樹的罩影。雕像下有曲曲彎彎、狹狹窄窄的小路,有一個岔道,通向田塍和房屋……畫廊展示的是上世紀50年代中國湖南鄉村的意境。“已經沾了春,地氣不同了,雪花才停住,坪里、路邊的積雪就都融化了。到處是泥巴。大路中間,深淺不一的爛泥里,布滿了木屐的點點的齒跡和草鞋的長長的紋印,有些段落,還夾雜著黃牛和水牛的零亂的蹄痕。”在清溪村,我已然熟悉了周圍的山嶺和河流。我把自己置換成了一個站在上世紀50年代的湖湘農人。那時候,我還沒出生。直到上小學時,讀了《山鄉巨變》的連環畫,印象深刻,由著名連環畫家賀友直繪制,據說賀友直先生為了貼切地表現原著,特意來此地居住,悉心揣摩,與農人一起勞動和生活,歷經三年,兩易其稿,叉從明清木刻版畫中尋找靈感,終于完成了這部大型的線描連環畫精品。
農人,敞開衣服,戴著草帽,裸腿赤腳,趟水田,插稻秧。形象是瘦弱的、精神的,臉上淌汗,佇立水田,走進田塍。眼前的周立波,既是一位干部,也是一位農人,更是一位理想主義者。那時候,每天下午,當天色漸晚,勞動結束,他一定會像索爾·貝婁所說那般“想著未來”的樣子:“霞光漸慚地變了,這是必然的。不過我總算再次見到了它,如同抵達了涅槃境界的邊緣。我就這樣,不加阻撓地讓它消失了,心里盼望著50年后它再重現。”人是有肉身的人,也是有理想的人。每個人都有三種世界,一個在內心,一個在外面,另一個則由本人創造。離開這三個世界,人是無法活下去的。
清溪畫廊主體畫是《山鄉巨變》小說內容。雖說是極少部分片斷,拍照卻不能滿足。拿出筆,在小本子上記錄,哪怕突然冒出一個微小的詞語。比如,50年代農人,經常穿的草鞋、解放鞋、圓口布鞋,或者赤腳,清淡歲月與譬喻聯類,生發諸多思考。當年,“農民都是把雜糧摻在大米里吃”“好多農民喂不起豬、雞、鴨”……1955年2月21日,周立波在寫給中央領導的信中,講述了他在家鄉益陽清溪村四個月所目睹的糧食短缺問題。糧食是現實農村的主要問題。民生是個大概念,要讀懂,需要深入。與農民一起生活,才有體會。
山嶺里到處都是桂花的香氣。自然山水是美的,農人的理念需要變一變。在創作短篇小說《蓋滿爹》后,1955年秋,周立波再一次回到故鄉益陽。比照小說里的人物——如果將現實里的人物,置放在同一個畫面、同一個時空里,又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境呢?從社會層面說,是一種“鏡鑒”的比照。從藝術上說,有如電影之“間離”的蒙太奇效果。一段段故事,一樁樁事件,帶著昨天的現實和今天的現實。在此進行有效比對,在此進行有意義的展現。長鏡頭、短鏡頭,慢慢打開、放大。這些雕像或畫,沒有花里胡哨,沒有斑斕蕪雜,恰到好處。1500米,有如1500個歷史閃回。歷史到了一定時候,戛然而止了。
還原“文學現場”,讓“文化地理”更具感染性。特別是宏大題材的鄉村敘事,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與思考。小說現場的“山鄉”,獨具形式和內容:山陵、河溪、田園、村舍,等等元素,都會激起人們的反響。與其空間斷續相反,立體主義者創造了結構的續接。我們不必從作品結論或意義來言說,情節的認知,就已足夠。廣場西北角,一眼水井旁,一座雕像,刻畫了《山鄉巨變》開篇,女干部鄧秀梅初來山鄉,向一位“愛笑的”姑娘問詢“鄉政府是哪個屋場”的聊天情景。這位姑娘,就是盛佑亭(亭面糊)的“房份”(宗族)侄女盛淑君。
鄧秀梅走上幾步,跟挑水的姑娘并排地走著。從側面,她看到她的臉頰豐滿,長著一些沒有扯過臉的少女所特有的茸毛,鼻子端正,耳朵上穿了小孔,回頭一笑時,她的微圓的臉,她的一雙睫毛長長的墨黑的大眼睛,都嫵媚動人。她膚色微黑,神態里帶著一種鄉里姑娘的蠻野和稚氣。鄧秀梅從這姑娘的身上好像重新看見了自己逝去不遠的閨女時代的單純。她一下子看上了她了,笑著逗她道:“你為什么猜我是搞兵役的呢?怕你愛人去當兵,是不是?”挑水姑娘詫異而又愉快地抬起眼睛,嘬著嘴巴說:“你這個人不正經,才見面就開人家的玩笑,我還不認得你呢。你叫什么?哪里來的?”
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人物對話,也把“愛笑的”山鄉姑娘盛淑君寫得靈動可愛。眼前的雕像,如同真人一般,將小說內容表達出來。健康的生命,在蓬勃的山鄉,“參與”了故事的講述——一是山鄉。曾經的山鄉村莊原型。二是人物。小說文本里的角色虛構。三是現實。自覺或不自覺的比照。三者達成了對“過去時”事件的“完成”的參與。在我看來:畫,只有通過“觀視”,才能完成它的存在價值。而在青山綠水映襯、故事發生地的“本土”,似乎又多了一個更為真切的“解讀”效果。這是一種“重喚”記憶的最佳方法。歷史是要被記錄的,只是方式不同罷了。小說往往更能自由發展故事的內在品質。作家或藝術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就會有所式微,少有人記得他深入生活的情境。有時候,我們可以獲知當時作家的想法,堅持理想,堅持現實主義創作。且所謂的“理想”,也一定是“發展”的。畫廊是記錄時代故事的載體,以諸多情節,提醒鄉村,我們沒有理由忘記,那一段不平凡的歲月。
石頭墻壁,掛著木刻畫。周圍草地,立著大比例的人物雕像。廊道的長亭棚頂之上,懸著玻璃版畫。小說里的人物,被不同的載體舉著、托著,栩然活脫,呼之欲出。藝術化了的小說情境審美,盡可能多地,在益陽清溪村的土地上呈現它的原貌——坐在扁擔、穿著草鞋抽煙的菊咬筋;赤著腳,手里拿著樹枝條,趕著水牛的亭面糊:與亭面糊說話的陳先晉:手里拿著文件的鄧秀梅;挑著滿滿一箢箕淤泥的劉雨生;溪邊放牛飲水的謝慶元;等等。以及大大小小的排成了路徑的石磨碾盤,還有灌溉農田的水車、溪邊鉗人泥土的大塊青石、老式的木制的脫谷機。那些雕塑幾乎與真人一般大小:拿著簸箕和漁簍、溪水里撈魚蝦的孩童,扛著镢鋤、挑著箕筐的漢子、牽著水牛的老倌子,從山上下來的背木柴的小伙兒……
進村子的大橋那里,有一塊水田。冬季的水田,水已不多。但可以透過凌亂的稻根兒,看得到它們在水中縱橫交錯的紋理。碎桿兒似的,輕快的筆觸,暗示的波動。陰影部分有如鉛筆繪畫的皴擦感。水里倒懸著橋墩的射影,像碩大的詞匯,光與光的真實表達,客觀上說,天地遠近,在此變得模糊。故事蒙在了氤氳的清霧里了。而所有的這些景狀,都似乎營造出一種真實性的存在。與小說里的情境相比較,有一種若即若離的驚詫感。
卜雪斌帶著我去梨園拜訪88歲的周兆民。老人面色紅潤,健談,一邊聊天,一邊摘菜。他是周立波先生的侄子。他說《山鄉巨變》是從“泥巴里”掏出來的一部小說。在周兆民的記憶里,周立波是個勤快的人,天沒亮就起床寫作。然后又到田里,做凼肥、插秧、扮禾。春耕翻土、早稻搶收、晚稻搶插,都和鄉親們一樣,腰系一條淺藍毛巾,扎腳勒手,汗流浹背,從早晨到傍晚,鄉親們叫他“立波胡子”。“今天早晨和上午幫農業社插田,在田里看見兩條螞蟥”“白天參加了田間檢查……來回走了二十多里路……”周立波日記這樣記述。周兆民說,周立波口袋里揣著小本子,村里的事情,他記在上面。特別是在“扮禾”時候,看到老把式們,身手擺動,將割下來的稻穗,摞在一起,再手腳配合,將沉甸甸的稻穗,放人打稻機,一陣轟隆聲中,金黃飽滿的稻谷,從機器的底部灑落出來,逐漸堆滿。有時候,他經常掏出一個小本子,記下鄉親一邊勞動,一邊說的風趣幽默的話,作為小說里的人物對話素材。
在溪水里玩耍、用竹箕撈魚蝦的“孩子”,凝固成了時間里的陳述。“孩子”會告訴現實里的孩子:該有一個怎樣的童年。人在童年和少年,所見的故鄉,印象最是深刻。也會由此形成獨立的判斷和價值取向。美好的人類圖景,就是在那個時刻形成的。其精神與靈魂,將是干凈的、美麗的。在一個人的腦海里,作家的故事,正以一種“世界圖像”浮現出來:流過青石的溪泉、起伏連綿的山脈、柔曼亮麗的田野。天人合一,自然之美,愉悅心靈。
小說猶似一把尺子,丈量著現實社會。每次我都會從畫廊走走,走約一千五百米,到百味果蔬園子,順村路向東走兩百來米,到“立波書屋”找卜雪斌聊天。某天大早,與詩人古玄一起游走畫廊。看到一牌刻一首詩:“說是清溪沒有溪,田塍道上草凄凄,山邊大樹迎風嘯,村外機車逐鳥啼。”隨口而作,沒有署名。古玄說,這是周立波當年的詩作《夢回清溪》。詩句析出許多詰問:有溪無水。草木凄凄。大風吹蕩。村外來往的車驚起鳥兒。好像訴說著什么,每一個字詞,都似乎進入一個年代,有些猶疑,也有些傷懷,更有些悵然失落。
淡淡的愁緒籠罩。當年村旁有條小溪,叫清溪。村人說,以前這條小溪很美。但是,60年代初期,清溪干涸了,兩旁山上樹木砍得太多。周立波心生悵然,寫了一首打油詩道出心情。后來經過農田改造,路邊樹木又多了起來,溪水也流得歡暢。周立波心里豁亮了起來,他又將此詩,進行了修改:“誰說清溪沒有溪,田塍道上草萋萋。鐵龍村外迎風嘯,紫燕林邊向日啼。”從憂到喜,從輕愁到朗然而悅,全部的情感,都蘊藏在詩意里了。
田野的肖像是需要訴說的。當年的顏色,或許會讓人想到波德萊爾和艾略特,也讓人開始了解時代的“前夜”到底是怎樣的跡象。時代的尷尬,在于價值體系的認知、莫過于理想是否有效搭配。梭羅說:“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諷喻性,似乎要遠遠超過真實性。”“除了更深地去愛,沒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療愛。”當年的心境,即是如此。周立波一直客觀思考改造山鄉的某種可能性。他抱有希望,是對自己的鄉土有極大興趣。也因此,他三次回到山鄉,也讓他“繪出”山鄉之圖像渾然天成。從而受到了人們的敬仰,也為時代所青睞。小說以“對話”為主要言說。行文中,有方言鉗人,這使得鄉土小說,更具有獨特的地域味道。若沒有個體的山鄉體驗,恐怕難以駕馭如此龐大的農村變革之宏大題材。
清溪村,與近在咫尺的市區有些微區別。或者,丟失了鄉愁的人,會在這個地方贖回。我十分介意鄉村的意境,亦要做類似的事情:在我到達采訪對象那里時,要用最快的半個小時或者更短的時間,站在這些雕塑和石刻畫面前,聽一小段故事或琢磨一件小故事,心生一段感想。或從周立波先生的某一短篇或長篇片段里,發掘一兩個問題——就跟當年的亭面糊或菊咬筋一樣,內心會有這樣那樣的想法。甚至僅僅是,換了一小片兒時空,便可見到、聽到本來陰郁的云天,所無法出現的那幾縷溫馨的陽光。當我認真思考鄉村現實如何改變人們的觀念時,那些曾經的懷疑和觳觫,又如何讓我認真并涌起點滴的詰問?
詩人古玄是本地人,他說每次來清溪,他都喜歡在這個廊道走走,每走一步,都要低頭看青石板上所刻的文字。然后,回到家里,打開小說,從里面,找出連環畫廊里的石板或石頭墻上讀到的人物。小說的歷史情境、現實陳設的內容,便會紛至沓來。
農業問題,就是世界問題。我想說的是,所有的問題或者等待著我們,離未知世界只有“咫尺”的距離。有些人呢,似乎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停下來,慢慢咂摸。
我專挑選一些清晰字跡來進行拍照。石塊,像打開的竹簡冊頁,歲月不能全部磨損記憶。沒有比石頭更明白無誤地呈現故事本身的了。石頭是冰冷的,也是熱誠的。呈現著凝固了的歷史。無論過了多少年,那段記憶,是不會改變的。小說的細節,往往會透露出些許時代的問題,更多的,是關于改變農業理念的問題。那些未曾中斷或已經終止了的路,是一條可以溯源的水脈。真正發生的事,帶來的,是一種轉變。換句話說,農業問題,就是糧食問題。就像石頭,你很難覺察其中堂奧,但是拂去蒙塵,剖剝見真。所選擇的段落,或有其代表性。每一個段落,都能勾起記憶。周立波是寫農村題材的作家,也是小說高手。這些石頭,是小說的細節,更使得文學地理,充滿了趣味。我的手機儲存卡里,蓄滿了斑駁于風雨濡瀝的石頭,像似找到了諸多的歷史遺跡,也因此有了某種無法言說的重量——
秀梅聽說過這個人,是個討得媳婦嫁不得女兒的家伙,不禁仔細瞅了他一眼,正在這時,有個短小的中年人走進會場,大春對秀梅說:“他是劉雨生的舅子張桂秋,綽號秋絲瓜,是個詭計多端的家伙。”
陳媽媽見他發火,忙帶著兒女,都去睡了。陳先晉獨自坐在火爐邊,把四十年來的苦日子一遍一遍地想,到雞啼也不想睡。陳媽媽在里屋喚道:“睡吧,明天還要去挖土哩。”
菊咬筋老婆是個厲害角色,可是怕菊咬筋,不敢多問,舀了碗冷水,給他扯痧。后頸窩、眉心、背脊,都扯出了一條條紅痧來。
感覺周立波就是一位畫家。他把握了農人的性格,描繪出了山鄉諸多人物的畫像。惟妙惟肖,蘊含靈趣。歡喜的、有心事的、疑慮的、徘徊著的,也有平靜等待著的。陳先晉,并不先進,而是對“改變”有著些許顧慮,也因此抵觸。劉雨生,面相和善;謝慶元,眼神陰戾;亭面糊與陳先晉的年紀、打扮差不多,但這兩人,一個沉穩,一個詼諧;菊咬筋,心事重重;秋絲瓜,讓人膽寒;盛淑君,聰穎調皮……但是,他(她)所具有的能量,決不甘于被其描述功能所完全吸收。從而讓一個時代不但認識到了小說的主題,也能從中領會到,那些個情境,如何被現實所認知、所辨析。人物個性,即是現實人性。人物特征,即是時代特征。現實主義所表達的,其實是人物個性與特征。文學如此,戲劇如此,美術如此,音樂如此,舞蹈如此。小說需要虛構,但是小說所傳播的現實,應該基于現實,而非悖離現實。
文學和藝術,是隨處生長的樹木,但絕不會是北方冬季都市街道兩邊的塑料花,那些沒有生命價值的存在,有等于無。現實主義相信的是:文學會記錄一個時代人的生存狀態和集體命運。文學要忠于時代,虛構中亦有真實的存在。對于作家而言,他所注視的時代像是一個祈禱的目標,一種可能接近的方式。即便無法抓住那樣的一個絕對,但當注視產生理想,那么,他一定會為這個理想而有些作為。小說的人物,反觀小說家的立場。一般來講,沒有人不會為自己的出生地無動于衷的。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這樣描述故鄉:“這個離城二十里的丘陵鄉,四圍凈是連綿不斷的、黑洞洞的樹山和竹山,中間是一大片大塅,一坦平陽,田里的泥土發黑,十分肥沃。一條沿岸長滿刺蓬和雜樹的小澗,彎彎曲曲地從塅里流過。”
畫中“人”是上世紀50年代的裝束,粗布頭巾裹纏著,鞋是自編的草鞋或老式布鞋,短衫褂子。是此前未曾有的,抓住文學作品里文字瞬間流露的人物個性,“逼似”概念下的時代理喻,而非單純的那種對小說作品的人物析論。這里不搞作品介紹或故事梗概。而是直接打開了“一部書”。每一次“翻頁”,都會找到熟悉的章節、段落,從而溫習和裨補了快要遺忘的故事。從對人物的描述里找到獨有的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讓在此地生活的人,認為自己仍然生活在小說情境中,也讓來這里的人們,直接進入“小說的現場”。
這些正是在規劃清溪時所規劃的重點:以畫廊為主體,結合地面鋪裝、雕刻畫板和駁岸設計,展示《山鄉巨變》巨幅連環畫,也拓寬了清溪渠,把對岸的水田做成稻田景觀,把周立波回憶清溪的詩句做成景墻,多形式、多角度,展示清溪村人文和民俗。
畫以小說為載體,讓主體人物活靈活現呈現,讓人們能夠分辨出人物的形態及其內心活動。雕刻家是一位高手,能掌控刻刀的力度,使得人物的精神風貌,吻合于小說情境。也與周遭搭成和諧。事實上,這是一個置于外部的“情景劇”,不同的是,它有三種人群的參與:一是小說中的人物:二是現實中的正在田里勞作的農人;三是游覽者本人或團體。臺詞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攜帶情節的石頭們,充滿了自信,慢慢展開其故事脈絡。即便打開了小說《山鄉巨變》,也不一定能夠跟得上。鄧秀梅、菊咬筋、亭面糊、陳先晉等等,無疑會被他(她)的讀者們,在各自的內心,重新詮釋,重新認知。
無論是石板刻畫,還是木刻烙畫,或是雕像,都極好地“搭配”村莊的景色。水清得隨手可掬。溪流時緩時急,時大時小。水中有碩大的石頭,也有中等的如南瓜般大小,也有小如拳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讓溪水發出了不同的聲韻。淙淙流水,又似管弦的聯奏。除了石板刻鋪成的小說情節,仍有麻石路徑,使得天降雨雪時,也不至于滑倒。這個畫廊之路,不封堵,不搞欄桿,完全是“敞開”的。這樣的敞開,讓腳步隨時進入田野,又可以直接上到西邊的路上向南北村路走走。草地有綠也有枯黃。容不得人們對其忽視,或者對其無意識存在的不察。那些新獲得的部分砌筑,也是有道理的。沒有生態破壞的修筑就是建設。人們走在這樣的路上,首要的,是有一種自在感,而非被風景所束縛。
想到了東側的田野在秋天豐收時的情景。像電影《云中漫步》,男女主角,與村里的鄉親一起,慶祝葡萄豐收的歡樂場面。那是一個夢境般的家園:葡萄園子、牲群、木屋、載歌載舞的人們。恍如回歸到了農業社會的古典原初。我所尋找的這樣的古老城村,正是“人類大鄉村”意象的存在。田塍的邊上,常有水井,以不加磨砂的麻石鋪鑲的井臺,方型的,圓型的,都有。井邊上,大大小小的磨盤,有的磨損得模糊了紋絡,有的勉強還算清晰。井水清澈,滿滿的,似要溢出的樣子。井是不凍井,即便冬天,也不結冰,也不能被雪覆蓋住。也可能有樹,但在田野里是極少的。樹們在宅屋門口、街路兩側、堂館那里,或者在山上。
生態就是佳境,自然就是美景。如今河岸也變了模樣,臨山的這邊,立著一棵棵粗壯的茶子樹,或者是香樟、冬青、烏桕、桂樹、樸樹和酸棗樹。身后是流水。那個時候,沒有閑雅,只有勞動。現在的清溪村,成了益陽人的打卡之地。因為周立波,因為《山鄉巨變》。見到美境,需要呼朋引類,一同分享,一同游走。櫻子說,她幾乎天天都來清溪村。有時候一個人來,有時候約上學校的老師,或約上女散文家斤小米一起來。前山和后山,哪個山坡,哪片竹林,哪個水塘,看清溪的角度,就有所不同,拍出的畫面也就會各有所好。
清溪村是得天獨厚的村子。一是離市區不遠。二是處于山谷地帶。水系包含了湖、溪、河、江,而且水源天然。比如河道的保護,由幾個村組——楓樹山組、高碼頭組、清溪村組、郎樹灣組、鄧家灣組、鄧石橋組、朱家村組、賈家灣村、栗山坪村、益清堂村等負責。因此,河流清澈,沒有污染。植物和菜蔬,繁茂、蔥蘢,成了一個富庶之地。自然之魅,是吸引周末城區的人來此采野菜的好地方。清溪村周邊沒有工業污染,也沒有企業排污,是一塊完好無損的山地區域。我第一次來時,正是初夏,樹木蔥茂,田野盈翠。這一次又逢大雪,復述的故事是寂靜的。哪怕什么也不用做,專來聆聽寂靜,也是好的。可以確定的是,與其說是來尋覓故事,不如說是來描述寂靜。寂靜之地沒有墻壁,向天空敞開。山谷、澤畔、田塍,美輪美奐的意境,讓我想起了王摩詰。我一直喜歡王維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有一次,在輞川游玩的王維,忽感獨游無趣,想起“彈琴賦詩,嘯詠終日”的老友裴迪,約他來山中一同賞景,托一采藥人(黃蘗人)給裴迪秀才帶去一封清雋雅致的信。他這樣寫:“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絛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錐。斯之不遠,倘能從我游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我來益陽的前一晚,恰好下了大雪。道路、街巷、公園、城鎮、山林,到處都是積雪,整個天地銀妝素裹。我與詩人卜寸丹、陳旭明、古玄、黃成玉,攝影家曾麗霞等一同游走清溪村。高興見到潔凈的山村。大口呼吸清冽的空氣。有時候,走路碰到竹子,還會有雪粉紛揚而下。走在臺階上,上有一些被腳印踩實了的雪冰,不小心的話,會滑倒,或者摔個踉蹌。那些被雪壓彎了的楠竹、埋在葉子和雪里的小金桔、被雪雕塑成的翡翠般的蔬菜、溪邊的水井,似乎將人帶到了另一個世界。有如《納吉亞傳奇》中的雪天,一群孩子進入了想象中的仙境、潔凈的“屋舍儼然”之山野之城,而非遍地雞鴨豬牛之遺味不堪嗅聞的村莊。能與“天機清妙者”,同游山野,隨時迎納清風,隨時摟抱細霰。如果在資江邊或者志溪河畔,也一定能看見白魚在水面上騰躍,飛鳥在天水間翱翔……此等“故人莊”之絕美情境,確有“深趣”。這樣的佳境,摩詰和裴迪,一定沉醉其中了。
初到黃州的蘇東坡,在《臨皋閑題》中描述:“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耳。”多么灑脫、多么樂觀!在這個遠離稅賦和官場爭斗的幽僻的黃州臨皋,雖不是他的故鄉,他卻將之當作了自己的故鄉——大江、清風、明月。這些沒有主人的自然風物,誰得見,誰就是美境的主人。在《記承天寺夜游》與《前赤壁賦》中,也都有呈露“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等等,這番對于自然大境的感悟,都是帶有“鄉梓情結”之心靈映現。
陶淵明、孟浩然、王維、蘇東坡、梭羅等,總是把自然大境納入詩性的、精神性的審美視域,從而完成生命歸宿意義上的“精神還鄉”。這種精神或靈魂的村莊,也許是他們的人生所向,是一個寄存夢想的地方,從而慰藉曾經的困苦和痛楚的心靈。不論時世如何改變,他們內心的山水總是純凈的。而一位詩人能給予別人的高貴禮物,就是他純凈的文字蘊藏的天地大美。一代大家正是以不凡的筆觸,讓我看見了一個個絕美的精神故鄉之所在,并且與他們一起去深愛。在他們筆下,大地村莊,山水挹趣,主客互融,物我一也。靈動的文字隱藏的文本喻意和人類大同之抒寫,實乃大家氣象。清溪村是歷史的村莊,亦是人文的村莊。
這個離城二十來里的丘陵鄉,四圍凈是連綿不斷的、黑洞洞的樹山和竹山,中間是一片大嘏,一坦平陽,田里的泥土發黑,十分肥沃。一條沿岸長滿刺蓬和雜樹的小澗,彎彎曲曲地從塅里流過……雖說是冬天,普山普嶺,還是滿眼的青翠。一連開一兩個月的白潔的茶子花,好像點綴在青松翠竹間閃爍的細瘦的殘雪。林里和山邊,到處發散著落花、青草、朽葉和泥土混合的、潮潤的氣味。一進村口,鄧秀梅就把腳步放慢了……
“眼界高時無礙物,心源開處有清波。”現實的清溪村,是鄉村振興的一個典型模板。在我看來,清溪村不僅僅是益陽的,還是整個湖南的;也不僅僅是湖南的,還要成為全國的。謝林港鎮有“城鎮一體化”的基本設施:劇院、飯莊、公園似的池塘、規范的鄉鎮衛生院、娛樂場地、幼兒園,等等這些,是對現代意義的“大鄉村”的詮釋。不限于設想,不限于人文學者構筑的理念范疇。人們徜徉在村子里,與游逛在城區公園,感受其實是一樣的。從人們走路姿態和語言,能夠判斷生活的質量和品味。
鄉村生活的進步,是人類生活的遠景。理想村莊的打造,需要幾代人,更需要返鄉歸來者。比景觀更重要的是文化。是清溪鄉那些充滿趣味的、平平凡凡的、融人了山水間的農民。它意味著人的福利、健康的生活和樂觀的精神,非一朝一夕所能一蹴而就。土地只有在充分利用前提下才是豪侈的。任何對土地的覬覦,都是錯誤的。正確的農業理想,反映給大地,都是簇新的、可持續發展的。“瓜瓞綿綿,爾昌爾熾”,時代變化,社會進步,人類精神是偉大的。從凈潔的清溪、平坦的主街、有標志的巷道、廣場等等,就可以反映出來。與人類文明的進度,是同向的。我在村子里游走時,發現路邊樹立著一個小牌子,上書兩行字:“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清溪村廣場在公路邊,城里來的人,可隨時下車觀游,也可在空地停車而不用擔心被收取費用。那次我們去桃江,亦男就將車子停放在了清溪村人口處的廣場西側空地,返回時再取的車。去桃江,車子是要從村子邊經過的。這里有一個大型群雕像、一大片麻石鋪成的廣場。清溪人過年過節,在廣場聚集,燃放鞭炮,觀看花鼓戲。
小說里的“人物”以另一種形態留存。樹木亦會像老物件那樣留住。清溪村在屋舍翻蓋、村道整治時,沒有掘挖樹木,也沒有伐鋸古樹,仍然保持山鄉之原生態。清溪村將古樹,全部保留下來。村子里的古樹,掛了“益陽市古樹名木保護牌”,編號、中文名、保護等級、樹的科屬、樹齡、養護責任單位等等一一注明。荷花塘,春萌嫩綠,夏染輕紅,秋舉蓮蓬,冬映枯槁。風物透視浪漫主義、表達印象派藝術。春天的荷葉萌出了莫奈的意境,秋天的荷葉勾勒出吳冠中的筆觸。不需將真實變形或解構。自然而生的藝術,才是大地的審美。來清溪的畫家,首先將最美的色彩和筆墨留給了清溪荷塘。蓮葉的舒展,芰荷的凈美。“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到清溪看荷、讀蓮,成了益陽人休暇必選。招引游客前來拍照打卡。鄉村向著桃源美源的方向行進,現代意義上的鄉村,是城市的一個天然有機整體,是城市結出的蜂巢。與之比較,城市反而變得局促、逼仄,如波德萊爾所說:“城市的形式。唉,變得比人心更快。”現在說,鄉村是城市依附的風水寶地。美好從來不是孤單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所謂的“美好”,應該是——無論是城市,還是山鄉,全都應該是:自然與人,相互襯托、相互輔助、相互提升精神境界,如此,才是真正的生態、真正意義上的曼妙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