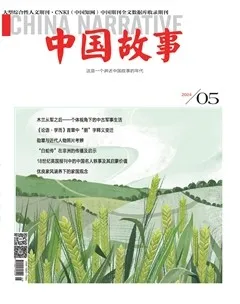清代咸豐年間貴州紅號(hào)軍起義與燈花教關(guān)系芻議
作者簡(jiǎn)介:楊慶麟,貴州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
【導(dǎo)讀】清咸豐年間,受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的影響,貴州爆發(fā)了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shí)間最長(zhǎng)、參與人數(shù)和民族最多的一次農(nóng)民起義。這場(chǎng)持續(xù)時(shí)間長(zhǎng)達(dá)近二十年、覆蓋貴州全省的大起義,是貴州歷史上一場(chǎng)規(guī)模空前的反抗斗爭(zhēng),其中就包括紅號(hào)軍起義。已有研究多是以貴州號(hào)軍起義為研究對(duì)象,較少對(duì)紅號(hào)軍自身進(jìn)行研究,其與燈花教之間關(guān)系亦少有關(guān)注。本文以紅號(hào)軍與燈花教的關(guān)系為對(duì)象,通過對(duì)史料的梳理,對(duì)兩者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討論。
近代以來(lái),清王朝的統(tǒng)治越發(fā)腐敗,致使地方社會(huì)民不聊生。而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的興起,則成為一根導(dǎo)火索,迅速點(diǎn)燃了各地民眾的反抗情緒,一時(shí)間全國(guó)各地紛紛爆發(fā)起義運(yùn)動(dòng)。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貴州爆發(fā)了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shí)間最長(zhǎng)、參與人數(shù)和民族最多的一次農(nóng)民起義——“咸同大起義”。這場(chǎng)起義以咸豐四年(1854年)獨(dú)山楊元保起義為開端,之后相繼爆發(fā)了桐梓楊鳳喜起義、銅仁紅號(hào)軍起義、甕安黃號(hào)軍起義、思南白號(hào)軍起義、張秀眉苗族起義、回民起義等。其范圍波及貴州全省及川、湘、桂、滇諸省及與黔毗鄰地區(qū),涉及漢、苗、侗、布依、回等諸多民族,一直持續(xù)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方才平息,前后歷時(shí)近二十年。
在這場(chǎng)聲勢(shì)浩大的起義浪潮中,先后有數(shù)十支不同規(guī)模的起義軍。其中以號(hào)軍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shí)間最長(zhǎng)。所謂號(hào)軍,主要是對(duì)咸同年間先后起事的紅、白、黃三色號(hào)軍的統(tǒng)稱。因三者起義發(fā)動(dòng)時(shí)間相近,起事時(shí)的范圍多有重合,加之三支起義軍與民間信仰均有密切聯(lián)系,起義時(shí)皆以布包頭為標(biāo)志,故將三者統(tǒng)稱為號(hào)軍。關(guān)于貴州號(hào)軍起義的研究,歐陽(yáng)恩良圍繞民間教門與號(hào)軍起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進(jìn)行考察,指出貴州號(hào)軍起義是一次綜合了民族矛盾、階級(jí)矛盾等多種因素在內(nèi)的民間教門起事。曾召南以劉儀順為切入點(diǎn),通過梳理燈花教的創(chuàng)立過程,對(duì)其領(lǐng)導(dǎo)貴州號(hào)軍起義的經(jīng)過、起義失敗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進(jìn)行論述。如前所述,已有的成果大多將目光聚焦在號(hào)軍整體,對(duì)于三支號(hào)軍的個(gè)案研究較少,特別是紅號(hào)軍與燈花教之間關(guān)系,尚未得到關(guān)注。本文以紅號(hào)軍為對(duì)象,通過對(duì)文獻(xiàn)史料的梳理與分析,嘗試還原紅號(hào)軍與民間信仰燈花教之間的關(guān)系。
一、紅號(hào)軍起義始末
紅號(hào)軍起義主要是指咸豐五年至七年(1855年至1857年),發(fā)生于銅仁府地區(qū)的以抗“折征”為目的,以徐廷杰、梅繼鼎、毛大仙等為首領(lǐng)的農(nóng)民起義。咸豐五年(1855年)十月,徐廷杰、梅繼鼎等率領(lǐng)民眾以反抗清政府實(shí)行的“折征”政策為口號(hào)起事,并迅速攻占了銅仁府。因起義軍“以紅巾蒙首”,故“名紅號(hào)”。紅號(hào)軍攻陷銅仁府后,略作休整,旋即開始向周邊清政府控制的府縣發(fā)動(dòng)進(jìn)攻。“銅仁賊初二日陷松桃廳城,署經(jīng)歷陳鏞死之。署同知恩彬、署副將鄂清遁。四日陷正大營(yíng)。十三日陷思南府,署知府福奎、署游擊信珠隆阿、署安化知縣吳云煦遁,教授張鴻奎死之。十五日陷印江縣城,代理知縣何維炘遁。十六日陷石阡府城,署知府黃培杰、署都司陳定元遁。各城旋復(fù),惟石阡為賊據(jù)。二十七日,陷玉屏縣城,署知縣吳曾保等遁。”至此,紅號(hào)軍不僅接連獲得勝利,還建立起起義軍根據(jù)地。之后為進(jìn)一步擴(kuò)大戰(zhàn)果,紅號(hào)軍四處出擊,“十二月,銅仁賊連陷思州、清溪,復(fù)陷玉屏。思州知府張瀚中,署玉屏縣兼管青溪縣事吳曾保均遁,賊旋去之。”在此過程中,隨著清政府從之前的驚慌失措的狀態(tài)中逐漸恢復(fù),以及鄰省清軍進(jìn)入貴州,起義軍的攻勢(shì)受到了不小的遏制。“(紅號(hào)軍)趨犯邛水,署縣丞劉侶鶴,署游擊楊家瑞出御,千總汪尚壎自鎮(zhèn)遠(yuǎn)來(lái)援,合擊敗之,敵還思州。湖南護(hù)辰沅永靖道翟誥等出境會(huì)擊,鳳凰廳土守備吳永清,舉人吳國(guó)瑞等先至松桃,敵退。”紅號(hào)軍與清軍進(jìn)入了相互對(duì)峙狀態(tài)。雙方秣馬厲兵,整頓軍備,均在為接下來(lái)的戰(zhàn)斗做好充分準(zhǔn)備,以期能迅速擊敗敵人,獲得勝利。
不久,清地方團(tuán)練發(fā)起進(jìn)攻,紅號(hào)軍主動(dòng)出擊打敗敵軍,但被聞?dòng)嵍鴣?lái)的清軍偷襲,石阡府被清軍占領(lǐng)。“六年(1856年)正月,舉人劉慶元,生員劉鳴盛、楊應(yīng)清、周橫等來(lái)援,敗死。上元監(jiān)生朱巨川、朱錫蕃赴援,又死之。既而賊眾往燒直橋,知府黃培杰、都司陳定元聞城內(nèi)空虛,悉屠城內(nèi)余賊。”清軍收復(fù)石阡府后,決定乘勝追擊,繼續(xù)向起義軍根據(jù)地和銅仁府方向發(fā)起進(jìn)攻。紅號(hào)軍雖頑強(qiáng)戰(zhàn)斗,但因寡不敵眾,不僅根據(jù)地被清軍攻占、摧毀,起義軍首領(lǐng)徐廷杰和梅繼鼎也相繼戰(zhàn)死。“徐廷杰等出城走死,梅繼鼎中炮早死,銅仁城亦復(fù)。敬烈、培杰等乘勢(shì)毀石阡荊竹,平賊營(yíng),賊退毛家寨,復(fù)毀之。”在此期間,起義軍另一名首領(lǐng)毛大仙,也因?yàn)榧t號(hào)軍內(nèi)部叛徒出賣,被清軍俘獲后處死了。“茶寨王士秀。士秀亦號(hào)大仙,先與合。至是縛獻(xiàn)大仙及其弟土福,印江教首李春林亦降,培杰誅之。”之后,雖還有一部分紅號(hào)軍仍然在繼續(xù)堅(jiān)持反抗斗爭(zhēng),但其聲勢(shì)和規(guī)模都大不如前,如朱元兆、劉世美、田瑞龍等所率的紅號(hào)軍余部。而清軍雖然收復(fù)了銅仁等地城池,但隨即又因折征、派捐、縱兵劫掠新收復(fù)之地等行為導(dǎo)致官民矛盾的激化。不久,銅仁府溪司所轄的五洞民眾就發(fā)起了反抗清朝統(tǒng)治的起義斗爭(zhēng),隨后又與紅號(hào)軍余部匯合,占據(jù)梵凈山,共同反抗清朝統(tǒng)治。“夏五月銅仁五洞民復(fù)以苛征為詞,起應(yīng)田瑞龍。秋七月,銅仁紅號(hào)據(jù)梵凈山。”為了能徹底消滅紅號(hào)軍,清軍不僅集中了銅仁等地的官軍和地方團(tuán)練武裝,還從湖南抽調(diào)軍隊(duì)進(jìn)入貴州參與圍剿。而紅號(hào)軍則憑借梵凈山等地復(fù)雜地勢(shì)頑強(qiáng)抵抗,在敵我實(shí)力懸殊的情況下一直堅(jiān)持到十一月,方才失敗。“湖南兵會(huì)思南,石阡兵練敗銅仁賊于鎮(zhèn)遠(yuǎn)、施秉,獲賊首吳燦奎、劉世美等,鐐遠(yuǎn)、余慶練團(tuán)亦獲田瑞龍等,解省伏誅。”
至此,隨著田瑞龍等人失敗被殺,最初起事的一干紅號(hào)軍首領(lǐng)幾乎盡數(shù)被誅。這就意味著,當(dāng)初以抗“折征”為目標(biāo)的紅號(hào)軍起義最終還是失敗了。之后雖然還有不少打著紅號(hào)軍旗號(hào)的起義部隊(duì),但其首領(lǐng)和起義目的均與之前的紅號(hào)軍無(wú)直接聯(lián)系,他們使用紅號(hào)軍旗號(hào),主要是因?yàn)榧t號(hào)軍的名字在銅仁一帶有較大影響力,使用該旗號(hào)能更容易地爭(zhēng)取到當(dāng)?shù)馗髯迕癖姷闹С郑瑥亩杆贁U(kuò)大自身實(shí)力。因此,這些“紅號(hào)軍”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
二、燈花教始末
清朝時(shí)期,如白蓮教一般的民間秘密宗教在清代下層社會(huì)普遍存在,并得到廣泛的傳播與發(fā)展。而清朝政府雖盡力遏制其發(fā)展,但往往成效不大。尤其是到了清中后期,由于吏治腐敗,剝削日重,這些民間秘密宗教在底層社會(huì)的傳播與發(fā)展更加迅速,并成為許多農(nóng)民起義軍進(jìn)行宣傳、組織的重要手段。本文所述的燈花教就是其中一例。
本文所說(shuō)燈花教,乃是指道光、咸豐年間,由劉儀順在四川、貴州等地創(chuàng)立、傳播的一種民間秘密宗教,其于咸豐七年(1857年)、八年(1858年)在貴州組織、發(fā)動(dòng)了著名的白號(hào)、黃號(hào)軍起義。而實(shí)際上,燈花教之名早在乾隆初年就有記載,并在乾隆末年就已在湖北傳教。而劉儀順?biāo)鶆?chuàng)立的燈花教與乾嘉時(shí)期的傳統(tǒng)燈花教并不完全相同,追溯其源流,實(shí)質(zhì)上是青蓮教的一支,“燈花教,又名青蓮教,又名清水教,實(shí)白蓮教遺孽也”。只是因?yàn)楸苊獗磺逭?zhèn)壓和方便傳播而融入了一些燈花教的東西。之所以認(rèn)為燈花教是青蓮教一支,主要是與以下兩點(diǎn)緣由有關(guān)。
燈花教創(chuàng)立者兼教主劉儀順本人與青蓮教之間有密切聯(lián)系。劉儀順,原籍湖南寶慶府,遷居四川宜賓縣。原名郭建汶。在其三十七歲時(shí),在宜賓遇見了楊光明(楊守一),受他勸說(shuō)習(xí)教,遂拜他為師。之后為避免被清政府抓捕,遂離開四川,前往各地進(jìn)行傳教。咸豐七年(1857年),劉儀順因貴州信眾最多,有深厚的群眾基礎(chǔ),故前往貴州組織教眾準(zhǔn)備起事。白號(hào)、黃號(hào)起義發(fā)生后,其本人被推為首領(lǐng),領(lǐng)導(dǎo)起義軍與清軍戰(zhàn)斗,一直到他被清軍俘虜并被送往四川處死。關(guān)于其與青蓮教之間的關(guān)系,首先是其曾拜楊守一為師,習(xí)青蓮教。楊光明即楊守一,曾為青蓮教第十三祖,道光七年(1827年)犯案被查,次年處斬。其次,道光后期,在青蓮教重新統(tǒng)一的過程中,劉儀順曾使用葛依元的道號(hào),并作為主要首領(lǐng)之一參與其中。之后因與其他首領(lǐng)不和,而從青蓮教中出走,創(chuàng)立了燈花教。倘若劉儀順不是青蓮教眾,如何能參與到重建青蓮教這樣重要的活動(dòng)中,并成為其中的主要成員?所以劉儀順本人先是青蓮教骨干,然后從青蓮教中出走并最終成立了燈花教。
燈花教的修行儀式中雖然有一些傳統(tǒng)燈花教的內(nèi)容,但由劉儀順?biāo)鶄飨聛?lái)的多數(shù)內(nèi)容和宗教經(jīng)典中,還是以青蓮教的內(nèi)容為主。如劉儀順向劉漢忠傳教時(shí),就曾向他傳授《三教經(jīng)》和《金丹大教》,其中就包含有吃齋和打坐運(yùn)氣的內(nèi)容。而青蓮教又稱金丹大道,且教內(nèi)也存在傳授吃長(zhǎng)齋和坐功運(yùn)氣的行為。此外,無(wú)論是青蓮教還是劉儀順的燈花教,都是以無(wú)生老母為主要供奉的神明。所以從其傳播的內(nèi)容上來(lái)說(shuō),燈花教與青蓮教有著較為密切的聯(lián)系,相反同傳統(tǒng)燈花教之間的聯(lián)系較遠(yuǎn)。因此,劉儀順的燈花教是青蓮教的一個(gè)分支應(yīng)無(wú)太大疑問。
綜上所述,無(wú)論是燈花教本身,還是劉儀順本人,都與青蓮教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換言之,其所領(lǐng)導(dǎo)的號(hào)軍起義也與青蓮教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三、紅號(hào)軍與燈花教關(guān)系
通過對(duì)燈花教的淵源和紅號(hào)軍起義始末情況的敘述,可以知道,在紅號(hào)軍起義的過程中,并未發(fā)現(xiàn)其與燈花教之間存在密切聯(lián)系的證據(jù)。盡管紅號(hào)軍的活動(dòng)范圍與燈花教領(lǐng)導(dǎo)的號(hào)軍多有重合;盡管在其起事過程中,有民間秘密宗教的參與,但這些都不足以說(shuō)明兩者間有著重要的關(guān)聯(lián)。而紅號(hào)軍之所以被認(rèn)為是燈花教領(lǐng)導(dǎo)的一支起義部隊(duì),主要有以下幾個(gè)原因:
紅號(hào)軍與黃號(hào)軍、白號(hào)軍一樣都是用有顏色的頭巾蒙首并用來(lái)制作旗幟,以此來(lái)作為起義軍的標(biāo)志,故而認(rèn)為三支起義部隊(duì)都與燈花教有關(guān)。但實(shí)際上,用有顏色的頭巾和衣物來(lái)作為起義軍的標(biāo)識(shí)并非咸同年間才出現(xiàn),這種方法其實(shí)古已有之。從東漢末年太平道張角組織發(fā)動(dòng)的黃巾軍起義,到元末韓山童、郭子興等領(lǐng)導(dǎo)紅巾軍,皆是以不同顏色的頭巾和衣物來(lái)作為其獨(dú)特標(biāo)志,并在歷史上留下黃巾軍和紅巾軍這樣的名號(hào)。與此相同的是,號(hào)軍之名也并非燈花教首創(chuàng)。早在乾隆末年開始的川陜楚等五省農(nóng)民大起義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以青、黃、紅、藍(lán)各色為號(hào),設(shè)掌柜、元帥、先鋒、總兵、千總諸偽稱。”之所以這幾支起義軍會(huì)選擇這樣的名字,很有可能是受到乾嘉年間的這場(chǎng)大起義和歷史上的紅巾軍等農(nóng)民起義軍的影響。他們因而選擇了號(hào)軍這個(gè)名字,并依照各自使用的頭巾顏色來(lái)加以區(qū)分。因此,僅僅以這幾支起義軍都是使用頭巾這樣的標(biāo)志就斷定他們是受同一組織領(lǐng)導(dǎo)的部隊(duì)不太準(zhǔn)確。
在號(hào)軍起義的過程中,各起義軍首領(lǐng)普遍依靠民間宗教來(lái)宣傳、組織起義活動(dòng),尤其是在起事發(fā)動(dòng)之前。如白號(hào)和黃號(hào)最初參與起義的部隊(duì)就多為燈花教教徒,而且其組織方式也多按照教內(nèi)原有的制度來(lái)進(jìn)行。同樣,紅號(hào)軍在最初組織和宣傳時(shí)也通過算命、算卦等民間教門手段來(lái)組織民眾,使得他們?cè)诤笫揽雌饋?lái)像是同出一源的起義部隊(duì)。但通過對(duì)紅號(hào)軍與其他號(hào)軍中的民間信仰因素進(jìn)行仔細(xì)比較,就能發(fā)現(xiàn)他們實(shí)質(zhì)上是有很大區(qū)別的。按照史料記載,紅號(hào)軍中所推行的民間信仰是以毛大仙為首的一支民間宗教。“徐廷杰、梅繼鼎皆府屬舉人,平日師事毛家寨巫者毛大仙,名正年,授乩筆咒,因以惑眾。”在扶乩的同時(shí),毛大仙還經(jīng)常向普通民眾宣傳“大劫將至,持齋醮、諷經(jīng)始得免”。而燈花教供奉的是無(wú)生老母,采取的主要修煉方法是打坐運(yùn)氣,并沒有提到過扶乩。據(jù)此推測(cè),毛大仙所傳與燈花教所傳并不相同,應(yīng)當(dāng)視兩者為不同的民間信仰。因此,以紅號(hào)軍中存在民間信仰因素就將其視為燈花教所領(lǐng)導(dǎo)的一支起義軍的結(jié)論過于武斷。
雖然紅號(hào)軍與燈花教領(lǐng)導(dǎo)的號(hào)軍起義一樣,都以反抗清政府的殘酷剝削和高壓統(tǒng)治為目的,但二者在本質(zhì)上并不相同。前者一開始只是想要廢除“折征”政策,并未想過要推翻清政府,之后因事態(tài)發(fā)展失去控制,才發(fā)動(dòng)起義。同時(shí),紅號(hào)軍雖然在后期也提出了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口號(hào),但實(shí)際上除了口號(hào)外并未有其他實(shí)質(zhì)性的東西提出。反觀燈花教,其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權(quán)的口號(hào)。因此,當(dāng)其起事成功之后,就迅速在其根據(jù)地建立政權(quán),并鑄印、鑄錢和刊發(fā)謄黃、告示。故將兩者視為性質(zhì)、目的相同的起義軍有待商榷。
通過梳理紅號(hào)軍起義的相關(guān)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在起義的大部分時(shí)間里,紅號(hào)軍的主要活動(dòng)范圍包括銅仁、石阡、思南等地。而劉儀順?biāo)⒌臒艋ń淘谫F州地區(qū)的教眾也多在這些地區(qū)活動(dòng)。倘若紅號(hào)軍是燈花教組織和領(lǐng)導(dǎo)的起義軍,那么文獻(xiàn)中為何沒有記載上述這些地方的燈花教信眾在其起事期間發(fā)動(dòng)起義進(jìn)行響應(yīng),或者為其暗中提供幫助的史料?因此,關(guān)于兩者間的隸屬關(guān)系問題,還需要進(jìn)一步深入考證。
四、結(jié)論
綜上所述,對(duì)于紅號(hào)軍與劉儀順?biāo)I(lǐng)導(dǎo)的黃號(hào)軍和白號(hào)軍之間的關(guān)系,無(wú)論是從起義軍以頭巾為標(biāo)識(shí)方面來(lái)看,還是從起義軍中的民間信仰因素方面來(lái)看,又或者從二者起義的性質(zhì)、目的來(lái)看,將紅號(hào)軍視為劉儀順?biāo)鶆?chuàng)立的燈花教組織和領(lǐng)導(dǎo)的一支起義軍尚值得商榷。想要得出確切的結(jié)論,還需要收集、整理更多的相關(guān)史料,并對(duì)其進(jìn)行仔細(xì)辨析。
參考文獻(xiàn)
[1] 歐陽(yáng)恩良. 民間教門與咸同貴州號(hào)軍起義[J]. 貴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5(6).
[2] 曾召南. 劉義順的燈花教與貴州的號(hào)軍起義[J]. 宗教學(xué)研究,1982(1).
[3] 顧久,主編. 黔南叢書(點(diǎn)校本):第12輯、第13輯[M]. 貴陽(yáng):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
[4] 貴州省文史研究館校勘. 貴州通志·前事志:第3冊(cè)[M].貴陽(yáng):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5] 凌惕安. 咸同貴州軍事史:第3冊(cè)[M].1932.
[6] 馬西沙,韓秉方. 中國(guó)民間宗教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 黃加服,段志洪. 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 25[M]. 成都:巴蜀書社,2006.
[8] 顧隆剛. 太平天國(guó)時(shí)期貴州農(nóng)民起義軍文獻(xiàn)輯錄與考釋[M]. 貴陽(yáng):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
[9] 秦寶琦. 清代青蓮教源流考[J]. 清史研究,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