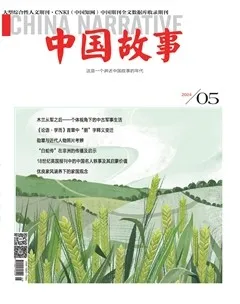侗戲的源流、特征及其傳承
作者簡介:常耀文,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
【導讀】貴州是我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之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誕生了許多優秀的少數民族文化成果,侗戲就是其中之一。侗戲作為侗族人民的文化結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精華,成為貴州對外文化宣傳的一張靚麗名片。對侗戲的溯源,不僅可以使人們領略少數民族的文化魅力,還可以使人們了解貴州的多彩文化。
侗戲是貴州少數民族侗族的特色戲曲,具有獨特的戲劇演唱方式、劇目內容,已成為貴州地域文化的一個耀眼標簽。侗戲從僅為侗族人民欣賞的劇種,逐漸發展成為今天各族人民皆可觀看欣賞的戲劇形式,經歷了長久的發展演變過程。侗戲雖然經過了時間的驗證,成為貴州乃至我國戲劇叢林中的一朵奇葩,但在今天仍然面臨著發展的困境。
一、侗戲的起源
(一)侗歌的過渡
侗族是一支善于歌舞的少數民族,在侗戲誕生之前,侗族就有著豐富的歌舞文化傳承。這為侗戲的產生打下了豐厚的文化基礎。
在侗戲之前,侗歌是侗族人民主要的文化表達方式之一。在唐朝之前,侗族雖仍處于原始社會狀態,但已出現了與其社會發展相匹配的文化表達形式:“耶”(即在祭祀和重大喜慶活動時用的歌舞)、“嘎”(歌)、“壘”(念詞)和“碾”(傳說)。這種早期的表演形式,承擔起了侗族早期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
經過宋、元、明三個朝代的發展,侗族進入了封建社會時期。中原地區以漢族為代表的各族文化,通過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方面進入貴州地區,對侗族產生影響,促使其藝術表現形式的發展。文化藝術上,出現了民族史詩類體裁作品,如《薩歲之歌》《祖公之歌》等,與此同時,傳統故事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如《昊勉的傳說》《林貴的故事》《楊太公救飛山》等。此外,中原地區的言情體裁、說明文學等也催化了一批獨具侗族色彩的作品的出現,如《朱桑之歌》《美德之歌》。
元以后,侗族出現了新的藝術表演形式。人們將侗歌的“壘”與“嘎”結合,變單一的演唱形式為復合形式,新的表演方式“綿”出現了。這為侗戲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明清之際,交通的開發使侗族對外交流更加便利,侗族的居住區域、游走范圍逐漸擴大,對外接觸比之前更甚。相應地,漢族為代表的其余民族也紛紛移居到其周圍區域,“漢族戲劇日益深入侗族地區”。而桂戲、湘戲、花鼓戲以及貴州其他地區的劇種也相繼傳入。這些戲劇新穎的表演形式,深受侗族人民喜愛,“侗族人民也喜歡這些戲劇的表演,有的村寨舉辦喜事,也邀請漢族戲師去演出”。在欣賞之余,侗族人民也會向漢族戲師進行討教,漢族戲師也會傳教“漢戲”。在侗語中,漢戲被稱為“戲嘎”,受到“戲嘎”的影響以及侗族人的學習,侗族說唱藝術以“綿”為基礎,于清代中期發展出了“一種用侗語道白和演唱的新的戲劇形式”。為進行區別,侗族人將“嘎”改為“更”,稱這種新出現的表演形式為“戲更”——即侗戲。
(二)侗族人的主動接受
對于侗戲的創始人,目前并無具體文獻記載。根據民間傳說以及調查研究,較為可靠的說法是,侗戲于1830年由黎平縣茅貢鄉臘洞村著名戲師吳文彩創立。當時漢戲、湘戲等一眾戲種進入侗族,但語言差異使侗族人民難以理解劇情,想去看戲與聽不懂戲的矛盾十分激烈。吳文彩面對此種情況,萌生了創建侗戲,以侗族語言唱出侗族人可以聽懂的戲劇的想法。經過大量實驗和多處改進,吳文彩(據說使用三年時間)創立了以侗語為演唱形式的戲劇,并改善了漢戲唱腔,創立了適合侗族戲人演唱的唱腔——平板唱腔。同時,吳文彩還根據新戲腔改編了兩部侗戲,一是根據漢族說唱本《二度梅》改編的《梅良玉》,一是根據漢族傳書《薛剛反唐》改編的《鳳蛟李旦》。這兩部戲可謂最早的侗戲劇本。在吳文彩的帶動下,侗族的歌師、戲師也開始了侗戲的創作,這些人充分發揮才識,為早期侗戲的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也有戲師效仿吳文彩,將其他漢族故事改編為侗戲。例如清代出現的改編漢族故事劇目有《毛紅玉英》《劉世堯》《劉高》《山伯英臺》《門良江女》《陳勝吳廣》《陳世美》等。另有部分戲師,在侗族民間傳說故事和民族史詩的基礎上,改編、創作出了一系列本土侗戲劇本。第一部侗族題材的侗戲是《金漢列美》,這是與吳文彩同時的著名戲師張鴻干(張鴻干,據傳說,也是侗戲的創始人之一,但由于廣為流傳的說法中吳文彩的認可度更高,因此,本文中不將其列為侗戲的創始人)根據侗族敘事詩《金漢》改編的作品,其他劇本還有《三郎五妹》《莽歲榴美》《甫義乃義》《元本》《田八漢》《美道》《花賽》等,這些早期侗戲的經典劇目,受到了廣大侗族人民的歡迎。
二、侗戲的發展
侗戲誕生之初,只活躍于侗族聚居的地區。由于交通不便,雖然各侗族分居地區皆有侗戲誕生,但封閉狀態下,侗戲的流傳十分有限。清宣統三年(1911年),侗戲《珠郎娘美》才廣為流傳于廣大侗族地區,在此之前,侗戲大多為獨自發展,流唱度取決于侗戲戲班的游走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周邊地區對侗戲的喜愛程度越來越深,通過拜師傳藝的傳承,侗戲傳播的區域也越來越廣。早期活躍在黎平、榕江、從江等地的侗戲,在眾多侗戲戲班的傳播下,沿水而下,一路傳播至富祿、梅林等河段地區,再往后,侗戲一度傳播至通道、龍勝、融水等區域。在南方,凡是侗族居住區域,皆可見侗戲表演。據不完全統計,在侗戲誕生早期,貴州黎平、榕江、從江地區存在500多個侗戲戲班,平均每個侗族村落都有一個侗戲戲班表演侗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侗戲的發展進入新時期。侗戲不再局限于過去的民間傳說和早期的話本故事,其內容更加貼近現實生活,大量反映侗族人民現實的戲劇劇本被創作出來,成為侗戲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小高峰。這一時期的劇本有:吳章窗的《奶挑》《喝喜酒》;梁浦安的《留糧四百七》《婚姻法》《張老三思想轉變》《雙季稻》《頌老三》《互助組》《新修公路》;湯世璽的《兩婆媳》《老中青三結合》《婚姻自主》。這些新侗戲緊扣時代與日常生活主題,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侗族人民的全新生活面貌,受到廣大侗族群眾的熱烈歡迎。
1958—1959年,貴州省文化局、貴州音樂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貴州分會,先后前往從江、黎平、榕江侗族居住區域,深入考察調研,對侗戲進行較為全面的摸排,前后收集傳統侗戲戲劇26部,其中17部(一說16部)為新編現代侗戲。其中對傳統優秀侗戲《珠郎娘美》進行了改編整理,漢譯本劇本《珠郎娘美》被發表于《山花》雜志,又于1960年改編為黔劇《秦娘美》,先后在貴陽、北京等地演出,受到眾多著名戲劇家的贊賞與好評。其故事情節優美,于1960年被上海電影制片廠改編為戲劇影片搬上銀幕。
進入20世紀60年代,侗戲的發展進入了沉默期,這一時期,侗戲被視為“四舊”,受到打壓。直至20世紀70年代,樣板戲的出現,打破了侗戲沉寂的狀態。侗戲開始朝著“樣板戲”的格式發展。《林海雪原》《紅燈記》等樣板戲被榕江縣文化中心引入侗戲,成為這一時期宣傳侗族地區的主要戲目。1978年后,榕江縣某侗戲戲劇表演團率先恢復了傳統侗戲的表演,并開始巡回演出。受其影響,各侗戲戲劇表演團開始活躍起來。侗戲發展迎來新春。
20世紀80年代,從江縣文化中心以黃能賦、石平姣、陳春元、全文武為首的創作小組,創作了第一部侗族歌劇《蟬》,為侗戲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1983年成立的從江縣藝術隊,在進行侗戲彩排時,除了對傳統侗戲、現代侗戲進行彩排外,還編排了《蟬》這一新劇。
三、侗戲的特征
(一)開放性
開放性是侗戲最大、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自侗戲誕生起,這一特征便伴其左右。侗戲是在漢戲、湘戲、桂戲以及貴州本土其他戲劇的影響下誕生的。吳文彩改編的侗戲《梅良玉》《鳳蛟李旦》便是借鑒漢族故事傳奇進行改編,使其侗族化。又如《山伯英臺》《陳勝吳廣》《陳世美》等戲劇,更是直接借鑒漢族故事。這些劇目成為侗戲早期流唱的經典劇目,為侗戲的發展添磚加瓦,使侗戲不至于因缺少戲劇劇本而早夭。
隨著時間的推移,侗戲的表演形式、戲劇劇本也越來越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侗戲戲劇家們積極接受新事物,不再局限于傳統侗戲劇本,積極迎合時代發展步伐,創立了許多新時代貼合現實生活的劇本,為侗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20世紀70年代的樣板戲,雖然有些死板,但其經典劇目,放在今天仍然是傳唱度很高的戲劇,可以很好地增加侗戲的對外宣傳。
早期的侗戲表演舞臺簡單,表演人員妝造簡單,可謂簡單樸素。但在不斷的發展下,侗戲表演者們廣泛吸收各個劇種的優點。表演人員由最初的兩人向多人同臺發展,表演者的動作神態受到漢族戲曲影響,更富神態,更加傳神。
(二)創新性
創新性是侗戲的又一顯著特征。早期的侗戲是以侗歌為基礎的。但其誕生之時并沒有按照侗歌的演唱方式演繹,也沒有直接采取其他戲種的演唱方式,而是采百家之長,結合侗族流傳的侗歌演唱形式,融合形成適合侗戲表演者演唱的戲腔——平板唱腔。這成就了侗戲獨特的風格與色彩,成為我國317個劇種之一。
另一方面,侗戲在發展過程中,并不拘泥于傳統的發展形式,而是積極采取新的表演方式。一般來說,戲劇的發展無非是創作新劇本,采取新的表演形式。但侗戲在發展過程中卻另辟蹊徑,創造性地引入了歌劇這一表演形式。從江縣文化中心以黃能賦、石平姣、陳春元、全文武為首的創作小組創作的新侗戲歌劇,無疑是侗戲發展的新標志。
(三)群眾性
侗戲作為貴州地區優秀戲劇之一,其受眾從最初的侗族人民向其他各族人民擴散,逐漸傳播到周邊省份侗族聚居的地方,直至成為不分民族皆可欣賞的戲劇表演。隨著時間的推移,侗戲的表演形式不斷進步,從鄉間草臺逐漸登上正式的表演舞臺,為更多的群眾所欣賞。1986年10月,在黎平縣舉行的湘黔桂三省(區)第二屆文藝會演時,上演的侗戲全部使用了燈光布景和天幕投影。這種新穎的表演方式,使侗戲的觀看群體遠遠超過過去單一的侗族觀眾,也讓舞臺侗戲為其他民族觀眾帶去更好的觀感體驗,從而大幅提升侗戲的流傳程度。
四、侗戲傳承的問題與解決策略
(一)傳承困境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地區經濟差異化的加劇,越來越多的青壯年人口流向了經濟發達地區。在侗族聚居的區域內,侗族的人口流失量也在逐漸上升,這直接導致了侗戲傳承人脈的斷層。侗戲的傳承,與其他劇種一樣,主要依賴于老一輩藝術家的言傳身教。再加上侗戲演唱語言以侗族少數民族語言為主,使得傳承的受眾十分狹窄,基本限定在了侗族的青壯年人群。
同時,現有的侗戲表演者大多年事偏高,且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在傳承侗戲時,他們大多仍采取老一套教學方式,未能與時俱進,缺乏選擇和創新教育模式的意識,導致侗戲的教學水平相對滯后。
此外,新的媒體傳播方式極大地沖擊了傳統文化。侗戲的表演主要靠一些節日慶祝之余的順便演出。而新媒體的出現填補了人們的空余時間。現代新興娛樂消費種類、樣式越來越多,短視頻的出現,更是占據了從青壯年到中老年的娛樂時間的大部分。因此,侗戲的表演次數和觀看人數越來越少。
(二)發展策略
新媒體的崛起對侗戲傳承來講,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新媒體強大的傳播能力是以往的傳播媒介不曾擁有的。雖然新媒體的存在沖擊了侗戲的生存空間,但反過來看,侗戲也可以搭乘新媒體傳播的快車,憑此擴大侗戲的傳播范圍,使表演者足不出省即可斬獲大量觀看者。但新媒體對侗戲表演者要求更高,需要其不斷創新表演方式,更新劇作內容,以長久不斷的新穎度吸引觀眾眼球,如此方可引起廣泛的關注,使侗戲可以頻繁地出現在觀眾視野內。
同時,侗戲要想長久不衰,終究是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人,只有這樣,侗戲才能保證擁有永恒的動力。在培養侗戲事業的接班人方面,學校教育是重要的一環。學校教育擁有民間教育不可比擬的優勢。其高度的教育水平、完整的教育模式,可以形成一條優于民間侗戲傳承模式的教育鏈。如此便可以為侗戲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傳承人,從而改變侗戲傳承青黃不接的狀況。
另外,政府有關部門應重視侗戲等傳統藝術,通過設立專業保護部門小組、提供相應的財政基金支持,為其提供堅實的保障。僅僅憑借侗戲自身的自力更生是很難堅持下去的,因此,政府應加大對侗戲傳承人的經濟扶持力度,獎勵那些對侗戲傳承作出貢獻的個人或者團體。政府也應加大文化宣傳力度,結合當地旅游資源,開發整體服務模式,將侗戲與其他文旅資源相整合,加深游客印象,形成有效的二次傳播鏈節。
五、結語
侗戲是我國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著豐富的社會價值與人文價值,是侗族人民智慧與文化的結晶。其獨特的表演形式,一度使其成為侗族人民百年來的娛樂項目。目前,侗戲的發展與眾多傳統藝術一樣面臨著窘境,但隨著后輩青年的不斷挖掘,侗戲這一藝術文化,終究會迎來其燦爛發展的前程。
參考文獻
[1] 吳定國. 侗戲的源流及特點[J]. 貴州文史叢刊,1992(2).
[2] 《侗族簡史》編寫組,《侗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編. 侗族簡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3] 《貴州通史》編委會. 貴州通史·第三卷[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
[4] 羅仙泗. 貴州侗戲的歷史演變與現實境遇[J]. 四川戲劇,2022(11).
[5] 向娟. 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下的侗戲研究[D]. 吉首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