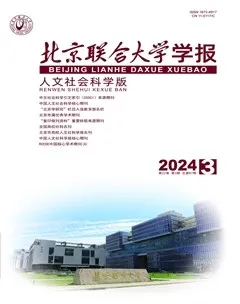法定法官原則:刑事管轄制度的確定性與救濟性
[摘 要] 刑事管轄作為程序性規則涵蓋預先確定性和可救濟性,發揮著保障司法公正之基礎功能。實踐中提級管轄適用條件模糊、指定管轄濫用及集中管轄正當性缺失等問題極大動搖了刑事管轄制度確定性根基,客觀上造成了管轄制度不確定性的“危機”;刑事被追訴方事實上的管轄異議權及程序性制裁措施闕如使得發生管轄錯誤時缺乏救濟途徑。《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在即,有必要引入國際通行的法定法官原則,嚴格按照法律預先確定標準劃分管轄法院的同時,也應明確被追訴人享有法定法官審判的權利,并規定違反法定法官原則程序效力相對無效的法律后果。
[關鍵詞] 法定法官;管轄確定性;管轄異議權;程序性制裁
[中圖分類號] 中圖分類號D925.2;D926.2[文獻標志碼]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672-4917(2024)03-0041-08
一、問題的提出
管轄是訴訟運行的前提和基礎,作為一項純粹的程序性規則,具有為公權力機關劃分受理案件的權限和職能,并為司法權的有效運行提供正當性證明[1]。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總則”部分以專章形式規定了刑事管轄制度,并將其置于回避、辯護與代理、強制措施等制度之前,旨趣之一在于彰顯刑事訴訟管轄解決的是刑事案件的“起點”和“入口”問題。刑事訴訟程序啟動之初應預設案件由哪一公權力機關受理并處置,既包括各機關之間職能分工的立案管轄,也含括審判機關內部在第一審刑事案件受理范圍分工的審判管轄,進而確保案件在中立且無偏見的環境中審理,防止因地域或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公正現象,特別是避免司法機關選擇特定法官進而操縱審判結果。
作為聯合國國際刑事司法準則之一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規定:“……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其中“依法設立的合格的法庭”就是指審判法庭的司法管轄權是預先依法確定的,而非為了某個案件臨時組成的,否則法庭設立不合格[2]。正是在刑事案件管轄范圍具有確定性之前提下,犯罪的偵查、起訴與審判才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3]。
為解決刑事管轄制度可能出現的“失靈”“錯位”難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條和第27條分別規定了移送管轄和指定管轄制度。雖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制度運用的靈活性,但從實踐運用角度觀察,可以發現這兩類管轄制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適用難題:一方面,移送管轄制度適用條件規定較為抽象模糊,司法機關對“必要的時候”“案情重大、復雜且需要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等情形把握不準導致該制度運行不暢,更為重要的是被追訴人是否擁有申請移送管轄的權利亦不明確。另一方面,指定管轄制度適用范圍較為廣泛且側重于打擊犯罪和訴訟需要,程序處理方式因缺乏訴訟性而難以充分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4]。近年來,司法實踐中更是出現了另一種管轄形式——集中管轄,誠然其可能具有破除地方行政干預、整合訴訟資源、促進辦案機關專業化等制度優勢,但也有學者質疑集中管轄適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認為其存在動搖法定管轄制度根基之嫌[5]。
由此觀之,法律預先確定的刑事案件管轄法院可能因移送管轄、指定管轄和集中管轄等產生“不確定性”,使得管轄法院的確定最終呈現出人為自行調整和改變的狀態。在該種情況下,即使案件存在管轄錯誤問題,司法機關也難以予以糾正,特別是在訴訟條件審查缺失狀態下[6],反而加劇了管轄制度的“不確定”危機[7]。筆者認為,刑事管轄制度確定性偏失的根源之一在于我國立法沒有明確刑事訴訟管轄規定的法理基礎——法定法官原則(Gesetzliche Richter)——雖然從關涉管轄制度的實定法律條文中可以推定反映該原則若干精神之存在。該原則要求刑事案件由何人承辦是依法決定,司法行政上級并無將具體刑事案件指定給特定法官承辦的權限[8]。換言之,刑事案件管轄法院和審判法官必須按照法律預先確定的標準進行劃分,而不能在某一法律糾紛訴諸法院后自由選定[9]。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法官原則的另一功能在于保障當事人的公平審判權。若刑事審判出現管轄不確定或錯誤之情形,被追訴人提出不服該院管轄的異議自是其當然之權利,以要求由法律規定享有管轄權的法院和法官審理,同時享有行使這一權利或放棄這一權利的自由。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刑事管轄不確定性具體情形之基礎上,提出引入法定法官原則并切實發揮其確定性和救濟性功用,以期充實我國刑事管轄制度理論基礎。在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明確賦予被追訴人管轄異議權,可以說正當其時。
二、偏移:刑事訴訟管轄制度不確定性缺陷
刑事管轄是為確定具體案件在同一或不同層級法院間如何分配的制度,核心內容在于管轄法院的法定性和預先確定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5條明確規定了刑事案件由“主要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并輔以移送管轄、指定管轄、專門法院管轄等制度設計防止不同管轄地法院間的沖突,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管轄地法定原則。實踐運行中有時會背離管轄制度立法初衷,以明確性指向為主要功能的管轄制度發揮有時不盡如人意,提級管轄適用條件不明、指定管轄制度濫用再加之集中管轄制度興起,使得刑事案件具體管轄法院籠罩“撲朔迷離”之觀感,某種程度上動搖了刑事訴訟管轄制度的確定性根基。
(一)提級管轄適用條件模糊
法院移送管轄(又稱移轉管轄)解決的是同一層級法院基于地域管轄特定、或不同層級法院之間由于級別管轄或其他特殊事由產生的管轄權移轉問題。從管轄確定性角度對移送管轄進行類型化區分,可以將其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管轄錯誤型移送管轄,主要是違反地域管轄和級別管轄規定而在法定管轄范圍內將案件移送其他辦案機關,即將案件從“無管轄權”法院移送至“有管轄權”法院。二是提級型移送管轄,下級法院基于特定事由不適宜審理案件,而由上級法院提級審理或由下級法院請求移送上級法院管轄。其特征在于突破了級別管轄限制,但提級管轄的廣泛適用可能使得案件在具體管轄法院上產生不確定性。也就是說,所有案件都有可能以“必要”或“重大復雜”為由進行提級審判,即使原管轄法院的上級法院是確定的。
《刑事訴訟法》第24條正是對提級型移送管轄的制度性規定,即上級法院在“必要時”可以審判下級法院管轄的案件,以及下級法院管轄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請求移送上一級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第17條第2款和第18條對“必要的時候”“案情重大、復雜”的情形作了細化規定,主要包括①重大、復雜案件;②新類型的疑難案件;③在法律適用上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案件;④本院院長需要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宜行使管轄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案件提級管轄規定相對抽象,一些具有規則意義或可能存在“訴訟主客場”現象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作出說明,提審的“特殊類型案件”是指由自己審理更有利于統一法律適用或者打破“訴訟主客場”現象的案件。[10]的案件難以進入較高層級法院審理范圍[11]。2021年《關于完善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改革完善了提級審理的適用條件,根據《實施辦法》第4條和第5條規定,對于下列案件可以適用提級管轄:①涉及重大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不宜由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②在轄區內屬于新類型,且案情疑難復雜的;③具有普遍法律適用指導意義的;④上一級人民法院或者其轄區內各基層(中級)人民法院之間近三年裁判生效的同類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適用分歧,截至案件審理時仍未解決的;⑤由中級(高級)人民法院一審更有利于公正審理的。
但問題在于,無論《刑事訴訟法》《刑訴法解釋》抑或《實施辦法》,對提級型移送管轄的條件規定都模糊且泛化,致使不同法院在具體案件應用中對提級管轄適用標準把握可能不一致,存在不當擴大或限縮移送管轄適用的空間。有實務工作者研究表明,“必要”“新類型”等屬于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其外延和構成要件亦不明確,用語模糊性可能使得制度應用產生歧義,雖能為法官提供正確的思考方向,但缺乏確定性和穩定性的弊端比較明顯,需要進行價值補充加以具體化[12]。此外,在提級管轄“審理者裁判”之要求下,案件是否由上級法院審理較大程度上依靠審判組織的自由裁量權[13]。一方面,提審機制可以由下級法院請求移送或上級法院主導。《實施辦法》規定的五類提級管轄的特殊案件,在實踐中可能出現需求錯位現象,即下級法院請求移送的往往是那種管轄利益不大,但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處理難度較大的案件。對于這些案件,上級法院法官也會認為是“燙手的山芋”,不太愿意提審處理[14]。另一方面,被追訴人在提審機制運行中參與不足。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尚且可以通過提出管轄權異議方式質疑提審決定或使上級法院關注待提審案件,[15]但在刑事訴訟中由于管轄異議權的缺失使得被追訴人難以提出己方意見。關于被追訴人管轄異議權問題,筆者后文將詳述之。
(二)指定管轄適用的突出問題
1.指定管轄適用范圍不當拓寬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7條明確規定了指定管轄適用條件和范圍,“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審判管轄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將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審判”。通過立法形式明確了上級人民法院在案件“管轄不明”常見于數個管轄法院之間對管轄的爭議或推諉。或“有管轄權法院不適宜管轄”情況下,享有變更和重新確定案件管轄法院的權力,但對于其他能依法確定管轄法院的刑事案件,上級法院不得濫用指定管轄權。2021年《刑訴法解釋》第20條對2012年《刑訴法解釋》第18條規定的指定管轄條件作了修改,將“上級法院在必要時”這一模糊的裁量條款,修改為“更為適宜”的指定原則,并授權上級法院可以將案件指定給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人民法院審判。原因在于,這類案件一般針對國家工作人員或其近親屬犯罪,不宜由犯罪地或者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以避免由其任職轄區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而引發爭議[16]。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規定明顯擴寬了《刑事訴訟法》第25條規定的刑事案件由“主要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的原則規定,使得作為下位法的《刑訴法解釋》所創設的規則明顯超出《刑事訴訟法》關于指定管轄規定的框架范圍,由此可能導致指定管轄沖擊法定管轄,加劇刑事管轄制度的不確定性。
2.指定管轄隨意性強,缺乏明確的規范引導
上級法院在選定管轄法院時通常考慮辦案水平高低、司法經驗是否豐富、換押時的交通便利條件等因素,但對這一過程缺乏明確的規范引導。有些案件在確定管轄法院過程中全憑領導個人喜好,將其交給自己信任的法院。這種情況極易催生下級法院“看領導臉色辦案”的現象,嚴重影響審判公正。公安司法機關靈活調整地區管轄與級別管轄,進而將敏感案件納入可控范圍內,而指定管轄制度本身未受到理論重視,其受到行政干預時具有一定隱蔽性[17]。《刑訴法解釋》第21條規定了上級人民法院只需將指定管轄決定書送達被指定管轄的人民法院,但對決定書所載明的內容并未詳細規定。也就是說,未要求上級人民法院對指定管轄決定形成過程進行說理釋明。實踐中指定管轄大多發生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前,在案件開庭審理過程中再通過指定管轄變更審理法院的情形也時有發生[18]。此種情況下,倘若隨意頻繁地調整案件管轄權以實現司法管理目標,容易將本質上屬于普遍化司法規則的管轄制度,人為改造成為一種“科層化”的行政規則。筆者與部分辯護律師訪談時得知,有法院在開庭審理后,出于內部原因亦通過指定管轄將案件移轉給其他法院審理。這一做法不僅浪費了大量的訴訟資源,極大損害了司法公信力,也可能因為管轄的隨意性而使得被追訴人失去在法定管轄法院審理案件的權利。此外,指定偵查管轄法律依據不足且未對指定管轄的次數作限制性規定,偵查機關為了及時偵破犯罪,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通過不限次數的重復指定管轄規避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適用條件亂象也較為嚴重,極大損害了指定管轄制度的司法確定性和公信力[19]。
3.指定管轄忽視對被追訴人權利保護
指定管轄的本質是“人定法官(法院)”,而非“法定法官(法院)”,因此可能與法治精神相沖突[20]。我國刑事訴訟指定管轄制度,基本上服務于打擊犯罪的需要,而不大考慮通過改變管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21]。一方面,指定管轄職權主義色彩較濃厚,側重于打擊犯罪和訴訟需要。司法實踐中,某一犯罪案件的指定管轄法院由上級機關依職權采用內部行政程序處理,其處理過程缺乏訴訟性。就職務犯罪指定管轄而言,如果按照被指定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掌握的量刑標準提出量刑建議、判處刑罰,就會與重大職務犯罪地的標準不一致,可能會出現定罪和量刑的不均衡現象,產生對被告人處罰不公的問題[22]。更為直觀的表現在于,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型犯罪被告人在欠發達地區接受審判,其犯罪數額對當地公眾的情感影響和對檢察官、法官造成的思想沖擊是不同的,并可能因此產生實體處理上的差異——如果司法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則會暴露出指定管轄制度“打擊偏好”和職權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典框架內,并無制度要求聽取或接受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意見。即便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在庭前會議提出管轄異議,但其僅能承擔了解情況和聽取意見的效力,法院通常也不會設置專門程序處理,使得指定管轄決定過程缺乏被告人的有效參與,可能影響被告人的權利保護。
(三)集中管轄正當性存疑
所謂集中管轄是指上級司法機關改變法定的地區管轄或級別管轄,將某一類刑事案件集中到區域內某一(些)特定的司法機關進行管轄[23]。如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市人民檢察院、市公安局《關于大連市內五區醉酒型危險駕駛刑事案件集中管轄的通知》要求,該市五區內所有的醉酒型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統一交由大連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分局集中偵查辦理,并向大連市甘井子區人民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由大連市甘井子區人民法院集中管轄[24]。縱觀我國刑事訴訟管轄制度體系,集中管轄并非歸為刑事訴訟管轄制度法定類別之列,基于其在提升辦案質效、加強辦案機關專業性等方面的顯著成效,因而在司法制度改革特別是管轄模式變革中得到進一步確立和演進。然而,集中管轄制度性質究竟為何,其正當性基礎何在?理論界的認識并不統一。從形式上看,集中管轄似乎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指定管轄制度的相關要求。故而,有學者認為集中管轄制度雖與現行訴訟法上的普通管轄制度相沖突,但并不違反法定法官原則,原因在于集中管轄制度的案件管轄范圍和標準仍然是事先確立的、統一的、規范化的[25]。筆者并不同意這一觀點,認為集中管轄制度在適用正當性上存疑,具體有如下幾點理由。
其一,集中管轄規范位階效力較低。2019年《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2條規定了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于需要集中管轄的特定類型案件可以指定管轄,并要求與相應的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協商一致。由此,通過指定管轄方式技術性地授予了下級人民檢察院取得對特定案件的集中管轄權,變“個案”指定管轄為“類案”集中管轄。這一規定的效力淵源為最高檢制定的司法解釋而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就管轄系屬一國訴訟制度之基礎地位而言,顯得法律效力位階明顯不足,反而帶來對集中管轄突破程序法定原則之質疑。
其二,難以從指定管轄立法中尋求正當性依據。有學者根據集中管轄運行情況以及司法改革動機,認為集中管轄屬于指定管轄制度產品的范疇,系指定管轄后的一種管轄變更方式[26],試圖從指定管轄制度角度為集中管轄提供合法性證明。這是對于管轄制度功能的一種誤認。指定管轄作為一種事后針對個案權宜式的管轄法院調整方式,其首要的制度價值在于確保案件得到更為公正的審理[27]。而集中管轄制度是上級司法機關在案件發生前,以行政命令方式直接確定某一司法機關管轄一定區域內所有同類犯罪,與指定管轄制度在適用范圍、價值定位等方面存在本質區別。正如有學者指出,集中管轄將上級法院的指定管轄權視為授權依據,是對指定管轄制度目的的曲解,屬于法無依據的自我授權[28]。
其三,忽視管轄制度人權保障功能。如前文所述,我國在規范層面上設定了嚴格的級別管轄與地域管轄制度,并輔以特殊情形下的指定管轄、移送管轄制度等,呈現出以地域和級別為標準劃分審判法院之圖景。而集中管轄制度實施大多以案件類型為標準預先設定具體管轄法院,如涉及知識產權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環境污染犯罪等。該種基于管轄便利的做法表面上獲得了管轄制度所要求的事先確立、統一且規范的確定性條件,實則突破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以犯罪地或居住地確立的管轄原則。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所要承受的心理壓力無疑大大增加,并被剝奪了在法定管轄法院受審的權利。
三、法定法官:刑事管轄制度糾偏與理論補正
刑事管轄從來都不是“誰管都一樣”的一般法律技術行為,管轄制度的設立目的雖不是專門保障被追訴人的訴訟權利,亦不是保障法官中立性與公正性,但若管轄制度確立和運轉不當,特別是出現錯誤管轄情形時,有可能對司法公正和被追訴人權利保障造成極大的損害[29]。明確合理地確定刑事案件的管轄,對于保證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以及刑事訴訟任務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0]。刑事管轄制度運行過程中凸顯的不確定缺陷,其產生根源在于以訴訟便利作為確立審判地的基本原則,忽視了法定管轄的內在價值,使得案件分配高效性反而成為管轄制度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顯然與維護程序法穩定性和確定性存在捍格之處。需要明確的是,筆者并非完全否定提級管轄、指定管轄和集中管轄等這類法定管轄例外機制本身所具有的效用和價值。相反,這些機制的有效運行能切實增強刑事管轄制度適用的靈活性,但需要嚴格控制其適用空間,以防侵犯被追訴方權利。為此,可以考慮借鑒大陸法系國家普遍設立的法定法官原則,從制度原則上對法定管轄予以明確,嚴格限制突破法定管轄的案件類型、適用條件和程序等,構建被追訴人救濟途徑及違反法定法官原則的制裁手段,以達消弭刑事管轄制度不確定的缺陷及保障被追訴人程序性權利之效。
(一)法定法官原則的引入
大陸法系許多國家或地區將法定法官作為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甚至規定為當事人的基本憲法性權利。法定法官原則源起于法國1791年《憲法》,后被許多國家憲法所接受。典型如德國《基本法》第101條提供了一個類似于基本權的請求權,規定“不得禁止任何人受其法定法官之審理”;《法院組織法》第16條規定國家應當預先地、抽象地去規定所有可能發生的案件究竟應該歸于哪一法院辦理,也即以立法形式明文規定地域、事物以及功能管轄權等[31]。其他國家或地區相關憲法性條文中亦可引申推導出這一原則的核心內容如《日本國憲法》第32條和第76條第2項;我國臺灣地區所謂“憲法”第8條、第16條和第80條。。
所謂法定法官原則是指必須事先以抽象的、一般的法律明確規定何等案件由何位法官承辦,不能等待具體的個案發生后才委諸個別處理[32]。該原則具有內、外兩層意旨。對內而言,在符合法律優位原則和司法自始原則的條件下,以對抗司法行政體系恣意性為基本要旨,容許審判者針對內部事務分配等事項制定分案規則及法官代理規則等;對外而言,以法律保留原則和明確性原則為核心,包括管轄、審判組織及其相關程序,而管轄法院應由法律明確規定,對該條文的解釋亦不得超出法條之文義范圍[33]。法定法官原則體現了國家立法權對司法權的授予和限制,在防止當事人合法權利遭到侵犯,保障當事人基本程序性權利與防止行政干預司法,特別是在明確提級管轄適用條件、阻止指定管轄隨意化和集中管轄擴大化等方面起到對應的正向作用[34]。
其一,提級管轄適用條件具體化。法定法官原則要求預先規定法院的管轄案件范圍、標準和規則等,禁止在案件發生后臨時組建或隨意移送管轄法院,但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部分案件基于其顯著的類案指導價值或因法院院長需回避等事由,對案件進行提級管轄更為適宜。故而需要對案件提級管轄條件予以明確化、具體化,以明晰“法定”之內涵,避免提級管轄適用標準不一。
其二,規范指定管轄運行程序。指定管轄制度因其事后行政化導致管轄法院模式表面上相悖于法定法官原則,但作為預定管轄的有效補充也被納入刑事訴訟管轄制度范疇,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預定管轄在特殊類型案件中的僵硬化問題。近年來,司法實踐中指定管轄適用呈現的諸多亂象,亟需在指定管轄制度中注入法定法官精神,改變現行上級機關單方確定管轄法院的做法。一方面,應向當事人說明指定管轄法院審理“更為適宜”的理由,并對指定管轄決定形成過程予以釋明;另一方面,應聽取被追訴人對管轄法院的意見,并給予其提出對指定管轄不服的異議權。
其三,為集中管轄尋求正當性證成。當下的集中管轄客觀上是為應對司法需求與資源不平衡矛盾而采取的頗具靈活性的管轄措施,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并無對該類型管轄制度的明確規定,而管轄制度又涉及訴訟根本,自然引人質疑。法定法官原則的確定性要求由法定的機關通過法定程序對管轄事項進行預先設定,而所謂“法定”之“法”的位階也應當與制定法相同。也就是說,如果集中管轄實屬客觀需要,需要在《刑事訴訟法》本次修改中予以言明,方能為集中管轄制度提供規范上的正當性。
(二)訴權救濟:刑事管轄異議權的確立
法定法官原則的另一功能在于可以為被追訴人享有由法定法官審判的權利提供充分解釋:被追訴人提出的刑事管轄異議正是為了使案件管轄回到“法定”狀態。揆諸域外主要法治國家,可以發現被追訴人管轄異議權是作為基本程序性權利予以保障的。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6條規定了被告人的管轄異議權,即在開啟審判程序后,被告有權提出該院審理無管轄權之異議。法院經審查認為異議有理由,在開啟審判程序后或在審判期日中,應分別依第206(a)條、第260條第3項終止訴訟[35]。《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21條規定,被告人可以提出管轄權異議的審前動議及申請移送審判的權利,但是必須在傳訊或傳訊前或者在規定時間內申請。若法院有理由相信,在被告人起訴的地區對被告人存在如此強烈的偏見以至于被告在該地區任何法院不可能受到公正審判時,應當將案件移送其他地區[36]。
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被追訴人管轄異議制度,相關內容只見于新近2021年《刑訴法解釋》第228條以及2017年《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第10條和第11條中關于管轄異議制度的若干規定,即向控辯雙方了解對案件管轄異議情況,聽取意見,但是否賦予被追訴人管轄異議權卻語焉不詳。在司法實務中,對于被追訴人提出案件管轄問題的審查也基本屬于“形式”審查,即使有部分法院認為被追訴人提出的管轄異議成立,在效果上也僅以法院依職權作出移轉管轄決定,進而構成被追訴人“事實上”的管轄異議權之外觀。
在人權保障和正當程序不斷完善的趨勢下,應當在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中明確被追訴人享有法定法官審判的權利,并可在無管轄權或管轄錯誤時,提出不服管轄法院審理的異議。而被追訴人的管轄異議申請也為法院啟動職權調查提供了必要判斷依據[37]。在具體的管轄程序構建上,應當明確被追訴人享有啟動管轄異議審查的程序性權利,并由被追訴人提出該法院管轄將違反法定法官原則的證據和相關理由。受理法院應當在庭審前根據控辯雙方對管轄異議的意見予以綜合評判,被追訴人管轄異議成立的,應當將案件及時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管轄異議不成立的,法院應當告知被追訴人異議不成立的理由,后者還可以向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中止案件審理。
(三)程序性制裁:無管轄權之訴訟行為相對無效制度
程序性制裁是公權力機關違反法律程序后,以宣告訴訟行為無效為核心的法律責任理論[38]。其所要懲罰的并不是違反法律程序的個人主體,而是通過宣告其訴訟行為的違法性——破壞了法律程序及其所包含的司法正義價值,使得那些受到程序性違法直接影響的訴訟行為失去法律效果[39]。
刑事案件由無管轄權法院審理抑或存在管轄錯誤之情形當然因違反法定法官原則而構成程序違法,在訴訟程序效力問題上,具有絕對否定和相對否定兩種模式。絕對否定模式不承認管轄錯誤情形下已進行的訴訟程序效力,一概予以程序性制裁,之前的訴訟行為歸于無效處置。例如,在法國刑事法律中,所有的管轄權規則均具有公共秩序性質,無管轄權將引起訴訟程序無效以及刑事法院所作判決無效。根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74條規定,法院可以“卷宗歸檔”的形式宣告證據無效。一旦證據材料被宣告無效,則不得在后續的訴訟程序中加以援引[40]。相對否定模式則具有裁量性,需要根據管轄錯誤的產生原因及后果進行判斷,制裁程度相對寬松,只有管轄明顯錯誤且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之情形才能予以程序性制裁。如德國法中對于所做判決之效力,按照占絕對支配地位的見解,如果是出于純粹的訴訟認識錯誤而確定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審判組織,則不違反《基本法》第101條規定的法定法官原則;惟以客觀恣意的方法確定審判組織的,即純粹基于不合事理的盤算,才屬于剝奪法定法官情形[41]。一言以蔽之,倘若公檢法機關由于利益之目的而故意管轄錯誤,即“有害錯誤”,則法院最后的判決必然是沒有效力的[42]。于我國而言,對于管轄違法或管轄錯誤的程序效力采用相對否定模式或許更契合刑事訴訟程序邏輯。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較少規定程序性制裁的內容,直接引入較為極端的絕對否定模式易造成適用“水土不服”可能,確實會浪費較多司法資源。另一方面,管轄作為程序性事項,即使發生錯誤,對案件結果走向也可能達不到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程度,對被告人權利影響較小的違法管轄案件可以承認其程序效力,需要實質性判斷對于相對方權利侵害之程度。
四、 ̄修法應以訴權保障為依歸
刑事訴訟管轄制度具有司法公正之保障功能,也是司法公正的生命線[43]。我國現行刑事管轄制度最大的缺憾在于僅關注管轄作為純粹案件分配功能,或者說工具功能,忽視了管轄制度與被追訴人權利保障之間的密切關系。近些年,學界關于管轄制度的討論不斷增多,給予被追訴人管轄異議權的呼聲亦從未中斷。有論者云,權利話語之所以會出現令人擔憂的衰弱,是因為解決有爭議的權利主張面臨著不可避免的困難,導致人們對一切有爭議或無爭議的權利話語的形而上基礎產生懷疑[44]。
事實上,本文僅探討法定法官原則在刑事管轄制度適用之一隅,更多的還涉及案件分配、審判組織、回避制度[45]等,應從具體場景切實發揮該原則確定性和救濟性功能。其實,本文描述的、引證的諸多刑事管轄亂象,更加反映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結構性問題,果不是一個,因更出自多方。在這個問題上,于本文尚未涉及的偵查管轄極大程度上裹挾審查起訴管轄和審判管轄現象而言,體現得尤為明顯。大意是,《刑事訴訟法》從未規定所謂偵查管轄制度,而實踐中偵查管轄幾乎決定了審判法院,這才有了本文提及的,諸如指定管轄等諸多問題。因為該問題關涉“三機關”關系,并非僅僅通過管轄視角即可條分縷析,需另文探討。
具言之,在新一輪《刑事訴訟法》修改業已啟動的當下,應從理念上真正激活2004年《憲法》、2012年《刑事訴訟法》確認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并將其作為本次修法的邏輯起點。“訴權重要”——在管轄制度修改方面更多地關注相對否定程序性制裁內容設置。“加強被追訴人訴權保障”從來不應該是一句虛話,果真欲將其落到實處,需從管轄制度改革、明確管轄異議權做起。
[參考文獻]
[1][20] 龍宗智:《刑事訴訟指定管轄制度之完善》,《法學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5—187頁。
[2] [奧]曼弗雷德·諾瓦克:《民權公約評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冊),畢小青、孫世彥譯,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42頁。
[3] 郭爍:《應對“首要威脅”的起點:網絡犯罪管轄研究》,《求是學刊》2017年第5期,第104—111頁。
[4][19] 郭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應對的程序性困境與完善》,《法學論壇》2023年第4期,第84—93頁。
[5][25] 萬毅:《論檢察機關集中管轄制度》,《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第105—112頁。
[6] 任禹行:《公訴權運行的外部監督:論公訴審查程序》,《求是學刊》2022年第1期,第115—129頁。
[7] 王一超:《刑事訴訟管轄的“不確定”危機及矯正——兼對管轄制度價值的檢討》,《財經法學》2016年第1期,第100—113頁。
[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112頁。
[9] 謝小劍:《法定法官原則:我國管轄制度改革的新視角》,《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第114—120頁。
[10] 周強:《對〈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在該院和部分地區開展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草案)〉的說明》,《人民法院報》2021年8月21日,第1版。
[11] 劉崢、何帆:《〈關于完善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的實施辦法〉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31期,第7—14頁。
[12]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課題組:《案件提級管轄標準和程序機制研究》,《人民司法》2023年第19期,第10—17+22頁。
[13] 李江蓉、寇建東:《基層法院報請提級管轄的進路》,《人民司法》2023年第19期,第18—22頁。
[14] 龍宗智:《審級職能定位改革的主要矛盾及試點建議》,《中國法律評論》2022年第2期,第164—172頁。
[15] 張衛平、劉子赫:《提審:制度機理與演進路向——以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為背景》,《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3年第1期,第102—118頁。
[16] 《刑事訴訟法解釋》起草小組:《〈關于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第19—45+51頁。
[17] 鄧子濱:《刑事訴訟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68頁。
[18] 郭爍主編:《刑事訴訟法案例進階》,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5頁。
[21] 龍宗智、白宗釗、譚勇:《刑事訴訟指定管轄若干問題研究》,《法律適用》2013年第12期,第38—44頁。
[22] 鄧思清:《我國重大職務犯罪案件指定管轄制度研究》,《政治與法律》2022年第6期,第84—95頁。
[23][29][40] 張曙:《刑事訴訟管轄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319、373頁。
[24] 《關于大連市內五區醉酒型危險駕駛刑事案件集中管轄的公告》,“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2024年4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iQm4mwjDbGQery-rdXwwSw。
[26] 桂夢美:《未成年人犯罪檢察案件集中管轄模式研究》,《河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第72—79頁。
[27] 張曙:《刑事訴訟集中管轄:一個反思性評論》,《政法論壇》2014年第5期,第167—175頁。
[28] 王一超:《刑事訴訟條件論》,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64頁。
[30] 王新清:《刑事管轄權基本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頁。
[31][41] [德]維爾納·薄逸克、薩比娜·斯沃博達:《德國刑事訴訟法教科書》,程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53、58頁。
[32][45] 林鈺雄:《公平審判、法定法官原則與法官回避事由——法官曾參與先前裁判之回避問題》,《月旦法學》2022年第12期,第88—109頁。
[33] 黃翰義:《從法定法官原則論牽連管轄之牽連及再牽連》,《軍法專刊》第56卷第3期,第163—187頁。
[34] 桂夢美:《刑事訴訟管轄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頁。
[34] 林鈺雄、王士帆、連孟琦:《德國刑事訴訟法注釋書》,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23頁。
[36] 《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編輯委員會編譯:《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美洲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630頁。
[37] 林山田、林鈺雄、何賴杰等:《刑事訴訟法改革對案——刑事程序法研討會系列(一)》,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56頁。
[38] 陳瑞華:《刑事訴訟基礎理論研究的若干思考》,《比較法研究》2024年第1期,第91—105頁。
[39] 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頁。
[42] 陳瑞華:《程序性制裁理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頁。
[43] 姜啟波、孫邦清:《訴訟管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44] 威廉·A. 埃德蒙森:《權利導論》,侯學賓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205頁。
The Principle of Lawful Judge: Certainty and Remediability
of the Criminal Jurisdiction System
Abstract: Criminal jurisdiction, as a procedural rule, is designed to ensure pre-certainty and remediability, thereby safeguarding judicial fairnes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system is plagued by issues such as the ambiguity of conditions for elevated jurisdiction, the abuse of designated jurisdiction, and the lack of justification for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These issues have severely eroded the foundation of certainty in the criminal jurisdiction system, leading to a crisis of uncertainty. The lack of a “de facto” right to object to jurisdiction for the accused and the lack of procedural sanctions means no remedy when a jurisdiction occurs. In light of these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a lawful judge, strictly delineate the jurisdi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tandards predetermined by law, clarify that the accused enjoys the right to be tried by a lawful judge and provide for relative ineffectiveness of procedures tha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the lawful judge.
Key words:lawful judge; the certainty of jurisdiction; right to object to jurisdiction; procedural sa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