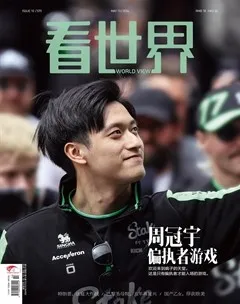在流淚與不流淚之間
索那瑜

為了“解放巴勒斯坦”,哥倫比亞大學等美國大學的學生們占領校園,警方則進入校園鎮壓與逮捕學生,激越之心擴散到世界各地,宛若反越戰的和平運動再起。
在遠方的我,無法加入這些抗爭,巴勒斯坦人持續遭遇的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苦難時時讓我感到痛苦。如果不讀不看不想,就會時常流淚。在流淚與不流淚之間,我還是選擇前者。
尼采在老年時,曾在都靈目睹過一匹老馬,這匹老馬因為太老、太病、太累而被主人鞭打。見此一幕,尼采沒有轉身離去,而是沖上前抱住老馬的脖子痛哭。此后,他一病不起,直到過世。法國哲學家德希達曾論道,人們總想成為看得最透徹、最正確之人,殊不知構成“眼睛”的最大要素并不是視覺,而是眼淚。我們可以選擇用一只眼睛看,但流淚時,是眼睛的全部在流淚。
人們爭論著這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學生們的激進行動是否是反猶主義。我認識的一位住在倫敦的猶太人奶奶跟我說,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街頭抗議,是支持哈馬斯消滅猶太人的,那使她很害怕,她已經不敢在大街上說希伯來文了。而地球的另一頭,在印度,以色列軍人殺害巴勒斯坦穆斯林時的勇猛,激起右翼印度教徒的崇拜,也使得印度境內的穆斯林極為害怕。
世人的恐懼與眼淚,是否分裂成二,逼著人們在兩者中選一?那一日,我在書中讀到一段歷史,猶太人的苦難與“木斯林”這三個字是緊密相連的。
原來,在集中營中,納粹軍人將那些被饑餓折磨到已形如槁木、近乎死亡的猶太人戲稱為“木斯林”(Muselmann)。“木斯林”本來是軍人之間的戲謔之語,后來成了集中營的通用語。
Muselmann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穆斯林男人”,沒有人能夠明確指出“木斯林”的真正典故。有幸存者認為,這是因為這些猶太人因極度的饑餓而導致肌肉萎縮,他們因而大部分時間一動不動地處于趴臥姿勢,如同穆斯林的俯拜形象。這些人問也不答、打也不跑,像是處在永久禱告姿勢的活人尸體。他們的表情是平板的,眼神是空洞的,似乎看不到活人的跡象。沒有精神、沒有情緒,甚至也沒有痛苦與憤怒,很難說這個存在的軀體還是個“人”。
意大利作家,也是集中營的幸存者普利莫·萊維曾說,已經被滅頂的“木斯林”無法為自己的苦難做見證,因為他們已失去語言與感知;而能言能語的幸存者也無法為“木斯林”所受的苦難做見證,因為他們并不明白其中的苦,甚至,其中是否還有“苦”。
將受盡折磨的猶太人戲稱為“木斯林”,嘲笑他們死前精神錯亂到膜拜別人的神,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惡意,何等的褻瀆與侮辱。
看著新聞上那些骨瘦如柴、即將餓死的孩童與大人,人們會聯想,如今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為,又何嘗不是將加沙“木斯林化”?
而世界上正在抗爭的人們,難道不是拯救垂死邊緣的“木斯林”?猶太人是否還記得,曾經一度“木斯林”指的是自己,是自己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