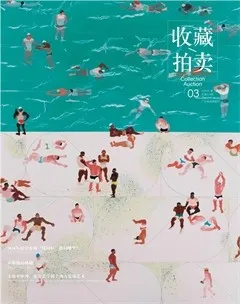一個文物修復師的發現,揭開百年謎團
劉瀟雨


Stepn?Stephen?
2019年的秋天,我踩著晨曦,第一次以文物修復師的身份,走進承德避暑山莊。就這樣,我見到了故事的“主人公”。
只見這件自鳴鐘的標簽底賬(保管部門的通用說法,意即文物的原始資料信息,又叫做文物底賬)上寫的是“烏木自鳴鐘”,從外觀看去,我能確定這是一臺英國產自鳴鐘,一是由于鐘盤上鏨刻了產地,二是在我所任職的故宮博物院的清宮收藏中,亦有見過與此件器物相似的藏品。這也從側面展現出,“日不落帝國”的自鳴鐘、八音盒等具有機械功能又兼具觀賞價值及趣味體驗的器物是當年海上貿易極受追捧的產品。它們通過粵海關流傳到中國境內,又因“康雍乾”三帝是其擁躉,尤以乾隆皇帝為甚,一時之間,自鳴鐘成為上至清朝王公貴族,下至權貴群臣之間的硬通貨。
當擦拭落灰的鐘盤時,鐘盤上的一行字——花體的“stepn,rimbault”“London”,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stepn”并不符合英文拼寫的規則,帶著這個疑問,我開始了檢索取證。經過一段時間的仔細考證,我得知“stepn”就是“Stephen”的縮寫。由于當時鏨刻的時候大小受限,制作者將“stepn”作為“Stephen”的簡寫標注在鐘盤上,得知這個信息,也讓我更方便地探索這件自鳴鐘背后更多的故事。
一幅自畫像
通過與相關文化學者的合作,我很快得到了關于這個人物的更多信息。
這位制表師是斯蒂芬·林博,他是一位著名的胡格諾派鐘表制作商。胡格諾派(Huguenots)是在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中興起于法國而長期慘遭迫害的新教教派。從1744年到1788年,他在英國從事鐘表設計和制作工作。他以擅制“十二調音荷蘭人”而聞名,這種時鐘可以播放十二個曲調,在裝飾的背景前有活動的人物。
在英國泰特美術館的館藏中,留有一幅這位制表師的自畫像。這幅逼真的油畫自畫像收藏自阿斯利特夫人,而這位夫人在1929年將這幅畫像遺贈與博物館收藏。制表師數不勝數,為何他的自畫像能被收入知名博物館中?
比起這位制表師,原來畫像背后的創作者才是更為大有來頭的。這幅自畫像的創作者叫做JohanZoffanzy,約翰佐·凡尼,他的作品非常有名,主要以肖像畫、對話作品以及戲劇題材而聞名,他與斯蒂芬·林博的淵源要從1760年說起。
幾經流轉,變成館藏
1760年左右,約翰佐·凡尼還是一個掙扎在溫飽線邊緣的畫家,因為英語不好,所以他很難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只能住在特魯里巷肖特花園一所房子的頂樓。
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個名叫貝洛迪的意大利音樂盒制造商,他為斯蒂芬·林博工作,主要負責給音樂鐘釘桶(古董鐘表內的一個零件,八音盒中亦有,長滿小釘子的滾筒,通過撥動釘桶可以使音錘敲打不同鈴鐺,奏出和弦音律)。貝洛迪把約翰佐·凡尼介紹給鐘匠,鐘匠雇傭其給鐘面上漆。隨后,他逐漸在鐘表的裝飾銅板上創造一些畫。通過這些設計,林博設計的鐘表更添風采。
根據家族傳統,林博把約翰佐·凡尼介紹給當地的一個名叫本杰明·威爾遜的畫家,他很欣賞約翰佐·凡尼在鐘面上的形象作品,付給他40英鎊的年薪,雇傭其為布藝和人物畫家。通過威爾遜,約翰佐·凡尼結識了演員兼經紀人大衛·加里克,后者成為他的第一位主要英國贊助人。據說約翰佐·凡尼畫這幅畫是為了感謝林博的知遇之恩。
這幅畫創作出來后,一直保存在林博家族中,最先由林博的侄子斯蒂芬·弗朗西斯·林博(StephenFrancisRimbault)保管。斯蒂芬·弗朗西斯·林博在當地的文藝界,有一定的地位。他不僅是一名風琴演奏家,而且是羅蘭森畫作的收藏家,同時是塞繆爾·韋斯利(SamuelWesley)的朋友,他在19世紀第二個十年將這幅畫掛在倫敦蘇活區丹麥街9號他家前廳的壁爐架上。在他過世后,這幅畫由他的兒子愛德華·弗朗西斯·林博(作曲家、古董商)保管。之后,這幅畫一直流傳有序,由愛德華·弗朗西斯·林博的教子E·林博·迪布丁保管,后者又傳承給了自己的女兒阿爾弗雷德·阿斯利特夫人。而這位夫人就是將這幅畫遺贈給泰特美術館的人。
了解了整個故事后,我不禁在想,文物與時間的關系,不僅僅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更是一種文化與時代的傳承。它們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人類過去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社會結構的關鍵線索。無聲無息中,文物以其獨有的方式,跨越時空,與歷史緊密相連,讓我們得以洞察先人的智慧,感受不朽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