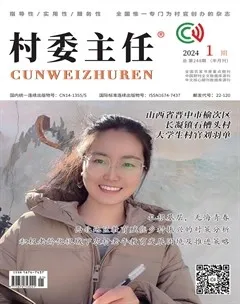基層干部奮戰鄉村振興的現實困境及實踐路徑
作者簡介:曹鵬召(1998—),男,漢族,河北武安人,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為黨建。
摘要:扎根于鄉土社會的基層干部,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和領導力量,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當前,基層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仍面臨鄉鎮人口資源不足、基層組織的主體性和自主性不強、基層治理人才短缺、治理能力不足等現實問題,可以從緊抓產業興旺、健全治理體系、強化人才支撐、強化精神文明支撐等實踐路徑進行解決。
關鍵詞:基層干部;鄉村振興;現實困境
文章編號:1674-7437(2024)01-0210-03 中國圖書分類號:D267.2;D422.6 文章標識碼:A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舉措。作為村級組織中的重要力量,基層干部承擔著協調村級工作、發展村級經濟、完善村級基礎設施等重要任務。然而,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基層干部也面臨著諸多困境和挑戰,因此,對可能遇到的難題進行分析并探究可行性對策顯得尤為重要。
1 基層干部在鄉村振興中的價值邏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1]基層是行政層級的“末端”,服務人民的“前線”,農村基層干部是聯系群眾、引領群眾和服務群眾的“主力軍”,是關系黨的執政地基穩固與否的關鍵“支撐者”,是施鄉村振興戰略發揮基層戰斗堡壘作用的“組織員”[2],其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鞏固黨在農村執政基礎、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著重要價值。
1.1基層干部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主力軍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12月23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是“國之大者”“民之大事”,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底線任務。在脫貧攻堅戰中,廣大基層干部始終堅持人民至上,不折不扣落實政策、全心全意做好幫扶工作,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性勝利。與其他干部相比,基層干部長期奮戰一線,對當地經濟狀況、資源條件、人口結構、風土人情等方面了解更為深入,與村民、企業家等各類人群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并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生活和管理經驗。與普通群眾相比,基層干部掌握更多的政策信息、市場信息、技術信息等資源,對鄉(鎮)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更具有預見性、前瞻性和指導性,隨著公共服務不斷向農村延伸,不少基層干部獲得了再學習和培訓的機會,業務水平和綜合素質不斷提升,更有能力引領產業發展和落實鄉村振興戰略。
1.2基層干部是鞏固黨在農村執政基礎的關鍵支撐
農村基層干部是農村工作的“火車頭”“領頭雁”,是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發揮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支撐。一方面,農村基層干部是黨組織在農村的代表,具有直接的行政和管理職責,負責組織和實施各種政策,維護農民的權益和利益,確保農村社會穩定和有序發展。另一方面,作為基層黨組織的骨干,農村基層干部是基層黨組織的重要成員,是保證基層黨組織能夠有效工作的關鍵。在鄉村振興過程中,黨組織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將更加凸顯,而基層干部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人物。此外,要實現鄉村振興需要全方位推進人才、土地、產業、生態、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工作。基層干部作為人民群眾的守護者,始終堅守在山水林田湖的第一線。
1.3基層干部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流砥柱
基層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治理有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也是基層“強身鑄魂”的“補鈣劑”。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文化豐富多彩,在推進鄉村治理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矛盾糾紛問題。鄉鎮干部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流砥柱,因此,必須加強鄉鎮干部在基層治理中的主體作用。
一方面,鄉村振興新征程上,我國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社會矛盾凸顯期“三期”疊加,群眾工作的對象、內容、領域和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3]。基層干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最為密切,是群眾身邊的“調解員”,更能從群眾的傾訴中了解具體問題的實質,從旁觀者的視角幫助群眾疏導情緒,用相關政策法規調解糾紛,解開群眾心結,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將問題解決在一線。另一方面,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承擔者,基層干部通過搭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梁,引導和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自治,構建了多元共治的新格局。
2 基層干部奮戰鄉村振興的現實困境
針對新時代“三農”發展現狀背景,鄉村振興的提出是由于鄉村發展面臨的階段性矛盾和困難,主要表現在鄉村發展滯后和發展動力不足。從我國國情來看,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鄉村地區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尤為突出。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取得重大階段性成就,鄉村振興形成新格局。然而,隨著鄉村社會形勢、治理基礎和群眾觀念等的變化,基層干部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仍面臨諸多難點和現實困境。
2.1發展不平衡矛盾突出,發展動力不足
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正在逐漸重塑城鄉關系的格局,諸多偏僻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有了較大改善,然而,盡管設施得到改善,農村留不住人的問題仍然存在,鄉村人口外流現象嚴重,鄉村發展面臨的階段性矛盾和困難主要表現還在于鄉村發展滯后和發展動力不足。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1年全國人口共14.11億人,其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2億,占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億,占36.11%,與2010年相比,鄉村人口減少1.64億多,數據顯示,過去20年里,平均每天有將近150個自然村落消失,農村出現凋敝現象。因此,農村缺乏發展機遇和經濟效益,是導致留不住人的主要原因。從脫貧實踐來看,主要是通過國家財政為脫貧地區修路、蓋房、提供教育醫療、產業分紅、低保救助及公益性崗位等措施來消除絕對貧困。然而,鄉村振興不僅僅是消除絕對貧困,而是要解決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需要政府和市場主體協同發力。
農村年輕人選擇外出打拼,導致鄉村人口流失,鄉村建設力量缺乏,本地農民缺乏接受市場觀念教育的有效載體,而有能力逃離農村的恰恰是那些經濟條件較好的人,這意味著消費外流,進而造成生產疲軟,效益低下,本地消費能力下降。此外,隨著電商的興起,部分農村的消費市場被瓜分,農村市場規模萎縮,導致農村的市場投資吸引力不夠,鄉村產業發展受到阻滯,鄉村振興動力不足。
2.2基層組織的主體性和自主性不足
近年來,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力和執行力得到了顯著提升,村級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和精神狀態也有了明顯提升。然而,在鄉村治理的新形勢下,一些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尤其是基層組織的主體性、自主性不足問題,導致基層組織在有效服務農民和有效治理農村方面面臨困境。
一方面,由于農村基層組織的主體性不足,導致基層組織在有效服務農民和有效治理農村方面面臨困境。隨著國家資源向基層下沉,國家權力、國家監督、國家規范和標準也向基層下沉,基層干部的考核標準越來越具體和規范。然而,由于上級一些部門文件缺乏統籌,各個職能部門通知繁雜,要求鄉鎮一級壓實責任,造成鄉鎮工作繁重。為了完成各種上級規定的任務,實現辦事留痕,消耗了基層干部的部分精力,對村民生產生活的需求方面的關注不夠,導致自治化程度較低,農民參與熱情不高漲。例如,出現了基層干部在前面清理轉運垃圾,村民就在后面若無其事的隨手扔垃圾的現象,以及村民家的房屋改不改造、廁所革不革命,怎么改、怎么革,逐漸變成基層干部自己的事,干部做群眾的事,群眾卻袖手旁觀等怪象。
另一方面,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村委會在村里的具體事務決策管理上發揮主導作用,但在實際運行中,鄉鎮基層治理對象是人民群眾,基層干部的中心工作是圍繞人民群眾,具有細小、瑣碎和偶發的特點,不同于簡單的窗口服務,需要充分發揮自主性并發揮真正實踐性智慧。然而,因缺乏共商共建共享的機制,導致基層組織自治性不足。
2.3人才短缺,治理能力存在短板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到,鄉村振興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強化鄉村發展的人力資源保障。然而,目前鄉村振興中存在著對專業人才的需求量大、供給不足的問題。
一是基層工作者數量不足,許多鄉鎮存在“空編”情況,人員不足導致個人工作量居高不下,工作壓力較大。例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只要糧食不出大問題,中國的事就穩得住。”[4]為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做好“三農”工作,穩住糧食安全這塊“壓艙石”,廣大基層干部在撂荒地整治上作出巨大努力。然而,現實的情況是農民種植糧食收入微薄甚至可能會虧本,糧食生產積極性在不斷減弱,這是一個市場行為,并不能簡單依靠嚴禁稻田拋荒,防止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等行政命令輕易扭轉。
二是權責匹配度不高。從體制上看,鄉鎮責大權小,是在快速轉型時期,我國應對基層復雜治理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種策略。然而,這種策略也客觀上增加了鄉鎮基層干部履職難度。例如,鄉鎮范圍內出現任何問題,鄉鎮都要承擔屬地責任,對于群眾訴求在街道、社區職權范圍以外的,需要聯合上級部門協調,時常延誤有效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群眾共建共治參與度較低。此外,基層工作者、居民群眾法治意識均有待加強,基層政府法治建設亟待完善。
3 基層干部奮戰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
3.1緊抓產業興旺,增強發展動力
“產業興則農業興,產業強則農民富。”產業興旺是一個地區農業穩定最直觀的體現,也是穩固農業最有效、最直接的“抓手”。
一是緊抓產業促振興,基層干部應深入調研地區氣候、地理條件、種養習慣等核心要素,學習掌握種養常識、技術、布局等現代化農業知識,充分“吃透”耕地紅線、糧食安全、生態環保等政策導向,重點以復合套作、種養循環等新興模式為突破口,高質量統籌好“糧經畜”協同發展,科學有度地規劃好產業發展“大藍圖”,既要立足“資源優勢”,也要賦能“特色稟賦”。要發揮“集聚效應”,因地制宜規模化發展主導產業,整合設備、技術、土地等資源,規模化種養殖,提高產業“集聚度”,促進“集約化”效益。
二是樹立“特色品牌”,瞄準“差異化”競爭,將地方特有資源轉化為致富優勢,深挖“土特產”的文化和生態價值,賦予農產品“新含義”“新特質”,創建迎合市場需求的特色品牌,做好全過程跟蹤服務。
三是深挖“附加價值”,以農村電商、產品深加工、生態研學游等為拓展重點,開發民宿、旅游、美食、購物等“多業態”項目,實現產業深度融合,在落實優惠補貼上不打折、不拖沓,切實提振農民發展信心。
3.2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凝聚治理合力
一是全力推進村民自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積極發展基層民主[5]。村民自治是鄉村振興平穩運行的“重要依托”,基層干部要夯實村民自治“陣地建設”,既要“多維發力”,也要“全面推進”。例如,依托村辦公室、文化廣場、村史館、集體經濟園區等點位打造“自治平臺”,提供“有事來協商”場所,構建“網格化”鄉村治理體系;通過培養優秀農村黨組織書記和村“兩委”隊伍,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協調好各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深化村民自治實踐;制定村規民約和自治協商機制,開展“板凳會”“院壩會”等豐富的文體活動,自主自治解決矛盾糾紛,提高村民歸屬感和精神認同,推動農村和諧發展。
二是統籌分類指導,提升治理成效。一方面要“上接天線”緊跟潮流,堅持黨建引領,以科學先進的治理思路為指導,大力聚合致富帶頭人、返鄉大學生、土秀才、田專家等各類人才,發揮人才引領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下接地氣”曉暢“農事”,摸清地方風俗、鄉土文化,堅持以農為本,深入挖掘傳統農耕文化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通過建設村史博物館、圖書館、文化墻等方式,推動德治、法治、自治深度融合,讓農村既有“發展之形”更有“人文之魂”。
三是建立健全讓法治、德治與自治“并駕齊驅”的機制。移風易俗是一個系統工程,亟須科學擺布、精準發力,建立機制,并細化配套措施和規范辦法。道德引領雖然見效慢,卻是管靈魂、管根本的基礎辦法,需要一以貫之持續推進。例如,可以加大政策宣傳、選樹典型和揭短亮丑的力度,并從未成年人開始抓起,讓真善美受熱捧,讓假惡丑遭唾棄,形成良好風尚的代際傳承。法紀懲處即使有時缺少人情味,但是必須及時、精準地施加到違法犯罪行為上,發揮懲惡揚善、大快人心的倒逼效應,同時做好權益受侵害群眾的走訪慰問和心理干預,保持總體社會穩定和大眾心理的理性狀態。同時,基層鄉鎮、街道黨委政府也應統一加強對村規民約的規范清理,在充分尊重村情民意的基礎上,對照相關法律和紀律規定,及時糾正違背憲法和法律的條款,讓村規民約、自治行為經受住法律的洗禮和群眾的質疑,讓村情民風和諧融入良法善治正軌。
3.3強化人才支撐,助力持續發展
“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人才是鄉村振興源源不竭的“動力源泉”,既要“引渠”,也要“活源”,切實強化基層治理人才支撐。
一是按需選人,拓寬發現人才渠道,在高等院校、職業技校、周邊土專家、優秀農民工、本土企業家等途徑引入“急需緊缺”的專業對口、技術硬核、經驗豐富的人才。
二是科學育人,優化培訓資源,配置最優最強的師資力量,將地方規劃政策、技能水平提升、經驗交流等全方位、無縫隙納入教育培訓課程。
三是“精準用人”,實行分類管理,讓真正懂行、在行、內行的人才深入種植養殖、鄉村治理、集體經濟、產業經營、鄉村治理等工作“最前沿”。
4 結束語
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踐行主體,基層干部起著肩負黨的初心使命、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發展成果的作用。為解決基層干部面臨的現實困境,需要政府、社會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建立起一個良好的鄉村振興生態系統。
參考文獻:
[1]劉凡熙.深入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現實困境及對策建議[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5(05):83-89.
[2]王玉珍,朱麗麗.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鎮干部工作狀態研究——以分宜縣F鎮為研究視角[J].特區經濟,2023(09):100-103.
[3]劉炳香.新時代基層干部治理能力內涵解析與提升路徑[J].國家治理,2022(09):2-9.
[4]韓俊.以習近平總書記“三農”思想為根本遵循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J].管理世界,2018,34(08):1-10.
[5]新華網.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四論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EB/OL].(2022-10-31)[2023-12-15].https://politics.gmw.cn/2022-10/31/content_361249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