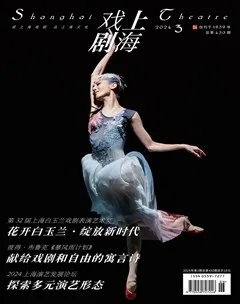《887》讓我們記住了什么?



編者按:5月4-8日,加拿大戲劇大師羅伯特·勒帕吉的《887》作為2024上海·靜安現代戲劇谷特邀劇目上演于大寧劇院。勒帕吉在舞臺上講述了自己兒時的故事,邀請觀眾跟隨著他的視線探索那獨一無二的記憶宮殿。讓我們一起來聽聽“海上青年戲劇沙龍”的作者們,看完這部作品有何感想……
李旻原|上海戲劇學院副教授
數字是神祕的科學,在宇宙中“萬物皆數”,卻顯少有人知其奧妙,有時就在我們的腦海中瞬時浮現,卻能意外拾起一聯串的記憶。勒帕吉藉由無法記下詩篇“Speak White”的緣故,在思考“記憶”的同時,回想起小時候居住的887號公寓房中的生活點滴,將每一戶街坊鄰居的家庭軼事串聯起國家政治的民族大事。
集編導演與裝置設計于一身的勒帕吉,用文本融合于舞臺裝置形成劇場性整體的敘事方法,以視覺符號配合語言將所指明確,淡化了能指作用所產生的歧義,巧妙的設計、美學的展示、精準的演繹、團隊的合作,建構出令人贊嘆的劇場幻影。或許許多觀眾因對魁北克的歷史與政治不熟悉而無法共情,但仍能因在劇場當下微妙細致的總體演出而有所共感。當下劇場性(thé?tralité)逐漸走入國內的學術視野開始被討論,《887》無疑是絕佳的演出實例。
張? 青|上海戲劇學院博士生
以高科技手段主導舞臺空間的羅伯特·勒帕吉這次在舞臺上完成了一次對歷史和社會的終極發問。《887》相較于其以往的戲劇作品,視覺沖擊和技術含量并不算突出,但整部作品在劇場中達成一種奇異的和諧,令人眼花繚亂的舞臺裝置在變換的過程中浮現出歷史的厚重與沉靜。勒帕吉以獨角戲的形式演繹了對20世紀60年代魁北克武裝斗爭的回憶以及對社會運動影響個人及家庭生活真相的質問。整體的敘述形式使這段歷史與回憶沾染了落寞的浪漫,而個人回憶往往脫不開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又不斷建構著變化的社會意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和記憶,在不斷翻滾的社會大潮中構成一幅幅具有歷史標志的圖景。
對于戲劇來說,故事既是中心,又是外殼。勒帕吉的故事看似是個人經歷與瑣碎的家庭事件,實則是一個時代下的社會圖景的縮影,意識流式的講述方式讓觀眾并不過分關注故事本身,而是在節奏分明的敘事過程中感受人與社會、歷史的緊密聯系。燈光,影像,音樂,轉臺,最終平靜,就如同人生,兜兜轉轉,反反復復,終于在激流中學會了順勢而為。
魯? 楠|上海戲劇學院博士后、講師
羅伯特·勒帕吉的《887》雖然以獨角戲的形式進行表演,但在舞臺上與他配合嫻熟,或者說被他運用自如的重要“搭檔”便是他的“機器神”(EX MACHINA)團隊精心打造的“時間魔方”。這是一個與勒帕吉等身高的“微縮景觀”旋轉舞臺,它的每一面都像是劇中所述的人類大腦的海馬體產生記憶時“記憶突觸”受到刺激而發出的短暫光亮,呈現了記憶被復刻又被遺忘的那一瞬間……
《887》是獨屬于勒帕吉腦中回憶的“海馬體”,他試圖向觀眾展示每一道褶皺、每一塊“記憶突觸”隱隱閃亮的記憶之光,而這些個體化的生活印跡無不籠罩在魁北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的社會動蕩、階級沖突、政治變革、身份認同的沖擊等等歷史事件的底色之下。在勒帕吉和他的團隊機器神打造的舞臺“時間魔方”之下,在一段段跳躍閃現的“記憶突觸”的光亮中,勒帕吉試圖“重現”宏大歷史書寫下的集體回憶和個體生命軌跡,在個體性的情感記憶和歷史性的客觀事件中,每一次轉動“時間魔方”都代表著一次戲劇空間的“割裂”與“縫合”,而勒帕吉最終是否完整地復原了這個“時間魔方”?
相信這不僅對于勒帕吉而言,同樣對于面對深邃歷史塑造下的集體和個體書寫的舞臺創作而言,仍是一個有待深思和探索的巨大挑戰。對于《887》而言,至少在層層折疊交織的舞臺空間里,在復雜的集體鏡像、歷史廣角碎片和細膩的個體生存溫度和呼吸中,勒帕吉“創造”了屬于自己的“記憶迷宮”。
熊之鶯|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在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世界邁入機械復制時代,先是誕生出“第七藝術”電影,隨后又有了足不出戶便可觀看的電視,遭遇危機的戲劇開始探求獨屬于自身的靈光。就方向性而言,參加本屆戲劇谷展演的導演中,羅伯特·勒帕吉選擇了與特佐普羅斯、彼得·布魯克完全相背的道路。后兩者幾乎放棄劇場中一切依賴技術的魔法,將全部的能量交付演員活生生的身體和觀演空間。而勒帕吉則將魔法運用到極致,驅趕著他的“使魔”——技術走上舞臺,成為“表演的機器”。
《887》是勒帕吉自編自導自演的自傳體獨角戲。雖說是獨角戲,但舞臺上實際有兩個“演員”。一個是勒帕吉本人,另一個便是他設計的裝置“記憶宮殿”。隨著勒帕吉的娓娓道來與“記憶宮殿”的千變萬化,他的私人成長記憶與作為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的集體記憶在舞臺上汩汩流動。
勒帕吉從電影中學到了新的觀看方式,即對同一場景的不同視角與景別切換。借助模型和即時影像,他成功將這種觀看方式搬上舞臺,讓靜態的空間充滿躍動感。而又因為一切在舞臺上發生,我們常能看到多個景別同時存在。勒帕吉在臺上重演童年送報時被士兵欺侮的一幕,是我見過的劇場中對即時影像最成功的應用。他將手機架在地上,拍攝自己的腳部由遠及近又緩緩退去。極低的仰視視角使畫面充滿壓抑感,只有腳部入鏡也意外地難以分清那屬于在場的成人演員還是遙遠記憶里的孩童。雖然明知影像來自此刻臺前正在進行的表演,但我們又忍不住相信它是當年的真實記錄。鏡頭語言的主觀性、影像的擬真性與舞臺的展演性共同作用,這是電影無法提供的、僅屬于戲劇的現場性體驗。不同時空在舞臺上重疊,過去與現在之間、回憶與真實之間、幻覺與表演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完美地契合了作品的“記憶”主題。臺上仿佛形成一個具有強大引力的黑洞,將觀眾吸入創作者的腦海中。
其實模型也好,即時影像也罷,從技術的角度來說都不算新穎,我也曾無數次在當代舞臺上見到導演們使用。只是多數時候,是肆意膨脹的技術“奪舍”了導演,將舞臺變成單純的炫耀之所。而勒帕吉的《887》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一個創作者將技術轉化為“超級傀儡”的范例。
韓樂樂|上海戲劇學院碩士研究生
在現實與詩意之間,《887》撕開一道令人不安的口子:魁北克分離主義運動的傷痛史被集體淡忘,勒帕吉的戲劇生涯被電臺一筆帶過,任何形式的文化記憶都難逃被篩選與被書寫的過程。歷史書寫者的魅影藏匿于黑暗中,個體可能左右自己的記憶嗎?當最后一縷車燈消散,我們又會如何記憶演出本身呢?在廚房與朋友爭執時,勒帕吉道出他對記憶的理解——“發自肺腑的記憶”,借助身體感官與記憶建立聯結。巧妙之處在于,這不僅是他在劇中背誦詩句的方法,也成為構作整場演出的美學原則:通過身體、燈光、聲音等元素喚起聯覺式的體驗,建立場景與觀眾之間的感知聯結,從而將文化與私人的記憶傳遞給中國觀眾。
因此,盡管勒帕吉多數時候面無表情、語氣平靜,我們卻能感受到情感與力量的起伏涌動。比如即時投影中并置了年邁勒帕吉的特寫和年輕姨夫的模型,中間的別墅大門將兩人隔絕。他平靜地重述精英姨夫多年前的忠告,然而演員臉上浮現的皺紋、質感的對比、視覺空間的沖擊,卻可以整體性地激發我們對魁北克的教育與階層問題產生情緒反應和理性思考。通過將個人敘事和公共話語轉化為神經末梢層面的身體傳遞,《887》呈現了一條記憶被遮蔽的歷史路徑。
王非一|編劇
整部劇彌漫著一種溫和的詩意,從承認“戲”與“非戲”的界限開始,羅伯特·勒帕吉在場燈開著時走上舞臺,介紹了本劇的緣起,希望觀眾關上手機……
故事從“我”接到一個詩歌朗誦的任務,卻無法順利背誦講起,場燈漸漸熄滅,觀眾跟隨著“我”,進入這個從“我”到“我的家庭”“我所在的樓宇”“我的朋友”“我所在的國家和時代”的大故事中。敘事看似無機,在“我”的主觀視角牽引下,實則呈意識流狀展開,每條線索如草蛇灰線,恰如記憶纏繞,伴隨著豐富的舞臺手段,精巧收納進溫和理性有力地表達中。
隨著精準流暢地轉場,一幕幕記憶在舞臺中心的“魔盒”中一層層折疊展開,汽車、每個家庭的室內場景、真實時間內燒開的一壺水、快餐店飲料機……小道具的設計采用事無巨細的自然主義,回不去的家和往事具象成微縮的道具和布景,浸滿了對回憶和情感的珍視。
在每個片段呈現中,即時影像、影戲等多種舞臺手段并置,卻并不單純為了舞臺趣味,而是區隔開了當下與回憶、真實存在的演員和所有非真實的表現手段,承認往事與歷史作為“場面”不可以再進入和更改,在微縮的場景里顯得龐大的“我”無法再次進入,只得俯身一次又一次溫柔地凝望、再訪回憶。
Q:為什么對獨角戲的創作形式情有獨鐘?
A:獨角戲的核心是有關孤獨感或者說是某種獨特的感覺。出于各種原因,我從小就總覺得自己跟周圍人不一樣,一直感到非常孤獨。如今這種孤獨感少了許多。不過,當一個人站在舞臺中間,獨自講述他的故事時,這本身就是一種孤獨的狀態。獨角戲意味著演員會在臺上表達出某種孤獨感,以便拉近與觀眾的距離。我相信,在欣賞獨角戲時,觀眾也期待得到演員的信任,使得這一切都變成更為個人化的體驗。仿佛舞臺上就只有一個人,而那個人就是你自己。
Q:在《887》中是如何處理記憶這個主題的?
A:在某種意義上,劇場離不開“記憶”。當你在臺上表演時,你必須依靠你的記憶,我們背誦臺詞、學習文本。此外,我認為戲劇本身就是回憶的藝術,并不是因為在表演的時候演員需要背臺詞,而是因為戲劇本身就是記憶的一種形式。比如在加泰羅尼亞,當佛朗哥決定消除加泰羅尼亞文化,他大肆焚燒書籍并禁止當地人講加泰羅尼亞語言,然而那些已經學過用加泰羅尼亞語寫成的歌曲、詩歌和戲劇的人,成為了承載這個民族文化的活著的書籍,依靠他們的記憶這個民族的文化從此得到了傳承。我們也可以依靠舞臺演出將我們的共同的回憶傳遞給下一代。
Q:與電影或書籍相比,劇場在處理記憶這個主題時有什么優勢?
A:我認為,不論什么主題,劇場都比書籍、電影、電視或任何視頻媒體有優勢,因為它是當下發生的,是此時此刻的表演。我曾經執導過一些電影,然后在10年、20年后,當我去參加電影節時,那些電影又再次在電影院呈現。然而我看到的是過去的我,而且那部電影表達的是我過去的想法、陳舊的理念。但當我在劇場表演時,臺上的我就是當下的我自己。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劇場始終是表達任何主題的最佳載體。當然,記憶這個主題通過劇場的形式會表達得更好,因為劇場是記憶的場所。
Q:您將自己的制作公司命名為Ex Machina,為什么這樣命名?
A:我一直對技術感興趣,而我所說的技術并不意味著先進的、大型的電腦化工程的舞臺裝置。它也可以是一支筆,比如你寫字用的鉛筆,鉛筆就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技術。我一直非常關注技術。我認為技術可以是一種寫作方式,一種雕刻方式,一種繪畫方式。在戲劇創作中,舞臺技術是時常被否定和忽視的環節,或者被認為是沒多大用處的小玩意兒。而我試圖將其用作一種寫作方式,我們公司叫 Ex Machina,是源于Deus Ex Machina這個詞匯(注:拉丁語詞組,翻譯自古希臘語,中文通常譯為“機器神/機械降神、扭轉乾坤的力量”),古希臘戲劇在演出即將結束時通常都會出現奇跡,“神明”通過人力操控的機械裝置從天而降,制造出意料之外的劇情大反轉。我們對這樣的意象很感興趣,也許可以通過技術以不同的方式來講述故事或解決創作中的問題。因此,我們制作公司的名字里去掉了“Deus”,保留了“Ex Machina”,因為實際上這個“機械降神”的橋段是完全由人操作的。
(采訪摘編自“上海靜安現代戲劇谷”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