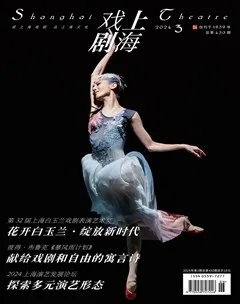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中的戲劇及改編
編者按: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在世界上是一個(gè)常青的話題,在中國更是一個(gè)繞不過的話題。因戲劇成就而獲此殊榮的劇作家也不少見,例如,比昂遜、埃伊薩吉留、梅特林克、霍普特曼、馬丁內(nèi)斯、蕭伯納、皮蘭德婁、奧尼爾、貝克特、索因卡、高行健、達(dá)里奧·福、品特、漢德克等。可以說,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中的戲劇作品是組成現(xiàn)當(dāng)代戲劇文學(xué)史的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這一期“青年·戲談”由上海越劇院青年創(chuàng)作沙龍成員、中國國家話劇院編劇鐘海清主持,與北京城市學(xué)院教師潘耕、上海歌舞團(tuán)編劇魏睿、上海越劇院燈光設(shè)計(jì)方瓊分別論述了莫言戲劇及其小說中的戲劇性表達(dá)、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中的戲曲改編、文學(xué)思想與舞美設(shè)計(jì)的關(guān)系。希望此次對(duì)談的探討,進(jìn)一步拓寬戲曲藝術(shù)與經(jīng)典文學(xué)的研究視野。
一、莫言戲劇及其小說中的戲劇性表達(dá)
鐘海清:我們對(duì)作為小說家的莫言是很熟悉的,但他也有豐富的戲劇創(chuàng)作。關(guān)于莫言的戲劇創(chuàng)作及其歷程,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潘 耕:實(shí)際上,莫言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非始于小說,而是《離婚》這部話劇劇本。莫言當(dāng)時(shí)對(duì)戲劇很有熱情,非常喜歡《于無聲處》這部話劇,所以在結(jié)構(gòu)、人物關(guān)系上都是從模仿開始的,但是他不滿足于《離婚》生吞活剝式的模仿,所以自己將這個(gè)劇本付之一炬。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他的戲劇作品共有6部,三部話劇《鍋爐工的妻子》《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戲曲《錦衣》《高粱酒》,還有一部歌劇《檀香刑》。
莫言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處處都滲透著戲劇、戲曲的精髓和養(yǎng)分。莫言的戲劇活動(dòng)也是非常豐富的。那么,都有哪些劇本和戲劇演出對(duì)莫言產(chǎn)生過影響呢?
從文本閱讀來講,他的戲劇閱讀分為幾個(gè)階段,第一是他青少年時(shí)期的興趣閱讀階段,這主要來源于他當(dāng)時(shí)的語文課本,比如老舍、曹禺、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在這個(gè)階段,他主要是對(duì)話劇語言特別感興趣。在莫言進(jìn)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初期,有一個(gè)重讀和再讀戲劇經(jīng)典的階段,他著重讀了郭、老、曹、《莎士比亞文集》等。到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成熟的高峰期,他又有一個(gè)廣泛閱讀階段,他的閱讀包括得過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劇作家,如奧尼爾、薩特等,以及中國當(dāng)代劇作家劉恒、鄒靜之等。在閱讀這些劇本時(shí),他的興趣集中在以下幾方面——戲劇語言、戲劇結(jié)構(gòu)、戲劇的思辨性等。
他對(duì)戲劇的觀摩主要來源于民間戲曲,就是山東高密的地方戲。在他的描述中,童年和青少年時(shí)期每一次戲劇演出對(duì)當(dāng)?shù)貋碇v就像一次盛大的節(jié)日一樣。他的人生觀、歷史知識(shí)等,很多都是從茂腔學(xué)習(xí)來的,后面就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沙家浜》等。
這些戲劇觀摩給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戲劇的現(xiàn)場環(huán)境和氣氛。在他的小說中,一些人物的動(dòng)作、語言的修辭表達(dá),常常呈現(xiàn)出夸張、濃烈的特質(zhì),這些都是與他感受到的戲劇氛圍有關(guān)。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不是淡淡的、詩意化的風(fēng)格,而總是強(qiáng)烈的、夸張的戲劇化風(fēng)格。后來,莫言也經(jīng)常有意識(shí)地觀摩學(xué)習(xí)戲劇,到各國看不同形式的戲劇展演。我認(rèn)為他主要關(guān)注的問題有以下幾點(diǎn):
一、藝術(shù)性和商業(yè)性并存的問題。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也特別重視這一點(diǎn),他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一些不僅有藝術(shù)性,而且能夠兼顧商業(yè)性的作品。
二、近年來他比較關(guān)注舞臺(tái)技術(shù)對(duì)劇本創(chuàng)作的影響問題。大家看他的《我們的荊軻》《霸王別姬》表現(xiàn)形式是偏傳統(tǒng)的,我們更期待看到他小說里的魔幻主義、魔幻色彩的表達(dá)出現(xiàn)在戲劇作品中。我認(rèn)為他在考慮了舞臺(tái)技術(shù)給文本提供的廣闊空間和豐富可能性后,或許會(huì)在劇本創(chuàng)作時(shí)有一些很不一樣的表現(xiàn)。
三、對(duì)臺(tái)詞的強(qiáng)調(diào)和重視。不管是戲曲還是話劇,莫言認(rèn)為臺(tái)詞寫作是第一位的,這也是他作為小說家寫戲劇的特點(diǎn)之一。莫言的戲劇作品跟他小說的語言有一脈相承之處,比如書面語言、口語、方言,大量的排比句、押韻的句式、無厘頭的句式等雜糅使用,尤其是他寫歷史劇時(shí),他的臺(tái)詞往往有大段的獨(dú)白呈現(xiàn)出這樣的特色。
莫言創(chuàng)作理念對(duì)我的戲劇創(chuàng)作也有影響。第一點(diǎn)是強(qiáng)調(diào)人物的動(dòng)作性戲劇沖突。莫言在小說里,擅長用動(dòng)作的反復(fù)去強(qiáng)調(diào)人物的主觀能動(dòng)性。這與我國傳統(tǒng)古典小說一脈相承。在古典小說中有“三顧茅廬”“三打白骨精”,人物一而再再而三的行動(dòng)能夠把在行動(dòng)過程中矛盾雙方的沖突激發(fā)起來,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戲劇性。在沖突的過程中,魔幻色彩和荒誕色彩的表達(dá)也隨之而來。
第二點(diǎn)是空間感。莫言的作品里隨處可見非常集中的、獨(dú)特的空間設(shè)置。我做過一個(gè)莫言短篇小說《拇指銬》的改編劇本,原小說的故事地點(diǎn)就是鄉(xiāng)間的一棵樹下,它本身提供的空間就具備了做一個(gè)獨(dú)幕劇的基礎(chǔ)。在他的長篇小說里,也有許多獨(dú)特的空間。首先,它的小說里反復(fù)出現(xiàn)一個(gè)“大舞臺(tái)”——高密東北鄉(xiāng)。他筆下的人、鬼、畜生、神靈都集中這里,有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感覺。另外,一個(gè)任意空間,有表演者、有觀眾,從戲劇來講它就形成了舞臺(tái)。他小說里有很多“小舞臺(tái)”公共空間,比如廣場、集市等。他特別善于寫各種狂歡慶典活動(dòng)、儀式,甚至很多帶有怪誕色彩的節(jié)日,比如“雪集”,這是他構(gòu)想出來的一個(gè)節(jié)日。在雪天里,民眾要挑一個(gè)雪公子到集市上游行,所有人都不能說話,他們都在用動(dòng)作和神態(tài)進(jìn)行交流,它的感覺特別像一場默劇。
二、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中的戲曲改編
鐘海清: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獎(jiǎng)?wù)叩淖髌吩谥袊袥]有被改編為戲曲?
魏 睿:有,但是與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易卜生、契訶夫等外國文學(xué)改編戲曲比起來,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獎(jiǎng)?wù)咦髌返膽蚯木幏浅V伲瑤缀跏乔缚蓴?shù)。
具體來說有兩種:一類是中國戲曲藝術(shù)家改編諾獎(jiǎng)作品,如中國臺(tái)灣當(dāng)代傳奇劇場吳興國創(chuàng)作演出的京劇《等待果陀》,改編自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四川劇作家徐棻的川劇《欲海狂潮》、河南劇作家孟華的曲劇《榆樹古宅》,都改編自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欲望》;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至今被改編為評(píng)劇、豫劇、晉劇、茂腔并已演出。另一類是諾獎(jiǎng)作家自己的戲曲創(chuàng)作,如高行健的原創(chuàng)戲曲劇本《八月雪》,和莫言原創(chuàng)戲曲劇本《錦衣》,莫言參與創(chuàng)作的山東茂腔劇本《紅高粱》,姑且把這些都稱為“諾獎(jiǎng)戲曲”。總體來說,可以說是少得可憐,是一個(gè)非常值得研究的有趣現(xiàn)象。
鐘海清:中國戲曲改編外國名著為什么不首選諾獎(jiǎng)的戲劇文學(xué)作品呢?
魏 睿: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自1901年開始頒發(fā),而19世紀(jì)末至20世紀(jì)中葉的西方戲劇正值現(xiàn)代主義思潮興起,如火如荼,并逐漸走向成熟,戲劇人顛覆了嚴(yán)格遵守“三一律”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如梅特林克的《青鳥》,霍普特曼的《沉鐘》,均是象征主義戲劇的代表作,皮蘭德婁的《六個(gè)尋找劇作家的角色》《亨利四世》等,均張揚(yáng)著象征主義、表現(xiàn)主義、荒誕派風(fēng)格。試想,這些作品本身帶有荒誕不經(jīng)的色彩,如何改編為程式化嚴(yán)謹(jǐn)、唱念做打齊全的戲曲?無論是元雜劇、明清傳統(tǒng)、傳統(tǒng)連臺(tái)本戲、新編戲的樣式似乎都無法削足適履,相反倒是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等兼具“三一律”與抒情性的戲劇作品與中國戲曲不謀而合,我認(rèn)為中國戲曲具有獨(dú)特的“三一律”屬性,是非常寫實(shí)的藝術(shù),這里不展開談,戲曲尚且無法全然對(duì)接跨越時(shí)空敘事、無厘頭敘事、多聲部敘事、蒙太奇敘事的另一重領(lǐng)域,這是國外諾獎(jiǎng)作品很難在戲曲中找到立身之地的根本原因。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吳興國敢于打破常規(guī),不破不立,他自編自導(dǎo)自演的《等待果陀》首演于2005年。吳興國為什么不像常人把京劇比喻成一件精美珍貴的古董,而是比喻成一個(gè)異化丑陋的怪物呢?我想這就是吳興國“世人獨(dú)醉我獨(dú)醒”的一面,當(dāng)一門古典藝術(shù)被人們吹捧得越高,就越容易固步自封、盲目自大、循規(guī)蹈矩,自卑與自傲共存,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這藝術(shù)若想真正完成時(shí)代的華麗轉(zhuǎn)身,便需要經(jīng)得起否定與批判,敢于打碎自己之后重組,不要把自己看作至高無尚的老祖宗,而是世界眾多藝術(shù)符號(hào)之一,隨時(shí)將其他符號(hào)拿來為己所用,也隨時(shí)可以融入其他符號(hào)。
吳興國的《等待果陀》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是諾獎(jiǎng)戲曲作品中至今無可超越的一座山峰,一方面在于他敢于用京劇“移植”荒誕派思想,并做了東方化、禪意化的重新闡釋,將西方人失去信仰之后的迷茫無措,轉(zhuǎn)指為東方哲學(xué)中無休無止的痛苦因果循環(huán)。同樣是怪誕戲謔的表演之下彰顯人心的漂泊無依,他呈現(xiàn)出另一番虛幻、漸悟的意味。另一方面,吳興國不唯戲曲的程式化表演體系馬首是瞻,他在《等待果陀》中,將傳統(tǒng)的程式動(dòng)作作了大膽的剪輯拼貼之后,強(qiáng)烈而夸張地增強(qiáng)了節(jié)奏感、韻律感、肢體表現(xiàn)幅度。
當(dāng)然,不是說若想成功地創(chuàng)作新編戲就要復(fù)制《等待果陀》,而是敢于不破不立,雖然人們論及“戲曲改革”“東西方思潮結(jié)合”“寫實(shí)與寫意結(jié)合”這樣的表述有許多年,好像有多么簡單,但是落在實(shí)踐層面,似乎還在摸石頭過河的階段。
鐘海清:為什么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欲望》會(huì)被改編為多個(gè)版本的戲曲呢?
魏 睿:劇作家徐棻是戲曲改編諾獎(jiǎng)作品的拓荒者,1988年她將《榆樹下的欲望》改編為川劇《欲海狂潮》,1989年首演,是一部突破傳統(tǒng)戲劇文學(xué)規(guī)則的作品。
用慣常思維來看,中國戲曲自古以來擔(dān)當(dāng)著高臺(tái)教化的任務(wù),是“忠孝節(jié)義”傳統(tǒng)思想的藝術(shù)載體,即便講述愛情也是文質(zhì)彬彬、詩情畫意、溫柔敦厚、嫻靜儒雅,即便有情欲描寫也難登大雅之堂,不會(huì)在舞臺(tái)上公開地演繹欲望,更絕不會(huì)探討欲望與人性的關(guān)系。但是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欲望》走上中國的戲曲舞臺(tái),是特殊時(shí)代的特殊現(xiàn)象。都知道,20世紀(jì)80年代是中國文化思想相對(duì)自由爭鳴的黃金時(shí)代,被壓抑扭曲的民族靈魂驚醒,隨著人們追求科學(xué)與知識(shí)的一時(shí)興盛,國門逐漸打開,各思想流派的一時(shí)涌入,催生出一系列文學(xué)與戲劇的精品。劇作家徐棻是將《榆樹下的欲望》改編為戲曲的第一人。
奧尼爾筆下的欲望有多重含義,有人本性中的相互征服,有兩性間的相親相愛,有來自生命本能的一種無法名狀的野性力量,在徐棻筆下了成為被壓抑幾十年的心靈為沖破“禁欲”而尋找的一把利劍。由女性扮演的“欲望”一角,似靈似魅,如影隨形地跟隨在主人公身邊。在此之前,川劇乃至戲曲舞臺(tái)上有無數(shù)神靈鬼魅,都是非常具象非常實(shí)在的角色,而純粹代表某種意象、幻想或者思想,或者是從《欲海狂潮》而始,這正是徐棻的智慧成就。
2013年,上戲戲曲導(dǎo)演碩士研究生佟姍姍將《欲海狂潮》改編為小劇場京劇《殺子》,用兩個(gè)演員扮演各種角色,全新地闡釋了欲望,我在現(xiàn)場觀看過,也比較精彩。
三、舞美設(shè)計(jì)與戲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
鐘海清:你覺得舞美設(shè)計(jì)與戲劇文學(xué)有怎樣的關(guān)系?
方 瓊:戲劇藝術(shù)的生命就在于文學(xué)性與舞臺(tái)性的統(tǒng)一整合。
作為一種文學(xué)樣式,戲劇文學(xué)具有自身的特征,除了可以聆聽劇情和閱讀劇本之外,最完整的呈現(xiàn)方式就是舞臺(tái)演出。戲劇文學(xué)作品通過舞臺(tái)性的“二度創(chuàng)作”,最后以舞臺(tái)形式呈現(xiàn)給觀眾。
當(dāng)然,作為舞美設(shè)計(jì),在作品中絕不止是表達(dá)自我的情緒和感受,而是要表達(dá)出真正具有戲劇性的意圖,因此需要注重與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戲劇文學(xué)作為文學(xué)作品中的一種特殊形式,也具有一般敘事性作品的共同要求,即突出舞臺(tái)性與時(shí)間、空間的高度集中,鮮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具有強(qiáng)烈的心理活動(dòng)。這些特點(diǎn)為舞美設(shè)計(jì)提供了一個(gè)創(chuàng)作思考的途徑和視角。如果對(duì)劇本內(nèi)涵深入解讀的話,可以創(chuàng)造出新鮮而獨(dú)特的視覺形象出現(xiàn)在舞臺(tái)上,這種解讀應(yīng)該是舞美設(shè)計(jì)的起點(diǎn)。當(dāng)我們真正地做到這一點(diǎn)時(shí),觀眾會(huì)說這是一部優(yōu)秀的戲劇作品,是真實(shí)的且值得去深思的。
2004年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的《櫻桃園》在北京上演了100周年紀(jì)念演出版。這個(gè)版本里,舞美設(shè)計(jì)和導(dǎo)演把失去了過去輝煌的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比喻成“櫻桃園”。在這種解讀下,《櫻桃園》劇本中規(guī)定的環(huán)境形象不再具有唯一性。舞美設(shè)計(jì)沒有按照劇本提示和當(dāng)年那樣來處理場景,而是把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百年歷史的舞臺(tái)大幕作為主要布景形象。開場時(shí),幕布就像通常大幕一樣閉合著,演出過程中,它們可以縱向往后翻轉(zhuǎn),再不斷重新組合,加上道具的設(shè)置,構(gòu)成全劇的所有場景。這種對(duì)經(jīng)典的重新解讀,為《櫻桃園》帶來新的演出形式和面貌。這種手法在當(dāng)代劇場里也經(jīng)常可以被看到。這是對(duì)舞美設(shè)計(jì)既有能力的挑戰(zhàn)。除了從導(dǎo)演角度考慮問題之外,它還考驗(yàn)了設(shè)計(jì)師對(duì)文學(xué)的理解力,以及自身所持有的哲學(xué)觀和價(jià)值觀。
鐘海清:舞美設(shè)計(jì)師如何在作品中體現(xiàn)文學(xué)性的思考?
方 瓊:舞美設(shè)計(jì)為演員的表演創(chuàng)造了詩性的空間,這樣一部新的戲劇就誕生了。有人說劉杏林的舞臺(tái)設(shè)計(jì)是“中式極簡主義”,他在傳統(tǒng)美學(xué)與當(dāng)代視覺藝術(shù)關(guān)系上尋求到了一種結(jié)合,產(chǎn)生出了獨(dú)具匠心的極簡風(fēng)格:留白的舞臺(tái)、空靈的意境,以及多意的表達(dá)。在傳統(tǒng)戲曲舞臺(tái)上雖然有一些雕飾的元素,但從意義上來說并不表達(dá)什么,這種空白似乎也給舞美設(shè)計(jì)留有一種表達(dá)的余地,可以用新的內(nèi)容填補(bǔ)上去,形成我們今天的表達(dá)。
伊沃·凡·霍夫?qū)а莸摹读_馬悲劇》中,演區(qū)和觀眾區(qū)是不受限制的,觀眾可以選擇坐在演區(qū)內(nèi),甚至可以自由進(jìn)出,去小賣部買熱狗和咖啡。舞臺(tái)被設(shè)計(jì)成了一個(gè)政治論壇,人們不斷地討論、說話,中間沒有暫停時(shí)間,讓大門保持開放,觀眾成為表演空間的背景,甚至是其中一個(gè)表現(xiàn)元素。現(xiàn)場設(shè)置了很多攝影機(jī)把實(shí)況投到演區(qū)的很多個(gè)電視屏幕上,這些電視屏幕代表著媒體和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舞美設(shè)計(jì)在處理“死亡”的時(shí)候,也用了一種充滿意象的表達(dá)方式。當(dāng)劇中每個(gè)角色死亡之后,都會(huì)躺在一個(gè)平臺(tái)上,通過一個(gè)軌道慢慢移到舞臺(tái)后方,這個(gè)過程也用了高角度的拍攝再投到屏幕上。眾所周知,在舞臺(tái)上處理“死亡”并不是處理真實(shí)的死亡,而是涉及一個(gè)死亡的意識(shí)。
總之,舞美設(shè)計(jì)需要為戲劇空間創(chuàng)造出詩性。一個(gè)優(yōu)秀的舞臺(tái)設(shè)計(jì)師除了具有一定的繪畫基礎(chǔ)外,并需熟知和了解東西方各種文藝流派及其風(fēng)格。
(整理:潘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