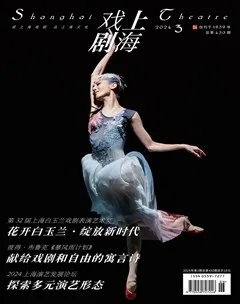劇場(chǎng)中的共時(shí)之旅
薛雪



5月1、2日,提奧多羅斯·特佐普羅斯的《等待戈多》亮相2024上海·靜安現(xiàn)代戲劇谷。薩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首次在中國(guó)上演是1986年,由上海戲劇學(xué)院的陳加林老師導(dǎo)演。在接下來(lái)的近40年中,孟京輝、林兆華、賴聲川等導(dǎo)演相繼在舞臺(tái)上呈現(xiàn)了他們對(duì)《等待戈多》的個(gè)性化解讀,體現(xiàn)出中國(guó)導(dǎo)演對(duì)于荒誕派戲劇以及對(duì)《等待戈多》的理解。
希臘導(dǎo)演提奧多羅斯·特佐普羅斯將這部作品搬上舞臺(tái)展現(xiàn)了一種與中國(guó)舞臺(tái)截然不同的演繹方式。在特佐普羅斯的引導(dǎo)下,觀眾與演員共同踏上了一場(chǎng)穿越時(shí)空的共時(shí)之旅。在90分鐘的表演中,觀眾與角色并肩走過(guò),共同體驗(yàn)著孤獨(dú)與絕望,在劇場(chǎng)中反思著生命的意義。這次演出不僅是對(duì)經(jīng)典戲劇的一次重新詮釋,也是一場(chǎng)情感上的觸動(dòng)和心靈的共鳴。
演出開(kāi)始前,扮演戈戈的演員不慎摔倒受傷,結(jié)果以頭部纏著紗布的形象出現(xiàn)在臺(tái)上,意外情況加深了角色本就具有的悲劇色彩。特佐普羅斯將他對(duì)古希臘悲劇的解讀方式應(yīng)用于《等待戈多》,為劇作帶來(lái)了新的表現(xiàn)形式。通過(guò)簡(jiǎn)約而富有象征意義的舞臺(tái)設(shè)計(jì)和獨(dú)特的表演風(fēng)格,在還原貝克特荒誕世界觀的同時(shí),給予了觀眾一種全新的體驗(yàn)方式,讓這部經(jīng)典劇作在當(dāng)代劇場(chǎng)中煥發(fā)出新的光彩。
《等待戈多》是塞繆爾·貝克特于20世紀(jì)40年代創(chuàng)作的一部?jī)赡粍。髌穱@兩個(gè)流浪漢在鄉(xiāng)間等待一位名為戈多的神秘人物展開(kāi),雖然表面上缺乏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故事或情節(jié),但卻深層探討了人類存在的荒誕性和不確定性。
在保留原作基本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上,本次演出通過(guò)對(duì)一些如“吃蘿卜、拉褲子、脫靴子”等原作中的笑鬧場(chǎng)面的刪減,更加突出了作品的悲劇性內(nèi)核。導(dǎo)演特佐普羅斯在舞臺(tái)設(shè)計(jì)上表現(xiàn)出對(duì)包豪斯風(fēng)格一如既往的喜愛(ài),即對(duì)規(guī)整的空間和幾何形狀造型的運(yùn)用。他在舞臺(tái)中心打造了一個(gè)由四塊矩形拼接而成的十字架表演區(qū)。這些板塊不僅構(gòu)成了舞臺(tái)的視覺(jué)焦點(diǎn),還在演出的過(guò)程中通過(guò)滑動(dòng),調(diào)整著表演空間的大小,起到交替顯現(xiàn)和隱藏演員的作用。而劇中至關(guān)重要的樹(shù)則被簡(jiǎn)化為一個(gè)小型的盆栽,放置在表演區(qū)前方的舞臺(tái)上,以極簡(jiǎn)的手法呈現(xiàn)象征意義,也讓戈戈和狄狄的上吊計(jì)劃顯得更加荒誕。
演出在防空警報(bào)的背景聲中拉開(kāi)帷幕,兩塊矩形緩緩上升,形成一個(gè)狹長(zhǎng)的表演區(qū),在這個(gè)宛如魚(yú)缸的逼仄空間內(nèi),主角戈戈和狄狄躺在暗黃色的燈光下,嬉笑聊天。背景音樂(lè)的哀婉與他們的笑聲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笑,沒(méi)有營(yíng)造出歡樂(lè)的氛圍,反而讓一股悲傷瞬時(shí)充滿了劇場(chǎng)。音樂(lè)全程伴隨著該版演出,時(shí)而是純音樂(lè)的樂(lè)器演奏,時(shí)而是教堂唱詩(shī)班的歌聲,這些音樂(lè)以其具有的悠揚(yáng)凄婉,為整個(gè)演出增添了沉重的情緒色彩。
在長(zhǎng)達(dá)15分鐘的時(shí)間里,兩位演員頭靠頭,復(fù)述著原作的臺(tái)詞,將漫長(zhǎng)且單調(diào)的等待具象化。隨后,演區(qū)上方的兩個(gè)相并的矩形逐漸分開(kāi),為演員提供了站立的空間。波卓從后緩步走出,而幸運(yùn)兒則緩緩從下方升起。他在狹窄的矩形空間里不斷來(lái)回踱步,小聲自言自語(yǔ),機(jī)械的行為營(yíng)造出了一種焦躁的緊張氣氛。特佐普羅斯戲劇美學(xué)中強(qiáng)調(diào)的“癲狂”元素,在此刻開(kāi)始萌發(fā)。
在特佐普羅斯看來(lái),現(xiàn)代高度技術(shù)化的社會(huì)讓人們已經(jīng)失去了自然表達(dá)的能力。他在格洛托夫斯基的“神圣的演員”理論和阿爾托殘酷戲劇中的“必要”原則的影響下,發(fā)展了一種新的演員訓(xùn)練方法,旨在讓演員的身體展現(xiàn)出“癲狂”的狀態(tài),達(dá)到像酒神信徒那樣的自由和解放,揭示出演員最深層的自我。這種訓(xùn)練不僅是技術(shù)上的突破,也是精神和情感的深度探索。
而幸運(yùn)兒的表現(xiàn)便是這種訓(xùn)練方法的具體體現(xiàn)。當(dāng)他按照波卓的指示,從十字架形的表演區(qū)走到舞臺(tái)前端跳舞時(shí),長(zhǎng)約一分半的舞蹈表演成就了一段挑戰(zhàn)常規(guī)的藝術(shù)表達(dá)。顫抖的身體和缺乏美感的動(dòng)作讓觀眾難以相信這是一段“舞蹈”,那近乎癲狂的聲音和身體動(dòng)作,使得原本就顯得無(wú)意義的臺(tái)詞在這一刻顯得更加微不足道。表演成功地將痛苦轉(zhuǎn)化為了身體的語(yǔ)言,將不安、焦慮和痛苦傳遞給了觀眾,使我們與臺(tái)上的角色一同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劇烈的情緒波動(dòng)。
舞蹈結(jié)束,幸運(yùn)兒與波卓離去,送信的小男孩隨即出現(xiàn)在表演區(qū)上方。我們似乎很難將眼前這個(gè)套著巨大十字架的高大男演員,與“小男孩”的形象相結(jié)合。他更像是一個(gè)被上帝奪走了靈魂的木偶,一個(gè)被命運(yùn)無(wú)情束縛的無(wú)辜者。他宣布了“戈多今天不會(huì)來(lái)了”的消息,回答了戈戈和狄狄的問(wèn)題,語(yǔ)氣機(jī)械而疲憊,但每一個(gè)字都是他用盡全力噴發(fā)而出的,通過(guò)演員身體的極限表達(dá),劇作中的壓抑、絕望得以直觀化的展現(xiàn)。于是,戈多的物理缺席轉(zhuǎn)化為了觀眾情感上的一種深刻體驗(yàn),使這場(chǎng)等待超越了時(shí)間和空間的限制,觸及了每個(gè)人內(nèi)心的某個(gè)角落。
在《等待戈多》中,臺(tái)詞通常不承載直接的意義,常常顯得凌亂甚至無(wú)意義。然而在特佐普羅斯導(dǎo)演的這版演出中,臺(tái)詞的運(yùn)用卻深化了劇作的情感深度。這種深化并非源自臺(tái)詞內(nèi)容本身,而是來(lái)源于演員們?nèi)绾卫米约旱纳眢w去發(fā)出這些臺(tái)詞。臺(tái)詞成為了演員身體奮斗與掙扎的直接產(chǎn)物,他們似乎是在能量耗盡的邊緣,依然努力擠壓出每一分力量,以聲音表達(dá)內(nèi)心的情感與想法。這樣的表演方式讓觀眾不只是被動(dòng)地接受信息,而是活躍地感受到了演員們的能量爆發(fā)和情感傳遞。那種從身體深處掙扎而出的言語(yǔ),讓我們?cè)诳此破匠5呐_(tái)詞中感受到了震撼的力量。
在第二幕開(kāi)啟前,防空警報(bào)和轟炸聲的設(shè)計(jì)不僅增強(qiáng)了劇場(chǎng)的沉浸感,還引入了戰(zhàn)爭(zhēng)的背景,一排帶著血的尖刀緩緩在十字架演區(qū)前落下,使得演出的氛圍變得更加壓抑和緊張。
熟悉《等待戈多》的觀眾都清楚,第二幕基本是對(duì)第一幕的重復(fù),如同演出一開(kāi)始那樣,戈戈和狄狄依舊躺在那個(gè)魚(yú)缸狀的表演空間內(nèi)。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不再是頭對(duì)頭,而是腳對(duì)腳,時(shí)間的循環(huán)感和角色之間的孤獨(dú)與絕望得以展現(xiàn)。當(dāng)波卓和幸運(yùn)兒再次登場(chǎng)時(shí),他們與戈戈和狄狄的對(duì)立站位形成了一個(gè)十字架形狀。在筆者看來(lái),十字架在這里不僅是宗教的象征,更深層地指向了人生的苦難與痛苦的普遍性,昭示了每個(gè)人在面對(duì)命運(yùn)時(shí)的無(wú)助與挑戰(zhàn)。
人物置于十字架形狀的站位,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他們共同面臨的人生困境和精神掙扎。伴隨著波卓一聲聲的“救命”,響起了“咚咚”的心跳聲,劇場(chǎng)在此刻不再是一個(gè)觀看戲劇的地方,而變成了一個(gè)體驗(yàn)共鳴和深層情感沖擊的空間。它讓觀眾不僅是外部的觀察者,而是讓他們成為這場(chǎng)精神和情感旅程的一部分,深刻體驗(yàn)到《等待戈多》中的主題——等待、絕望與對(duì)自我的探索。這樣的演出不僅僅是視覺(jué)和聽(tīng)覺(jué)的盛宴,更是對(duì)觀眾內(nèi)心世界的一次深刻觸動(dòng)。
要使《等待戈多》的演出引人入勝并非易事,因?yàn)樵搫”举|(zhì)上缺乏具體的情節(jié),主要展示的是兩個(gè)角色在同一場(chǎng)景中的對(duì)話和等待。但特佐普羅斯做到了,在這部缺乏情節(jié)的劇作中,他憑借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將孤獨(dú)與絕望這一主題展現(xiàn)得深入人心。
此外,他的成功還體現(xiàn)在創(chuàng)造了一種共時(shí)性的體驗(yàn)上。在常規(guī)的劇場(chǎng)演出中,通常是演員演出,觀眾觀看,兩者角色分明。然而,在特佐普羅斯的《等待戈多》中,觀眾不僅僅是被動(dòng)的接收者,更是被帶入到劇中,與演員一同體驗(yàn)情感的起伏和哲學(xué)的思考。這種共時(shí)性體驗(yàn)的創(chuàng)造是特佐普羅斯對(duì)傳統(tǒng)戲劇形式的一種革新。在他的演繹下,觀眾不再是遠(yuǎn)離舞臺(tái)的旁觀者,而是被巨大的沉浸感環(huán)繞,成為了演出的一部分。哀婉音樂(lè)和“咚咚”的心跳聲總是能夠在關(guān)鍵時(shí)刻響起,加劇了劇場(chǎng)內(nèi)的或壓抑或緊張的氛圍,使觀眾的情緒與劇中人物的情緒同步升降。這種全方位的感官和情感的共振,不僅讓《等待戈多》的演出不同于傳統(tǒng)劇場(chǎng)的體驗(yàn),也使得這部劇作在探討人類存在的主題上更加深刻。
在科技飛速進(jìn)步、娛樂(lè)選擇多樣化的今天,我們?yōu)楹稳孕钁騽。刻刈羝樟_斯的《等待戈多》給出了完美的回答。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