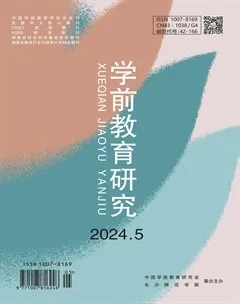兒童主體能動性概念溯源及其理論進展
王友緣 陳夢瑤
[摘 要] 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在國際范圍內獲得廣泛關注,其概念正在被重新審視。主體能動性存在內在的緊張關系,即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個人的能動性與社會的能動性的二元對立。這一緊張關系被兒童主體能動性理論直接移植,并在新童年社會學與《兒童權利公約》的推動下進一步加劇。在調和及其超越這一緊張關系的背景下,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呈現四種不同的理論進路:自由主義范式、社會文化范式、后結構主義范式與實用主義范式。四種范式的理論解釋力及在經驗研究中的影響各有不同。對于我國學者來說,在開展相關研究的過程中,不僅要把握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核心論爭與前沿趨勢,參與到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學術建構中,也要助力打破全球北方的主導局面,發出中國學術的聲音。
[關鍵詞] 兒童;主體能動性;童年研究;新童年社會學
兒童的主體能動性(childrens agency)是童年研究的關鍵概念之一。[1]隨著兒童觀的轉變與兒童地位的提升,兒童是有能力的社會能動者這一觀念受到廣泛認可。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著名學者大衛·奧斯維爾(David Oswell)指出,20世紀是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時代。[2]兒童具有主體能動性,已經成為習以為常、無需檢視的學術話語與日常用語,而在實踐層面,并非所有的兒童都有成為決定和影響自身生活的能動者的機會。[3]近年來,關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研究大量涌現。新童年社會學的著名學者艾倫·普勞特(Alan Prout)曾于2000年指出,“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概念還遠遠沒有被理論化。[4]十一年后,凱莉·瓦倫丁(Kylie Valentine)同樣指出,“在童年研究中主體能動性很少被界定或理論化”。[5]如今,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相關研究獲得長足發展,不少學者試圖重構主體能動性的概念。但由于主體能動性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與曖昧性,以及不同理論流派的影響,關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探討仍然處于紛繁雜陳的狀態。不同學者對于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有不同的理解,在跨學科研究,特別是童年研究中,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概念也在不同的范式和層面上被使用。本研究旨在厘清兒童主體能動性概念的來源及其不同理論進路,以期進一步推動兒童主體能動性理論在童年研究與童年社會學研究中的核心作用。
一、主體能動性內在的緊張關系
主體能動性是一個動態的、高度爭論的概念。[6]通常,主體能動性意指有意采取行動的能力,能動性與意向性相聯系,從而表示某種意圖或意識,或至少是一種形式的實踐反身性。[7]主體能動性概念有兩大起源,其一可追溯至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起源,其二來源于社會科學傳統。啟蒙運動繼承了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傳統,以“理性主義”為指導思想,進一步肯定了個人作為“自由人”能夠為自己和社會做出理性選擇的獨特地位。可以說,哲學視角下的主體能動性概念相對更加關注個體本身的能動性,這成為我們后面要討論的西方自由主義的主體能動性的由來。社會學是主體能動性概念發展的另一重要沃土。社會學家高度肯定主體能動性的概念,認為能動性的發揮影響著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然而,究竟應該強調社會結構對于個體行動的決定作用還是強調個體以其能動性借助結構在行動過程中形塑社會的作用?這成為社會學中經典的二元對立的問題。主體能動性的哲學起源與社會學起源共同推動了主體能動性這一概念內在固有的緊張關系。特別是“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個人能動性與集體能動性”之間的二元關系尤為突出。
(一)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
主體能動性和社會結構的二元對立植根于現代社會學理論的二元對立中。[8]在現代社會學理論下,社會結構隸屬“宏觀”的社會范疇和過程,代表了某種堅實而持久的東西,可以解釋相對恒定或相似的人類行為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連續性、延續性、復制性和分布性,而能動性則指向“微觀”的社會范疇和過程,是指某人或某物具有行動和取得成就的能力或潛力,這意味著,主體可以用變革性或創造性的方式對自身及其所處環境產生因果影響,抑或抵抗來自外部的某種影響。[9]因而能動性代表著動態的、創造性的行動時刻。結構性的相對恒定和延續復制與能動性的動態多樣和創造變革形成鮮明對比,二者的對立關系由此而生,長久以來,社會結構因其主導性地位被視為阻礙和弱化個體能動性的絕對存在。
(二)個人的能動性與社會的能動性
宏觀與微觀、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一直充斥著整個社會學研究,關于主體能動性的來源也存在外部主義者和內部主義者之爭。[10]一方面,以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及新童年社會學的一些理論家為代表,他們認為主體能動性是個體的潛力或能力,可以說是存在于個體內部的某種特質。盡管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總體來看,這些理論家非常重視行動者本身的作用,因此其觀點可被概括為“個人的能動性”。另外一種思路則強調能動性產生于社會聯系中,各類組織、結構資源等要素共同架構了能動性。他們主張能動性并非實體的,[11]而是分布在網絡中的,人類只是特定網絡中的某一節點,因此能動性不應也不能僅局限在個人身上,[12]反而視角應聚焦在產生能動性的社會聯系或社會網絡中。這類觀點被稱為“社會的能動性”或“集體的能動性”。
“個人的能動性”與“社會的能動性”的主要分歧在于其側重點的不一致,“個人的能動性”傾向于分析行動者本身的作用,而“社會的能動性”則更加關注個體所處的結構環境。簡而言之,“個人的能動性”的支持者認為能動性更多的是一種個人屬性,而非社會屬性,[13]能動者可以發起具有個人意義的個人行為。“社會的能動性”的支持者對此進行了強烈批判,他們認為“個人的能動性”的觀點忽略了主體能動性的社會層面,即忽略了主體能動性是依賴并受制于社會結構的。此外,他們批判其夸大了人作為行動者的作用,并聲稱社會制度、條件、系統和意識形態不會因個人思維和行為的零碎變化而改變。[14]最后,他們主張“社會的能動性”不是以基本生物屬性來定義的,而是集體性、聯系性的。從這個角度出發,一個人(或事物)“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所處的位置,換言之,當某些非生命物體在其所處網絡中的位置足夠重要時,它也可以發揮出能動性。[15]
可以說,主體能動性內在的緊張關系主導著主體能動性理論的發展,在后文兒童主體能動性主要理論進路的討論中將看到這一影響。以往關于主體能動性的研究很少會涉及兒童,兒童通常被看作是未完成的成人,需要被改造為完整的社會成員,是缺乏主體能動性的。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提出,使得兒童的地位與能力獲得廣泛關注。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早期興起并非是在克服這一概念內在緊張關系的基礎上實現的,相反,其進一步加劇了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個人的能動性與社會的能動性的二元對立。
二、兒童主體能動性溯源
兒童主體能動性得到明確關注,得益于20世紀末理論與實踐層面對于兒童觀念及兒童權利的推動,一是新童年社會學的興起及發展,二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在世界范圍內的簽署。
(一)新童年社會學:兒童是社會能動者
20世紀80年代新童年社會學興起,新童年社會學的旗手艾莉森·詹姆斯(Allison James)和普勞特在新童年社會學的重要著作《童年的建構與再構:當代童年社會學問題》(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一書的前言中提及:“兒童能夠積極參與自身與所處社會生活的建構,不能再被簡單地看作是被社會結構決定的被動主體。”[16]艾莉森·詹姆斯與阿德里安·詹姆斯(Adrian L. James)直接指出應該把兒童看作社會能動者(social agent),[17]2012年出版的《童年研究中的關鍵概念》(Key concepts in childhood studies)也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兒童的主體能動性,并把兒童的主體能動性界定為“個體獨立行動的能力”,[18]指出“兒童可以被視為獨立的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①的觀點是發展兒童和青年研究新范式的核心”。[19]由此,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成為新童年社會學的關鍵概念。兒童被看作是能動地建構自己的童年與社會生活的社會能動者成為新童年社會學聲名鵲起的重要論述,也是新童年社會學對于童年研究的重要貢獻。
早期新童年社會學強烈批判現代社會中童年的結構和社會文化狀況阻礙并扭曲了兒童行動創造的基本能力,[20]在其框架下,兒童的主體能動性被看作兒童發起行動的能力或潛力,這一主張直接移植自現代社會學理論中主體能動性的二元矛盾,過于強調兒童自身的能力與內在潛力,忽視了其所身處的社會結構的作用,進一步加劇了兒童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
(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簽署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是兒童主體能動性概念的另一大起源。[21]1989年通過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看待;兒童特別應有機會在影響到兒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以符合國家法律的訴訟規則的方式,直接通過代表或適當機構陳述意見。同樣,第13條和第5條分別側重于兒童的陳詞權和根據其“發展的能力”獲得適當指導的權利,承認兒童有能力在影響其生活的事項上做出決定,同時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的原則對承認兒童的個人權利至關重要。《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主體能動性的肯定和對兒童權利的倡導推動了將兒童視為積極能動、具有權利的主體的觀念的傳播,一些學者將權利和參與視為兒童體現主體能動性的標準。[22]
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話語的流行,特別是《兒童權利公約》的簽署,兒童的主體權利、兒童參與逐漸獲得重視,兒童主體能動性概念的政治意涵也越發凸顯。瓦倫丁明確指出,主體能動性的概念對于兒童的權利與兒童參與事業尤為重要。[23]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日益被視為是一種能把兒童從結構約束中解放出來的力量,并且是一種應該更充分地承認、重視和鼓勵的東西,從而具有天然的內在倫理性。這一趨勢將兒童的主體能動性看作為兒童內在的積極的力量,忽略了社會結構及社會關系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個人的能動性與社會的能動性的緊張關系。
在早期新童年社會學以及《兒童權利公約》的推動下,作為為兒童賦權、個人自主和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全球話語下的主體能動性的概念被廣泛接受,兒童內在的力量與能力進一步凸顯,這使得主體能動性內在的緊張關系進一步加劇,而克服這一內在固有的緊張關系則成為后續諸多兒童主體能動性理論流派發展的使命。
三、兒童主體能動性的主要理論進路及其發展
基于兒童主體能動性固有的緊張關系,產生了兩個關鍵問題:其一,如何理解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本體論特征,即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是內在于兒童的個人屬性還是外在于兒童的結構特征?其二,如何看待兒童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即兒童的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是二元對立的關系還是相互依賴的關系?圍繞這兩個關鍵問題,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理論呈現出不同的理論進路,試圖調和或超越其內在的緊張關系。本部分主要聚焦童年研究中常用的主體能動性理論,圍繞關于兒童主體能動性本體論特征及其與社會結構關系的不同觀點,辨析不同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理論進路,并分析相關理論進路下實證研究的特點,以期增進對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理論與實踐的認識。
(一)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
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起源于啟蒙運動的哲學傳統,如前所述,該傳統孕育了強調個體作為“自由人”能夠為自己和社會做出理性選擇的概念,將兒童定位為理性、自主和有能力的人。主體能動性被看作是個體相對穩定的某種基本特征或原始品質,[24]它在生命過程中不斷延伸和變化。在本體論角度,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被認為具有本質主義取向,強調主體能動性是內在于兒童的屬性,即兒童的某種能力。[25]
因此童年研究涌現出大量關于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②背景下求證兒童在家庭、教育機構、公共空間中具有主體能動性的經驗文章,強調兒童具有某種程度的意識、策略與能力,來證明兒童擁有主體能動性,應重視兒童的經驗世界。兒童被看作積極的社會能動者,這一顛覆性的觀念讓研究者重新看待兒童的力量,也促進了研究視角的轉換。以家庭研究領域為例,傳統的家庭研究通常把兒童看作家庭變故、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把兒童看作具有反思性的社會能動者的觀點使得研究者紛紛關注到兒童在家庭變故、家庭暴力中的能動性。在分析兒童所經歷的家庭暴力及其應對家庭暴力的方式時,安妮塔·莫里斯(Anita Morris)引入了一個“兒童能動者模型”,該模型為兒童建立了一個安全的關系網絡,并展示了兒童作為思考者、觀察者、行動者和家庭中積極主動的變革推動者的角色。[26]
與此同時,主體能動性的概念為促進兒童權利,特別是與兒童利益密切相關的參與權、公民權和選擇權提供了基礎。在此背景下,強調兒童權利、兒童參與、兒童保護的研究開始關注兒童的主體能動性。在傳統的兒童福利和兒童保護研究中,兒童通常被描述為“沉默的證人”、“目擊者”、一群“暴露于”暴力的人,僅被視作研究的對象,[27]作為受害者的未成年人往往被剝奪了發言權和能動性。在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框架下,研究者開始關注兒童的公民身份、兒童權利及兒童的觀點。如關注兒童對于福利的看法、[28]對童工的意見,[29]歡迎兒童參與到福利政策的制定中,[30]在定義、衡量、評估、決策以及防止兒童虐待方面充分考慮兒童的視角和主張。[31]
對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特別是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的強調、宣傳與慶祝不僅有助于兒童研究視角的轉變,也有助于為兒童賦權的解放性事業。然而,在此視角下,主體能動性被視為兒童普遍具有的動態的抵抗或突破外部結構的創造性行動能力,進一步加劇了能動性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有學者指出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有將兒童行為浪漫化的危險,使得我們更難理解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矛盾性與復雜性。[32]
來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經驗研究對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框架提出了挑戰,質疑作為普遍特征的主體能動性的概念大多基于全球北方的情境脈絡,忽視了全球南方的兒童及其童年生活。全球南方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主要聚焦困境兒童,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兒童主體能動性的限制性環境上,否認全球北方框架下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普遍性與獨立性,強調關系性特質,認為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發揮與其所處的環境、制度文化及政策支持有密切的關聯。[33][34]全球南方的經驗研究挑戰了作為普遍的獨立于社會結構的主體能動性的概念。弗洛里安·埃塞爾(Florian Esser)等人組織編寫的著作《主體能動性與童年的再概念化——童年研究的新觀點》(Reconceptualising agency and childhood: new perspectives in childhood studies)明確批判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是一種基于去歷史、去社會化、以個人為中心的行動理念。[35]自由主義范式在兒童主體能動性理論研究中的熱潮已經褪去了,但在經驗研究中仍有不少研究者堅持該框架,一些研究者開始在批判自由主義范式的基礎上嘗試新的突破方向。
(二)社會文化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
瓦倫丁于2011年發表《論兒童的主體能動性》[36]一文,成為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社會文化范式的重要開拓者。瓦倫丁系統批判了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理論,批判其把兒童的能動性看作與政治、社會無關的兒童個體的內在特征,對兒童的主體地位與權利過度浪漫化。瓦倫丁認為,兒童的能動性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的影響,并反映了他們所生活世界的等級性,因此,她提出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社會模式,強調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本質上具有社會嵌入性,在借鑒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提請注意兒童與成人以及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之間主體能動性的差異。
社會文化范式強調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涉及主體形成過程中的內在精神和社會力量之間的關系,以及主體能動性對維護社會規范和等級制度的重要性。[37]其理論基礎源自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維果茨基將參與文化實踐作為學習和發展的動力。因此,社會文化理論非常強調如何通過文化工具(如語言)來調節個人的行為。換言之,該理論強調,主體能動性從來不會在真空中發生;相反,主體能動性是由他者、文化藝術品和行動對象創造并受其約束的。[38]就其本體論特征而言,在社會文化范式下,兒童的主體能動性并非兒童的內在屬性,其本質是社會性的,是外部社會力量的產物。
社會文化理論對外在結構資源的強調使得它被認為是集體能動性的推崇者,部分學者開始批判這一理論缺乏對能動者自身主體性的關注。為回應這一批判,社會文化理論開始關注個體本身的主體性,相應出現了一種新的分析觀點——以主體為中心的社會文化視角(a subject?鄄centered socio?鄄cultural perspective)。[39]這種視角認為個體的能動性包含個人目的,是在社會環境中行使并發揮作用的,同時又受到這些社會文化和物質環境的制約。因此,盡管個人與社會在分析上來說是獨立的,但實際上二者是相互構成的。該視角十分肯定個體的作用,認為個人的身份、經歷、理想、動機、經驗、知識、能力、興趣和目標等,都對其能動性的表現和發揮起到重要作用。每個人都是具有不同經歷和能力的獨特生命體,因此不能將其能動性僅僅看作是結構環境的架構,而是要關注每一個個體與世界具體的實際聯系,了解他們在自己生活的范圍內如何協商發揮自身的能動性。受該視角影響,兒童研究也開始關注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意識(childrens sense of agency),[40]兒童自身的主體能動性經驗成為此類研究的焦點。
就實證研究而言,社會文化范式是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主流理論范式。在社會文化范式下,研究主要聚焦于挖掘不同情境背景下兒童能動性的多元發揮方式、多種因素如何影響兒童的主體能動性以及兒童主體能動性的類型等。有研究基于社會文化范式,探究兒童主體能動性的類型,將兒童主體能動性的表現方式區分為順從性和適應性能動性(agency of compliance and accommodation)與抵抗性能動性(agency as resistance)。[41]“順從性和適應性能動性”是指個體表現出的行為與特定環境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規范、價值觀相符合。在學校環境中,這種類型的能動性通常出現在“好孩子”和“聰明孩子”身上,他們通過對學校規則的高度遵守以及特意表現出教師認可的行為等行動來展示自身的歸順。“抵抗性能動性”是指兒童在面臨社會期望與個人利益和欲望之間的沖突時,選擇拒絕參與、逃避甚至顛覆固有規則的能動性。在學校環境中,這種類型的能動性通常與學業水平不太理想的孩子相聯系。[42]
社會文化理論極具批判性潛力,它批判將主體能動性當作兒童內部的固有屬性,強調社會文化對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的嵌入、調節和影響,然而,這一理論仍然沒有徹底克服個體與社會、主體能動者與社會結構的二元對立,在一定程度上它低估了兒童主體能動性的自主性,有將兒童的主體能動性還原為社會文化的危險。
(三)后結構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
在童年研究中,后結構主義往往被視為社會文化方法的進一步延伸與發展。通常意義上,后結構主義,一方面指向超越一個中心的、預先給定的人類主體的概念,另一方面指向超越結構主義的立場,即超越主體性是由結構(語言)構成的這一立場。因此,它既要避免主體在結構主義中的徹底消失,又要避免啟蒙運動中超越理性的個體。后結構主義范式是當下兒童主體能動性勢頭最為強勁的理論范式。
后結構主義理論與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吉爾· 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和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等學者密切相關。特別是福柯的理論在兒童研究中影響較大。福柯通常被看作是權力理論家,在其重要著作《規訓與懲罰》中,兒童的日常生活與日常實踐被看作是微觀權力行使的典型實例。然而,眾所周知,福柯對將權力分析作為一種現象并不感興趣,而是對人類成為主體的過程感興趣,雖然前者在兒童研究中的影響力更大。福柯的“主體化”(subjectivation)是與“話語”“知識”和“權力”分不開的,主體化在話語的形成和權力關系技術的運作中得以形成,話語和權力成了“主體”的塑造者。如果我們將主體能動性理解為一種微觀權力,那么,根據福柯的觀點,它可以被理解為影響其他行動的行動。這種行動沒有任何內在的倫理價值。權力倫理取決于權力是如何被行使的,權力是通過何種主體、何種關系、何種手段和何種技術來行使的。權力可能產生解放、統治、顛覆、殖民、說服、參與、合作、加劇或減弱沖突等效果。[43]在這個理論視角下,與自由主義范式相反,兒童的主體能動性并不具有天然的內在倫理性,關鍵在于考察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是通過何種主體、何種關系、何種技術、在哪里、經過什么過程產生的。
因此,在后結構理論視野下,特別是在福柯的理論影響下,不少研究者轉向關注兒童在其所處的異質性元素(如話語、體制、人、物體、動物、科技等)構成的關系網絡中如何發揮能動性。其中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鄄Network Theory)近年來在兒童主體能動性的領域得到了廣泛關注。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社會是許多異質性事物之間的聯系,并不存在實體性的社會,有的只是處于不斷發生、變化和消亡中的聯結,社會即是由行動者所構成的異質網絡。行動者有不同的類型,既可以是兒童或成人,也可以是諸如組織、藝術品和科技等非人類,他們共同存在于一張人與物共同作用的復雜的網絡中。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下,童年被看作是各種不同的、時而競爭、時而沖突的異質性秩序的集合體。兒童自身只是某種網絡中的特定節點,其作為節點的位置和重要與否也會隨著不同網絡的更迭而發生變化。兒童的主體能動性不再是發于其主體意識,反而是源自主體、身體、材料、環境和技術的分布式網絡。[44]因此在探討兒童是否擁有能動性時,首先需要關注他/她在具體網絡中的特定位置,當其所處位置重要至可將其看作行動者時,那么他/她便自然而然擁有了能動性。反之,倘若非生命物體可以擁有同等的重要地位,那么也可將其看作是具有能動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行動者—網絡理論并未將能動性看作是人特有的東西,也并未在人與非人的能動性之間做出界定與區分。
伯納德·普拉斯(Bernard Place)[45]在他關于重癥監護室兒童身體的研究中較早地應用了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視角。他提出“技術形態體”(technomorphic body)的概念,其中有不同的元素(如心臟、血壓、氧氣面罩和孵化器)集中在一起。這個技術形態體是護士和其他工作人員的操作對象。這就意味著技術設備成為兒童身體的一部分,進而成為兒童主體能動性的一部分。兒童則被視為是由特定的權力與知識制度構建起來的,“兒童這一部分”(child part)本身也是影響兒童生活的構成要素,兒童成為被賦予能力的集合體,既包括兒童這一生命體,也包括材料、技術等非生命體。這也就意味著兒童的能動性并非獨立的,而是在與其他行動者的關系中建構起來的。
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基礎上,關系性主體能動性的概念發展起來。前文提及的埃塞爾等人編著的《主體能動性與童年的再概念化——童年研究的新觀點》一書中,對關系性主體能動性進行了系統化闡述。他們明確反對把主體能動性看作是兒童所擁有的內在能力,并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旗幟鮮明地提出關系性主體能動性的概念,指出“主體能動性不是個體實體所固有的,這些實體本身和他們的能動性最初是在關系中產生的”。[46]這些關系從不形成一個剛性的結構,而是構建一個動態的、情景化的網絡。在此理論下,兒童并非獨立的社會能動者,他們的主體能動性往往嵌入在代際或同儕依賴中,他們所處社會的不同位置產生了不同的主體能動性。這一新的取向將引導實證研究關注在這個由人類和非人類參與者組成的異質網絡中兒童處于什么節點?兒童在不同的社會網絡位置會產生何種主體能動性?
在此理論視角下,兒童身處不同的性別、階層、年齡群體,他們的能動性也由此不同,這不僅構成兒童之間的差異,同樣地,兒童身處不同的社會關系中也可能具有不同的能動性。兒童處于某一網絡的某一節點時,擁有與之相應的身份、控制與影響能力,兒童可以在不同的網絡域(netdom)中進行轉換。[47]兒童能動性的展現依賴于不同的網絡、不同網絡中的轉換、網絡中的不同節點及其所擁有的身份與控制能力。由此,主體能動性被看作是社會系統的一種流動屬性,可以在人類行動者及其社會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關系中被發現。因此,關系能動性能夠超越兒童作為有能力的社會能動者與社會結構的二元關系問題,這就意味著并非去探討主體能動性的發揮是否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問題的關鍵在于分析擁有不同屬性的社會能動者處于何種社會網絡的節點,以及他們在不同的社會網絡節點中如何獲得能動性。
后結構主義視角突破了兒童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二元對立的固有框架,兒童的主體能動性不具有本體性特征,也不具有內在的倫理性,增進了對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的復雜性、差異性與動態性的理解。然而,這一理論對于兒童能動性的核心特質,即意圖與反身性的探究不足。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事實上徹底消解了兒童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將兒童等同于其他非人類物質。
(四)實用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
實用主義理論批判已有的主體能動性的研究忽視了時間維度,只聚焦于某一事件或個體當下的動向,而忽略了更廣闊的背景。因此,實用主義理論認為我們應當將關注點擴展至個體生活的整個背景,甚至是整個生命歷程。在此基礎上,主體能動性的生命歷程方法被提出。生命歷程方法一般與時間維度相聯系,即把時間作為主體能動性的某種結構要素進行分析,提倡主體能動性的視角應建立在終身和發展的原則之上。[48]以穆斯塔法·埃米爾拜爾(Mustafa Emirbayer)和安·米什(Ann Mische)的研究為代表,[49]他們認為在分析行動者的能動性時,倘若能將時間要素納入進來,將有助于更清晰全面地了解能動性的復雜性。行動者發起行動的結構背景從根本上來講就是關系性的,這種關系性又深深嵌入在時間流之中,因此社會行動者可以對時間采取多種重疊的排序方式,從而呈現出不同的能動性取向。在此基礎上,他們將主體能動性定義為行動者在時間關系的背景下,在應對變化的歷史形勢所帶來的問題時,通過習慣、想象和判斷的相互作用,在與結構的互動過程中既復制又改造這些結構。相應地,他們以時間為依據將主體能動性分解為三個組成要素,其中,“迭代”(iteration)面向過去,指行動者有選擇地重新激活過去的思維和行動模式,并將其納入常規活動中,從而保持對個體當前身份的復制或加強對現有社會秩序的維持。“投射”(projectivity)面向未來,指行動者根據其對未來的希望、恐懼和欲望等,突破并改變當下已有的結構或目前所接受的思想,是行動者對未來諸多行動軌跡的一種想象性生成。“實踐性評估”(practical evaluation)則立足于當下,指行動者在面臨一些不確定因素或者突如其來的困境時,有能力在各種可能的行動軌跡中做出基于實際的規范性判斷。埃米爾拜爾和米什將這一理論框架稱為“三和弦”理論,“和弦”旨在說明這三個要素并非完全獨立,而是相互交織、彼此互擁的形態,盡管在某一時間段內某種要素可能占據主導地位,但總體而言,社會能動者在任何特定時刻都同時面向過去、現在和未來。
新童年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人物威廉姆·科薩羅(William A. Cosara)較早地利用主體能動性的三和弦理論來進行兒童幻想游戲中集體能動性的研究,[50]展示了三和弦理論的理論解釋力。他在兒童的角色游戲、幻想游戲中區分出能動性展現的三種方式:迭代的能動性,指向兒童幻想游戲中對于過去獲得的共享知識的利用、拓展與轉化;投射的能動性,指向兒童在游戲中納入對于未來因素的考量;實踐性評估的能動性,指向兒童在面對沖突時立足當下的情境,綜合調動過去、現在、未來的因素予以協調。來自科薩羅的經驗研究向我們證明了三和弦理論分析視角的可操作性,為我們從時間維度解讀兒童日常活動中的主體能動性貢獻了智慧。
兒童主體能動性由于其本身的曖昧性與動態性,特別是被《兒童權利公約》所賦予的合法性與倫理性,使其在發展中獲得廣泛關注,促成了一系列的跨學科研究,同時也充斥著理論論爭,形成了充滿活力與張力的理論空間。就其本體論特征而言,自由主義范式將兒童的主體能動性看作是兒童的內在屬性,具有內在的倫理性,被稱作本質主義取向,這一取向招致了激烈的批判,但目前仍有大量經驗研究采取這一框架。社會文化范式、后結構主義范式均拒斥這一主體能動性的本質主義取向的框架,前者將主體能動性看作兒童與社會文化、社會資源及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特別強調社會結構的作用;后者將主體能動性看作是社會系統的一種流動屬性,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是借由其所處的社會網絡節點及其與其他人類行動者或非人類行動者的相互關系建構起來的,將兒童等同于其他非人類行動者,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兒童的主體地位。實用主義范式下的兒童主體能動性,特別是時間取向的主體能動性理論,則在承認兒童主體能動性關系性的基礎上加上了時間維度,深化了對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思考。
就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關系而言,除卻自由主義范式,其他三種范式都明確反對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二元對立傳統,均以不同方式嘗試超越或部分超越主體與結構、個人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就四種范式的理論解釋力與對經驗研究的影響而言,自由主義范式的理論解釋力已日漸式微,其分析性潛力不足,沒有提出具有解釋力的概念與框架,對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的內部結構與動態發展缺乏解釋力,但在經驗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社會文化范式、后結構主義范式及實用主義范式具有較強的理論解釋力,對于經驗研究的影響則各自不同。社會文化范式得到了明確的關注與應用,可看作經驗研究中主流的理論框架。后結構主義范式在理論層面上的成果非常豐富,但在實踐研究中由于其理論的可操作性不強,雖然得到了關注與運用,但還未成為主流范式。實用主義范式在實踐研究中得到部分研究者的關注與運用。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四種理論范式并非涇渭分明、不相融合的,有些學者會綜合運用這些范式進行兒童主體能動性的探究。如在一項對于學前兒童能動性的研究中,即將社會文化范式與自由主義范式結合起來運用,將主體能動性看作是個體的一種行動潛能,這種潛能并非個體的內在能力,而是個體在既定的資源和環境限制下通過社會互動創造意義、采取行動、協商地位、重塑世界的能力。[51]
四、中國背景下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可能方向
我國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研究較為鮮見,一方面為對西方童年研究、兒童研究中涉及兒童主體能動性的引介與討論,[52][53]一方面為基于中國本土情境的實證探索,旨在揭示兒童在同伴文化與幼兒園生活中的能動性經驗。[54][55]我國兒童主動性研究雖處于起步階段,但也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間。在開展兒童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不僅要把握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核心論爭與前沿趨勢,參與到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學術建構中,也要助力打破全球北方的主導局面,發出中國學術的聲音。
(一)探究兒童主體能動性在中國背景下的多維性、復雜性與動態性,建構更具解釋力的本土理論框架
已有關于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理論框架大多基于西方的情境背景,或對實證研究關注不足,或解釋力不足,難以回應因中國情境下的具體問題。因此,關于兒童主體能動性更深層次、更具解釋力的本土理論框架還需探索。此外,由于兒童身處環境與關系的復雜性以及兒童本身的特殊性與發展性,因此,研究者需要關注兒童主體能動性產生的多維性、復雜性與動態性,關注中國兒童在不同場域下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發揮方式及限度,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下兒童主體能動性的共性與差異,不同發展階段兒童主體能動性的變化等,這些都將是未來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的努力方向。
(二)深化經驗性研究,挖掘兒童發揮主體能動性的深層機制
兒童具有主體能動性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但由于兒童主體能動性這一概念目前仍未得到充分理論化,現有實證研究依舊停留在發現和描述的層面,兒童主體能動性也因此獲得了一定的關注與重視,但卻被當作是孩子們固有的、以前被忽視的特質。本質主義取向的兒童主體能動性框架仍然在實證研究中頗有市場。這種取向忽略了兒童主體能動性內部與外部的復雜性和兒童發揮能動性的深層機制,如在兒童的日常生活中,何種類型的能動性可以得到支持?何種又往往被抑制?兒童為何只在某些情況下去實踐能動性,而其他情況則不會?兒童、成人、無生命的非人類參與者又如何利用自身所處的異質社會網絡位置生成能動性……對能動性的觀察描述應是分析兒童主體能動性的起點,而非終點,[56]在更深入的經驗性研究中關注兒童發揮主體能動性的深層機制,特別是在后結構主義范式下如何捕捉兒童的主體能動性應成為未來研究的著力點。
(三)助力打破以全球北方為主的研究局面,發出中國學術的聲音
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研究已然形成以全球北方為主的局面,部分全球南方的系列研究正在實現突破。已有全球北方兒童主體能動性的研究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即便這一影響已受到廣泛的批判與關注。我國有其獨特的本土情境,集體主義、儒家文化、個體主義、消費主義的碰撞與融合,催生了獨一無二的中國情境、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對我國學者而言,在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相對滯后的背景下,挖掘并探究我國獨特境遇下兒童日常生活經驗中的主體能動性,揭示中國兒童實現主體能動性所面臨的獨特挑戰及機遇,呈現出中國背景下兒童主體能動性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這不僅有助于推動我國童年研究的本土探究,也將有助于打破全球北方在兒童主體能動性研究領域的主導局面,增進對于不同理論范式的經驗研究與理論反思,更有助于促進對于兒童主體能動性進行全面、深度、復雜、動態的研究與對話。
注釋:
①社會能動者(social agent)與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這兩個概念往往互換使用,Maylal等人對兩者進行了區分,社會行動者是指做某事的人,而能動者是與他人一起做某事的人,前者強調行為表現,后者則強調關系性,包括社會和文化再生產過程中的代際關系。見MAYALL, BERRY. Generation and gender: childhood studies and feminism[C]//Childhood in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2003. 除了英文原文引用的社會行動者,本文中統一用社會能動者。
②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用來區分世界各地區的術語,基于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發展標準,而不僅僅是地理位置。全球北方通常指的是經濟發達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主要位于北半球。這些國家往往擁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先進的基礎設施、技術能力,并在全球舞臺上具有較大的政治影響力。相反,全球南方一般指的是經濟發展較不發達的國家,通常位于南半球。這些地區可能面臨貧困、發展不足、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有限、政治不穩定等挑戰。在童年研究中,全球北方是指以歐洲中心主義為主導的世界觀與認識論,全球南方被視為非歐洲中心主義的、多樣化的理解、認識、經驗世界的方式,并通常被系統性地忽視和邊緣化。童年研究中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分類,旨在理解和研究兒童生活經歷、權利以及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時存在的全球不平等和差異,以揭示不同地區兒童面臨的獨特挑戰和機會,促進全球兒童權利的實現和兒童福祉的提升。當下也有學者提倡從超越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視角來理解兒童與童年。相關論述具體見 P?魪REZ MS, SAAVEDRA C M, HABASHI J. Rethinking global north onto?鄄epistemologies in childhood studies[J].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2017,7(2):79-83; IMOH, A.T.D., BOURDILLON, et al. Global childhoods beyond the north?鄄south divide[M]. Springer,2018.
參考文獻:
[1][18][19]JAME A, JAMES A L. Key concepts in childhood studies[M]. SAGE,2012:4,3,4.
[2]OSWELL D. The agency of children: from family to global human right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
[3]HART C S, BRANDO N. A capability approach to childrens well?鄄being, agency and participatory rights in educ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18,53(3):293-309.
[4]PROUT A. Childhood bodies: construction, agency and hybridity[C]//The body, childhood and socie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2000:16.
[5]VALENTINE K. Accounting for agency[J]. Children & Society,2011,25(5):347-358.
[6][35][46]ESSER F, BAADER M S, BETZ T, et al. Reconceptualising agency and childhood: an introduction[C]//Reconceptualising agency and childhood: new perspectives in childhood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16:12,6,9.
[7]AHEARN L M. Language and agenc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1,30(1):109-137.
[8]JAMES A L. Competition or integration? The next step in childhood studies?[J]. Childhood, 2010,17(4):485-499.
[9]SZTOMPKA P. Evolving focus on human agen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M]//Agency and structure: Reorienting social theory. Routledge,2014:25-60.
[10]SUGARMAN J, SOKOL B. Human agency and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sketch[J]. New Ideas in Psychology,2012,30(1):1-14.
[11][15][24]RAITHELHUBER E. Extending agency: the merit of relational approaches for childhood studies[M]//Reconceptualising agency and childhoo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16:89,97,94-95.
[12]SAX W S. Agency[C]//Theorizing rituals, volume 1: issues, topics, approaches, concepts. Brill, 2006:471-481.
[13][14]RATNER C. Agency and culture[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00,30(4):413-434.
[16]JAMES A, PROUT A.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0:4.
[17]JAMES A, JAMES A L. Constructing childhood: theory, policy and social practice[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4:23.
[20]JAMES A. Agency[C]//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hildhood stud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2009:34-45.
[21]ABEBE T. Reconceptualising childrens agency as continuum and interdependence[J]. Social Sciences,2019,8(3):81.
[22]STOECKLIN D. Theories of action in the field of child participation: in search of explicit frameworks[J]. Childhood,2013,20(4):443-457.
[23][36][37]VALENTINE K. Accounting for agency[J]. Children & Society,2011,25(5):347-358.
[25]GREENE S, NIXON E. Children as agents in their worlds: a psychological?鄄relational perspective [M]. Routledge,2020:39-45.
[26][27]MORRIS A, HUMPHREYS C, HEGARTY K. Beyond voice: conceptualizing childrens agency in domestic violence research through a dialogical le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20,19:1609406920958909.
[28]FATTORE T, MASON J, WATSON E. When children are asked about their well?鄄being: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guiding policy[J].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2009,2(1):57-77.
[29]OMOKHODION F O, OMOKHODION S I, ODUSOTE T O. Perceptions of child labour among working children in Ibadan, Nigeria[J]. Child Care Health & Development,2010,32(3):281-286.
[30]MASON J A. childrens standpoint: needs in out?鄄of?鄄home care[J]. Children & Society,2010,22(5):358-369.
[31]KOSHER H, BEN?鄄ARIEH A.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 new role for children in the field of child maltreatment[J]. Child Abuse & Neglect,2020,110:104429.
[32][43]GALLAGHER M. Rethinking childrens agency: power, assemblages, freedom and materiality[J].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2019,9(3):188-199.
[33]KLOCKER N. An example of “thin” agency: child domestic workers in Tanzania[C]//Global perspectives on rural childhood and youth. Routledge,2007:100-111.
[34]EVANS R. Sibling caringscapes: time?鄄space practices of caring within youth?鄄headed households in Tanzania and Uganda[J]. Geoforum,2012,43(4):824-835.
[38]FISHER R. Young writers construction of agency[J].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Literacy,2010,10(4):410-429.
[39]ETEL?魧PELTO A, V?魧H?魧SANTANEN K, H?魻KK?魧 P, et al. What is agency? Conceptualising professional agency at work[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2013,10:45-65.
[40]HILPP?魻 J, LIPPONEN L, KUMPULAINEN K, et al. Childrens sense of agency in preschool: a sociocultural investig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2017,24(2):157-171.
[41]KIRBY P. Childrens agency in the modern primary classroom[J]. Children & Society,2020,34(1):17-30.
[42][51]CHOI Y. A preschoolers agency: why relational types of agency emerge in peer interactions?[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2018,190:10,1525-1536.
[44]TURMEL A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thinking, categorization and graphic visualiza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45]PLACE B. Constructing the bodies of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an ethnography of intensive care[C]//The body, childhood and socie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2000:172-194.
[47]ESSER F. Neither “thick” nor “thin”[C]//Reconceptualising agency and childhood: new perspectives in childhood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16:52-56.
[48]FU G, CLARKE A. Teacher agency in the Canadian context: linking the how and the what[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2017,43(5):581-593.
[49]EMIRBAYER M, MISCHE A. What is agenc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8,103(4):962-1023.
[50]CORSARO W A. Collective action and agency in young childrens peer cultures[C]//Studies in modern childhood: Society, agency, 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2005:231-247.
[52]鄭素華.從“舊”童年社會學到“新”童年社會學—發展與爭議[J].學前教育研究,2023(11):1-17.
[53]王燕.從“規訓”到“能動”:當代西方童年研究的空間視角轉向[J].學前教育研究,2023(04):69-78.
[54]林蘭,金香君.學前兒童同伴文化生成路徑的民族志探究[J].學前教育研究,2022(04):28-46.
[55]高鈺霞,王海英.“潛隱劇本”的誕生:幼兒闡釋性再構班級規則的民族志探究[J].學前教育研究,2024(01):38-51.
[56]PROUT A. Childhood bodies: construction, agency and hybridity[C]//The body, childhood and socie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0:1-18.
Tracing the Roots and Progress in Theories of Childrens Agency
WANG Youyuan1, CHEN Mengyao2
(1Shanghai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ge,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childrens agency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worldwide, with a renewed focus on its conceptualization. Childrens agency embodies a fundamental dichotom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agency, and between childrens agency and social structures. This dichotomy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heory of childrens agency and has been intensified by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In the context of navigating and surpassing this dichotomy, studies on childrens agency have evolved into four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 liberal, the socio?鄄cultural, the post?鄄structuralist, and the pragmatic paradigms. Each framework provides uniqu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impacts empirical research differently. For Chinese researchers, delving into this area not only means engaging with the central debates and forefront developments of childrens agency studies but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scholarly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area. Moreover, it entails challenging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Global North in this domain to amplify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academic perspectives.
Key words: childrens agency; childhood studies; the 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
(責任編輯:劉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