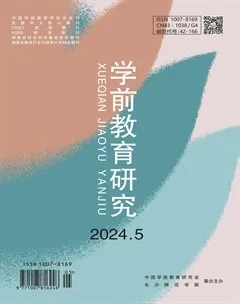語言與家庭教養:不平等童年的社會建構
[摘 要] 語言,既是家庭教養的內容,也是其實踐媒介。在家庭教養造就不平等童年的運作機制中,它可謂是軸心要素。首先,家庭有意識的語言教養是最表層的實踐。不同階層家庭的語言教養表現出“兒童中心—情境中心”的模式差異,為兒童語言習得搭建了不同的“腳手架”。其次,家庭教養中的語碼模式也隱性地形塑著不同階層兒童的語言模式。借助于語言的表層和深層實踐,家庭教養不只影響兒童的語言社會化,還影響他們的思維和認知方式、行為模式以及自我認知等。家庭語言社會化的階層差異推動著兒童整體社會化的階層分化,促成兒童文化的“階層區隔”。面對學校教育標準的衡量,底層兒童在學校教育中的“弱勢”是多維的,他們遭遇到學習、社會交往以及自我認知等多方面的適應困難。從語言層面探究家庭教養的階層分化,展現了教育過程不公平的形成機制,使研究者在家校關聯中理解了教育過程不公平的微觀運作。
[關鍵詞] 家庭教養;語言;不平等童年;教育的階層分化
美國學者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和家庭生活》一書中,憑借其理論想象力深度描繪了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差異,從文化資本層面填充了階層與學業成就間的邏輯斷層。作為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家庭教養方式是一種“慣習”的表征,它“隱蔽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子女……影響他們與學校或其他社會組織的互動方式,進而影響學業表現”。[1]這一分析理路不僅凸顯了家庭教育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且將理論關注點深入至教育過程不公平的微觀運作機制,為教育公平研究從“社會—外延”向“個體—內涵”[2]的范式轉換提供了理論框架。如此,我國教育公平實踐才能從追求以數量為中心的資源公平邁入以質量為中心的過程公平,①實現教育公平的發達水平——“教育過程參與機會公平”。[3]
在國內,有關家庭教養的階層分化研究并不鮮見,一批嚴謹而有說服力的佳作不斷涌現。②它們多聚焦于家庭教養期望、家庭教養理念、親子陪伴與互動、兒童學習的參與和家庭與公共機構的互動等維度,通過實證資料分析系統展現了不同階層家庭教養方式的特征。然而,這些維度之下還隱藏著一個更具統整力的要素——語言,但它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學術關注。③海德格爾的名言——“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道出了語言對于人的存在性意義。它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更在意識深處主導著人們的思維,影響人們對世界及意義的思考和表達。由此而言,語言既是家庭教養的內容,也是家庭教養的媒介,影響父母的家庭教養實踐。
社會語言學摒棄了從語言內部尋求標準規則的結構主義理路,視語言為特定社會文化情境建構的產物。早在20世紀20年代,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便提出:“語言無法脫離文化而存在,也即無法脫離那些決定我們生活結構的社會繼承性實踐和信念。”[4]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繼承語言的社會文化建構觀,強調實際言說者所擁有的能力并非形成無限的語法完美的語句,而是生產適合于特定情境的表達的能力。[5]他們秉持語言的文化多元性,認為不同文化群體在語言上呈現類型學上的“斷裂”。將此立場遷移至社會階層分析,不同社會階層間的“語言區隔”便顯露出來。不同階層的成員在語音、語法、詞匯以及語用習慣、風格等方面存在著區隔。當語言的階層差異得以彰顯,語言內在于家庭教養并建構階層區隔的運作機制也逐漸清晰。因此,基于語言與家庭教養的內在關聯,研究者能夠更為深層地展現家庭教養的階層分化,從而發現隱藏在教育過程中的不平等現象及其形成機制。
一、家庭的語言教養:文化區隔的表層實踐
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第一場所,也是兒童語言習得的首要場域。美國語言社會學家費希曼(J.A.Fishman)視家庭中的語言習得為學校語言教育成敗的先決條件。他指出:“家庭是母語代際傳遞、連接、使用和穩定的基礎。已有研究顯示,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或者雙語能力的保持更多依賴家庭,而不是學校。而如果沒有家庭支持,學校語言政策的效果也難以保證。”[6]就母語代際傳承的途徑而言,兒童在家庭中的語言習得是極為復雜而多樣的。其中,成人有意識的語言教養是最為顯在且最具針對性的語言習得途徑,是家庭語言代際傳遞的表層實踐。它廣泛存在于各種不同社會及文化的家庭教養實踐之中,是語言人類學研究能夠常常觀察到的語言社會化現象。語言人類學家斑比·席費林(B. Schieffelin)和埃莉諾·奧克斯(Elinor Ochs)發現:“在不同文化中持續觀察到的是,兒童照顧者在一系列反復發生的活動及事件中對說什么以及如何說給予明確指導的實踐。”[7]一般而言,這種指導實踐都采取成人“顯性提示”(explicit prompting)的形式,如特殊的語言指令(比如“說”)、語言范例(通過特定的語音或語氣提示兒童進行重復)等等。④它們向兒童標明語言教養實踐(區別于其他語言交流形式)的進行,并將兒童帶入其中。這些于家庭中實施的語言教養為兒童搭建了一個語言學習的“腳手架”。借助于此,兒童能夠更好地理解語言的意義,掌握語言的技能,實現語言的社會化。
家庭的語言教養實踐雖廣泛存在,但并非所有社會文化群體都采用同樣的語言社會化程序。事實上,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中,成人會選擇不同的方式為兒童語言學習搭建“腳手架”。它與所在社會的整體文化系統相契合,表現為家庭語言教養的文化差異。在語言人類學領域,有關語言社會化的眾多研究成果為此觀點提供了經驗性支撐。通過對薩摩亞兒童家庭語言交流的民族志研究,埃莉諾·奧克斯曾提醒道:“這里,重要的是指出所有社會并非依賴于同樣的語言社會化規程。盡管提示兒童如何說話廣泛存在,但拓展兒童的話語表達、使用引導性問題、告知兒童活動/事件的發生以及簡化詞匯和語法等做法卻存在文化間差異。”[8]如今,在某種程度上,這已成為此研究領域的理論共識。階層,作為社會文化分析的重要結構性維度,也是家庭語言教養差異形成的結構性要素。由此可推斷,家庭語言教養在不同社會階層間具有不同的實踐方式,是階層間文化區隔的實踐及表征。
家庭中的語言教養實踐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文化系統,對其階層差異的比較研究也極為煩瑣而艱難。為實現家庭親子交流的文化差異比較,斑比·席費林和埃莉諾·奧克斯透過層層細節深入至親子交流的深層模式,創建了一個新變量:“兒童中心(child?鄄centered)—情境中心(situation?鄄centered)”連續體(continuum)。在兒童中心的交流中,照顧者從兒童的角度組織交談并理解兒童的表達。它具有“兒童中心的主題、適應兒童自我中心行為的傾向以及經常將兒童作為交談伙伴的愿望”[9]等特點。情境中心的交流則表現為照顧者期待兒童適應當下情境中的人和活動。他們會選擇“對兒童使用一系列情境適合的語體風格,與兒童中心的交流對‘兒語(baby talk)的高度依賴截然不同”。[10]這一連續體變量從交流模式層面為家庭語言教養的階層差異研究提供了一個深層而具統合力的分析維度。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安妮特·拉魯發現中產階層家庭傾向于采用“協作培養”模式,與之相對,工人階層和貧困家庭則使用“成就自然成長”的教養模式。拉魯如此描述這兩種教養模式的“關鍵元素”:在“協作培養”模式中,“家長主動培養并評估孩子的天賦、主張和技能”,[11]而“成就自然成長”模式中的家長則“照顧孩子并允許他們自由成長”。[12]具體至家庭的語言教養實踐,家庭教養的這兩種文化邏輯便表現為“兒童中心”與“情境中心”的差異。換言之,“兒童中心—情境中心”這一連續體變量也適切于家庭語言教養的階層差異分析。在“兒童中心—情境中心”的連續體中,中產階層家庭的語言教養實踐更靠近“兒童中心”一端,而底層家庭的語言教養實踐則更偏向于“情境中心”。
不同階層家庭的語言教養實踐所展露出的“兒童中心—情境中心”差異根源于他們對兒童交流角色——是否為獨立對話者——的不同定位。在中產階層家庭中,剛出生不久的嬰兒便會被視為獨立的對話者,成人在照顧過程中會有意識地與之交流:告訴他們周圍事物的名稱、正在發生的事件等等,對他們進行語言的輸入。底層家庭的成人在嬰兒出生至特定年齡間則不會如此,他們認為此時兒童還不是交流的對象,與兒童的對話是無意義的。⑤在此階段,成人會在兒童面前談論各種事物和事件,但不會有意識地對兒童進行表達。在對美國卡羅來納州皮埃蒙特市兩個不同階層家庭的親子交流進行觀察時,S.B.希斯(Shirley Brice Heath)也發現了兒童交流角色定位的階層差異。她描述道:“Trackton⑥的成人并不將嬰幼兒視為日常交流的合適伙伴。將語前兒童而非成人作為交流伙伴則會被認為是一種冒犯或奇怪的行為。當嬰兒坐在他們的大腿上或在他們附近時,成人之間會進行交流,或者討論嬰兒或幼兒。然而……他們很少專門對幼兒進行表達。”[13]在城市中產階層家庭中,親子交流則被視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幾乎從懷孕開始,嬰兒就被作為是潛在的對話者……這種將兒童視為對話者和獨立認知者的觀點一直持續到兒童出生后。在醫院,父母、祖父母和親戚朋友們隔著育兒室窗戶和嬰兒對話。一旦到家后,成人和年長的孩子會和嬰兒說話并回應他。”[14]不同階層對兒童的定位不同,賦予兒童的交流角色也存在著差異,最終形塑了不同的家庭語言教養模式。
中產階層家庭中,成人在將兒童視為獨立的對話者并與之交流時,面臨兩個方面的障礙:如何使兒童聽懂以及如何聽懂兒童。為使兒童能夠理解自己,中產階層成人傾向于將表達簡化,如減少詞匯量、使用通用術語而非專業術語、選擇單語素詞匯、簡化語法(不使用從句、不改變語序等)、降低語速等等。另一方面,面對兒童的難以理解的語言表達,中產階層成人會根據特定情境中的線索(某個事物或事件)猜測其中的意義,對其不清晰之處進行拓展,幫助兒童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借助于表達簡化和拓展,中產階層家庭構建了一套異于成人間交流的獨特語言風格——“兒語”。由于兒語在某些方面是正常語言的簡化版本,C.A.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稱之為“簡化語體”(simplified register),“通過省略正常語言的復雜性并進行調整,使其得到澄清并適合于兒童的能力,兒語更容易被理解”。[15]作為一種簡化語體,兒語具有“交流和自我表達的功能”,它維系了中產階層家庭語言教養實踐中“兒童中心”交流模式的運行。
在底層家庭的語言教養實踐中,研究者并未發現簡化語體的使用。當底層家庭兒童做出意義模糊的表達時,成人要么視其為無意義行為而予以忽視,要么“只是提供一個具有情境和文化契合性的‘注解,而不會去琢磨兒童僅部分可理解的話語所要表達的真實意義”。[16]基于對兒童話語表述意義猜測之上的語言拓展在底層家庭的語言教養中是不存在的。S.B.希斯在工人階層家庭中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成人并不認為嬰幼兒有能力或有必要進行語言表達……即便在一些情境中嬰幼兒的話語能夠很容易聯系到某個事物或事件,成人也不會視其為某種稱謂……他們不會重復兒童的話語,不會認為它是某個事物或事件的稱謂,也不會將這個‘詞匯置于拓展了的短語或句子之中”。[17]至一定年齡階段,當兒童被視為對話者時,成人不會根據兒童調整語言風格,他們不會選擇使用兒語,即便他們知道這種簡化語體的存在。在S.B.希斯所觀察的美國Trackton社區,“成人既不使用兒語在某些方面的簡化(如縮短詞匯的語音結構,用簡單發音替代復雜發音,減少音調變化以及使用特殊詞條)也不選擇其澄清特征(如降低語速,使用特定音調或語調模式以及用名稱替代代詞),盡管他們知道在他們撫養孩子的方式外存在著兒語的使用”。[18]當他們對兒童進行有意識的語言指導時,他們往往只是為兒童提供情境契合的表述,要求孩子重復或記住,而不會考慮到兒童的理解,更不會因此調整自己的語言。重情境而非兒童是底層家庭中親子交流的中心,“情境中心”是底層家庭語言教養實踐中的交流模式。
二、家庭教養的語言:文化區隔的深層實踐
家庭中,成人有意識的語言教養僅是兒童語言習得的顯在路徑,是影響兒童語言學習的“顯性文化”。在此之下隱藏著兒童語言習得的潛在途徑——不以語言為目的的家庭教養(或可稱之為家庭的非語言教養),構成了影響兒童語言學習的“隱性文化”。事實上,這種家庭教養與兒童語言能力發展間的關系已在很多經驗研究中得以展露。吉暉通過對CFPS⑦數據的統計分析,指出:“父母參與及教養方式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系數較大,……父母參與度高,父母與子女相處的時間越長,其有效的語言輸入也越多,相應兒童語言能力發展越快、水平越高。……父母的鼓勵可以激發兒童的學習動機,促進語言能力的提高。”[19]這雖然揭開了家庭教養影響兒童語言習得的方式,卻未能觸及其深層要素——家庭教養的語言。家庭教養,無論其內容為何(語言或非語言),大都需要以語言為媒介。在家庭教養的實踐過程中,成人所使用的語言會在顯性的教養內容之下潛在地影響兒童的語言習得,構成兒童語言習得的深層動力。
家庭教養實踐中,成人所使用的語言并非公共的,而是特定階層“語言慣習”的體現。在“場域”理論的社會結構想象中,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強調,語言使用并不遵循索緒爾所追尋的語言“內在規律”,“結構”(場域中的位置關系)對其有著限制作用。“社會性是語言的內在特征之一……異質性是語言的固有品質。”[20]家庭教養語言也是如此,由場域結構決定。不過,場域結構對家庭教養語言的影響并非直接而機械的,而是借助于“語言慣習”的作用。語言慣習是場域結構中不同位置上人們的階級慣習的一個方面,是各個位置在歷史中所形成的關系在個體身體內的沉積,是客觀而共同的語言規則、語言價值的內化。語言慣習以“下意識而持久的方式”體現在個體行動者身上,表現為行動者所具有的語言圖式,主導他們的語言認知、語言思維和語言行為。這樣,我們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布迪厄反對“語言怎么說,現實就是什么樣子”,而是堅持“現實是什么樣子,語言就怎么說”。[21]作為家庭教養媒介的語言,也取決于成人在社會場域中所處位置的“現實”,是特定階層的“文化資本”。換言之,不同階層家庭在實施家庭教養時所使用的語言是不同的,家庭教養語言存在著階層間的“斷裂”。
不同階層的家庭教養語言有何具體差異?對于此問題,巴茲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提出的一對概念——“大眾語言”(public language)和“正式語言”(formal language)具有相當的概括力和解釋力,可借以對不同階層家庭教養語言進行對比分析。在教育子女時,底層家庭使用的是大眾語言。這種語言“含有大量簡短的命令,簡單的表述和問題,其符號意義是描述的、實在的、具體的、直觀的,并且具有較低的普遍性,它的重點在于情緒而非邏輯含義”。[22]中產階層所使用的正式語言則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它“富于個人的、個體的限制條件,其形式表明了一系列高級的邏輯操作;語音和語調以及其他非語言的表達方式雖然很重要,但卻處于第二位。”[23]拉魯在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發現,她指出“中產階級黑人家庭……父母用語言作為管教孩子的關鍵性機制。這種方式常常導致日常家庭生活中大量的談判磋商、討價還價和牢騷抱怨。……對于其他家庭來說……特別是貧困黑人家庭,語言的使用則更具實用性。……這些家長在與孩子交流時會使用指令性的語言,而不是進行大量的磋商”。[24]
在我國,很多經驗研究也發現了家庭教養語言的階層差異。有研究指出農村家長的教養語言表現出大眾特征。“在平時的語言交往中,家長除了用語言向孩子提要求外,很少主動和孩子平等、自在地聊天,……家長對孩子的不期望行為多采用‘解決問題式的控制方式,即用命令、轉移注意、嚇唬、哄騙、責罵等方式,較少看到家長給孩子講道理。”[25]這不同于中產階層家長的教養語言。在中產階層家庭中,父母“會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制造親子聊天的機會,試圖在過程中了解孩子各方面的發展與想法,并將所要傳達的概念透過聊天或者說故事的方式與孩子共同討論”。[26]與此不同,勞動階層的教養語言則表現出“片段式的單向對話”特征。“家庭對話鮮少會圍繞著長篇大論的議題進行,一般而言,親子之間交談的句子簡短,用詞亦相當簡單。”[27]在和孩子交談時,父母經常沒有回應或者只是給予簡單的回應。
面對不同階層的教養語言所表現出的差異,研究者往往將其歸因為不同的教養觀念。社會底層家長不懂得講道理的重要性,秉持家長權威的觀念,因此更多地在家庭教養中使用簡短的、指令性的語言。不過,這之下還掩藏著一個更為根本的要素——語言編碼模式。它是語言系統的深層組織結構,決定著人們在語言表達時對詞匯的選擇以及組織編排。“在心理層面這些編碼模式可根據促進(精致編碼)或阻礙(局限編碼)用清晰的語言形式將意向符號化的傾向來進行區分。”[28]工人階層在語言表達時,往往會使用“局限編碼”(restricted code)模式。這種語言編碼模式傾向于主要依靠非語言形式進行個體意向的表達,如語調、重音、表達特征等等,針對特定意向的具體語言規劃被縮小。因此,表達者所選擇詞匯范圍較小,語言結構的可預測性較高,但語言意義的可預測性卻較低,也即語言表達的普適性低,意義模糊。與此相對,中產階層習慣于使用“精致編碼”(elaborated code)模式,他們傾向于通過語言規劃來明確表達自己的意圖,對非語言要素的依賴較少。這樣,他們所選擇的詞匯范圍相對更大,語言結構的可預測性大大降低,但語言意義的可預測性則明顯提高。這樣,社會底層所使用的局限編碼模式早已將“講道理”“磋商”“長篇大論的雙向對話”排除在家庭教養之外,而無論其是否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
在語言編碼模式的差異背后,是社會環境及其形塑思維模式的不同。具體來說,“中產階級身處更具流動性、陌生化和異質性的社會環境……而工人階層……身處缺乏流動性、成員同質性程度高、熟人型的社會環境”。[29]在異質性的社會環境中,中產階層習慣于關注個體(或事物)間的差異,基于“關系矩陣”對個體(或事物)進行認知和定義,形成了一種“結構敏感型”的思維模式。生活于同質社會環境中的社會底層則無法看到個體(或事物)間的關系,他們習慣于從“邊界”對個體(或事物)進行認知和界定,養成了“內容敏感型”的思維模式。在“結構敏感型”思維模式下,中產階層將兒童看作獨立的個體,在教養實踐中立足于個體間差異和關系(將對方看作和自己不同)來選擇詞匯并進行組織,習慣于選擇精致編碼模式,傾向于使用正式語言。相反,“內容敏感型”思維模式使得社會底層在教育子女時將其視為具有相同“背景性知識”的“圈內人”,他們選擇局限編碼模式,其語言表現出大眾語言的特征。在家庭教養過程中,成人不僅向兒童傳遞著具體的教養內容,其語言及思維也傳遞至兒童,形塑著兒童的思維及語言編碼模式。可以說,語言是家庭教養階層差異的重要方面,也是建構并維持不同階層兒童文化區隔的深層符碼。
三、學校生活與語言:文化區隔的教育后果
無論是家庭的語言教養,還是家庭教養語言的隱性影響,它們雖有不同的存在樣態及運作機制,但卻共同參與了兒童在家庭中的語言社會化過程。然而,社會階層對兒童語言社會化的影響并非囿于語言層面,而是多維度的。兒童語言社會化不僅是兒童學會使用特定語言的過程,還是兒童通過語言習得助力自身社會化的過程。憑借語言習得,兒童掌握了學習和思維的工具,獲得了認知事物(或事件)的基本框架,他們還內化了社會行為準則并建構了獨特的社會世界,同時也建構著對自我的認知。兒童語言社會化的階層差異造就了不同階層間兒童的“文化區隔”。從社會底層兒童的立場來看,他們與學校文化間的“鴻溝”就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而是寬泛意義上的文化層面的。語言的差異造就了底層兒童在學校生活中的多維“弱勢”。
兒童語言階層差異的直接后果便是他們在語言類科目(例如語文)中的不同學習困境及學業表現。陳敏倩等人指出,“在需要較多的學習經驗和較高層次認知能力的語言任務上,家庭背景的作用就十分突出地顯示出來,例如接受性語言中的同音識別、復句理解;表達性語言中的詞匯的豐富性、表達的清晰性和邏輯性;早期閱讀中的圖畫理解和故事預測;作為聽者和說者的語言運用技能等方面。”[30]不同階層兒童具有顯著的差異,其語文學習表現及學業成就的差異也便是可想而知的。在對外來務工子女語言的質性研究中,齊學紅等人詳細描述了語言慣習的階層差異給外來務工子女的語言類科目學習所帶來的困境:“對于學校教育的標準語言,常常不能游刃有余地駕馭,因此暴露出其對該語言有限的駕馭力;更多的時候,他們對教師的提問無言以對,呈現出失語的狀態。”[31]在作文寫作時,他們只能對簡單事件進行簡單描述,而無法對復雜事件進行清晰、生動的描寫,作文表達模糊而平淡;在課堂教學中,他們無力理解教師的提問,更無法組織語言進行回答,在課堂交流中陷入“失語”和“沉默”,被排除于課堂教學之外。在語言類科目的學習中,底層兒童需要經歷艱難的語言適應,這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學業負擔。
底層兒童的思維及語言編碼模式還給他們學習科學類科目(如數學)帶來了困難。科學類科目使用的是邏輯語言,具有簡潔、抽象和客觀等特征。由于具有不同的語言及思維模式,不同階層兒童掌控邏輯語言的能力也不同。在結構敏感型思維模式的驅動下,中產階層兒童能夠同時關注多個事物(事件)并從結構關系層面對其進行認知,賦予意義。這種認知傾向使得中產階層兒童具有更強、更廣泛的探究好奇,“導致他們獲得對周圍環境正式秩序的認識,形成了它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概念,這便是早期解釋性概念形成的開端”。[32]具備此解釋性概念,中產階層兒童能夠深入至事物間的結構或事物內各要素間的結構來認識和解釋某一事物,能夠更快地掌握科學類科目的邏輯語言,在此類科目的學習中游刃有余。與此不同,內容敏感型思維模式將底層兒童的認知限于相互獨立的單個事物,他們不會關注事物之間的結構關系,更不會形成時間和空間的擴展概念。在此過程中,底層兒童便形成了“一種描述性的認知模式,例如將A、B、C、D事件作為獨立而無聯系的要素進行認知,或者至多能夠建立粗略而隨意的聯系”。[33]對于特定事物,他們無法保持長久的探究好奇,只能停留于對其特征的簡單描述,無法概括其內在各要素的關系,或超越此事物以認識其與其他事物間的聯系。內容敏感型思維與科學類科目的思維格格不入,底層兒童在完成此類科目的較高認知任務時會遭遇困難。
除學科知識的載體外,語言還是社會交往媒介,對兒童學校生活有著廣泛的影響。語言教養模式及語言模式的差異還會介入兒童與教師的社會交往,形成不同的師生交流效果和師生關系質量。從底層兒童的立場來看,家庭語言教養的情境中心模式使他們無法將自己作為獨立對話者實現與教師的深層交流。他們往往傾向于將特定情境下教師所提供的語言表述視為范例,在不同情境中進行機械性遷移。話語重復成為底層兒童在與教師交流過程中不自覺的選擇。面對更為開放和深入的交流需要,他們大多只能保持緘默,陷入失語。此外,語言模式的差異也限制著底層兒童與教師間的有效交流。在局限的語言編碼模式中,底層兒童習慣于從非口頭語言(如語音、語調、語氣等)中獲取有關“個體特征”的信息,很難從口頭語言化的“個體特征”中提取意義。這樣,底層兒童常常無法“聽懂”教師的指令和要求,被教師視為“不遵守紀律”的孩子。在S.B.希斯的研究中,一位教師也描述了類似的現象:“事情需要被一遍一遍地重復。我發現自己需要大喊才能讓他們都聽從。”[34]更為重要的是,底層兒童的局限編碼語言是“一種地位平等者間的語言,因為它很少提及社會身份”,[35]無法適切地表達班級中學生和教師間的身份及地位差別。在與教師交往的過程中,底層兒童的語言行為,例如何時以及如何“插話”、稱呼的使用、禮貌語的使用等在教師看來是無法接受的,甚至是帶有敵意的。語言模式的差異使得底層兒童成為教師眼中的問題學生,阻礙了他們與教師建立高質量的師生關系。
底層兒童因語言差異而遭遇的弱勢并不囿于學習和社會交往,它還擴展至兒童對自我的認知中。在學校中,當底層兒童陷于學習困境而無法逃脫時,他們便傾向于作出自己不適合于學校教育的價值判斷,形成對自我的消極認知。與此同時,由于高質量關系的缺乏,底層兒童在師生交往過程中從教師那里所獲得的評價和反饋常常也是消極的。這不僅使他們無法獲得教育及情感支持以走出學習困境,更強化了其消極的自我認知。文森特·汀托(Wincent Tinto)在分析學生中途輟學時提出,“學校系統內部存在學術系統與社會系統兩個子系統,兩者之間既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又相互影響,這兩者的表現會影響學生的內在知覺,當學生身處學校環境,又無法與學校生活整合時,就會破壞個體與學校的聯結關系,造成缺乏規范的失序現象,輟學的行為就容易發生”。[36]底層兒童在學校學術系統和社會系統中的雙重弱勢造成了其與學校生活的區隔,他們要么雖身處學校之中,但卻被排擠于教育過程之外;要么直接逃離學校,成為輟學者。
四、結語
通過對語言階層差異的深度分析,研究者得以觸及家庭教養方式階層差異的深層要素,展現不同階層兒童間“文化區隔”的建構機制。借助不同的語言教養實踐,不同階層家庭為兒童語言學習搭建了不同的“腳手架”;以不同語言及思維模式為媒介,不同階層家庭的教養實踐隱性地影響了兒童的語言及思維模式,并賦予其一套認知及行為模式。這構成了不同階層兒童在進入學校前的“語言準備狀態”,決定了他們對學校教育過程的不同參與程度。就底層家庭的兒童來說,他們雖身處學校,但卻無法真正進入學校,他們是教育過程中的“局外人”。在語言與家庭教養復雜的互構機制中,不同階層家庭為兒童所構建的童年生活表現出階層間的不平等。
為改變底層兒童在教育過程中的“局外生存”狀態,使其能夠公平地享有高質量教育,教育研究和實踐者需將視野從學校拓展至家庭,在家校關系中探究教育公平的理論及實踐。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雙管齊下”,從家庭和學校兩端同時用力。就家庭來說,家庭教育指導者需要從語言及語言教養模式層面理解底層家庭的教育困境,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的規劃。他們需要讓底層家長了解學校語言及教養模式,并嘗試在家庭教養過程中進行實踐。不過,改變底層家庭語言及教養模式的過程是艱難的,效果的出現也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我們還須同時著力于學校教育教學方式的改變。具體來說,當遇到學習、社會交往以及自我認知方面存在適應困難的學生,學校教師不能僅局限于用同樣的語言模式為其提供重復的指導、說教甚至是指責。對于底層學生而言,這種教育幫助是一種無效的負擔。學校教師需要將目光潛入至適應困難的學生的語言準備狀態,理解這類學生的語言及思維模式,將學校教育內容建立于學生“自己的語言”的基礎上,并以此為教育的出發點。不僅如此,教師還需要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語言”和“學校語言”之間的橋梁,將學生引入學校教育的標準語言體系中。如此,底層學生才能在家庭語言和學校語言間自由游走,擺脫學習、社會交往以及自我認知等方面的適應困難,真正參與至學校教育過程之中,公平地享有高質量的學校教育。這應是實現“以‘人為中心的‘個體—內涵式教育公平”[37]的可行路徑。
注釋:
①在《新教育公平引論——基于我國教育公平模式變遷的思考》一文中,程天君描述了“社會—外延”式的教育公平研究模式。它主要指的是“從教育的外部因素如教育經費、師資配置,也即起點和資源平等來加以探討,而相應的教育公平評價指標和測量體系也側重入學機會、教育質量、資源配置等方面”以及“從制度層面加以分析,認為我國教育主要受制于國家的政策和制度,教育不公平主要體現為教育制度的不公正”這兩種研究模式。這兩種研究模式所持有的觀念預設都是“以數量為中心的資源公平”,因為制度層面的分析所追求的也是如何通過公正的教育制度保證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在程天君看來,這種教育公平模式是無法真正實現教育公平的。他倡導一種基于“個體—內涵”的新教育公平模式,“‘教育正義必須超越分配正義的邊界,而進入教育活動內部,走向承認的正義……這種教育正義的實現必須轉向以人為中心,即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具體來說,也就是“鼓勵個人充分發揮個體的潛能、尊重個人的選擇,以實現自身的價值”。這種研究模式所關注的是“以質量為中心的過程公平”,所追求的是每個學生都能在教育過程中享受高質量的教育,參與至教育過程中并充分發揮自身的潛能。但是,學生在進入學校之前并非一張白紙,他們已經是經歷了家庭教養的初級社會化過程的多樣化個體。孤立地關注學校教育過程不能發現每一個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的參與及潛能發揮的差異。這也就是說,只有將關注點前推至家庭教育,在家校聯系中研究者才能更好地發現不同階層家庭的學生在相同教育過程中的參與差異以及個體潛能發揮的差異,并探索這種差異的形成機制。這樣,教育公平研究才能邁進“個體—內涵”式的新模式。
②國內有關家庭教養的階層分化研究積累了較豐富的成果,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陳欣怡、劉欣的“父母養育觀念與文化資本的代際傳遞”(“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冬季論壇”工作論文);洪巖璧、趙延東的“從資本到慣習:中國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4期);藍佩嘉的“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臺灣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27期);吳瑩、張艷寧的“‘玩耍中的階層區隔:城市不同階層父母的家庭教育觀念”(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田豐、靜永超的“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劉浩的“中國家庭教養實踐與階層分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蔡慶豐的“社會資本、家庭教育期望與階層流動——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實證研究與思考”(教育發展研究,2021年第20期);蔡玲的“育兒差距:家庭教養方式的實踐與分化”(青年探索,2021年第3期);李雅楠的“收入不平等與家庭教養方式選擇:事實與機制”(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等等。
③在國內,從語言的階層差異層面探討教育不平等的文獻較少。它們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理論性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前者的代表性成果有盛冰的“語言資本與教育不平等”(教育研究與實驗,2005年第2期),湯美娟的“教育不平等的語言邏輯”(上海教育科研,2011年第5期)和“教育不平等的語言視角及其本土化路徑”(教育學術月刊,2012年第6期);后者的代表性成果有余秀蘭的“城鄉孩子的語言差異:一種文化資本的傳承”(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8期),趙翠蘭的“語言權力視角下城市學校農民工子女教育過程不平等探析”(教育學報,2013年第3期)和“語言公正視角下城市學校農民工子女精神家園建構之探究”(教育研究與實驗,2011年第2期),齊學紅、湯美娟的“語言、權力與教育不平等——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校生活語言的定性研究”(教育學報,2011年第12期)。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學校教育的過程之中,分析了不同階層學生的語言差異及其在學校教育中的不同遭遇。然而,學生語言的階層差異是如何形成的?現有研究未能深入家庭教養的語言層面來探討語言的階層分化和完整展現教育過程不平等的形成機制。
④在《不同文化中的語言社會化》(Language Socialization across cultures)中,埃莉諾·奧克斯(Elinor Ochs)列舉了其他一些比較常見的“顯性提示”方式,如:告訴孩子將要發生、正在發生、應該或不應該發生的活動/事件(“我們來看看這本書”“這些女孩正在欺負那個小男孩”“她不應該嘲笑那個男孩”等等);通過提問的方式指示兒童接下來要說什么(“你會怎么說呢?”“這本書的結尾是什么?”等等);簡化提示語和活動/事件的語義內容和語法結構;向作為參與者或目睹者的兒童重復言語活動/事件;拓展兒童的話語表達,使其適合于參與某種活動/事件(孩子:“落水了。”媽媽:“下雨了。”)通過這些提示,家庭中的成年人將兒童帶入至語言交流之中,實施語言的教育。
⑤在兒童成長過程中,何時被視為獨立對話者存在著社會文化的差異。在某些社會中,兒童開始牙牙學語時,成人便會與他進行交流;在其他一些社會中,兒童的牙牙學語則被視為無意義的行為,成人要等到兒童掌握更多的語言技能時才會跟他們進行對話。
⑥Trackton是皮埃蒙特市的黑人工人階層社區。
⑦北京大學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該調查覆蓋了25個省、市、自治區16 000戶的目標樣本,占全國總人口的95%,是一項全國性、大規模的追蹤調查,調查內容涉及家庭經濟、教育、家庭關系、人口遷移、健康、價值觀等眾多研究主題。
參考文獻:
[1]田豐,靜永超.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化[J].社會學研究,2018(06):83-101.
[2]程天君.新教育公平引論——基于我國教育公平模式變遷的思考[J].教育發展研究,2017(02):1-11.
[3]吳康寧.教育機會公平的三個層次[N].中國教育報,2010-05-04(004).
[4]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21,100.
[5][20]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7,34.
[6]李英姿.家庭語言教育不可小視(N).光明日報,2018-03-25(12).
[7][8]SCHIEFFELIN B, ELINOR OCHS.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cross cultur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5,6.
[9][10][16]SCHIEFFELIN B, ELINOR OCHS. Language socialization[M]. Ann. Rev. Anthropol,1986 (15):163-191.
[11][12][24]安妮特·拉魯著.不平等的童年[M].張旭,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1,31,103.
[13][14][17][18][34]Shirley Brice Heath. Ways with words: language, life and work i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65,161-162,59-60,71,175.
[15]FERGUSON C A. Baby talk as a simplified register, in talking to children: language input and acquis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219-236.
[19]吉暉.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分析[J].語言文字應用,2019(03):30-39.
[21]李紅滿.語言與符號暴力——多維視野中的布迪厄語言觀探析[J].外語學刊,2007(05):19-23.
[22][23][28][32][33][35]BASIL BERNSTEIN. Class, codes and control(Volume I):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language[M]. London: Routledge,2003:21,21,58,22,25,25.
[25]廖貽,周亞君.農村嬰幼兒家庭教養狀況研究報告[J].學前教育研究,2002(02):24-29.
[26][27]許殷宏,朱莉嬛.社會階級與家庭教養之探究——以兩個家庭個案為例[J].教育學術月刊,2014(03):3-14.
[29]高水紅.學校再生產的理論脈絡及其啟示[J].南京社會科學,2020(04):129-135.
[30]陳敏倩,馮曉霞,肖樹娟,等.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兒童的入學語言準備狀況比較[J].學前教育研究,2009(04):3-18.
[31]齊學紅、湯美娟.語言、權力與教育不平等——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校生活語言的定性研究[J].教育學報,2011(06):108-117.
[36]常寶寧,李錄琴.基于自我認知的普通高中學生輟學意愿研究[J].中國教育學刊,2022(08):58-63.
[37]程天君.以“人”為核心評估域:新教育公平理論的基石——兼論新時期教育公平的轉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01):116-123.
Language and Family Upbringing: Social Construction of Unequal Childhood
TANG Meij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Inner?鄄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both the content and media of family upbringing. It is the core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equal childhood. First, the conscious language teaching in family is the surface practice. The language teachings in family of different classes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ld?鄄centered model” and “situation?鄄centered model”, and put up different scaffoldings for the childrens learning of language. Second, the language code model of family upbringing also shapes the language model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classes. By the surface and deep practice of language, the family upbringing influences not only the languag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but also their thinking and cognition model, behavior model, self?鄄cognition, and so on. Different language socializations in families of different classes boost the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of childrens whole socialization and lead to the hierarchical segmentation of childrens culture. Facing the measurement of schools standard, the disadvantage of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in school education is multi?鄄dimensional. They confront with adaptation difficulty of learning, social interaction, self?鄄cognition and so on. Exploring the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of family upbringings in the aspect of language show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e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enabling researchers to study the micro?鄄operation of ine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in the view of home?鄄school connection.
Key words: family upbringing; language; unequal childhood;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of education
(責任編輯:劉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