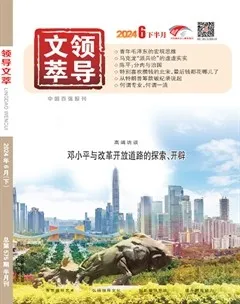青年毛澤東的宏觀思維
張錦力

入學湖南一師之后,通過跟楊昌濟學哲學,毛澤東的最大收獲,就是站得高了,看得遠了,判斷事物,不再拘于細枝末節(jié),而是能從大局觀、全局觀去考慮。
他說:“登上高山之巔,方可一覽眾山小,只有殫精研思,窮高極遠,才能拿得定,看得透。”
蕭三也證實,“那時,他就愛對大家講,要多從大處著眼,多往遠處著想”,不能舍本逐末,只看眉睫,不見泰山,丟了西瓜,撿了芝麻。
這種抓大放小的眼光,讓毛澤東入學沒多久,就顯示出了非凡的見識。比如議論時局,其他人都愛就事論事,為些小點喋喋不休。毛澤東則不然,他是站在時代的高度,以一種全局的思維,對現(xiàn)實問題進行點評和分析。所以,每次聽了他的話,大家都會感到豁然開朗,耳目一新。
另外,在觀察問題上,毛澤東也喜歡追根溯源,非要弄出個理來。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他就懇言:“但凡天下之物,只有知其理,才可益窮之。圣人之所以通達天地,知曉未來,皆因抓住了事物的本源。故吾決心,今后,要將全副工夫,都向大本大原處探討,至于那些枝葉扶疏,不再妄論短長,占去日力。”
說到看本源,毛澤東最生動的例子,莫過于1917年夏,他對當時憲政改革的看法。
大家知道,袁世凱死后,黎元洪、段祺瑞政府上臺,為了收買人心,重提憲政口號,這讓許多文人政客,都覺新機再現(xiàn),于是,紛紛獻計獻策,私下展開活動,以圖在新的政治版圖中,也能撈上一點資本。然而,面對這場熱烘烘的鬧劇,毛澤東卻很不感冒。他說:“如今的變法,俱從枝節(jié)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tǒng)、內閣、軍事、實業(yè)、教育等等,其實這些皆非本源,不過權宜之計矣。”
那么,在毛澤東的眼里,什么樣的改革,才算抓住了本源呢?給黎錦熙的信中,他就寫道:“今人,之所以為強有力者顛倒之,播弄之,皆因民智污塞,人們失去了主觀靈性。所以,如果人心這個問題,不加以解決,民眾不能覺醒,任何枝節(jié)的改革,都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只能支離破碎。”
正鑒于此,他大聲疾呼:“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又焉有不能者乎?”
聽了毛澤東的分析,開始同學都覺得,他對形勢的估計,未免太悲觀。然而,接下來的幾年,國家的政治走向,卻完全驗證了他的這種預判。眼見軍人政治愈演愈烈,黎民百姓怨聲載道,就連聲稱“不談政治”的獨秀先生,也坐不住了。1919年2月,在《我的國內和平意見》中,他也激憤地說:“如果國民不覺悟,南北軍閥不廢除,一切政治法律,都是空談。”
給黎錦熙去信時,毛澤東不過二十出頭,只是一介中專生,可他的政治預見,竟比陳氏這樣的大哲,還有先見之明。由此可見,經(jīng)過哲學的訓練,毛澤東的思想,是多么深邃,他的思維又是多么特別。難怪接其信后,黎錦熙不禁感嘆:“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實乃可大造也。”
除思考問題時講宏觀、求本源,在事務的判斷上,毛澤東也提出了“不蔽于物、不瞀于情、不絯于智”的做事三原則。
毛澤東所講的這三點,按現(xiàn)行的話說,就是做事情不要被表象所蒙蔽,不受情感沖動而驅使,更不能僅憑經(jīng)驗習慣,一拍腦袋了事。
正因如此,求學期間,毛澤東就要求自己,無論做什么,都應反復思考,認真論證,決不能輕易下結論,急著做判斷。他說:“大宇之內,萬象之眾,息息相通,惟明而后斷,只要用心,則小物也能辟大理。”
當然,毛澤東所提的這種境界,別說常人無法企及,即使睿智之人,也實難做到,可當時的他,就是以如此苛刻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磨礪自己,這讓他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自然也越來越高。
同學張國基就說:“他分析能力之強,觀察眼光之高,是當時任何同學都無法比擬的。他看問題不僅比大家深,比大家遠,而且,還極具前瞻性。”
好友蕭三對他的這一點,更是佩服得不得了。蕭三說:“潤之的頭腦,真是太特別了,他無論分析時局,還是探討學問,總能剝離表面的東西,一下抓到事物的本質,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所以,那時不管誰有了疑問,只要和他一談,都能迎刃而解,一如冰釋。”
說到毛澤東的預判力、前瞻性,有兩件事特別生動。
第一件事,是1915年秋,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上調教育部,成為新教科書的編審。對于黎錦熙的高升,別人紛紛道賀,而毛澤東卻大煞風景,一再勸黎錦熙:“北平臭腐,不可久居,急戀君歸。”在信中他還說:“當今政府,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其收攬名士政策,絕非真心政改,而是欲將天下有志者,乃為其所用矣!”所以,他反復叮嚀恩師:“北京如冶爐,所過必化。弟聞人言,為之心悸,固來書勸師,速歸講學,如待有為,絕不可急欲圖進。”毛澤東的危言相勸,讓黎錦熙甚是感動,坦然納之,但也有人覺得,他的此舉,未免小題大做。然而沒過多久,袁世凱果真祭起復辟大旗。在這場鬧劇中,正如毛澤東所預料,一些名流之士,“均墮袁氏術中”,為袁氏登基鼓噪抬轎子,搞得身敗名裂。
此事過后,許多師生都對毛澤東的政治預見驚嘆不已,說此生年紀輕輕,就嗅覺如此了得,真乃棟梁之材也。
而毛澤東的另一件事,則更讓人驚嘆。1916年夏,在給蕭瑜的信中,毛澤東就對中日關系的走向,做出了這樣的預測。他說:“思之,思之,日人實為我國勁敵也。二十年內,非一戰(zhàn)不足以圖生存。而當今國人,卻猶酣未覺,注意東窗事少。”在信里,他還預言,日后倭寇侵華之路徑,是“先滿蒙,北邊動,而后,胡馬骎骎入中原”。為此,他慨言:“欲完自身,以保子孫,只有磨礪,以待日本。否則,即使縱橫江山萬里,也會屈于三島,民眾四萬萬,也將被三千萬者所奴役。”
毛澤東發(fā)表此言時,北洋政府正為軍費開支,私下里與東鄰眉來眼去,打得火熱。所以,聽了毛澤東的預測,很多人都不以為然,有人就講,二十年的光陰,人間滄桑,世事難料,僅憑一己之見,就妄下斷論,未免有點杞人憂天。
然而,時事的發(fā)展,卻正如毛澤東所料,十五年后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占領東北,二十年后“七七事變”,日軍又大舉進攻中原,中日全面開戰(zhàn)。
面對此情此景,再回想起二十年前毛澤東的先知先覺,許多同學都不禁感嘆:“其料事如神之功,實乃天人可比也。”為此,當時,就有人預言,以毛澤東的這種天分,必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干出一番驚天動地之事。
回顧毛澤東的一生,可以說,他對大局的緊抓,他對宏觀的看重,一直情有獨鐘。無論戰(zhàn)爭年代,還是國家建設時期,他總是要求,“無論做什么,都應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
他的這種思維模式,與對手蔣介石形成了明顯反差。“蔣介石這個人,在軍隊管理上,有時過于拘泥細節(jié)。比如,部隊怎么設防,武器怎么配備,甚至,連士兵系沒系風紀扣這樣的小事,他都操心。而毛澤東則相反,他的眼里盯的都是大事。比如,是‘誘敵深入,還是‘圍點打援,是‘隔而不圍,還是‘圍而不打。至于具體戰(zhàn)斗,該怎么攻,怎么打,則交給手下的將軍說了算。”(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所以,從戰(zhàn)略層面上講,蔣介石的思維,也遠遠遜于毛澤東。
(摘自《解讀青年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