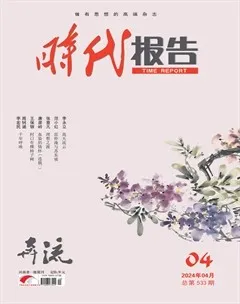遼河灣
遼寧境內,一處向陽的山坡上有我熱戀的故鄉。小村不大,只有100多戶人家。蟒蛇擺尾般曲曲彎彎的公路兩旁,錯落有致的房屋像無數個高矮不等的士兵一樣守望著村莊,守望著家鄉的黑土地。滋養這片熱土的就是那環村而過的遼河余脈,它們經風沐雨,跨過歲月的年輪,或胖或瘦,或急或緩,日夜不停地追趕著歲月,生生不息地從我家門前流過……
小的時候,讀過私塾的奶奶牽著我的手,指著家門前的遼河上游對我說:“那里曾經是昌圖八景之一的‘通江晚渡,通江口曾是水路碼頭,當年客棧、貨棧、錢莊、當鋪、飯館、茶社、浴池、藥房等商業網點一應俱全,碼頭上南來北往,四通八達,熱鬧非凡。艄公的號子響徹遼北大地,繁華盛景早已隨風而去。”聽著奶奶的講述,望著濤濤的遼河水,那商賈如履、游人如織的繁忙景象仿佛就在眼前了。時常想,頗具盛名的“遼河渡口”,不知何時還能恢復一如當年的繁華?
追趕著時光的腳步,永不停歇的遼河,承載了幾代人的夢想。兒時的童趣,少年的憂郁,中年的沉淀,都流淌在涓涓的河流里,有喜悅,有憂傷,有歡笑也有淚水。
每逢春夏之際,多干旱天氣,河水日漸消瘦,殘存的河水有些渾濁,也有些憂郁,它用生命守護著懷里的“寶藏”。那些掩藏在水里的魚蝦、河蚌、泥鰍等,成了兒時快樂的“藥引子”,一旦喝下,就會“中毒”,時常忘記吃飯和睡覺。小伙伴們常常三五成群,撒著歡地奔向河里,抓魚摸蝦。手忙腳亂間,一不小心,被小伙伴推進泥水里,褲子濕了,鞋也陷進泥里,泥人一樣從河里掙扎上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二妞,狗剩回家吃飯了!”娘高一聲低一聲地呼喚,時常在小村的上空飄蕩。傍晚,炊煙裊裊中,魚蝦醬的美味蜂擁著從家家戶戶門邊、窗戶縫里飄出來,在村莊里彌漫。
冬天,白茫茫的河灣,一如曼妙女子的水袖舞,她揮一揮衣袖,那盤旋的玉帶就將小村纏繞,無限風情,盡在一顰一笑間。滑冰,成了兒時最大的樂趣。滑冰用的冰車種類很多,單腿的,雙腿的,蹲著的,坐著的,還有雙腳一起滑的,形態各異,舞姿翩翩。不遠處,一會兒有人滑倒了,一會兒有人摔跟頭了,一會兒又有人鬧個屁股蹲。頓時,歡笑聲沖淡了嚴寒,成了冬天里一抹誘人的風景。
少年不識愁滋味。只顧一路歡笑著成長,卻不知遼河在帶給人們歡笑的同時,也有很多的無奈和缺憾。多年來,河流得不到治理,河水泛濫時,那份洶涌著實讓人頭疼。
那年秋天,雨水較大,一向溫和的遼河發了“脾氣”,它澎湃著呼嘯而過,將兩岸的莊稼一口吞下。鄉親們望著瞬間被河水淹沒的農田,唉聲嘆氣。一向沉默寡言的老父親一拍大腿,一屁股坐到地上,潸然淚下。他費盡心力經營的40多畝水田,是我們一家人一年的希望,就這樣毀于一旦,當年顆粒無收。父親和鄉親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維持生活。被擱荒的土地,蕭瑟凋落,就像茍延殘喘的老人。
那時的遼河,成了北方大地上一道令人心痛的傷口。全面開展的遼河流域治理,讓家鄉的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美,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走綠色生態發展之路,讓遼河成為涵養兩岸人們生存的生命之源。父親和曾經出走的鄉親得到這個好消息,歡欣鼓舞。他們辭去外地的工作,相繼奔回家鄉,投入火熱的遼河流域治理當中。
遼河岸邊,人聲喧嘩,機械轟鳴。轟轟隆隆的抓鉤機,氣勢龐大的推土機,唱著歡歌的拖拉機,火熱的場面如夜鶯的歌唱,把沉睡的遼河喚醒,它舒展腰姿,露出難得的笑容。仿佛涅槃重生,渾身上下透著蓬勃的朝氣。蘇醒后的遼河,又恢復往日的風采,它用博大的母愛滋養著兩岸的土地和人民。
記得去年秋收時節我回老家,正趕上老父親打糧食。機械轟鳴中,金燦燦的玉米唱著歌謠在空中飛旋、舞蹈,打個旋,跳到車斗里,奔向更廣闊的天地。父老鄉親一邊幫著裝玉米袋子,一邊歡快地說笑著,那幸福的場景讓人感同身受,一種簡單的滿足就在踏實的日子里。老父親撂下手里的鐵锨說:“沒想到今年河水這么給力,兩岸莊稼獲得了大豐收,玉米產量猛增,農民的腰包也鼓了。”轉過頭,我看到一張張喜滋滋的笑臉,在陽光的映襯下甚是可愛。
村里好多人都過上了好日子,可我還是惦記著四哥。我小時候身體不好,經常要吃好多湯藥。母親端著碗站在我身邊哄我喝下。可我一看到苦澀的黑湯藥,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掉,說什么也喝不下去。后院的四哥像哄小孩一樣哄我,有時還不知道從哪里給我弄來一塊糖,或者一塊小點心,變著法地哄我喝藥。多年過去了,那個場景仍在眼前。前幾年,四嫂意外病故。四哥一輩子無兒無女,現在他已是近80歲的老人了,日子過得怎樣呢?
父親說,你就放心吧,如今你四哥日子好著呢,頭幾年村里給他蓋了2間扶貧房,他享受“五保戶”的待遇,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他吃得好,睡得香,身體可硬實了,就是耳朵有點兒背,所以不愛出門。
聽說四哥生活得那么好,心里也就釋然了。如今鄉村振興的新舉措,不光是讓農業農村有個跨越式發展,讓新時代的農民富起來、美起來,更給農村老人以生活保障。
弟弟大學畢業后放棄在城里工作的機會,毅然回到家鄉,立志用所學知識改變家鄉面貌。他競聘當上了村黨支部書記,近兩年,新農村建設吹響號角,弟弟乘勢而上帶領村民搞農業合作社,借著遼河岸邊的優勢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實施規模經營,讓土地發揮更大的效益,村民的日子就像芝麻開花一樣節節高。一望無際的田野上,一棟棟新房拔地而起,呈階梯式分布在向往的山坡,寬敞平坦的水泥路兩旁,花香撲面,微風陣陣,景色怡人,不覺沉醉其中,仿佛有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清涼的夜里,明亮的路燈像一個個堅守崗位的衛兵守護著家園,那溫馨的光撫慰著每一個鄉親的心。老父親說,你弟這幾年沒白努力,給老百姓干點兒實事。現在咱們村不光是環境好,60歲以上的老人逢年過節還都有禮品發放,每人一份米、面、油,老人們可知足了。看著父親滄桑的面容上掩飾不住的喜悅,我也高興地一拳打在弟弟的肩上:“行啊!真有你的!”“哈哈姐,羨慕不?回來住不?好日子還在后頭哪!”我從心里佩服弟弟有這樣的抱負。認真地說,等姐退休了,一定回來,在哪里也不如家好。“水流千遭歸大海,樹高千丈葉落根。人行萬里還故鄉,冬去春來總有時。”人啊,最牽動靈魂的永遠是故鄉。
每每回到家鄉,我都久久地駐足在遼河岸邊,遼河就像一個老朋友一樣年年歲歲癡癡地等在那里,清清的河水映照著身邊的花草樹木,藍天白云,也映照出爺爺、父親和我幾代人的影子。身邊的那片綠草地上,我曾拿著一本書,邊看書邊放牧一群雞鴨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在漸行漸遠的歲月里。我彎下腰,蹲在河邊,撩撥著水花,輕輕捧起涼絲絲的河水,暢快地洗一把臉,那份清爽就順著肌膚一點點鉆進心尖尖里,瞬間清爽,滿心通透,就如剛剛與知己一場傾心長談一樣暢快。
遼河的水呀清幽游,嘩啦啦地從我家門前流,兩岸稻花香,十里織錦繡。站在遼河岸邊,聞著稻香,吹著遼河兩岸清新的風,聽著遼河濤聲,我時常想,假如沒有遼河的滋養,我的家鄉會不會是另一番景象?
作者簡介:
柴寶俠,遼寧鐵嶺市作協副主席,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首屆自然資源作家研修班學員。作品發表在《經濟日報》《大地文學》《中國自然資源報》《中國煤炭報》《中國礦業報》《散文選刊》《海燕》《遼河》等報刊, 2020年獲得第十屆“遼寧省傳記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