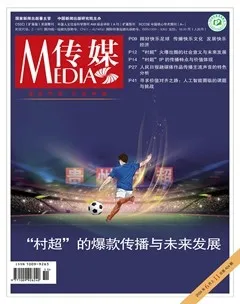國際傳播中“人民形象”的立體構建
王蕊
“人民形象”是“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是中國故事的主角也是我國國際傳播的題中之義與價值導向。有學者認為,以“集體”為表征的“人民形象”往往難以在以“個體”為關照的西方媒體中引起共鳴。長期以來,“人民形象”也處于“他塑”而非“自塑”的窘境中。然而,國際媒體對2023年貴州舉辦的三寶侗寨足球賽(“村超”)、和美鄉村籃球賽(“村BA”)(以下簡稱“兩江村賽”)的報道則呈現出對“人民形象”的積極關注與正面播報。源于鄉村的民間賽事,是如何打破外界對中國“人民形象”的刻板印象并實現立體構建與正面傳播的,值得分析思考。
國際媒體對兩江村賽的播報概況
國際媒體對兩江村賽關注時長超一年,突破了網絡傳播事件“新陳代謝”快的“命運”,呈現播報語態積極、話題泛化深入、關注人民主體的特點。
海外媒體長時段廣泛播報。兩江村賽在國內“火爆出圈”的同時,國際主流新聞媒體和社交平臺廣泛轉發,其傳播效應也從國內外溢至海外。
一是傳統媒體積極播報。境內媒體海外版的多篇(個)文章、視頻被海外媒體全篇轉載。英國廣播公司(BBC)、《經濟學人》,美國《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日本《經濟新聞》,新加坡《海峽時報》、《聯合早報》等國際知名媒體紛紛積極播發兩江村賽相關報道。
二是社交媒體多方催化。其一,知名人士“引流”。官員、駐外機構、社交媒體影響者等,紛紛利用海外賬號或在國際社交媒體積極宣傳兩江村賽;國際球星以不同方式表達對“村超”“村BA”支持。其二,網絡平臺“蓄流”。CGTN在臉書(Facebook)直播“村超”決賽盛況,當日觀看量突破40萬,點贊超過2400萬次。國際知名體育網站ClutchPoints(@ClutchPoints)推特(“X”)上傳NBA球星吉米·巴特勒到訪“村BA”視頻48小時內播放量超過49.5萬次,法語賬號@50NuancesDeNBA播放量12.3萬次。其三,評論反饋“聚流”。決賽日跟評環節多語種討論,境外輿論熱度升至頂峰。
話題迅速泛化深入。通過對14篇(個)圖文報道/視頻的文本分析發現,境外媒體對兩江村賽的播報話題具有不斷泛化、深化的特點。從話題發展趨勢來看,從早期關注賽事的規模和場面,到中期關注賽事的群眾自發性和文化特色,再到后期開始廣泛關注對地區經濟、文化、旅游的促進和刺激作用,最后寄予“乒乓外交”的期待。
從敘事立場來看,延續了國內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對兩江村賽引發的正面關注。在談及鄉村賽事帶動民族文化發展、鄉村振興、文旅產業、經濟效益等話題時,也多以中肯偏積極的語言進行報道描述。國際媒體的報道顯示,兩江村賽已經逐漸超越體育賽事的單一性,逐漸成為深度、立體、真實展現中國“人民形象”的傳播案例。
“人民形象”成為播報焦點。國際媒體中,兩江村賽的“人民形象”呈現出角色具象化、情感草根化和時代反差化的特點。
一是角色具像化。國際媒體報道中“人民”(People)一詞的出現頻率是27次。但考慮到中外表述差異,以及“人民”涵義的延展性,應將以下詞匯都納入到統計范疇中,包括:“中國人”(Chinese)、“群眾”(Mass)、“球員”(Player)、“村民”(Villager)、“觀眾”(Spectator)、“草根階層”(Grassroots)、“本地人”(Locals)、“居民”(Residents)等,總詞頻量達到279次。可見,外媒的關注焦點雖落腳于“人民”,但更傾向于將“人民”角色具象化。
二是情感草根化。從情感傾向上,表現出對民間“草根”崛起的欣賞。從注重描繪村民觀看賽事的生動氛圍和畫面著手,逐漸過渡到鄉村體育賽事對“熟人社會”情感鏈接和紐帶的強化,甚至表現出對“拒斥”資本的“欣賞”,以及對賽事獎品回歸“鄉土生活”的津津樂道,最后以草根球員比肩專業球員。這種對“草根逆襲”的喜聞樂見,與國內報道和網絡輿論幾乎相差無幾。
三是時代反差化。從敘事向度來看,包括時間向度、空間向度、物質-精神向度。如《經濟學人》對榕江縣的歷史描述是“紛紛外出務工”“兒童不得不與父母分離”;《華爾街時報》對臺江縣過去的描述是“偏遠鄉村”。而回到兩江村賽的場景中,人民則展現出“樸實”“富足”“熱情”等特質。增加對“歷史貧困”的描述不但沒有矮化兩江村賽的影響力和人民形象,反而“補充”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必經過程,即由生存到溫飽、從離鄉到回歸,從物質層面延伸到精神層面的動態發展過程,增加了中國故事的真實感與可信度。
如此廣泛報道、長時段關注、把敘事落腳點統一于“人民”的國際涉華報道案例并不多見。因此,有必要分析,兩江村賽中“人民”究竟是以何種形象存在于國際媒體觀察下的。
兩江村賽中“人民形象”的立體構建
兩江村賽如同一個萬花筒,將“人民形象”依次綻放、遞次呈現,完成和實現了國際傳播中有效的立體構建。
角色疊加中的人民形象。過往,基層群眾鮮少作為“主角”站在聚光燈下。在兩江村賽的案例中,賽場上的激情、生活中的樸實、文化里的深厚,在不同空間場景中疊加構建出真實可信的“人民形象”。
一是賽場上拼搏的運動員。“村超”場上,耐力比拼、戰術合作令觀眾的情緒起伏不定,倍感緊張和興奮。“村BA”驚險刺激的快攻和緊張的對抗成為吸引觀眾的核心視覺元素。體育賽事的觀賞具有國際通約性,不存在語言轉譯帶來的文化折扣。基于共同比賽規則的“文化接近性”原則,共觀體育賽事成為全人類“共享儀式”。
二是生活中的普通百姓。在兩江村賽中,運動與生活是“形影不離”的。穿上球衣,是協力合作的隊友,脫下球服,成為“我們”中的普通一員。當場上的汗水與生活的不易結合起來,當運動角色打破社會身份的邊界,鄉村賽事就轉化為最真摯的語言,比任何“外語”都更能通達人心。許多國際體壇巨星都出自貧民窟和貧窮社區。類似的經歷能夠喚起海外廣大受眾的真實記憶與體驗,在對體育的熱愛中實現共情與共鳴,在對體育與生活的樂觀態度上實現共通與共振。
三是文化里的少數民族。兩江村賽發生地——貴州黔東南州是苗族侗族自治州,具有深厚的少數民族文化和體育文化積淀。濃郁旺盛的鄉村體育文化、古老的宗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在信息化時代催生出別樣的精彩:苗迪、侗歌、鼓藏儀式等,極大深化了身份認同、娛樂需求和文化供給滿足。
多重角色在兩江村賽的舞臺中有機地統一起來,既兼具了對個體興趣愛好、人生追求的關懷,又關照了對集體、群體責任,團結、協作的統一,有效跨越了中、西方“個人”與“集體”二元對立的鴻溝,實現了“人民形象”的立體構建。
反差融合中的人民形象。反差融合,將兩種不一致甚至對立的特質通過不斷交鋒協調,呈現出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戲劇效果。兩江村賽在現代與古樸、身份與場域、專業與草根的“沖突”中,實現了“人民形象”的動態呈現。
一是“土洋結合”的基層風貌。萬眾矚目的精彩賽事在曾經閉塞的少數民族地區,通過現代性的傳播媒介向全國乃至世界播報,這本身就是極具戲劇性和沖突性的傳播事件。足球、籃球勃興于西方,在俱樂部運營模式下,往往打上西方資本主義精英體育的深刻烙印。然而在兩江村賽上,古樸本土文化傳統以“反功利主義”的形式逆流而上,與現代的巨大反差相互碰撞、轉化,成為網友口中:“土”到極致就是“潮”。碰撞與融合中又融入中國最真實的基層國情,與中華文化傳統互相嵌入,既“極具沖突”又自然合理、相得益彰。
二是“至真至善”的人文場域。兩江村賽超越了對比分絕對追求的“錦標主義”,在場內場外、線上線下成功營造出“至真至善”的人文場域。“至真”是對運動的支持與熱愛:比賽經費全村拼湊,啦啦隊道具手工合力打造,看臺上扶老攜幼、搖旗吶喊。賽事已成為虔誠的追求與榮譽的象征。“至善”是打破身份隔閡,對普通人和陌生人的尊重與真誠關懷:村民熱情“投喂”,球員自發免費擺渡,本地人騰出臥室接待游客,小販童叟無欺,警察、城管高溫下耐心維護秩序。“至真至善”的場景比比皆是。
三是“草根逆襲”的旺盛生命。出身貧寒、依靠個人奮斗成長起來的勵志故事是全世界久聽不膩的“精神食糧”。在大山鄉間地頭野蠻生長起來的“下里巴人”,在賽場上卻踢出睥睨世界杯的精彩瞬間,被中外網友用來打趣“中超”。在輿論世界里,真實世界中的力量對比出現顛倒:人數龐大的基層群體在輿論世界中展現出巨大影響力。在對“人民賽事”保持高度振奮的同時,也暗含著對體壇表現的失望和改革的期待。這種比較下的強烈情感反差被中外媒體捕捉,進一步推高人民辦賽的火爆程度。
傳統與現代、溫情與熱烈、業余與專業,反差因素的疊加不但沒有帶來突兀和不協調,反而令兩江村賽奇拔出眾、相得益彰,催喚出鄉村農民生機勃勃的精神面貌和人民體育巨大的生命力。
時代洪流中的人民形象。基礎設施的巨大提升、人民地位的堅不可摧、社會治理的開放高效,這些都是“隱藏”在兩江村賽背后,需要用心體悟的中國式現代化最深刻的“言外之意”。
一是時代交匯中的同頻共振。兩江村賽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榕江縣足球文化緣起于抗日戰爭期間廣西大學遷入帶來的運動之風,臺江縣籃球文化可追溯至1936年。進入新時代以來,偏遠的西南鄉村又迎來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機遇。高速路和高鐵聯通了山鄉與外界;體育設施普及讓人民熱愛隨處綻放;5G網絡全覆蓋實現順勢“出圈”。兩江村賽的成功離不開新時代十年所奠定的物質基礎,離不開淳樸而厚重的少數民族文化孕育出的高質量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堅如磐石的主體地位。兩江村賽是源自民間、經歷史滌蕩后流傳下來的屬于人民的體育運動。人民在時代的變化發展中始終成為組織主體、參與主體、成果分享主體和榮譽建設主體。當人民主體地位以實踐的形式呈現出來,生活的色彩和角色的多元一下子就豐富多彩起來,多樣性和創造性自然發生。在14篇國際媒體報道中,有11篇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兩江村賽的人民主體性。不努力表現,不使勁拔高,輕松愉快,把行為主體和發聲主體讓與人民,反而成為外媒競相報道的中國好故事。
三是自信開放的文化胸襟。自信方能開放,開放展示自信。自信開放在兩江村賽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歷時數月,數萬人的賽場秩序井然,數百場賽事中未出現一起安全事故,這體現的不僅僅是對賽事的自信,更是對執政能力、治理能力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從賽程設置來看,前期,主要面向農村戶口的村民;后期,隨著影響力逐漸擴大,還邀請省內、省外甚至國際球員前來交流。自信開放的文化胸襟成為推動“民心相通”的國際文化大舞臺。
啟示:處理好國際傳播中的幾組關系
在兩江村賽的國際傳播中,“人民形象”的立體構建與國際媒體報道中的播報邏輯相契合,說到底還是處理好了幾組關系。
在生活中搭建“人民”與“公民”的互構關系。歷史文化差異決定了不同國家對“人民”與“公民”的關注差異。認為兩種概念能夠自然融合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同樣,若以“集體至上”和“個人利益至上”來簡單劃分兩者的差異,作為拒斥彼此的理由也無法解決具體矛盾。因此,需要在“人民”與“公民”共通的邏輯區間——“生活”中尋找最大公約數。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兩江村賽的國際傳播不但沒有隱去群體形象,相反,國內外媒體都熱衷于報道賽事人山人海的熱鬧場面。德國哲學家狄爾泰認為,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旁觀”生活,而是作為參與者“糾纏”其中。兩江村賽有效彌合了“人民”的抽象性和“公民”的世俗性,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從抽象到具體、從“旁觀”到“糾纏”的橋接點。當把獎杯換成具有鄉村特色的物品時,具象化生活化的獎勵喚起熟悉“公民”社會的海外受眾的情感體驗和草根逆襲的記憶體驗。既貼近微觀生活,又關照宏觀語境,生活化敘事解構了公共歷史的本體論,既是碎片本身,又包孕著總體性的一切內容與可能,成為個體、家庭、群體的故事,更是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主體力量的展現。“人民”與“公民”中共同的平民個體也將成為“人民形象”的塑造者、傳播者和詮釋者,實現“在互相講故事的過程中找到最深刻的友誼”。
在傳播中重構“民間”與“官方”的顯隱關系。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切為了人民”的務實形象。這種“務實形象”在國際傳播中該以何種形式展現,決定了國際傳播的成敗。在兩江村賽的輿論聲音中,官方幾乎“隱身”。地方黨委和政府在報道中的比例和作用被主動淡化,讓譽于民,只在背后默默開展社會管理、旅游服務、秩序維護、醫療保障、交通疏導等服務保障類的工作。雖然“自己不說”,但從國際傳播的反饋來看,這種“自我隱身”的做法奠定了兩江村賽在對外傳播中的廣泛認同基礎,立意更高遠、更高明。隱性傳播以非直觀的表意方式,給予海外受眾充分的“思想自由”。通過人民性的充分表達,保留海外受眾由“現象”及“本質”的“追問空間”,在“人民至上”的表征中諦觀中國共產黨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
在共通中破除“他者”和“我們”的刻板邊界。“他者”被看作排除在主體外的陌生的對立面或是否定因素。當“他者”不斷壯大后,又被視為挑戰因素。只有發掘“他者”和“我們”的共通要素,才能從中尋獲破除兩者邊界的契機。在上述報道中,多個國際媒體提到了“足球、籃球是源于西方的運動”(由此可見部分媒體樂見兩江村賽的態度根源)。的確,發生在中國的鄉村賽事也能在海外找到民間呼應,如遍布英國各社區的業余聯賽和同樣為足球狂熱的盧頓小鎮(Luton Town);美國西雅圖的CrawsOver 聯賽、象征街頭籃球文化的“洛克公園”(Rock Park)。高明的傳播者往往更懂得主動引入共通要素,帶動“別人講”,實現“借嘴說話”。從這個角度而言,“體育”是共通要素,“人民”是互通基礎。唯有人民才是國際傳播的最大公約數。
作者系中共貴州省委黨校(貴州行政學院)副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博士生、村超“一帶一路”國際傳播顧問
本文系貴州省2023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貴州‘村BA‘村超對外傳播中的跨文化認同研究”(項目編號:23GZYB5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編輯:曲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