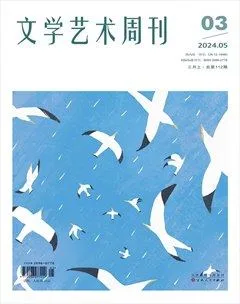西方科幻烏托邦批評的敘事機制研究
作為人的創造活動,文學與科技都是以人 能夠更充分發展自身為目的。但信息技術的沿 革對傳統文學媒介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對文學 的生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消解了傳統文 學的內容、結構、表達方式,由此美國文論家 米勒在 21 世紀初提出了“文學消亡論”。實際 上,科技在消解文學的同時,亦延伸、開闊了 文學的想象,科技與文學處于一個“破壞與補 償”同時進行的過程。[1] 科幻文學作為在此背 景下異軍突起并日漸繁榮的文學形式,已然不 再適用于傳統文學評價標準,它們迫切需要更 貼合科幻文學實踐的批評理論。在此語境中, 西方科幻烏托邦(Utopia)批評的興起,既是 對科幻文學實踐發展的回應,也是反思現實和 構想未來的現實需要。
一、西方科幻烏托邦批評與詹姆遜
以詹姆遜為代表的西方科幻烏托邦批評, 興起于 20 世紀 70 年代,以科幻文學的邊緣地 位為突破口,為科幻文學確立了文類品格,并 發掘了其中的批判功能。這一流派認為科幻文 學不僅具有娛樂效果,還有對現實說不的反抗 精神。詹姆遜作為一個將形式與歷史的關系視 為自身理論發展線索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認 為科幻文學因其認知功能和實驗功能成為表達 新時代烏托邦沖動的重要形式,以烏托邦為關 鍵詞不斷豐富科幻文學的理論研究。由此,有 必要對烏托邦與科幻文學的密切關聯做出更為 細致的梳理。
“烏托邦”概念最初由英國哲學家托馬斯 ·莫爾提出。德國社會學家卡爾 ·曼海姆在 《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中認為:“一種思想狀 況如果與它所處的現實狀況不一致,則這種思 想狀況就是烏托邦。”換句話說,烏托邦常常 產生于希望對現實狀況進行改變的心理。從古 希臘到 20 世紀,“烏托邦”一詞主要指代對美 好社會、理想藍圖的追求,是政治烏托邦。而 到了經受兩次世界大戰后的 20 世紀,政治烏托 邦逐漸沒落。在蘇文、詹姆遜等人的努力下, 烏托邦以文本形式在科幻文學中復活。
烏托邦在藍圖規劃上的能量消解和在文本 形式上的能量復活,與科幻小說的誕生、興起 存在著極為緊密的關聯。[2] 身處西方后現代狀 況中的人們由于遭受街頭運動失敗與戰爭創傷 的打擊,不再相信烏托邦的藍圖規劃能夠實現。 而與此同時,科幻小說作為后現代文化的產物, 是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邊界被消解的重要表 征,以文化想象的方式包納了工業時代的最新 成果,以文本形式思考諸如科技與自然、人與 科技之間關系變化等現實問題,蘊含著極為豐 富的烏托邦沖動。通過一種隱秘且特殊的敘事 機制,科幻文學思考與批判現實的烏托邦功能 得以實現。因此,烏托邦能夠在科幻文本中復 活,正是由于二者在形式方面的契合性。蘇文
[1]?? 出自胡亞敏《高科技與文學創作的新變——中國馬 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視域下的文學與科技關系研究》,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 年第 3 期。
[2]?? 出自王峰《走向后烏托邦詩學:科幻敘事對政治烏 托邦的解放》,《外國美學》2020 年第 2 期。
較為嚴密地論證了這一觀點。蘇文受到布洛赫 的影響,認為科幻文學同樣具有烏托邦的“尚 未”功能,能夠促使人們通過想象尚未到來的 未來以觀照當下現實。在文本形式上,蘇文進 一步推進了科幻小說的烏托邦功能的發展,不 僅確立了科幻小說作為文學形式的獨立性,將 之與奇幻小說區別開來,還在《科幻小說面面 觀》中頗具沖擊力地提出“烏托邦是科幻小說 的一個社會經濟的子類型”的觀點。畢竟,在 此之前,文學只是作為烏托邦的藍圖規劃之一 而實踐。這些觀點促使蘇文成為科幻文學之 “烏托邦轉向”的關鍵人物。
詹姆遜批判性地汲取了布洛赫與蘇文的觀 點,更加關注烏托邦沖動及其表達問題。對于 他而言, “烏托邦沖動”作為人對美好要素的 本能性向往,不同于烏托邦藍圖在物質層面的 規劃,而是如同弗洛伊德的“無意識”一般無 處不在的隱晦意識。烏托邦的功用在于揭示人 類想象理想藍圖過程中的困境,而不在于指導 具體的藍圖實踐。詹姆遜認為科幻文學是烏托 邦沖動的當代文本表達形式,并在《未來考古 學》綜合了前期對科幻文學與烏托邦所做的考 察。在現實世界“實際怎樣”與烏托邦想象世 界“應該怎樣”的互相觀照中,科幻烏托邦依 靠敘事的認知測繪功能,擁有了詹姆遜所說的 “為我們自己的經驗宇宙提供實驗性變種的能 力”,是從未來想象現實進而把握現實的“先 兆式的考古”,即“一種在特殊的歷史時刻把 握社會制度冷暖的特權途徑”。
二、科幻烏托邦的敘事機制
詹姆遜認為“敘事”是人把握過去經驗和 在當下關系中進行自我定位的重要方式。因為 歷史性的經驗轉瞬即逝,只有通過文本的敘事 行為才能把握歷史經驗的一個側面,為當下與 未來提供把握世界的支點。而“機制”在美學領域的應用,正如學者黃鳴奮通過詞源學考察 后指出的,是審美體驗、藝術作品在特定的社 會文化語境中得以表現、作用的方式與過程, “是‘方式與‘環境的統一”。由此,基 于對烏托邦沖動的表現機制的探求,對于科幻 烏托邦的敘事機制考察就成為題中之義。
在詹姆遜看來,科幻小說的敘事特征是以 “各種預想不到的、掩飾的、遮蓋的、扭曲的 方式”表達烏托邦沖動,因而科幻烏托邦的敘 事機制關注的是烏托邦沖動如何得以表達、烏 托邦沖動如何在表現形式上得到破譯的問題, 即創作者和讀者在文本上的視野融合問題。就 后者而言,必須考慮到詹姆遜從阿爾都塞和馬 舍雷那里繼承而來的癥候式閱讀方法。癥候式 閱讀,旨在挖掘文本沒有說的空白、失誤、歪 曲,并從這些裂隙中找尋到被意識形態所遏制 的意義層次。因而詹姆遜在《科幻文學的批評 與建構》中認為敘事分析要做的是揭示文本沒 有說的,或者在敘事機制中沒有記載的東西。 這為他探尋科幻烏托邦的敘事建構方法、元框 架和策略提供了基礎。
( 一 )建構方法:世界縮影
基于科幻批評實踐,詹姆遜從勒奎恩、羅 賓遜等人的科幻作品中提煉出一種敘事建構方 法:世界縮影。在詹姆遜看來,這一方法的生 成是以科幻小說的“思想實驗”功能為基礎的, 并在作者建構異于現實的文本世界、表達烏托 邦沖動的意義上起到重要作用。
關于“思想實驗”,詹姆遜實際上也受到 了科幻作家勒奎恩的影響。勒奎恩將“思想實 驗”從自然科學領域引入文學領域,認為科幻 作品都是思想實驗場:把現實的科學系統中的 科學元素進行想象性發揮,將之與現實中可能 產生的影響結合起來觀察,如此假設,從而合 理推論人們的行為以及社會結構會發生怎樣的 變化,一次次地將推演具體化并試圖找出可能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
所以,科幻小說以世界縮影,將科幻文本 世界與現實世界聯系在一起,從遙遠的未來折 回,正視產生文本世界的當下情境,從而達到 鞭策當下、警示現實的作用。
在對勒奎恩的科幻小說《黑暗的左手》的 分析中,詹姆遜認為該文本世界是一個以世界 縮影呈現各種方法的試驗場。《黑暗的左手》 中設定了一個遠離現實的烏托邦孤島——極度 寒冷的冬星,在那里人種單一,雌雄同體,沒 有資本主義但高度文明。這種對現存秩序的極 度顛覆的設定,暗示了《黑暗的左手》是如何 回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壓迫等現實中 討論曠日持久的議題。這種世界縮影方法的使 用,以烏托邦式的排除方式將真實世界的成分 壓縮簡化,再投放到新的烏托邦土壤之中,試 圖以“推斷”的方式進行合理化的情節推進, 最終得到一個較為合理的結果。
但必須注意的是,詹姆遜并不認為所有 的科幻烏托邦都是以世界縮影為敘事建構方法 的。他要表達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世界縮影 為科幻文學進行某種區別于現實世界的烏托邦 實驗提供了可能路徑。
(二)元框架:復調式烏托邦
詹姆遜討論烏托邦沖動的表達問題時, 之所以專注于科幻小說這一體裁,其中的一個 重要原因在于他認為科幻烏托邦具有巴赫金所 言的復調性。由于烏托邦在結構上的不可實現 性,各個群體的烏托邦形態不一并相互博弈, 使讀者能夠在烏托邦文本中聽到“不同立場之 間,為了爭取絕對地位而進行的巴赫金式的 對話或爭論”[1]。科幻小說作為后現代文化的 產物,同樣具有后現代文化的多樣性與非均質 性。科幻烏托邦疊加了這種多樣性。對此,詹 姆遜稱“假如烏托邦能夠對應這種多樣性的 話,那么它們必將是酒神式的,是狂放不羈的巴赫金復調”。在巴赫金看來,復調強調文本 中眾多彼此差異且不可約的聲音、觀點的多元 共存,與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未完成的對話相 映照,是較之“獨白”更為理想的真理探索方 式。詹姆遜汲取了巴赫金的這一觀點,主張復 調式敘事的烏托邦框架,反對獨白式的傳統烏 托邦。但相比巴赫金,詹姆遜更強調對話之間 的沖突和對抗性。在對科幻烏托邦的分析中, 他意圖揭示現實中的邊緣聲音如何被話語霸權 所壓抑,又是如何重獲話語權的。
因此,復調式的科幻烏托邦作為敘事的元? 框架,是由多個烏托邦組成的烏托邦文本世界。? 其中的各個烏托邦自給自足而相互獨立,由此? 形成了不可約的差異性。當需要在這文本世界? 做出取舍時,展現各個烏托邦的這種差異性,? 或許可以促使人們發現人類的最短的那塊木板。 差異性促使并置于文本中的多個烏托邦沖動產 生對話,為各自的主張而努力。文本世界成為? 不同烏托邦之間交流對話的空間。在科幻小說? 中,其后現代文化特征與巴赫金式的復調性、? 對話性形成呼應。因此并不存在完美烏托邦對? 眾多烏托邦的統合,而保持文本世界中多種多? 樣的烏托邦的對話、共生狀態,是形成不同思? 想的復調和聲的重要前提。因而科幻小說作為? 不同烏托邦的并置空間,在烏托邦之間的相互? 對話、碰撞中,不僅催生了高張力的文本,也? 激發了人們思考當下的沖動。
(三)辯證的策略:反 - 反烏托邦主義
詹姆遜意圖恢復烏托邦在科幻文本中的活 力時,也關注到了反烏托邦與烏托邦之間的復 雜關系。在詹姆遜在《時間的種子》中明確表 示,反烏托邦與烏托邦的立論點是一致的,都 是被忽視的烏托邦沖動的表達形式,都意圖為
[1]?? 出自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 小說》,吳靜譯,譯林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更美好的未來做出努力。因而,作為烏托邦沖 動的不同表達形式,科幻文本中的烏托邦與反 烏托邦是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
對于反烏托邦的敘事文本而言,完美的獨 白式烏托邦是反烏托邦進行反叛工作的標靶。 反烏托邦的解構方式,就是呈現出各種生態災 難、秩序混亂的世界圖景。但這幅圖景中往往 隱藏著在各種沖突中突圍的烏托邦沖動,為情 節推進到最后的開放式結尾提供潛在的驅動線 索——指向一個烏托邦式的未來。所以詹姆遜 才會說:“災難電影最終顯現出了一種烏托邦 的性質。”[1]
對于詹姆遜而言,人們亟須鍛煉被資本現 實所束縛的想象力,而科幻烏托邦是處理這一 問題的恰當中介。這正是因為科幻烏托邦的敘 事機制中存在著一種反 - 反烏托邦主義的辯證 策略。這一策略正如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 ·迪 克、勒奎恩所身體力行的,以否定面貌的烏托 邦敘事反抗反烏托邦主義。這種辯證的策略, 使科幻烏托邦能夠在美學形式上通過對種種想 象性的解決方案的推演來回應社會現實問題。 詹姆遜在分析其學生羅賓遜的科幻代表作“火 星三部曲”時,認為其關注的焦點是可能的烏 托邦如何發生沖突,以及涉及烏托邦本身的爭 論。這種敘事模式超越了烏托邦的再現問題, 具有一種社會批判與實驗的功能。在此意義 上,詹姆遜十分贊同政治哲學家諾奇克的“烏 托邦多元化”觀點,即認為烏托邦是元烏托 邦,是彼此差異的多種烏托邦共存的框架,是 人們能夠充分發展自身且不強制干涉他人的場 所。實際上,這就是詹姆遜如此重視科幻文學 的烏托邦功能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并非未來世界的唯一形態,人們有必要積極參與 歷史進程,去創造更好抑或避免更糟的未來世 界 [2] ;而文化形式以其實驗功能與想象性的解 決方案,成為參與這一過程的重要途徑,應得 到足夠關注。
三、結語
科幻文學被視為敘事性文學作品,因而要 以之為底本對烏托邦沖動何以得到表現進行追 問,就必然要探析形式與敘事的作用機制。詹 姆遜的科幻烏托邦批評理論以未來考古學方法 和辯證批評為基礎,以文本批評實踐的方式, 在形式層面分析了科幻文學的敘事建構方法、 元框架以及策略,體現出復調式烏托邦共振的 實驗、批判功能。其科幻批評理論為科幻文學 和科幻批評的發展提供了理論視野上的開拓。 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以詹姆遜為代表的西方 馬克思主義科幻批評流派,幾乎止于對烏托邦 的功能研究,更多維度的批評理論還有待開發。 任何理論的發展都必須來源于和應用于實踐, 因此科幻文學在如今被一片唱衰的文學生態中 異軍突起的趨勢,帶來了批評理論研究發展的 契機。但科幻文學的創作與批評理論是否能保 持同一步調,中國的科幻批評理論研究是否能 隨著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而實現“彎道超車”, 則需要給予更多時間和空間再去斷言。
[ 作者簡介 ] 蔣麗微,女,漢族,四川廣安人,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 向為西方文藝理論。
[1]?? 出自詹姆遜《政治無意識》, 王逢振等譯, 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2]?? 出自李鋒《從〈未來考古學〉看詹姆遜的烏托邦思 想》,《當代外國文學》2013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