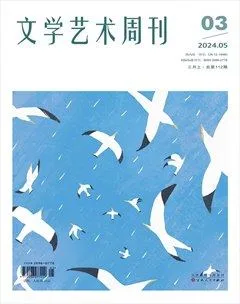圖式互動對社會認知差異的影響分析
《追風箏的人》是美國籍阿富汗裔作家卡 勒德 ·胡賽尼的第一部小說,主人公阿米爾是 一個出生在戰亂年代的阿富汗男孩,小說講述 了阿米爾與自己的過去不斷和解,最終獲得救 贖的過程。近年來,國內學者的研究和評論大 多集中在小說的主題——“成長與救贖”、象 征主義手法及隱喻的運用分析、人物形象與身 份認同的分析,或者對意象的解讀上。本文認 為,在小說背景中的殖民和后殖民時代,“沖 突”亦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在這部作品中,文化沖突貫穿人物發展 的始終,這意味著社會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決定 了故事的發展方向。對于這一主題,國內外學 者主要采用文學分析法,著重運用文學理論對 人物形象進行探討。本文則主要以圖式理論為 支點,受認知發展理論、認知文體學等理論模 型的啟發,試圖闡明話語世界中人物的圖示互 動如何影響他們的認知,追溯其思想行為的成 因,試圖證明圖式理論也可以用于分析文本和 人物的心理活動。
一、圖示理論及應用
( 一 )定義和發展
圖式理論最早由德國哲學家康德在 18 世 紀提出,他認為圖式是指人們對經常遇到的情 況產生的刻板印象。英國認知心理學家弗雷德 里克 · 巴特利特提出人們對于事件的回憶并不 是簡單的“復制”,而是一個記憶建構的過 程。在建構過程中,以前的經驗(或是已經儲 存在腦海里的知識)會與當前接觸的信息形成一種獨特的思想表達。而后認知心理學領域的 研究進一步強調,圖式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 建立經驗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認知結構。當遇到 新事物時,現存的圖式發揮作用,以幫助人們 正確理解新事物。圖示理論可以說是關于知識 的理論,關于如何以一種特殊方式表達知識并 幫助使用知識的理論。
(二)圖式理論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
在文學人物分析上,以文本內容對人物進 行靜態剖析是較為傳統的觀點,而以喬納森·卡 爾佩珀為代表的人物塑造理論強調,人物塑造 是文本信息和讀者意識信息互動的產物,對人 物塑造的充分論述必須涵蓋認知和文本兩個維 度:一是基于讀者長期記憶中的知識結構(即 圖式),二是由文本中的各個元素決定。由此 可見,圖式在理解人物形象的過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具體而言,由于每個人的知識體系存在 差異,個體認知必然不同,運用圖式理論可以 解讀人物形象復雜性背后獨特的認知心理。據 此可以推斷,除了現實世界的讀者與文學作品 間的圖式互動,虛構世界的人物對外部世界亦 有自己的結構性認識。因此,筆者試圖分析話 語世界中主人公認知圖式的演變過程,重點關 注圖式互動如何影響人物的認知心理,借此證 明圖式理論強大的應用性與闡釋力。
二、主人公認知差異的分析
( 一 )差異的起源——主仆圖式
在阿米爾的童年時期,對階級差異的認知
一方面來自家庭生活。阿米爾的父親是擁有高 貴社會地位的普什圖人,居住的房屋是整個街 區里最華麗的。阿里是哈扎拉人,是阿米爾的 父親的仆人,服侍著他幾乎所有的生活起居。 哈桑是阿里的兒子,自然“繼承”了哈扎拉人 的血統。作為小主人,阿米爾生活得很愜意, 他可以去上學, 日常事務都有哈桑為他打理, 而哈桑只能留在家里不停地干活。如此習以為 常的生活和顯而易見的差距讓阿米爾逐漸形 成了與哈桑關系的認知:哈桑是這個家里的仆 人,關系認知上的主仆圖式由此形成。
另一方面,周圍人的言語和行為不斷影響 著阿米爾,強化他心中的主仆圖式,最直接的 體現就是哈桑的態度。哈桑稱呼阿米爾為“Amir agha”(阿米爾少爺),“agha” 一詞來自土 耳其語,是一種等級稱謂,意思是首領、主人 或領主,而且哈桑從未拒絕過阿米爾的任何要 求。當目不識丁的哈桑指出阿米爾原創小說的 情節破綻時,阿米爾的內心獨白卻是:“他懂 得什么,這個哈扎拉文盲?他一輩子只配在廚 房里打雜,他膽敢批評我? ”不難看出,認知 主體哈桑對阿米爾行為的默許和接受,進一步 刺激阿米爾的認知選擇,主仆圖式從雙方關系 的客觀(被動)建立,逐漸發展為地位極其不 平等的主動交際選擇。同時,社會背景中的其 余認知對象也從側面肯定這一主仆圖式。風箏 比賽結束,阿米爾向路邊老人詢問是否見過哈 桑,老人說道:“幸運的哈扎拉人,有這么關 心他的主人。”在這些映射下,阿米爾認為哈 桑的忠誠是理所應當的,哪怕目睹了哈桑為了 追回代表勝利者的風箏被強暴,他的內心獨白 卻是: “也許哈桑只是必須付出的代價……這 是個公平的代價嗎?我還來不及抑止,答案就 從意識中冒出來:他只是個哈扎拉人,不是 嗎? ”阿米爾目睹了哈桑為自己犧牲,這是一 種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心靈震撼,他質問自己: “這是個公平的代價嗎? ”可是對于哈桑來說,這個問題沒有公平的答案。在當時阿米爾 的認知里,他堅定地認為哈桑是他的仆人。雖 然哈桑遭遇強暴的情境使阿米爾的認知世界發 生了一些變化,但他當時的認知圖式(即主仆 圖式)并沒有因為這個刺激而更新或者改變, 他依然用主仆圖式處理與哈桑之間的關系。可 以說,阿米爾與哈桑的一切關系中,始終存在 著不平等的主仆圖式。
(二)差異的顯現——朋友圖式
阿米爾心中主仆圖式的形成深受阿富汗社 會背景里等級觀念的影響,這成為他與哈桑之 間無法逾越的鴻溝。哈桑前去追風箏時對阿米 爾說的“為你,千千萬萬遍”,這是哈桑對阿 米爾一生的承諾,是哈桑對阿米爾真摯的友情 的體現。然而,故事中的阿米爾卻無法承認這 份友情,無法對哈桑沉重的感情做出回應,這 正是兩位主人公在認知上的最大不同——朋友 圖式。
阿米爾和哈桑相繼出生,從兩人童年的交 際行為上看,他們是很好的玩伴和朋友,但阿 米爾從來沒有這樣承認過。當野蠻的阿塞夫質 問阿米爾“你怎么可以當他是‘朋友”,阿 米爾幾乎脫口而出: “他并非我的朋友! ”他 質問自己: “我真的想過這個問題嗎? ……我 對哈桑很好,就像對待朋友,甚至還要更好, 像是兄弟。但如果這樣的話……為什么我只有 在身邊沒有其他人的時候才和哈桑玩耍? ”相 反,當哈桑拿到屬于阿米爾的風箏,卻被阿塞 夫一伙威脅交出風箏時,阿塞夫諷刺哈桑像狗 一樣忠于阿米爾,但哈桑卻堅定地回答道:“阿 米爾少爺跟我是朋友。”盡管哈桑因此受到了 極大的屈辱,事后他仍然想和阿米爾做朋友。 兩人在關系認定上產生差異的原因是阿米爾的 認知圖式在受到刺激后無法順應。
正如前文所說,阿米爾已經主動建立了與 哈桑間的主仆圖式,根據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當認知刺激與已有圖式產生沖突時,存在 同化和順應兩個過程,同化只在原圖式基礎上 更新,而順應需要適應刺激形成一個新圖式。 一般情況下,接受新信息的過程會出現一種認 知偏差,這意味著人們對圖式具有天然的依賴 性,不愿意放棄或修改既有的認知圖式。然 而,同化和順應是一對相互依存的矛盾體,只 有兩者共同作用認知才能得到發展,缺少一個 環節則會造成認知發展失調。具體而言,阿米 爾在面對與哈桑超越主仆圖式的交際行為時, 無法做到順應這種改變形成朋友圖式,這種不 完全的圖式更新導致阿米爾的認知失調,即使 他盡力以原圖式合理化兩人關系的改變,由于 缺乏新圖式,必然導致他與哈桑的關系失去平 衡,逐漸走向畸形。
(三)平衡的結局——兄弟圖式
風箏比賽后不久,阿米爾因為無法處理自 己的認知矛盾,利用卑劣的手段將哈桑和他的 父親趕出了家門。阿米爾沒有想到,這份痛苦 與自責一直影響著他成年后的生活,直至接到 拉辛汗從巴基斯坦打來的電話,拉辛汗的那句 “那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把阿米爾拉回多 年以前,也讓真相浮出水面:阿米爾和哈桑是 同父異母的兄弟,他們之間本該存在平衡的結 局——兄弟圖式。
拉辛汗告訴阿米爾,哈桑是阿米爾同父 異母的弟弟。阿米爾的父親為了自己的名譽和 威望隱藏了真相,剝奪了哈桑本應該擁有的身 份、地位和生活。這個謊言導致了哈桑悲劇的 人生,也成為影響阿米爾與哈桑認知關系的重 要原因。倘若童年時期的阿米爾知道哈桑是自 己的兄弟,他便不會堅持與哈桑間不平等的主 仆地位,他對哈桑的關系認知圖式會超越主仆 與朋友,成為血脈相連的兄弟,因無法重構新 圖式而產生的認知發展失調也將不會存在。阿 米爾不會失去善良,失去哈桑,不會終其一生背負罪責。
在認知主體的發展中,只有通過同化和順 應的過程才能達到認知平衡,人的認知結構只 有在平衡中才能得到發展。由于同化和順應是 一直在發生作用的,所以平衡也是不斷變化的。 面對真相,成年阿米爾的認知再一次受到了極 大的刺激。這些因為掩蓋秘密而不存在的“事 實”成為阿米爾必須重新接受的新圖式。最后, 阿米爾終于明白: “哈桑曾經深愛過我,以前 無人那樣待我,日后也永遠不會有。”哈桑對 阿米爾不計回報的愛和同父異母的親情紐帶使 得阿米爾徹底改變了原有的認知圖式,完成了 同化和順應的過程。這是阿米爾認知發展建立 新平衡的體現,暗示他找回了兩人本該有的平 衡。
三、結語
認知語言學家強調,圖式是一種動態的、 可變化的知識結構。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發現, 無論是現實世界的人,還是小說中的人物,其 社會認知的建構都會隨著圖式的更新或變化而 調整。一個完整、正確、嚴謹的圖式對于人們 認知的建構和交際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然而 由于人們對既有圖式的嚴重依賴,即使其為錯 誤的圖式,往往會繼續沿用,從而導致錯誤的 判斷和預測,正如阿米爾與哈桑之間的圖式互 動對兩人認知差異造成的影響。同時,借用圖 式理論,我們不僅可以以讀者的身份形成對小 說內容的個人理解,還可以以參與者的身份對 小說人物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分析,從而更好地 理解人物形象和文章主題。
[ 作者簡介 ] 邢鈺婷,女,貴州貴陽人,貴陽職 業技術學院教師,畢業于愛丁堡大學,碩士, 研究方向為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