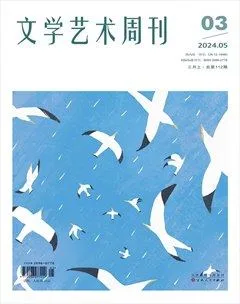新好萊塢電影歷史源流與藝術(shù)風(fēng)格初探
20 世紀(jì) 60 年代是美國社會經(jīng)歷大變革的 時期,政治、經(jīng)濟、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顯示 出與傳統(tǒng)的背離。一方面,民權(quán)運動、女權(quán)運 動、黑人爭取平等自由的斗爭風(fēng)起云涌 [1];美 國嬉皮士運動、反越戰(zhàn)學(xué)生運動迭起,使得右 翼保守勢力和“新左派”的沖突日益加劇。另 一方面,美國電影業(yè)在這一時期不得不面對體 制改革和自我定義的雙重壓力。大制片廠制度 的倒臺、高預(yù)算作品的失敗、電影電視行業(yè)間 的激烈競爭都迫使好萊塢電影另尋一條吐故 納新的轉(zhuǎn)型之路。美國青年為新好萊塢電影離 經(jīng)叛道的思想顛覆和大膽新穎的風(fēng)格手法所吸 引,長大成人的“嬰兒潮”一代已然成為電影 市場的觀影主體和生產(chǎn)者。新一代導(dǎo)演面對著 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的藍本,吐故納新,構(gòu)建出自 己在影像世界里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他們對歐洲藝術(shù) 電影的經(jīng)驗進行嫁接,以尋求最大限度的影像 真實。文章將通過對比新舊好萊塢電影的異 同,展示新好萊塢電影在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舊 好萊塢電影)的地基上重建起影像真實的途徑 和方法,以及戰(zhàn)后歐洲電影運動帶給新好萊塢 電影的影響和作用,并指出兩者間存在的差 距,進一步分析說明新好萊塢電影追尋的“真 實”是如何在當(dāng)時的文化背景下,與當(dāng)時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相呼應(yīng),試圖在此基礎(chǔ)上為新好 萊塢電影研究做出補充。
一、以經(jīng)典好萊塢為地基
新好萊塢電影的出現(xiàn)是美國電影發(fā)展史上? 的重要轉(zhuǎn)折點。隨著“派拉蒙公司仲裁案”宣? 告好萊塢大制片廠制度的崩潰,以及電影與電? 視從對立走向融合的斗爭結(jié)果,美國從“二戰(zhàn)” 后短暫的“豐裕社會”正式進入一個動蕩、無? 序的時期。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已經(jīng)無法回應(yīng)社會? 多元震蕩的需求,觀影者尋求的是更加貼近現(xiàn)? 實的影片,而不是營造現(xiàn)實效果的符碼和慣例。? 面對這樣的戰(zhàn)后困境及大眾焦慮,新好萊塢電? 影應(yīng)運而生。文章將通過比較研究,以經(jīng)典好? 萊塢電影為基本盤,以歐洲藝術(shù)電影為參照系,? 從新好萊塢電影重建的影像世界中反觀其表達? 的真實性。筆者認(rèn)為新好萊塢電影有意識地展? 現(xiàn)出當(dāng)時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理性與感性、? 傳統(tǒng)與反叛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這些轉(zhuǎn)變可能代
[1]?? 出自張愛華《“新好萊塢”:難忘的年代——評〈逍 遙騎士, 憤怒公牛——新好萊塢的內(nèi)幕〉 》,《電 影藝術(shù)》2009 年第 4 期。
表不了真實的社會面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不同時代背景下社會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
就觀影者而言,真實感往往是觀者對來源 于現(xiàn)實生活的體驗同影像語言間所產(chǎn)生的共情 效果,由于不同個體對外在世界的認(rèn)知不同, 對待同一事物選擇不同視角切入,導(dǎo)致真實性 的最終呈現(xiàn)大相徑庭。1967 年,阿瑟 ·佩恩導(dǎo) 演的《邦妮和克萊德》掀起了美國的新浪潮, 作為新好萊塢電影的開端,其帶有鮮明的反主 流文化特征,為日后新好萊塢電影的創(chuàng)作打響 了第一槍。反觀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的衰落正是由 于其創(chuàng)作逐漸背離了觀眾的需求,影片中的世 界幾乎全是美好奢華的烏托邦,它們違反了電 影的“真實本性”,并且無視貧困、不公與性 別、種族歧視等真正的社會問題,經(jīng)典好萊塢 電影展現(xiàn)的虛幻現(xiàn)實是不可能為戰(zhàn)后一代青年 觀眾所喜愛或認(rèn)同的。
長期以來,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在《海斯法 典》的制約下禁止拍攝觸及社會的主題,且不 允許出現(xiàn)色情暴力的鏡頭,影片主人公必須是 正面形象,無論是表現(xiàn)何種社會問題,經(jīng)典好 萊塢電影呈現(xiàn)的技巧和公式化的準(zhǔn)則只會把這 些問題變得更加背離現(xiàn)實。首先,在情節(jié)架構(gòu) 上,新好萊塢電影突破了以往的戲劇性單向敘 事模式,不再追尋古典“三一律”和情節(jié)間的 因果聯(lián)系,在時空轉(zhuǎn)換上更加靈活。例如《邦 妮和克萊德》中沒有交代邦妮為何愿意跟隨克 萊德,甚至是毫無邏輯地讓兩位主角踏上了搶 劫逃亡之路。影片將主人公放置于美國 20 世紀(jì) 30 年代經(jīng)濟大蕭條的時代背景下,邦妮和克萊 德是兩位江洋大盜,他們?nèi)螕尳巽y行,卻從 不掠奪窮人的財產(chǎn)。強盜不再十惡不赦,面對 社會的壓迫每個人似乎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的鏡 像,反英雄式人物同樣令人同情。其實,早在 1931 年經(jīng)典好萊塢強盜片《人民公敵》中寫實 風(fēng)格已能窺見一斑,同樣是盜匪,湯姆被塑造 成貪財貪色,沒有道德底線的黑幫小弟形象。
但湯姆的家庭背景又決定了他工人階級的社會 地位,他大肆揮霍靠違法手段得來錢財?shù)那楣?jié), 也能讓身處經(jīng)濟大蕭條的一部分美國中下階級 人民會心一笑,為新好萊塢電影通過影像真實 擴大觀影受眾奠定基礎(chǔ)。
其次,在場面調(diào)度上,新舊好萊塢電影也? 顯示出了區(qū)別,尤其是布景和燈光方面。 “不? 少士兵、小業(yè)主、家庭主婦和工廠雇員對回到? 和平時期的經(jīng)濟狀況產(chǎn)生幻滅感。人們已經(jīng)厭? 倦了看了十幾年的一成不變的棚內(nèi)街景,這? 無法滿足他們更為可信更嚴(yán)酷的美國現(xiàn)實的要? 求。”[1]《邦妮和克萊德》通過克萊德第一次在? 邦妮面前進店搶劫時的實景拍攝,展現(xiàn)出街道? 兩旁行人寥寥、商店緊閉的破敗荒涼景象。這? 種真實環(huán)境的展現(xiàn)隱喻及諷刺了美國經(jīng)濟危機、 工人失業(yè)、銀行破產(chǎn)帶來的后果。三點式布光? 法是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的基本技巧,就像是希區(qū)? 柯克在《辣手摧花》中的燈光使用,舅舅幾次? 與侄女產(chǎn)生沖突前影子的運用都營造出了進一? 步的懸疑感,調(diào)動起觀眾的真實情感。而在此? 基礎(chǔ)上,與《邦妮和克萊德》同年上映的《逍? 遙騎士》將實景拍攝和自然用光的新好萊塢電? 影特征發(fā)揚光大,自然光線下產(chǎn)生的串串光斑? 都被導(dǎo)演忠實地記錄下來,摩托小子在公路上? 行駛的鏡頭大多采用遠景,展現(xiàn)主人公與大自? 然融為一體的寓意。相比較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的? 美學(xué)幻覺而言,新好萊塢電影不再徘徊在戲劇? 真實和自然真實之間,而是重建起屬于自己的? 影像真實來反對精英文化、抵抗主流。
二、以歐洲藝術(shù)電影為鑒
20 世紀(jì) 40 年代初,意大利結(jié)束了漫長的 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憑借樸實、
[1]?? 出自陸川《體制中的作者 : 新好萊塢背景下的科波? 技研究 (上)》,《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報》1998 年第 3期。
真摯和深刻的藝術(shù)影片迅速崛起,對新好萊塢 電影運動產(chǎn)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除了上述新 好萊塢電影采用的實景拍攝、自然用光和去因 果鏈條的敘事手法外,非職業(yè)演員和長鏡頭的 運用同樣給新好萊塢電影以營造影像真實的借 鑒。例如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的代表作《偷自行 車的人》,導(dǎo)演德 ·西卡拒絕了明星演員而啟 用一名真正的失業(yè)煉礦工人出演那位絕望的父 親,讓觀眾更加感同身受。影片將偷自行車的 賊與男主角和他的孩子放置在一個畫面中,觀 眾通過長鏡頭看到了盜竊的完整經(jīng)過,正應(yīng)對 了巴贊提出的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他認(rèn)為鏡頭應(yīng) 該對準(zhǔn)“生活”,強調(diào)一種未加解釋的“現(xiàn)實 本身”。在新好萊塢電影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類 似的長鏡頭運用,例如《逍遙騎士》中,一個 近三分鐘的環(huán)搖長鏡頭不僅交代了周圍環(huán)境, 還使飯前所有人禱告的儀式更具真實感。又如 1967 年的電影《畢業(yè)生》中,長達一分鐘的 長鏡頭跟隨本恩來到依琳的學(xué)校,拉開至大全 景,再從只有本恩一人疊化至熙攘的人群。觀 者不會因為鏡頭語言失去戲劇化而感到無聊, 相反大多數(shù)青年觀眾從中感受到了新好萊塢電 影努力重建的影像真實。
20 世紀(jì) 50 年代末,來勢洶涌的法國“新? 浪潮”運動無疑成為 20 世紀(jì) 60 年代中后期興? 起的新好萊塢電影運動的一個參考模板,比照? 《邦妮和克萊德》與法國“新浪潮”導(dǎo)演戈達? 爾拍攝的《筋疲力盡》,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影片主? 角都是一對青年男女,偷盜和逃亡元素貫穿其? 中。《邦妮和克萊德》里大量的跳切、快速? 剪輯 [1]、手持拍攝和刻意暴露攝像機位置等技? 巧手段,都能與《筋疲力盡》中的“新浪潮” 特征一一對應(yīng),他們的目的如同戈達爾所言,? “藝術(shù)不是現(xiàn)實的反映,而是反映現(xiàn)實的過? 程”。再來看另一位法國“新浪潮”導(dǎo)演特呂? 弗的代表作《四百下》,影片刻意制造出粗糙? 隨意的外觀,最后的畫面是小男孩面朝大海,表情迷茫無措的特寫鏡頭。這種開放性的結(jié)尾? 在新好萊塢電影中運用廣泛,如《畢業(yè)生》在? 本恩和依琳乘上了不知開往何處的公交車后結(jié)? 束;馬丁 ·斯科塞斯的《出租車司機》在男主? 角查韋斯主動拒絕心上人,開著出租車消失在? 紐約街頭的夜色中落下帷幕。法國“新浪潮” 的電影美學(xué)革命是新好萊塢電影前行路上的引 ?航者,觀眾不再受限于故事的邏輯,在影像真? 實的引導(dǎo)下從感性回歸到理性,對美國社會進? 行發(fā)問。
最后,再來對照一下早于新好萊塢電影幾 年的新德國電影運動,來自慕尼黑的青年導(dǎo)演 們發(fā)表了著名的“奧伯豪森宣言”,他們與傳 統(tǒng)電影決裂,運用新的電影語言制作不同的電? 影。其中在思想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紋身》,? 講述了一名 16 歲的少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殺 害養(yǎng)父的結(jié)局,影片的色彩隨著情節(jié)的激化愈 發(fā)鮮亮,代表了西德青年一代對傳統(tǒng)空想社會 的抵抗。于 1972 年上映的新好萊塢電影《發(fā)條 橙》,同樣以大膽創(chuàng)新的風(fēng)格化色彩運用著稱, 影片主人公艾利克斯是一名有暴力傾向的少年, 卻在入獄接受治療后成了任人宰割的階下囚。? 無論是艾利克斯母親紫色的頭發(fā)還是被害者家 中大紅大綠的擺設(shè),色調(diào)越夸張,觀眾越能體 會影片中的沉重。艾利克斯在實施暴力行為時 總要配上他喜愛的高雅音樂,當(dāng)暴力成為一種 娛樂,影片有意為之的疏離感更能讓觀者產(chǎn)生 間離感,獲得影像帶給他們的真實。
三、新好萊塢電影中重建的個人化真實
跨入 20 世紀(jì) 70 年代,新好萊塢電影導(dǎo)演 群體漸漸以“電影小子”為他人所知,他們大 都畢業(yè)于電影學(xué)院,了解電影美學(xué)、電影攝像
[1]?? 出自李薇《淺析好萊塢經(jīng)典電影的剪輯技巧》,《傳 播與版權(quán)》2017 年第 4 期。
及電影史,他們是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傳統(tǒng)的仰慕 者,是歐洲電影運動的擁護者。1972 年起,科 波拉拍攝的《教父》系列收到的良好反響令人 矚目,該片成為黑幫類型片和家庭傳奇劇相混 合的模板,受眾群體囊括了憤世嫉俗的青年、 藝術(shù)電影鑒賞家和主流觀影群體。我們能夠看 到善良與險惡、家庭與社會、文明與暴力等諸 多二元對立的沖突。就暴力場面而言,影片中 最激烈的一場戲是背叛者路卡布拉西被勒死時 雙眼暴凸的特寫鏡頭,雙方甚至沒有打斗,也 不見血,類似長時間對準(zhǔn)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客 觀視角讓觀眾直接參與暴力過程。幾乎所有混 戰(zhàn)都去除激烈的打斗,這種單方面審判的暴力 手段成為科波拉個人化的影像表述,也間接說 明了新好萊塢電影運動區(qū)別于其他電影運動的 獨特性。
如果說《教父》系列是游離于外界體制的 專制個體,那么從 1975 年斯皮爾伯格《大白 鯊》的成功賣座,我們可以看出各個社會階層 開始走向合作,代表政府的警長布羅迪和代表 知識精英的海洋學(xué)家胡泊存活下來,而最終代 表個人主義的老水手奎特葬身鯊口。影片通過 精準(zhǔn)的影像節(jié)奏調(diào)動起觀眾的情感,雖然那時 沒有數(shù)字技術(shù)的加持,機械模型大白鯊仍然能 達到完美的驚嚇效果。除了對新好萊塢電影影 像手法的成熟運用,可以說人們似乎更加認(rèn)同 隱藏在《大白鯊》影像中的真實表意。從 20 世 紀(jì) 60 年代末《邦妮和克萊德》《逍遙騎士》 對向往真正自由的探討,到《畢業(yè)生》對年輕 人生存異化的迷惘,再到《教父》系列對社會 制度的抵抗,1973 年“水門事件”使美國群眾 的信仰大廈倒塌,1975 年美國在越南戰(zhàn)爭的 失敗,這些社會現(xiàn)實都直接與新好萊塢電影重 建的影像真實產(chǎn)生指向性的聯(lián)系。作為德國電 影紀(jì)實理論學(xué)派的主要人物,克拉考爾強調(diào), “其他藝術(shù)消化素材,電影藝術(shù)展現(xiàn)素材”。
當(dāng)我們再次回到戰(zhàn)后歐洲電影運動的語境下,新好萊塢電影里重建的影像真實與前者 要求的“真實”確有不同。無論是法國“新浪 潮”、意大利新現(xiàn)實還是新德國電影運動,他 們更偏向于新聞式的直接記錄,在美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 域發(fā)展其影像真實,相較新好萊塢電影運動而 言,沒有那么明顯的社會焦慮表達。《大白鯊》 和 1976 年斯科塞斯的《出租車司機》已經(jīng)將不 同階層進行了現(xiàn)實聯(lián)系,不再只局限于青年觀 影市場,力求通過影像真實重建每個個體對應(yīng) 的意識形態(tài)機制,引起更廣泛觀眾的共鳴。
四、結(jié)語
20 世紀(jì)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新好萊塢 電影在短短十余年時間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它面對曾經(jīng)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建構(gòu)的真實影像世 界,拿起歐洲藝術(shù)電影的指揮棒,通過“電影 小子”等一批新導(dǎo)演影像手法的融合革新,重 建起一棟名為“影像真實”的高樓。此時的美 國人民面對動蕩不斷、紛爭迭起的社會,身處 制度、經(jīng)濟、文化的矛盾旋渦,且高樓最底層 的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地基已無力承受外部社會的 多重震蕩。人們踏上新好萊塢電影效仿歐洲風(fēng) 格的旋梯,透過影像的窗戶直接觀看現(xiàn)實世界 的種種問題,干凈的玻璃投射出不加過濾的真 實,每向上一層看到的影像就越完整、越直接, 高樓里容納的群眾也就越來越多。新好萊塢電 影導(dǎo)演們也愈發(fā)成熟,他們不再需要達到戰(zhàn)后 歐洲電影運動的審美高度,而是需要契合美國 當(dāng)時社會的文化圖景,結(jié)束新好萊塢電影工程, 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在重建的高樓里找到與個 體相對應(yīng)的影像真實。
[ 作者簡介 ] 金紫宸,女,漢族,浙江寧波人, 上海師范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戲 劇影視編導(dǎ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