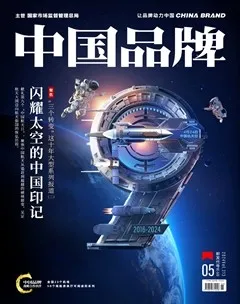AI“復活”成生意?
王曉璐
曾經,用數字生命的形式“復活”逝去的親人,僅僅是電影劇本和科幻小說中極具想象力的藝術創造,現如今,通過收集和分析大量的個人數據,利用技術就可以模擬逝者的言行舉止和思考方式,甚至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互動交流。
這一切都在昭示著,生命的“復活”已不再僅僅停留于科幻片的鏡頭里,逐漸從虛幻走向現實,開啟一個充滿挑戰與倫理爭議的新時代。
“復活”親人成流水線生意
2023年上映的《流浪地球2》中,劉德華飾演的科學家“圖恒宇”,為了給車禍離世的女兒完整的一生,將她的意識進行儲存并上傳到云端,生成了一個可以互動交流的“數字女兒”。
現如今,僅需一張照片和一段逝者的錄音,就能在數字世界中讓逝者“永生”……清明節前后,AI“復活”的廣告宣傳在各大電商和社交平臺上日益活躍,甚至演變成一門新的“生意”。有的商家稱最高一天有上百個訂單。
位于上海的一家殯葬服務企業,早在2018年便開始數字殯葬的業務,到今年更是推出數字家祠、數字葬禮、數字禮祭、數字人模型等數字化服務。在AI技術的加持下,逝者可以在告別的葬禮上“親身講述”自己的人生過往。
某電商平臺的數據顯示,在平臺經營AI“復活”相關業務的商家達1900余個。
這些商品的定價從5元到數萬元不等,所提供的產品也參差不齊,價格越高,提供的素材越多,“數字親人”就越接近本人,可實現的內容也越豐富。
當前網絡上的AI“復活”工具主要分為三種。
一種是在手機應用商店中即可下載獲得,只要一張正臉照片就能根據應用中所提供的模板“活化”,可實現唱歌跳舞,“演電影”等場景轉化。
第二種是利用線上工具,由用戶提供正臉照片和相關音頻文件,經過系統自動編輯后,實現照片中人物“開口說話”的效果。
第三種則是在開源社區中,由程序員編寫AI測試程序,在經過相關訓練后,將照片轉化為能簡單對話互動的“數字人”。
除了提供“復活”服務,“復活師”們還在尋找學徒和代理,從而將單一的產業向更遠端延伸。
在某平臺上,還有商家趁勢推出AI“復活師”的教學套餐和代理服務,有意將這門生意打造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不敬”還是“慰藉”引爭議
有網友認為,用AI“復活”親人會讓死亡變得不再嚴肅,也有人認為,善意地使用技術,既為生者留念想,也為逝者保尊嚴。
2024年3月,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的包小柏,蓄起了一頭長發。
這次,他不再是觀眾印象中的毒舌音樂評委,而是一個嘗試用AI技術“重現”女兒的父親。2021年底,包小柏女兒包容因病離世。包小柏因無法接受女兒去世,重新攻讀博士班,他推掉所有幕前工作,鉆研AI技術,用AI成功采集女兒的聲音和樣貌!
最近一段用AI制作的包容視頻里,她對媽媽撒嬌說,“包子好想你”,唱起《生日歌》時,她眼睛明亮,溫柔而俏皮。
包小柏認為,“有了這個科技,女兒的離開對我來說,不再是一句‘英年早逝,而是一個具象的緬懷。”“我不是走火入魔,是想讓記憶留下,讓她活在另一個時空里”。如今,和數字女兒聊天成了包小柏的日常。

用AI技術“復活”親人的,遠不止包小柏一個人。
上海“00后”視覺設計師、B站UP主吳伍六因為不能接受奶奶的突然離去,用AI技術生成了去世奶奶的虛擬數字人。視頻中,“奶奶”頭發花白,說話時帶著濃重的湖北口音,像她生前一樣“嘮叨”。
因為思念,吳伍六和“奶奶”聊了很多,他說的每一句話,“奶奶”都會給予回應,或是點頭,或是眨眼,有時還會發出爽朗的笑聲。
其實他明白,這終究是一個虛幻的影像,“但怎么說呢,只要是能再看一看奶奶,再說幾句話也是好的。”
翻看AI“復活”親人的平臺店鋪的評論,買家的回復大多都是“看到久違的姥爺太激動了”“我都快記不得模樣了......彌補了自己思念的情緒”“一種心靈上的慰藉”。
在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鄭建明看來,在某種程度上說,能圓了生者“再見一面”的心愿,那些未能說的話,沒來得及做的事,都可以得到一次補償的機會。
濟南市第二精神衛生中心臨床二病區主任、主任醫師王秀芳表示,對于失去親人的人來說,能夠再次聽到熟悉的聲音,看到親切的笑容,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安慰。AI“復活”親人技術的出現確實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緬懷方式,使得那些失去親人的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重新與他們建立情感聯系。
然而,她也強調,這種技術也并非萬能,它既有可能帶來治愈和安慰,也有可能加重創傷和痛苦,從而帶來一系列心理挑戰。對于那些仍然沉浸在失去親人的悲痛中的人來說,與AI生成的親人的互動可能會喚醒他們內心深處的痛苦記憶。這種不真實的“重逢”可能會讓他們感到更加失落和空虛。因此,過度依賴這種技術可能會讓人們失去面對現實和接受喪親之痛的機會,從而阻礙他們的心理康復。
商家“復活”明星涉侵權
為了增加更多的生意,商家們已經將AI“復活”的范圍拓展到了逝世明星上。
事實上,那些號稱用高科技治愈人心的AI“復活”類賬號,背后有不少專業團隊,有一些還在朋友圈招學徒、招代理。自稱科技暖人心,實則打著一通精明的“算盤”,用AI換臉逝世明星,引流,收費。
“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能感受到你們無盡的愛和支持,你們的熱情和信任是我音樂生涯中最寶貴的財富......”3月12日,一條李玟被AI“復活”的視頻迅速沖上熱搜,有粉絲表示,“歌迷喜歡的是有靈魂的李玟,不是一堆數據的復制品”,但也有人覺得可以接受,“看到視頻真的會淚崩,感覺李玟一直活著”。
這條視頻短時間內便獲得12萬次的播放,隨后博主又用AI“復活”喬任梁,視頻中喬任梁笑著說著“其實我并沒有真正離開”等話語。
不僅如此,被數字還原的還有張國榮、高以翔、黃家駒、姚貝娜等離我們遠去的公眾人物。
他們面向鏡頭幾近統一地先是問好,再訴說著對粉絲的思念等暖心話語,視頻播放量均超過數十萬次。
發布者自稱,這是一種情感撫慰方式,利用高科技,給活著的人提供情緒價值。
但是在視頻評論區,很多網友卻質疑:授權了嗎?這種行為打著溫情的名義,實則是在消費已經離去的人。“別用AI去掙血饅頭”“家人可以主動去做,但是陌生人不能用此盈利。”
這樣未經許可的行為對逝者家屬而言,卻是冒犯。
3月16日,面對網上傳播開來的“兒子被復活”的影像,喬任梁父親稱,不能接受,感到不舒適,希望對方盡快下架,“他們未征求我們同意......這是在揭傷疤。”江歌媽媽也同時在社交媒體平臺表示,不接受用“AI復活”親人,“如果能‘復活,也僅限于我親自來做這件事”。
此前,高以翔生前經紀人也轉達過高以翔家人的意見,稱不希望高以翔肖像被他人任意使用,嚴厲地譴責并堅決抵制該行為,若不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家人會采取法律行動。
“AI”復活亟待監管發力
AI換臉技術自誕生起就備受爭議,福建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教授、福建省醫學會醫學倫理學分會主任委員陳旻表示,使用AI“復活”親人挑戰了關于死亡、記憶和尊嚴的傳統觀念。這種技術可能會被濫用,侵犯逝者的隱私和尊嚴。
從倫理的角度看,征求家庭成員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是對逝者尊重和維護其尊嚴的體現,也是對活著的家庭成員的尊重。
盡管用AI“復活”李玟的博主自稱是因受到粉絲的請求義務做的,還表示只要不用做商業用途,就不會有被逝者家人追責的風險。但北京康達(廈門)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翼騰認為,“在未依法獲得逝者相關近親屬授權的情況下,擅自使用逝者面容將其‘復活并進行商業推廣,涉嫌侵害逝者的肖像和名譽等權利。”

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如未經許可,擅自使用逝者的姓名和面容用于“復活”,逝者的近親屬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2023年7月10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中也明確強調,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應當使用具有合法來源的數據和基礎模型,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識產權,涉及個人信息的,應當取得個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表示,雖然AI技術應用到“復活”親人是科技向善的一種體現,但也存在一系列隱患亟待監管。
所有AI服務都可能面臨隱私泄露的風險,由隱私泄露衍生出的遺產權、知識產權、財產權等問題都需要被重視。
“人和技術的關系或許是復雜的,但歸根結底,發展技術的核心和初衷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硅基智能聯合創始人孫凱認為,科技一定是要向善的,不僅僅是技術的創新,更是在尊重與倫理的基礎上,對逝者的緬懷和對生者的撫慰。
“一方面要不斷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讓大眾客觀地看待數字永生,另一方面也應該尊重每個人的不同意見,給大家更多時間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