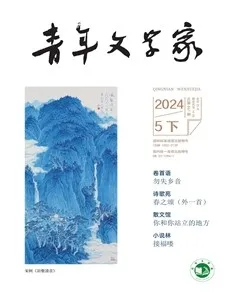傳記批評視角下《邊城》與《伊豆的舞女》的比較研究
寧夏 李官福
1934年,中國文學大家沈從文以“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為小說背景,創作了充滿人性美的作品《邊城》。而早在八年前,日本文學泰斗川端康成以自身經歷為原型,創作了昭和時代的青春之歌《伊豆的舞女》。兩部作品都描寫了朦朧期的少男少女情,通過少女相似的愛情悲劇奏唱一曲溫婉而凄美的女性之歌。
沈從文和川端康成作為同時代的東亞作家,依據自身的創作經歷不約而同地在少女的愛情中展現了亞洲文化里男女情感的內斂與含蓄,透露著相似的靜美與隱痛。在中日兩部作品中,我們不僅看到相似愛情悲劇的清郁之美,還看到女性與自然的融合之美,人物和諧的人性之美,這一切看似渾然天成,但處處精雕細琢。作品中所透露的情與哀與作家的親身經歷或文學世界密切相關。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采取平行研究的方法,從傳記批評視角出發分析作家與作品的聯系,以及兩部作品所體現出的相似的自然美、人性美和愛情美,以期更深入地認識兩位作家的文學世界,感知不同地域的文學魅力。
一、《邊城》與《伊豆的舞女》的梗概
及可比性
傳記批評注重探尋作品與作者之間的聯系。在城鄉沖突和新舊文化沖突的背景下,沈從文于1934年發表了中篇小說《邊城》。作品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邊界的茶峒為故事背景,講述了翠翠與儺送無果的純真愛情。川端康成于1926年發表了《伊豆的舞女》。小說講述了“我”因無法忍受“孤兒根性”,獨自一人踏上了前往伊豆小鎮的旅行。在旅程途中邂逅了舞女熏子,舞女一家對“我”表達的善意撫慰了“我”孤獨而憂郁的心靈。“我”與舞女熏子互相萌生愛意,但這剛泛起的愛情也如翠翠與儺送一般無果,最終,“我”與熏子分別。
從傳記批評視角來看,兩位作家在創作的不同層面呈現出偶然的一致性。首先,兩位作家都注重將少女的形象與自然風物聯結,揣摩少女在愛情面前的含蓄與羞澀。其次,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和川端康成筆下的伊豆是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統一。作品在自然美中彰顯人物形象的美,凸顯作家對自然美的熱愛和人性美的追求。最后,是民族鄉愁的相似性。兩位作家站在各自的國土上思考相似的民族家園重建的理想。此外,因作家的生活經歷和面對文化沖突下自主選擇的不同,反映到作品中就是在女性與自然的融合、對待事物的心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而有同有異,便有了比較的基礎。
二、《邊城》與《伊豆的舞女》的相似性
(一)自然美
沈從文的《邊城》在建構“邊界”,回避現實的污穢,走向自然,走進被山水浸潤的茶峒。川端康成的演講《我在美麗的日本》中提及,他眼中的日本是那個擁有古典文學意象的日本。日本受惠于大自然的山川日月,最初美的意識來自對人與自然的共生,在文學作品中反映自然的美是日本作家的本能表現。
《邊城》中的茶峒依山而建,一泉溪水繞茶峒,滋潤萬頃青山,溪水清晰見底,游魚可數,青山之間溪流作弓背,山路作弓弦,青山綠水裝飾茶峒的風光景色,盡顯自然本色。溪水浸潤了山城,也使得這里的人們溫潤而富有靈氣。翠翠是沈從文筆下自然的女兒,自然養她、育她,使她像嫩綠的翠竹,像清澈的溪水,像山頭的黃麂,一雙光光的眼睛透出少女的青澀與純凈,將人渾濁的心靈洗滌干凈。伊豆也如茶峒一般,山路迂回曲折,驟雨籠罩著杉樹林,群山空翠,竹林蔥蘢,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隨著“我”與熏子一家一同前行到下田,一幅村鎮與自然交雜的風景圖在移動。熏子潔白的胴體與修長的雙腿,站在那里宛如一株小梧桐。她像梧桐,像花,像自然界里的草卉花木,純粹而美好。
(二)愛情美
沈從文在《湘西散記》中說:“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小女孩脫胎而來。”沈從文在《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自傳中提及:“我懂得這個有喪事女孩子的歡樂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純厚和愛好一樣多一樣深切。”“喪事女孩子”是翠翠,“你”正是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沈從文塑造翠翠時,取絨線鋪女孩的品性,取喪事女孩生活的必然,取妻子性格的樸素式樣,三者合一。川端康成于1918年到達伊豆遇到舞女一行人,1922年再次到伊豆寫成回憶錄《湯島的回憶》。《伊豆的舞女》就是根據回憶錄中這一部分于1925年末到1926年初改寫而成的小說。1922年,川端康成遭遇戀愛失敗,與其訂立婚約的伊藤初代背棄了他,他的失意與痛苦只能通過回憶錄得到療救。鄉下人和失戀人在兩個美麗但不幸的故事中,表現出長期壓抑的痛苦情感,這種情感需要借這兩個美麗的愛情故事宣泄一番,內心才能達到一種平衡。
翠翠為了看到迎婚送親的喜轎,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她內心也在憧憬著愛情的到來。當天保托人說媒時,翠翠雖佯裝無心,但“耳朵卻把每一句話聽得清清楚楚”。她心里念的是端午托人送她回家的儺送。翠翠與儺送的邂逅,少男少女互生情愫,念念不忘。翠翠被邀到船總家看龍舟,內心抵不住地高興。本以為天保和儺送的唱歌求婚會讓翠翠采摘到代表愛情的虎耳草,但隨著天保的意外去世以及儺送的離開,這段互生情愫的愛情還未真正開始就戛然而止。在《伊豆的舞女》中,熏子同“我”下棋,“她顯得有些不自然,那秀美的黑發幾乎觸到我的胸膛。她發覺后,臉倏地緋紅了”。“我”想邀請熏子一起看電影,但千代子拒絕了,百合子也一聲不吭,阿媽也不允許熏子一同前往。熏子茫然若失地回到“我”身邊,當“我”離開時,她只是默不作聲地撫摸著小狗,“我”走在街道上,眼淚不禁流了下來,這段“情思”也隨著“我”的離別而深深埋藏于心。情思似云似霧,為茶峒和伊豆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三)人性美
沈從文在《邊城》中希望人們看到鄉土中國的另外一面,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從文文集》)。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在顛簸中前行,西方文化的涌進使得日本固有的傳統文化遭到巨大的沖擊。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繼承了日本審美傳統的“物哀”精神,以日本傳統的哀婉為基調,呈現日本的古典美、風情美和人性美。
《邊城》中的老船夫不論晴雨,必守在船頭,且從不收過渡人的錢。船總順順雖富貴,但不貪婪驕奢。凡向他求助,必盡力幫忙。天保和儺送兄弟倆在追求愛情時,也是胸襟磊落。這淳樸的民風和人性美滲透到了邊城的每個角落,處處散發著醇美而又樸實的幽香。《伊豆的舞女》中的熏子頭上梳著一個大發髻,發式古雅而又奇特,把熏子那鵝蛋形臉龐襯托得玲瓏小巧,十分勻稱。川端康成隱藏現實舞女的缺點,聚焦舞女的古典美,彰顯傳統的古典風情。“我”眼中的巡回藝人并不低賤,她們傳遞出的善意使得“我”與巡回藝人的關系十分親密。所以,當聽到熏子夸贊“我”是個好人時,“我”認為這是天真地傾吐情感的聲音,內心歡喜。即便老太婆用輕蔑的語氣回答舞女的落腳處,“我”也愿意同舞女一家同行,“孤兒根性”的心靈創傷被美好的人性所感染而被治愈。川端康成在作品中表達出對巡回藝人命運的同情,正如他在《文學自傳》中所說,他被卑賤的美所吸引,煙廠女工下班比女子學校放學更帶有抒情味。
三、《邊城》與《伊豆的舞女》的差異性
(一)少女與自然的關系
沈從文在翠翠外形的處理上放大了翠翠的自然性而縮小了社會性。翠翠為人天真活潑,儼然一只小獸物。對翠翠“野性美”的描寫最能體現其與自然的交融。加上翠翠以自然的景物為娛樂的對象,蘆葦楊柳、蚱蜢夏蟬、青蔬果園等,是其生活不可缺失的部分。在翠翠身上也多次出現了母親的影子。她愛母親如同愛自然一般,母親也如茶峒的山水一直陪伴著她,貌似自然便是她的母親。因此,《邊城》的自然是母性的自然。而在描寫熏子時,作品更多體現的是熏子少女的特性。作品在描寫伊豆的自然風光之后緊接著寫“裸體女子”的出場,通過熏子的神態、動作以及背后的心理和伊豆這鮮艷明亮的風光相扣合,展現自然美與女性美的相互映襯,彼此獨立。熏子和阿媽的關系可見是疏離的,并未展現自然是永恒的母性。
(二)生活態度的迥異
沈從文的少年經歷使他擁有豁達的心態,從容面對生活發生的種種變化。他以一個“全能敘述者”的身份去講述以翠翠為中心的故事,面對儺送的離開,翠翠的等待,“我”也無能為力,不能把控他們的命運,只能留白,給讀者無盡的想象和期待。川端康成作為“參加葬禮的名人”經歷了太多的離別傷逝,孤兒的生活經歷使川端康成敏感而內向。熏子同“我”在聲聲笛聲中離別,《伊豆的舞女》也籠罩在無盡且濃郁的悲哀中。
四、《邊城》與《伊豆的舞女》異同性的原因探析
(一)孤獨的心靈
作為一個“鄉下人”,家庭的敗落、隨軍的痛苦與都市文化的沖擊,使得沈從文面對繁華的京城時難以融入,自卑感油然而生。川端康成也是孤獨的。他的孤獨主要來源于家庭生活。童年的悲涼、體弱的病痛與漂泊他鄉的苦楚造成了他寂寥的心境。孤獨和哀傷與川端康成形影相隨。作家是孤獨的,他筆下的人物也是孤獨的,抑或作家孤獨的影射。翠翠是個“孤兒”,爺爺對翠翠的愛不能深入內心,翠翠對儺送的情也沒有實現心與心的交流。最后,翠翠只能望穿秋水,等待一艘傷心的渡船。而在《伊豆的舞女》中,“我”也是孤獨的。“我”因不能忍受“孤兒根性”而到伊豆旅行,即便與熏子的相處很幸福,最后也只能分別,“我”再次孤獨地踏上新的旅程。孤獨的心靈使得作家親近自然,更多地描繪出自然風光的美。
(二)人性的缺失
沈從文和川端康成的經歷與生存環境雖然不同,但這種差別形成了兩人相似的內心缺失。川端康成想在伊豆創建“純美世界”,沈從文想在湘西構造一座神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我的頭腦恍如變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來,后來什么都沒有留下,頓時覺得舒暢了。”《邊城》和《伊豆的舞女》最后的結尾耐人尋味,讓人歡喜于兩人的情竇初開,哀嘆兩人的無奈別離,情思隨渡船遠去,如清水滴流,回味這美麗的消逝。
但在人性光輝構建上,兩位作家又有些許的不同。川端康成偏重于個人層面;沈從文更偏重于鄉土中國置身現代化的危機,致力民族道德的重建。故兩人在作品中對妓女或藝人的描述也大有不同。沈從文在《邊城》中用“渾厚”形容妓女,將其從道德層面解脫出來,還原妓女身上可貴的情;而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描述了社會對藝人充滿了偏見與歧視,不僅在村口處立牌禁止藝人入內,而且在言語中充滿了輕蔑、鄙視之意。也正是如此,沈從文的《邊城》更似人性的烏托邦。
(三)沖突下的不同選擇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和日本處于東西方文化交匯碰撞的階段,兩位作家在文化沖突的批判中走向了兩條不同的道路。川端康成對西方文化的批判是溫和的。他希望實現日本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精神的融合,在作品中呈現內在的和諧。《伊豆的舞女》便是新感覺派的產物。在小說的結尾處,“我”的頭腦如清泉涌出,實則是思念滿溢。由直觀感覺“我”的思念化作清泉,強調新奇的感覺和瞬間的印象。沈從文面臨更多的文化沖突: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舊文化與新文化的沖突,先楚文化與苗文化的沖突。因此,他對文化的批判是廣泛的。他堅持本土文化的“正統”地位,將苗文化的血性注入先楚文化中,批判的鋒芒指向現代文明的弊端。此外,川端康成深受佛家遁世的影響,主張遠離現實的困擾。沈從文受儒道思想的影響,道家出世的思想使其在作品中輕現實、重幻想,故《邊城》似桃花源,美得不真實。儒家的入世思想使他不愿放棄文學所引起的社會療救的作用。因此,《伊豆的舞女》更多表現的是脫離社會生活,孤立地描寫身邊的瑣事和心理活動;《邊城》則偏重讓世人看到鄉土中國的另外一面,引發文學對現代人的療救。
沈從文和川端康成根植于各自的民族土壤,結合自身的經歷,將人物置于自然中,刻畫了美而不艷的少女,借少女的愛情故事排解作家長期壓抑的孤獨情感,力圖創建人性的烏托邦。而生活經歷和生活態度的迥異,作家在沖突下的不同選擇也使得作品在寫作手法和思想內容上呈現一定的差異性。從傳記批評角度研究文學作家和作品,也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人深入了解在山水和愛情交織下,充滿人性光輝的茶峒和伊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