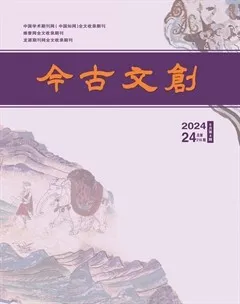論《西廂記》中的審美表達(dá)
馮霞 姬婷陽
【摘要】元代王實(shí)甫的《西廂記》歷來被視為中國古典戲劇的經(jīng)典著作。本文旨在以四組相反相成的元素來鑒賞其審美表達(dá)。第一部分是佛教與儒教的對立與交融,形成“和諧統(tǒng)一美”的審美表達(dá);第二部分是情與禮的斗爭與交融,形成“均衡美”的審美表達(dá);第三部分是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儒文化的斗爭與交融,形成“對立美”的審美表達(dá);第四部分是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矛盾與斗爭,形成“反差美”的審美表達(dá)。從這些相反相成的結(jié)構(gòu)要素中可以看出真與善的美、人性美、反差美等審美屬性,它們共同形成一個(gè)和諧統(tǒng)一的整體,構(gòu)成一種“統(tǒng)一均衡”的美感。本文提供一種新的分析角度探究《西廂記》審美表達(dá)。
【關(guān)鍵詞】審美表達(dá);北方草原文化;《西廂記》;和諧美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4-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4.001
美國美學(xué)家阿恩海姆將“張力”一詞引入美學(xué),認(rèn)為張力既是蘊(yùn)含于對象中的相互牽引力,這兩種力的相互作用,使人從靜態(tài)的藝術(shù)等審美對象中能夠看到似動、運(yùn)動;使人從各種力的相互作用中,使小說的意義空間和情感空間無限敞開,產(chǎn)生了富有沖擊力的審美效應(yīng)。而《西廂記》中正存在著幾種相對立的元素,使得《西廂記》具有了審美屬性,它們構(gòu)成了《西廂記》中不同的審美表達(dá)。
對于《西廂記》中的反封建思想。1921年郭沫若撰寫了《〈西廂〉藝術(shù)上之批評與其作者之性格》,認(rèn)為《西廂記》是有生命的人性戰(zhàn)勝了無生命的禮教的凱旋之歌。王兆才在《情與理的沖突——談〈西廂記〉中崔鶯鶯形象的塑造》 (發(fā)表于1994年)中,通過分析鶯鶯形象,寫出了《西廂記》中愛情追求與儒家禮教之間的沖突。周志波、談藝超在《元明清戲曲中的花園意象》 (發(fā)表于2008年3月)中指出花園擺脫了封建禮教的束縛,是人的原始欲望生發(fā)的隱喻式場景,滋養(yǎng)了青年男女的愛情果實(shí)。杜瑤瑤在《論〈西廂記〉的情禮妥協(xié)與人倫重建》 (發(fā)表于2021年6月)中,指出《西廂記》表現(xiàn)以情抗禮的斗爭精神這種觀點(diǎn)經(jīng)不起推敲。她認(rèn)為王實(shí)甫把認(rèn)同儒家傳統(tǒng)文化作為前提,對情與禮進(jìn)行調(diào)和,強(qiáng)調(diào)對人倫秩序的重建。筆者對《西廂記》的反封建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從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對立角度,再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的社會背景,探尋蘊(yùn)含在《西廂記》中的均衡之美。
對于《西廂記》中的禪意。孫愛玲在《論〈西廂記〉惠明形象之禪趣》(發(fā)表于2016年9月)指出惠明修行全在心性上,充分彰顯了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康保成在《金批〈西廂〉》中的“無”字及其“綺語談禪”解謎探源》 (發(fā)表于2020年9月)提出“以文說禪”是《西廂記》本身的禪意和金圣嘆對它的挖掘與釋放。“以禪說文”,是金圣嘆對《西廂記》表現(xiàn)手法和藝術(shù)境界的高度概括,與唐宋以來“綺語談禪”的文學(xué)傳統(tǒng)一脈相承。這種繞路說禪的語言風(fēng)格,對于《金批〈西廂〉》也帶來了局限。這里涉及到《西廂記》本身的佛教禪意。本文創(chuàng)新點(diǎn)在于,繼承了上述論文的佛教禪意觀點(diǎn),同時(shí)發(fā)現(xiàn)了《西廂記》中,佛教與儒教兩種思想觀點(diǎn)存在交融斗爭的情況,在這種矛盾運(yùn)動中體現(xiàn)出和諧統(tǒng)一美。
對于《西廂記》中的草原搶婚習(xí)俗。楊波在《略論元明戲劇中的搶婚與收繼婚風(fēng)俗》 (發(fā)表于2015年3月)中認(rèn)為《西廂記》中就包含著少數(shù)民族搶婚的風(fēng)俗,包括明搶、暗搶、獨(dú)搶、爭搶等形式。馬會在《論金元兩代草原文化對“西廂故事”的介入》 (發(fā)表于2018年10月)中探討金元兩代草原文化在介入“西廂故事”時(shí)的不同表現(xiàn),對草原搶婚習(xí)俗和草原文化女性觀兩方面的介入進(jìn)行分析,指出由金到元草原文化對“西廂故事”的介入逐漸趨強(qiáng)。結(jié)合以上幾種觀點(diǎn),筆者認(rèn)為儒家禮教與北方草原文化在婚戀觀上也存在對立關(guān)系,體現(xiàn)出對立美。
筆者在《西廂記》中尋找對立的結(jié)構(gòu)元素架構(gòu)全篇,從《西廂記》佛與儒、情與理、北方草原文化與儒文化、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對立與交融中,探尋其中的審美表達(dá)。
一、《西廂記》中的“和諧統(tǒng)一美”
《西廂記》中“和諧統(tǒng)一美”的審美表達(dá)主要表現(xiàn)為佛教與儒教的交融對立。佛教自唐代起分為南禪宗和北禪宗,安史之亂后,南禪宗壓倒北禪宗并盛行一時(shí)。南禪宗代表人物惠能反對北禪宗的禁欲苦修,他認(rèn)為本心即佛,只要本心不變,一悟即至佛。元代時(shí)期,禮崩樂壞,科舉停考,這時(shí)南禪宗提倡的無拘無束、放蕩不羈正是士大夫夢寐以求的境地,使得文人得以逃避現(xiàn)實(shí),偏安一隅。在《西廂記》中,佛教思想和儒學(xué)思想存在對立交融關(guān)系,從這兩種張力的運(yùn)動中,可以見出其中的美感,挖掘出無限的審美意蘊(yùn)。
代表佛教的住持法本和不忌酒肉的和尚惠明,積極為張生與鶯鶯這段愛情牽絲引線。當(dāng)孫飛虎兵圍普救寺時(shí),法本智激惠明,讓惠明送信解圍。白馬解圍后,張生問法本自己的親事如何,法本答道:“鶯鶯親事擬定妻君。”可見法本是張生婚事的堅(jiān)定支持者。具有俠義心腸的惠明,在普救寺被圍時(shí),他挺身而出,突圍送信,為崔張婚事保駕護(hù)航。而代表封建綱常倫理的老夫人卻是這場愛情的最大阻力,一句“三輩不招白衣女婿”,就是儒學(xué)中積極入世、仕途經(jīng)濟(jì)觀念的最佳詮釋。代表佛教的法本與惠明是這場愛情姻緣的有力助攻,他們愿意成人之美。而儒家仕途經(jīng)濟(jì)的代言人——老夫人,棒打鴛鴦,是這場姻緣的阻攔者。這就是愛情姻緣與仕途經(jīng)濟(jì)這兩種結(jié)構(gòu)成分的斗爭,是佛與儒兩種力的第一重對立。
南禪宗不拘泥于外在修煉形式,不過分執(zhí)著于守戒,念經(jīng)、禮懺、參禪、守戒等。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惠明不看經(jīng)禮懺、不戒酒肉,他身上有一種“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狂禪之風(fēng),不受任何世俗理念的羈絆,生活的無拘無束。與之相比,崔鶯鶯在禮教熏陶下長大,她的身心都被禮教束縛著。她看到張生的簡帖后,佯裝發(fā)怒斥責(zé)紅娘,聲稱這種簡帖侮辱了自己相國小姐的身份。張生跳墻赴約時(shí),她臨時(shí)變卦,翻臉不認(rèn)人。崔鶯鶯心理與行為的矛盾正說明了她內(nèi)心的掙扎。她的自由思想一次次與儒家秉持的男女之大防思想相斗爭,所以才會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從兩個(gè)人的不同行為可以看出,文本中存在遵從本心與遵從禮教這兩種思想的斗爭,這兩種成分的斗爭就是佛與儒兩種力的第二重對立。
王實(shí)甫通過以上兩重對立來表現(xiàn)佛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的交融、斗爭,兩種思想文化都統(tǒng)一蘊(yùn)含在文本中,雖然有斗爭,但也相互交融。比如用兩種文化的斗爭來表現(xiàn)王實(shí)甫本人的不同性格側(cè)面,他對儒家禮教文化充滿矛盾立場,使他游走于無拘無束的佛家禪意思想中。再如通過表現(xiàn)惠明的向善、向真,弘揚(yáng)佛與儒共同的“真善美”審美理念,這是兩種文化的融合。通過兩種思想文化交融與對立構(gòu)成了“和諧統(tǒng)一美”的審美表達(dá)。
二、《西廂記》中的“均衡美”
《西廂記》中“均衡美”的審美表達(dá)主要表現(xiàn)為情與禮的交融對立。食色性也,即使是君子也不能免俗。王實(shí)甫在《西廂記》中表現(xiàn)了人性情欲與克己復(fù)禮之間的交融與斗爭,主要是從人物行為以及花園這一意向來表現(xiàn)的。
鶯鶯與張生在普救寺初見時(shí),張生看見鶯鶯就被迷住,大膽上去自我介紹,而鶯鶯作為一個(gè)大家閨秀,不僅沒有立即回避,反而緊緊注視著張生,當(dāng)紅娘拉走她時(shí),她還頻頻回望。這時(shí)兩個(gè)人全然把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禮教道德忘之腦后。這是情欲與禮教的第一次交鋒。
在奉行禮教的古代社會,男子在前堂議事、社交,女子只能在閨閣、花園等隱蔽的后庭活動。因此遠(yuǎn)離社交場合的“后花園”通常是待字閨中的小姐們僅有的活動空間。《西廂記》第二折寫道崔老夫人治家嚴(yán)謹(jǐn),內(nèi)外并無一個(gè)男子出入。應(yīng)門五尺之童非召不能進(jìn)入中堂。可知,在禮教森嚴(yán)的大家庭中,女眷的活動空間很小并且受限制。所以就有了鶯鶯在花園上香的情節(jié)。鶯鶯在花園上香時(shí)許愿了三個(gè)愿望,一是愿亡父早升天界,二是愿老母平安無事,三是愿配一個(gè)如意郎君,雖然第三個(gè)愿望是出自紅娘之口,但從鶯鶯深深兩拜和倚欄長嘆的動作來看,鶯鶯并不喜歡崔老爺給她訂下的與鄭恒的婚約。這時(shí)候,墻外傳來鄭恒吟詩的聲音。一邊是崔老爺?shù)撵`堂,一邊是張生與鶯鶯月下和詩。兩個(gè)人,一個(gè)藍(lán)閨寂寞,一個(gè)芳春無事,彼此惺惺相惜。在守喪期間,鶯鶯與張生的愛情在花園這個(gè)隱秘空間悄悄萌芽,人性情欲與禮教道德又一次發(fā)生沖突。作為融合作家情感的審美對象,《西廂記》中的花園具有獨(dú)立于人物之外的審美意蘊(yùn),花園雖然束縛了鶯鶯的活動,但是花園中充斥著大自然的美景,各種植物煥發(fā)出勃勃生機(jī),仿佛是人性情欲張揚(yáng)的表征。花園為張生隔墻酬韻、翻墻私會、聽訴琴心提供了空間上的可能。所以從表層來看,花園指的是女眷私密的活動空間。從深層來看,花園催發(fā)了兩人愛情,是張揚(yáng)人性欲望的烏托邦,開拓出了一個(gè)與壓抑陳腐大宅子完全不同的藝術(shù)審美空間,所以顯出人性情欲與禮教道德的巨大審美表達(dá)。它的審美價(jià)值在于為男女主人公提供了相愛的最佳的場所,同時(shí)也具有思想文化意義:“弘揚(yáng)正常人性、健全人格發(fā)展”。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設(shè)置的張生“翻墻”情節(jié),表面上“墻”的作用是隔絕花園與外部世界,實(shí)際上墻是嚴(yán)守男女之大防的禮教道德底線。張生得到鶯鶯的簡帖后,翻墻赴約,這是對封建禮教底線的第一次挑戰(zhàn),雖然遭到了鶯鶯的拒絕斥責(zé),沒有成功,但是這一翻墻行為的情節(jié)設(shè)定加速了兩個(gè)人情感的發(fā)展。后來鶯鶯夜晚探望患相思病的張生,并且與之結(jié)合,這時(shí)這堵墻從思想層面被跨越,禮教的道德底線被打破,因此王實(shí)甫設(shè)定“翻墻”情節(jié),是沖破禮教束縛的道德文化的表現(xiàn)。
在人性情欲與倫理道德對立中,既有弘揚(yáng)人性自由描寫,又有“存天理滅人欲”表現(xiàn)的描寫,放縱人性與克己復(fù)禮這兩種力交融斗爭。讓我們看到鶯鶯對封建禮教的反抗與對自由人性的向往,因而具有了“人性美”的屬性,在兩者對立與交融中構(gòu)成了“均衡美”的審美表達(dá)。
三、《西廂記》中的“對立美”
《西廂記》中“對立美”的審美表達(dá)主要表現(xiàn)為北方草原文化與儒文化的交融對立。在《西廂記》中,張生和孫飛虎,一個(gè)書生一個(gè)武將,兩個(gè)人都想得到鶯鶯,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張生靠才華吸引鶯鶯,孫飛虎是靠武力搶奪鶯鶯。這其中蘊(yùn)含著“以才服人”和“武力搶親”這兩種對立的結(jié)構(gòu)成分,這兩種結(jié)構(gòu)成分對立的背后,蘊(yùn)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色彩。
首先是才子佳人小說的定位,就決定了男主角才子的身份地位,那么孫飛虎在故事中就是作為反派人物出現(xiàn),與正派人物張生形成對立,鶯鶯作為這場斗爭的勝利果實(shí)符號,得到她的方法就必定是男主通過考得狀元獲取社會地位,而不是野蠻武力的強(qiáng)取豪奪。
其次,儒家文化中,除了提倡仕途經(jīng)濟(jì)與綱常倫理的思想文化外,還有關(guān)于結(jié)婚禮制的文化,這一文化就與北方草原文化的婚俗傳統(tǒng)大相徑庭。擅文的張生得到鶯鶯的途徑是按禮制明媒正娶。在儒家典籍中婚姻總是與禮相輔而行,《詩·鄭風(fēng)·豐箋》:“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婚姻的本義是指嫁娶的禮儀。所以在儒家文化看來,只有按禮嫁娶而形成的婚姻才是正當(dāng)?shù)摹I梦涞膶O飛虎為了得到鶯鶯采取的方法是“搶婚”。搶婚涉及到蒙古族的文化,蒙古族自古便有搶婚習(xí)俗且一度盛行。因此,《西廂記》中元代搶婚民俗色彩十分鮮明。從宏觀角度來看,以張生為代表的儒生是象征中原一脈相承的儒家文化,孫飛虎則代表了原始野性的北方草原文化。表面上是武力搶親與才華求娶這兩種結(jié)構(gòu)成分的對立,實(shí)際上是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儒家文化這兩種張力的對立。
王實(shí)甫通過擅文擅武的對立、武力搶親與才華求娶的對立,展現(xiàn)出了儒家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交融、斗爭,這是兩種文化下不同的婚戀觀交融斗爭形成的“對立美”的審美表達(dá)。
四、《西廂記》中的“反差美”
《西廂記》中“反差美”的審美表達(dá)主要表現(xiàn)為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交融斗爭。花園僅僅為崔張?zhí)峁┝怂綍目赡苄裕瑥埳肴⒌铭L鶯,僅有花園這個(gè)要素還不夠,在封建社會,還需要一個(gè)能在社會立足的身份,才能與佳人相配。在《西廂記》中,現(xiàn)實(shí)與理想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
縱觀中國古代戲曲作品,幾乎都離不開“中狀元”的情節(jié)描寫,在《西廂記》中“狀元”這個(gè)符號的意蘊(yùn)十分耐人尋味。老夫人之所以不同意崔張婚事就是因?yàn)閺埳恰鞍滓赂F士”,所以老夫人提出的現(xiàn)實(shí)條件就是張生要高中狀元,也就是在社會上獲得一個(gè)可以立足的身份和名頭。
這樣看來,他要娶到鶯鶯,就要滿足老夫人的愿望,順從當(dāng)時(shí)封建社會傳統(tǒng)對貧民書生的要求。結(jié)局張生高中狀元,就是與老夫人站在了同一戰(zhàn)線,向封建社會傳統(tǒng)臣服。那么問題出現(xiàn)了,作者既然設(shè)置了“花園”場景符號來表達(dá)自己的愛情自由的理想以及沖破禮教束縛的愿望,為什么不讓張生抗?fàn)幍降祝瑤еL鶯私奔呢?為什么遵循封建社會傳統(tǒng),先金榜題名后洞房花燭?現(xiàn)實(shí)與理想之間構(gòu)成一種張力,這與古往今來的反封建主題形成巨大反差,原因如下。
元朝時(shí)期,科舉一度停考,在儒士做官問題上,存在民族歧視政策和權(quán)力分配不平等,這些因素導(dǎo)致文人地位驟降、境遇窘迫,甚至有過“十丐九儒”的說法。對于窮困潦倒的書生來說,私奔是最下等的選擇,其結(jié)局大概和魯迅的《傷逝》一樣,沒有物質(zhì)的愛情遲早會被雞零狗碎的生活消磨殆盡,在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下,與家庭決裂最后只能換來孤墳一座。對于走投無路的書生來說,“中狀元”是一道救命符。這就是為什么在元雜劇中,“狀元”符號常常是人物命運(yùn)或劇情矛盾的轉(zhuǎn)折點(diǎn),它可以使張生名正言順娶到崔鶯鶯。這樣來看,通過中狀元獲得社會地位,愛情與名利雙收,是元代文人的一種美好人生理想。《西廂記》“狀元”符號的審美意蘊(yùn)由此可見。“中狀元、娶佳人”的結(jié)局體現(xiàn)的正是古代文學(xué)大團(tuán)圓敘事結(jié)構(gòu)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既有惡劣現(xiàn)實(shí)的真實(shí)描述又有美好理想的展望,在兩者矛盾斗爭中形成了“反差美”。
總之,《西廂記》中的審美表達(dá)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gè)方面。第一方面,在佛與儒對立與交融中可以看到“真善美”理念的弘揚(yáng),這是兩種文化立場呈現(xiàn)的“和諧統(tǒng)一美”的審美表達(dá);第二方面,情與禮對立的背后是弘揚(yáng)健全人性與反封建禮教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這是弘揚(yáng)人性與克己復(fù)禮兩種思想形成的“均衡美”的審美表達(dá);第三方面,元代草原文化與儒文化交融與斗爭,這是兩種文化構(gòu)成的“對立美”的審美表達(dá);第四方面,在現(xiàn)實(shí)與理想對立中,現(xiàn)實(shí)越丑惡,理想就越美好,惡劣現(xiàn)實(shí)與美好理想之間形成“反差美”的審美表達(dá)。這些相反相成的結(jié)構(gòu)要素形成了一個(gè)統(tǒng)一和諧的整體,它們都具有美的屬性,《西廂記》審美表達(dá)就是表現(xiàn)在這些結(jié)構(gòu)要素并沒有單純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在配合比例上非常恰當(dāng)構(gòu)成了審美對象,使這些相反相成的結(jié)構(gòu)要素達(dá)到統(tǒng)一,共同服務(wù)于文本這個(gè)整體,體現(xiàn)了一種“統(tǒng)一”與“均衡”之美。
參考文獻(xiàn):
[1](元)王實(shí)甫著,吳曉鈴校注.西廂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
[2]趙炎秋.文學(xué)批評實(shí)踐教程[M].長沙:中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7.
[3]康保成.《金批〈西廂〉》中的“無”字及其“綺語談禪”解謎探源[J].文學(xué)評論,2020,(05):119-129.
[4]馬會.論金元兩代草原文化對“西廂故事”的介入[J].前沿,2018,(05):131-136.
[5]沈笑穎.從元雜劇書生形象觀照元代文人心態(tài)[J].前沿,2014,(05):228-229.
[6]孫愛玲.論《西廂記》惠明形象之禪趣[J].咸陽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6,31(05):117-120.
[7]李瑜,史繼東. 《西廂記》敘事空間的構(gòu)建與轉(zhuǎn)換[J].貴州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39(07):4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