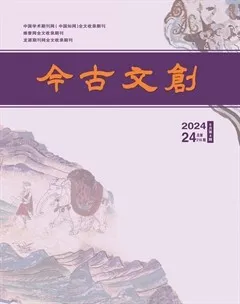品特戲劇中的共同體困境
李亞琴
【摘要】哈羅德·品特的戲劇作品從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三個層面書寫了戰后英國社會普通群體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狀態,呈現了共同體所面臨的困境,傳達了劇作家深切的共同體意識。
【關鍵詞】品特;共同體;困境
【中圖分類號】I561?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4-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4.015
基金項目:本文系馬鞍山學院校級重點項目(QS2020004)階段性成果。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品特(1930—2008)是戰后英國劇壇最負盛名的劇作家之一。品特生活于英國社會動蕩和轉型時期,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精神創傷和信仰危機,也見證了戰后英國社會變遷和新舊秩序交替下普通群體的生活遭際。他的作品聚焦小人物群體,關注人與人之間、個體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再現了“國家實力下降,社會高度分化和生存環境嚴重異化背景下的共同體困境”[1]56,彰顯了劇作家對個體與共同體關系的思考及其深切的共同體關懷。迄今為止,學界對于品特戲劇的研究如汗牛充棟,但對其戲劇中共同體表征的關注較少。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有機的生命體”,是一種“持久的和真實的共同生活”[2]71,“人們通過自己意志、以有機的方式相互結合和彼此肯定的地方,就會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共同體形式。”[2]88他將共同體分為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三種形式,其中共同體內成員的關系依次表現為親屬、鄰里和友誼。三種共同體互相關聯,呈階梯式遞進。本文借助滕尼斯對共同體的闡釋,剖析品特戲劇中不同形式的共同體生活,揭示其對共同體命運的關注。
一、血緣共同體:愛的缺失
滕尼斯認為個體之間的血緣紐帶是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因為家族親屬關系是“是一種植根于意志的形塑共同體的趨勢和力量”,“最有可能發展成共同體的萌芽”[2]77。母子關系、夫妻關系和兄弟姐妹關系衍生出來的共同體稱為“血緣共同體”。共同體成員之間互相依賴,休戚與共。“家”是品特戲劇中血緣共同體的主要表現形式。然而,“品特筆下的家多是些空殼子”[3]91,家庭成員并沒有因婚姻和血緣的締結而形成凝聚力,血緣共同體面臨分崩離析的情境。
品特戲劇中的婚姻主題隨其創作生涯的延續而一直處于變化之中,但整體而言,其作品中的婚姻生活中充斥著不和諧的聲音。在早期的“威脅喜劇”中,夫妻雙方常因拒絕交流或缺乏溝通而呈現出冷漠或疏離的狀態。如《房間》中,夫妻間的對話由于丈夫的沉默而變成了妻子喋喋不休的獨白;《微痛》中的丈夫因妻子的漠視而最終精神崩潰,家庭也隨之解體;《生日晚會》中單調、壓抑的交流方式更是將夫妻間孤獨、隔絕的狀態展露無遺。隨后的記憶戲劇中,夫妻之間大都夾雜著一個來自現實世界抑或是記憶世界中的插足者,從而對婚姻關系的穩定構成威脅。同時,這類戲劇中夫妻雙方均視婚姻為游戲,“背叛”成為婚姻的主旋律,進而背離了倫理道德的內核。《情人》無疑是呈現這類主題的典范之作。整部劇中,理查德和薩拉表面是恩愛和睦的模范夫妻,卻突破傳統倫理綱常,玩起假扮情人的“幽會游戲”,呈現了一種扭曲的婚姻關系,給觀眾帶來強烈的道德沖擊。在后來的《背叛》中,品特則更是直接呈現了夫妻雙方的婚外行為對婚姻倫理秩序的破壞,演繹了游戲與虛幻并存的婚姻本質。可以說,品特戲劇的夫妻關系中矛盾遠勝于情感關懷,彼此間無法構建和諧共生的家庭共同體。
血緣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為穩固的關系,親屬之間和諧融洽,親密無間。然而,品特戲劇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間互相傾軋,缺乏理解與支持,難以形成相互依賴、共享共生的狀態。《歸家》中便刻畫了這樣一個叢林般的原始血緣家庭,家庭成員之間因“領域之爭”而進行著蠻荒的蠶食戰爭。父親馬克斯試圖以父權制大家長的身份操縱和控制家庭成員以維持自己的權威地位,而家庭成員對此卻不以為意,肆意挑戰父親的權威。伴隨著長子特迪及其妻子露絲的歸家之旅,這個血緣家庭中的矛盾不斷升級,直至走向解體。面對長子的歸來,父親及兄弟非但沒有表現出“家庭團聚”的喜悅,反而怒不可遏、言語無狀。老馬克斯與兒子的初次見面就針鋒相對充滿火藥味,并對兒媳破口大罵,不愿認可兒子的婚姻事實及兒媳的身份。同樣,特迪的弟弟們對于多年未歸的兄長也只是簡單的問候,并無過多溫情。當看到露絲一個人獨處時,弟弟萊尼甚至主動上前攀談、搭訕并引誘露絲以妓女的身份留在家中。劇終,特迪默許了家人對妻子露絲的安排,獨自離開了家中,歸家之旅使其最終面臨無家可歸的窘境。該劇中的家就像是“一個離心花瓣一般,家人間的關系則像是章魚的觸手”[4]226,愛的殘缺導致家庭成員們之間未能生成關懷意識,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共同體的構建面臨困境。這樣的家庭關系在品特的家庭戲劇中俯拾皆是,父子關系抑或是母子關系總是處于對抗之中,因為“每一個人物似乎都深陷在不動聲色的仇恨當中,不能自拔,看不到半點愛的陽光和溫暖。”[5]84
對于劇作家而言,家庭應當是“充滿愛、溫暖和安全感的天堂”[6]81,能夠滿足彼此間心理上的情感需求,是由成員共建的命運共同體。但其戲劇中,不論是婚姻家庭還是血緣家庭,家的形象都是殘缺的,家庭成員之間都因愛的匱乏而缺乏凝聚力。家只是一種機械聚合的存在,缺乏持續、長久的活力,血緣共同體喪失了其賴以生存的根本。
二、地緣共同體:家園的想象
“地緣共同體直接表現為居住在相同的地方”[2]87,是人類生活的一種相互關系,包括家庭,鄰里及社群關系。在共同體中,成員通過自由意志,以有機的方式相互結合且彼此肯定。品特戲劇中的人物以“房間”為棲居場所。“房間”既是一個地理上的空間場所,使身居其中的人因地緣而聯結在一起,也是一個如家園般溫暖的精神存在,讓人物有“安慰、舒適感、歸屬感以及伙伴和共同體的關系”[7]5。但是,房間所給予人物的只是一種“想象出來的安全感”,同時也只是一個想象中的“精神家園”[7]5。
“家宅庇護著夢想,家宅保護著夢想者,家宅能讓我們在安詳中做夢。”[8]5作為理想的共同體形態,家園“似乎總是被用來激發美好的聯想”[9]76。品特戲劇中的房間也總是給予人物以光明和溫暖,是人物的避難所。在《房間》中,房間內的溫暖舒適和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鮮明對比。主人公羅斯多次透露出對所居住的房間的滿足。但隨著劇情的展開,房間不斷有陌生人闖入。房東基德、桑茲夫婦和盲人賴利先后來到,他們或是覬覦房間內的物品,或是覬覦房屋本身,或是直接對房間內的人有所企圖。伴隨著這些外來人員的闖入,羅斯的心理日趨不安,房間內的穩定性,以及房間帶來的安全感也隨之被破壞。房間這一地緣共同體并未如主人公預想般美好。另一方面,房間內部的動蕩同樣也影響著其穩定性。羅斯和伯特雖共同生活在同一房間,但兩人之間溝通并不順暢,且存在明顯的對立和沖突,他們之間并沒有因共同居住在同一區域而形成親密的共同體經驗,從而導致地緣共同體內部缺乏向心力,在面臨外來威脅時顯得脆弱不堪,時刻面臨解體的風險。同樣,《生日晚會》中的斯坦利、《微痛》中的愛德華等人物也都視房間為安全的天堂,但最終房間都無一例外地因為來自內外的威脅而岌岌可危,呈現出散裂、脆弱的特點。
房間中的人物還通常在回憶中構建帶有個人理想主義色彩的共同體,呈現了與現實中的共同體生活相沖突的存在,繼而預示著現實中共同體的斷裂。在《無人之境》中,赫斯特居住在精致舒適的大房子里,表面看來他和兩個仆人同心協力,驅逐了外來者斯普納的入侵,維護了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地緣共同體的利益。然而,現實房間內的共同體生活于赫斯特而言卻如同枷鎖和牢籠。赫斯特與仆人雖居住在一起,彼此間相互熟知,且遵循著約定俗成的秩序與規則,但個體自由的喪失最終使其難以對居于其中的共同體產生認同感。此外,赫斯特與仆人在階層上的差異和地位上的不平等,使他們之間難以享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從而造成了地緣共同體成員間的嫌隙,破壞了共同體的穩固性。出于對自由與理想共同體圈層的渴求,劇中的赫斯特反復提及過去,運用往事的“碎片”,構建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回憶共同體。昔日鄉下的小屋、草地上的茶會激起人們對美好的田園生活的聯想,是“一個純真年代的意象,一種真正的英國性之所在”[10]181,這也成為赫斯特的精神慰藉之所在,體現了其對往日美好共同體生活的幻想。但是,回憶中的理想生活終究只能永遠停留在赫斯特早已發黃的相冊中,是一個“失去樂園和天堂”,但同時“又是人們熱切期望重新擁有重歸其中的世界”[8]5。人物沉湎于過去,以回憶建構“精神家園”,是品特戲劇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回憶承載著人物對于理想生活的緬懷,以及對現實共同體生活的失望。過去與現在的對立也暗示了現實共同體必然面臨的重重危機與考驗。
綜上所述,品特戲劇中的人物雖居于“房間”中,但這一地緣共同體的穩固性和完整性卻不斷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而面臨崩潰的困境。共同體成員沉溺于對美好共同體生活的幻想中,展露了人物對美好家園的向往,也體現了對理想共同體生活的訴求。
三、精神共同體:個體的分裂
滕尼斯指出,精神共同體“可理解為心靈性生命之間的關聯”,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體”[2]87。共同體成員能夠在共享的認知框架和價值觀基礎上,相互交流、合作且彼此影響,達成情感上的共鳴,實現精神上的聯結。然而,品特戲劇中,共同體成員因共同情感和價值追求的缺失,彼此之間陷入孤立隔絕的狀態,未曾達到精神上的契合,從而導致共同體的崩塌。
“文學家們對于共同體的構想從來都是充分運用會話元素的”,且“會話的態度、語氣與共同體的精神密切相關”[11]63。品特戲劇中人物無邏輯且自相矛盾的話語,呈現了荒誕不經的會話場景,揭示人物迥異的精神狀態,直喻共同體內部的無效溝通及精神共同體的崩裂。戲劇中的人物話語瑣碎啰唆,充斥著日常話語中的重復、停頓和沉默以及大量的市井俚語,表意含糊不清。這就意味著話語已不再是交流和溝通的工具,人物間的對話前言不搭后語。例如《房間》中的羅斯和伯特、《生日晚會》中的梅格和皮特以及《微痛》中的弗羅拉和愛德華等人物間的對話皆是斷斷續續、無厘頭的詞語堆砌,讓觀眾困惑不已。而在中期的記憶戲劇中,幾個人物相對而坐,但他們之間的對話卻如同永不相交的平行線,更是凸顯了人物彼此間孤立隔絕的精神風景。因而,戲劇中語言的能指和所指意義分離,話語喪失了表意的功能,會話所展示的是個體精神的隔絕和人際關系的割裂,進而表征精神共同體的崩潰。“共同體的一個根本前提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深度溝通/交流”[12]74。人與人之間存在溝通障礙,也就無法實現深度的精神交流,其所在的共同體也就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
語言的多重功能是品特戲劇的另一重要特征。人物常滔滔不絕或沉默不語,以掩飾自我的真實情感和動機,因為“談話就意味著暴露,容易把自己薄弱的一面展示于人”[13]113。此外,人物也將語言當作武器,以達到威嚇、攻擊對方的目的。換言之,品特的戲劇“探索人與人之間的敵意”,但人們“不是用刀劍進行決斗,而是用詞語和沉默”[13]154。非理性的語言下隱藏著說話者的真實自我,揭示了人物內心的焦慮、惶恐以及欲望,由此人物間的對話也暗示人際關系中各種矛盾紛爭和權力博弈,繼而直指共同體成員相互攻訐、明爭暗斗、爭權奪利的真實關系,進一步預示著共同體的瓦解。
共同體的凝聚力“取決于每個成員怎樣想象自己所在的共同體,包括想象陌生人”[14]6。因而,共同體的深度不僅體現在成員之間的精神聯結,還體現在成員與外來陌生人的關系方面。“假如一個共同體容不下陌生人,或者讓陌生人受到冷遇,那它就毫無深度可言”[15]81。而品特戲劇恰恰展現了共同體與陌生人之間的一系列矛盾和沖突。劇中的陌生人因各種原因試圖進入共同體,引發共同體成員的不安和恐慌,進而遭遇了來自共同體成員不同程度地抗拒和排斥。譬如《房間》中的羅斯對于外來者盲人賴利的到來充滿抵觸情緒,話語交談中也是處處防備,而伯特則更是直接暴力地將其殺死;《看房人》中的流浪漢戴維斯作為弱勢群體渴望融入共同體生活,但卻受到了米克身體和語言上的雙重欺凌,最后共同體成員聯合起來將戴維斯驅逐出去;《無人之境》中的斯普納同樣因期許能在房間中獲得立足之地而與房間內的成員不斷發生摩擦,最終也未能如愿進入共同體。共同體成員對于陌生人的態度揭示了共同體內部渙散,缺乏包容心和共情能力。不可否認,陌生人之所以難以被共同體所容納的一個原因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異質性給共同體帶來的潛在破壞性,但更重要的是共同體成員對外來者充滿恐懼,難以建構心靈相通的友誼關系,從而無法接納異己,聯結彼此。這也是共同體內部協調機制與靈活性缺乏的表現,使其無法以恰切的方式來溝通以調和這種矛盾。
表面看來,品特戲劇刻畫了個體人物因無法交流或拒絕交流而陷入孤立隔絕、甚至是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實質上,它表現了品特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深思以及對精神共同體崩潰的憂慮。現代性將維系共同體生活的價值觀和情感紐帶銷蝕殆盡,帶來個體生活中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最終導致個體分裂,難以建構以共同情感為基礎的精神共同體。
四、結語
品特以巧妙的構思和豐富的想象力,抒發其強烈的共同體沖動,表達了對美好共同體生活的憧憬。從血緣共同體內愛的缺失,到地緣共同體成員對家園的想象與緬懷,再到精神共同體中個體的情感分裂,劇作家對戰后英國社會普通群體的境遇、訴求和命運予以全面的觀照,展現了共同體在個體日益缺乏安全感且人際關系日益冷漠的現當代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從而使其作品具有普世價值。其筆下的共同體書寫回應了當代的共同體議題,同時也引發了觀眾對共同體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并積極探索如何突破共同體困境,構建理想的共同體形式。
參考文獻:
[1]李維屏.論英國文學中的命運共同體表征與跨學科研究[J].外國文學研究,2020,(3):52-60.
[2]費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3]Wandor,Michelen.Post-War British Drama: Looking Back in Gender[M].London:Routledge,2001.
[4]King,Kimball.ed.Modern Dramatists:A Case of Major British,Irish,and American playwrights[M]. New York:Routledge,2001.
[5]Trussler,Simon.New Theatre Voices of the Seventies[M].London:Eyre Methuen,1981.
[6]Pinter,Harold.Various voices,Prose,Poetry, Politics,1948-1998[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8.
[7]Said,Edward W.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M].Cambridge:Harvard UP,1983.
[8]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M].歐陽景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9]加斯東·巴拉什.空間的詩學[M].張逸婧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10]Esslin,Martin.Pinter:the Playwright[M].London:
Methuem,2000.
[11]李睿殷企平.“共同體”與外國文學研究——殷企平教授訪談錄[J].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21,(2):59-65.
[12]殷企平.西方文論關鍵詞:共同體[J].外國文學,
2016,(2):70-79.
[13]Raby,Peter.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rold Pinter[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4]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London:Verso,1991.
[15]殷企平.華茲華斯筆下的深度共同體[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5,(4):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