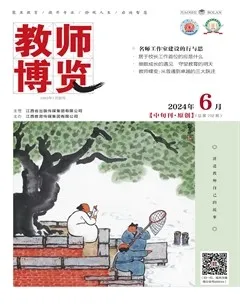燈如繁花
李冬鳳
認識劉翮天,是偶然中的偶然。
在新都,店家打烊,廊檐下的燈漸次亮起,各具特色的馬頭墻隱沒在燈光中,朦朦朧朧。玻璃柜里儲藏的陶瓷了卻繁華,悄然睡去。我躊躇,孑然一身,往深處走,如溺水者,黑漫過膝蓋,漫過脖頸,漫過頭頂。
手機響起,是余老師:“等我,走走。”
銀色的院門很闊,但并不獨特。余老師喊了幾聲,無人應答,他便伸手摸索著,門開了。
微風,竹影,廊亭,燈從院子的每個角落亮起,一位老人步履蹣跚,迎向我們。
進了廳堂,恍若進了瓷器博物館。一排一排的置物架,陳放著大大小小、花色各異的瓷器,有粉彩、青瓷、釉里紅……我的眼睛像被吸住了一樣,腳步像失重,撲向置物架。所幸此時心智正常——初次造訪,豈能失態(tài)?我收回腳步,隨老人家的指引落座。
廳堂右側(cè)是茶室。茶桌碩大,幾乎塞滿茶室,一端放著各種名茶,還有幾盒藥。老人家先是煮茶杯,再沖上一小壺茶。茶桌太寬,需站起方能接到遞過來的茶。茶的湯色微黃,啜一口,苦味浸潤舌尖,再順咽喉而下,茶香才開始漫出來。
“是柴火窯?”余老師不說茶,只看手中的杯子。
“什么茶?味道很獨特。”我說的是茶。
“福鼎白茶。”老人家先回答我,再看向余老師。
“是的,柴火窯。”老人的聲音低沉,操著濃重的方言,唇齒有點不關風。聽他講話,得眼耳并用、心思集中方可。
余老師和老人聊天毫無章法,吃藥,心臟手術,接瓷器活兒……想到哪兒說哪兒。我不在他們同一圈子,生活也少有交集,任何話題,都很難接上話茬兒。我一直保持沉默,偶爾刷下微信,或起個身,接過老人給續(xù)的茶。
老人遞給余老師一包煙。“煙,真好!您也來一支?”余老師說。
“5月份,我進過ICU,身上插滿了管子,與死神搏擊了半個月。轉(zhuǎn)入普通病房,醫(yī)生把收繳的煙還給我。醫(yī)生說,再抽煙,ICU也救不了你。”老人苦笑說,“你說是命重要,還是煙重要?”
老人起身去內(nèi)室。
余老師看向我說:“這老人不是普通人。他叫劉翮天,是頂級專家,去過很多國家。與智者交流,常常會讓你釋然。”
對智者,我是頂禮膜拜。我在網(wǎng)上查詢到,劉翮天是江蘇阜寧人,1966年畢業(yè)于南京化工學院陶瓷專業(yè),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原任江西省陶瓷工業(yè)公司總經(jīng)理、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長……他的陶瓷作品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影青作品注重將宋代影青瓷的制作技巧與現(xiàn)代審美情趣相結(jié)合。他的作品多次參展并獲獎,具有相當高的收藏價值。
劉老從內(nèi)室出來。我放下手機,端起茶杯。
想接近一個人,就得找這個人喜歡的話題。我指指旁邊的茶杯問:“柴火窯?和我手里的杯子有啥不一樣?”
很小的青花杯,著了幾片葉子和一只螃蟹,如此簡單。我看不出手中的杯子和旁邊的杯子區(qū)別所在。
“柴火窯燒制的青花古樸、溫潤、通透,且色澤豐滿;而電窯燒制的,粉瓷晶瑩,乍看漂亮,但細細把玩,少了些韻味。”余老師講得很仔細。
“幾筆畫,小東西,一天能畫多少?”我問。
“我畫得再多,不如劉老一個掌心般的杯子!”余老師拿起杯子,繼續(xù)說,“好作品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繪畫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個人風格和內(nèi)涵盡在其中……”
我們的談論果然引起了劉老的興趣。他從茶桌的對面轉(zhuǎn)過來,站到我們中間,翻開手機,點開微信對話框:柴火窯,老板杯,十個青花,每個一千元;二十個粉彩,每個二千元……
“活到我這把年紀,錢已經(jīng)不是事兒了。”劉老興致來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已經(jīng)有很多國家超越了中國的制瓷技術。我?guī)F去蘇聯(lián)考察,目的是引進蘇聯(lián)的陶瓷生產(chǎn)技術……”劉老講述了他的一段人生經(jīng)歷,于我觸動很大。
三年前,機構(gòu)改革的浪潮把我推到了教育科研崗位。我的日常工作便是教育,自然也了解劉老的家鄉(xiāng)江蘇的教育。教育與經(jīng)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經(jīng)濟的騰飛必然帶來教育的發(fā)展,教育的發(fā)展一定能助推經(jīng)濟的發(fā)展。教育好的地方,學生就多。留住了學生,就留住了家長。留住了家長,也就留住了勞動力。有了勞動力就有了創(chuàng)造力。有了創(chuàng)造力,就不愁經(jīng)濟不發(fā)展。我想江蘇就是如此。
劉翮天天資聰慧,從小就很會念書,且順利考進南京化工學院,專業(yè)方向是硅酸鹽。他大學畢業(yè)后便被分配到景德鎮(zhèn)。在這個三步一作坊、五步一窯戶的陶瓷世界里,他如魚得水。他潛心研究硅酸鹽在陶瓷中的運用。
陶瓷因具有高強度、高硬度、高耐磨、高耐化學腐蝕等優(yōu)良性能,應用越來越廣泛。當時,如醫(yī)療、建筑、汽車、航空等行業(yè)都在陶瓷原料和陶瓷技術上尋求突破,并向已有建樹的劉翮天拋出橄欖枝。劉翮天接受組織任命,去江西省陶瓷工業(yè)公司擔任負責人。
“Made in China”是因為景德鎮(zhèn)瓷器走向了世界。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走向世界,還少不了要擦亮景德鎮(zhèn)瓷器這張名片。劉翮天不斷地閱讀國外的相關資訊,尋找最佳合作伙伴。蘇聯(lián)與中國交好,對中國的援助也很多,去蘇聯(lián)合適。誰去?自然是他。請翻譯,是必然。但是他譯不如自譯更準確,因為一般翻譯不一定懂陶瓷的專業(yè)術語。劉翮天在蘇聯(lián),逮住一切與外國人交流的機會,比畫著說,模仿著說。中蘇制瓷友好合作簽約會如期舉行,看著三十多頁的英文合同,翻譯傻眼了,團隊其他人也傻眼了,里面有各種專業(yè)名詞和術語,還有各種特定表述。劉翮天拿著合同,手心冒汗,這是幾百萬的合作項目啊!幾百萬在20世紀80年代算是天文數(shù)字。
舊事重提,劉老手依然有些顫抖。他從茶桌底下拉出一個箱子,翻出一疊紙。我湊近細看,有手工繪制的機器圖紙、各種演算稿、英文手抄合同等。他指著英文合同稿說:“付款方式、結(jié)算程序、安裝進度都與國內(nèi)不一樣,為了能弄懂厚厚的合同文本,我硬是把自己關在賓館三天三夜,查找字典,查找范本……”
劉老學英文是如此,學俄文是如此,學德文也是如此,他走過很多國家。他不僅與俞炳林一起翻譯過蘇聯(lián)的《陶瓷原料與制品的干燥》,還翻譯了很多其他國家的作品。
我開始仰視他。
他淡然一笑說,讀能用得上的書,才越讀越有勁,或者說,讀有用的書才可以讀得進去。
我心頭為之一震,這就是有效教育。讓教育歸位,何其重要!
城市的夜晚燈如繁花,繁花中一定有屬于我的那盞燈。
(作者單位:江西省都昌縣教育科學研究中心)
(插圖:珈 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