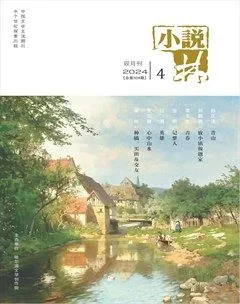青山
一
我姥家姓章,姥爺叫章魁武,在我們漁場村的最東頭。過了蚊子溝的小木橋,過南北路,到這兒,就不用問了,路東,唯一的人家,就是我姥家。姥家再往東,就是青山的西坡,陡,蓋不了房子。
姥姥在母親小的時候就病故了,姥爺領著兒女們過日子。等到我記事兒的時候,姥家就是大舅母在操持家務了。我們村都管舅母叫舅們,音是“們”字音,至今也不知道是哪個字,為啥?我們叫,舅母答應,如今要寫到文字上,才去想這個字兒。還是按國人的標準,叫舅母。
姥爺的孩子,按年齡排,大姨、二姨、大舅、二舅是一個媽的。二舅五歲的時候,先姥姥病故了。姥爺再娶,就是我母親的母親,我的親姥姥。姥姥結婚五六年沒有懷孕,便越發地對先房的幾個孩子好了。到了第七年,姥姥才生了三舅,接著是生了母親、四姨、老姨。
姥家的院子,南北六七米寬,往南是一道三尺高的土墻,墻南面是園子。園子有七八十米長,二十多米寬。這不算二舅家的,二舅家從分家就把院子和園子都分出去了。中間有一道南北墻,隔出了兩家的地界。姥家走的是西門,出了門就是大道。二舅家走的是東門,出了東門,要從房后轉到西邊才上大道。母親說,這都是二舅娶了后來的二舅母之后,才有的中間這道墻。之前,二舅是從姥家的院子直接到西邊的大道。
姥家除三間正房外,西邊有一間倉房,存放著糧食和雜物。在倉房的地中間,擺放著一口油漆好的大棺材,也叫壽材。壽材上面蓋著一領葦席,壽材前后露著,畫的樓閣、松柏、祥云,可能是深藍色用得重了,總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一進倉房就能看到。姥爺有時間就進來看看、拍拍,嘴里叨咕著誰也聽不清的話。
姥爺在查干湖打了半輩子魚,等成立了漁民社,他歲數大了,就沒加入。到了漁民社改成了漁場,大舅進場當了工人。姥爺閑在家里,沒事干,就喜歡種樹,房前屋后道路兩旁全是他種的楊樹。家中只有大舅一個人在漁場上班,在大車隊里趕大車,就是四匹馬拉的膠輪大車。大舅母在家里養豬、雞、鴨、狗,做一家人的飯。大舅母長得瘦小,一桶豬食提不動,就一次提半桶。盡管這樣,她也不會讓別人幫她一把,就是后來長大的兒女在身邊,她也不會支使一下。從沒聽過大舅母埋怨過別人。
大舅母叫竇秀娥,娘家住青山村。青山不高,也不大,南北六七里地,東西三四里地。青山村在青山東,也叫青山里,我們村在青山西,叫青山外,里外也不過五六里地。青山在地圖上太小,沒有名,可是因出土過一萬多年前的人類化石,位置在青山的南頭,起名叫青山頭人,這才有了點名氣。可這一切跟當地百姓似乎沒什么關系。山里的村子就是種地,靠天吃飯。那時,周邊村子的女孩子嫁到漁場,算是高攀了,至少不用起早貪黑地下地干活兒了。在漁場上班是工人,有工資,吃商品糧,旱澇保收。更重要的是,魚雖然是菜,可是也頂糧食用,這就比城里的那些職工要強得多,餓不著。雖然說那時場里管得嚴,不讓私自下湖打魚。可是守在水邊,整點魚吃,家家還是有法兒的。就比如姥家,到了晚上,大舅就把掛子圍到水溝里成堆的蘆葦周邊,然后進里面去一拍打,魚往出一跑,都給掛住了。人們叫快當網。多的時候,能掛住百八十斤。往少了說,一家十幾口人吃一頓足夠。
大舅母娘家窮,男孩子上個小學,識個眼前字,女孩子都沒上過學。整個大布蘇草原,這是常事。大舅母在娘家,去得最遠的地方,是塔虎城,家東十多里路。那是夏秋時節,大舅母和村里幾個孩子去東面甸子上采韭菜花,有人說再往前走,就到了塔虎城了,那里是遼代皇帝住過的地方。一聽說皇帝住過的地方,就都來了精神。果然,又走了不到一個小時,到了塔虎城。
塔虎城,遼代長春州,駐有常備部隊韶陽軍,遼帝“春捺缽”辦公的地方。后來大金滅了遼,改成新泰州,元又滅了金,從元、明、清到現在,荒了幾百年,城里成了百姓的耕地。站在城外看,有護城河,顯著城墻高高的,一眼看不到頭。沿著塌了的城墻土坡,上到城墻上,城里都是莊稼地,一間房也沒有。這讓大舅母很失望。沒有人,沒有供銷社,有啥好看的。大舅母沒往城里走,只是站在高臺上看一眼,歇一下腳,就往回走了。這就是大舅母一生走得最遠的地方,也是她后來常向子女們講的古城。
大舅母那天走得急,怕晚飯前回不到家母親不高興。農村的晚飯,全看太陽。太陽不落山,天不黑,下地干活兒的人不收工,那就不能吃飯。雖然飯菜不全是給下地干活兒人做的,但一定要以他們為主。那天,大舅母太陽高高的就到了家,她把采來的韭菜花洗凈,加上鹽,放進蒜缸里搗。韭菜花香味,是草原人最熟悉的味道了。因為有了韭菜花,沒人去問她干啥去了。大舅母一直把這件事藏到婆家,才在閑說話的時候,說出來她一生中的遠行。
大舅母十六歲的那年秋天,村里媒人上門給介紹對象,就是大舅。那一年大舅十八了,剛被漁場招工。招上了,就是正式的工人了。大舅中等個,國字臉,略有點黑,更顯得人長得結實,不愛說話,也不會說個啥,讓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種老實厚道人。陪大舅來相親的,是大舅的繼母,我的親姥姥。姥姥和大舅,沒人能看出是繼母,娘兒倆親,所有看到過這娘兒倆的,都一致認為:母慈子孝。
那天去的時候,姥姥告訴大舅,要是女家留咱吃飯,就是人家看中咱了。你要是看中了姑娘,就朝我點一下頭,咱就在那兒吃飯。你要是沒看中,就搖頭,咱就別吃飯。媒人說啥你不用管。
那天去了之后,媒人介紹完,大舅母給大舅倒了一杯水就出去了。可是大舅因離得太近,沒敢看,就在大舅母一轉身的時候,大舅看到了大舅母黑黑的大辮子,還有耳朵后面白白的三角。就這一眼,讓大舅相中了。大舅說不出啥好,這是他第一次相親。他朝姥姥點了一下頭。姥姥看大舅母第一眼,就看出是個本分姑娘,只是身子太單細了。不過看她父母,身體都不錯,姥姥想,結了婚會發福的,姑娘家,苗條點兒好,秀氣。再說了,按村子里的習俗,大兒媳婦個子不能太高,往后應一個比一個高,日子就會越過越好。
女方同意了就殺雞,這是多少年的老規矩。俗話說:“新姑爺進門,老母雞丟魂。”不年不節的,殺雞,那就算是大事了。
雞吃了,婚事就算定下來了。接下來,就是彩禮。雖然不講究那些老規矩,如“放定”“換盞”“三媒六聘”什么的,可是總得有點表示。
農村女方要彩禮,那是千百年留下來的老習俗了。彩禮要得多,表示姑娘尊貴,這是最好聽的一種。大概有這么幾種情況,一是父母認為養一回閨女,咋的也得要倆兒錢養老。二是家中還有兄弟,要了彩禮給兄弟娶媳婦。三是最開明的,就是不要彩禮。話是這么說的:“再窮也不能賣閨女。”大舅母的父母就是這最開明的。可爭的不夠,讓的有余,越是不要的,越是不能低于當時的行市。
女方不要彩禮,姥姥說:“他們不要,咱不能不給。養那么大一個閨女,父母也不容易,都是臉面上的事,咱不能讓人笑話。有胭脂擦臉上。”這彩禮當中就有姥姥當年的嫁妝在內一起過給了大舅母娘家。
明白人好辦事,雙方都這樣,就海闊天空了,事就一順百順了。
二
大舅母結婚的第二天早上,她想早點兒起來,做一家人的飯。這是出嫁時娘家媽說的:“從明天起,你就是章家的媳婦了。要知道孝順,多少小姑多少舌,多少大娘多少婆。由他們去說,你做好你的事,總有熬出頭的時候。”可是當大舅母起來,來到外屋的廚房,見婆婆把飯都做好了。我姥姥說話透亮,見大舅母出來,說:“大媳婦,起來了。早飯我做就行,你們年青人覺不夠睡。”姥姥說這話的時候,還不到四十歲。可她是婆婆,這在她沒有兒子那一天就想過的,一定要把兒媳婦當成自己的閨女待。雖然這是先房的兒媳婦,可是她當成了自己的親兒媳婦。
大舅母說:“在我們村,天不亮就出工下地干活兒了,半夜里就起來做飯了,我們家都是我早上起來做的。”
姥姥說:“咱這兒不用,除了冬捕拉大網要起早,平日里都是到點上班。飯做好了,豬也喂了,你先回屋歇一會兒吧。這個家呀,以后就交給你掌管了。干活兒的日子在后邊呢,等三天回門回來再做吧。”
大舅母聽姥姥這么說,眼淚便含在眼圈。她見過太多的,是婆婆罵兒媳婦。為了不讓眼淚流出來,大舅母便去找活兒干。可是一時真的找不到活兒,她拿起掃地掃帚,把地上的柴草葉往外掃。姥姥見了,說:“大媳婦,掃這屋地,要從門口往里掃。老禮是這么個規矩,把柴(財)都掃進來。過年的時候,更要注意。”
“我知道了,娘。”大舅母說這話時,心里暖暖的。
姥家的廚房,就是五間房中間的屋,開著南門和北門。北門到了冬天就封起來,過年的時候,在北門那兒掛上一領葦席,前面就是供奉老祖宗的地兒。東西各兩間住人。進了門,左右各有兩口大鍋。一口是做飯的,一口是溫豬食、放泔水的。養豬,是家中最大的副業。過年殺豬不僅僅是解決一家一年吃油,還有一個臉面上的事。請大家來吃豬肉,那是禮尚往來,那是臉面,那是姥爺在人前的風光。假如自家沒豬殺,別人來請吃豬肉,去不去?實在是件尷尬的事情。殺豬請客,那不僅是村子的習俗,也是大布蘇草原的習俗,一年中的人情往來,一年中的恩怨,一頓豬肉吃下去,都解了。人怕見面,樹怕扒皮,吃豬肉就是中介。沒有豬殺,就是請客也沒個好由頭,這一年之中,男人在外面都抬不起頭來。
姥姥告訴大舅母,鍋是連二鍋,燒外面的鍋做飯,余熱就把里面的鍋也帶熱了。冬天里,豬要喂熱食,要不沒等吃完,就凍在豬食槽子里了。只有吃熱豬食,才長膘,才出油。豬肉膘,那是鄰里間過日子暗中較勁的直接表現。膘厚,豬養得好,日子過得也好,也是一個冬月、臘月里人們常說的話題:
“看人家那豬,一拃厚的膘,香。”
“寧吃肥中瘦,不吃瘦中肥。”
大舅母一邊用心地記著,一邊點頭答應著。她知道,這就是她今后的活兒,今后的目標,喂養肥豬,一拃厚的膘。
姥姥把屋里的告訴完了,就領著大舅母去西倉房。一進門大舅母就嚇一跳,倉房的地上擺了一口大棺材。雖然上面用葦席蓋著,可那棺材頭一眼就能認出來。那是人們都見過的,雖然畫的樓閣、祥云、松、鶴,可那是死人的天堂。雖然和姥姥一起進去的,大舅母的頭皮還是一陣陣地發奓,姥姥的話大多沒聽清楚就出來了。只聽清楚,這是爹的壽材。在村子里,人們認為最有正事的,就是準備壽材,這是早晚必用的。有時有了大病、急病,就安排人先把棺材做上,稱攢料子。攢,是往一起合;料子,是木料板材。這也是驅趕病災的一種習俗,叫“沖”。古代帝王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選墓地、修墓。百姓能做到的,就是給自己選一口壽材。
出了倉房,大舅母才算長出了一口氣。接著就是院里的雞架、狗窩什么的。雖然之前大舅母也來過,可那時,她只是跟著父母還有媒人吃了飯就回去了。如今,這就是自己的家了。大舅母看得仔細,并不斷地想著這些活兒的做法。
雞架上靠墻是一排的雞咕簍,那是雞下蛋的地方,用谷草編的。姥姥說:“咱這兒有老黃,晚上一定要把雞架和鴨架門擋好。”
老黃,大舅母知道,就是黃鼠狼。大布蘇草原和查干湖一帶,到處都有。只要擋住了門,它進不去,也就沒事了。
早飯,是婚禮上剩下的飯菜,這已是比過年還豐盛的了。飯桌分東西屋擺,東屋,是姥爺的炕桌。西屋也是炕桌,全家人都在這兒吃。姥姥讓大舅母上桌吃飯,可她自己還在地上站著,給孩子們舀飯、拿筷子的。大舅母見姥姥不上桌,她也在地上站著,看大舅和一桌的孩子吃飯。直到孩子們都吃完了,姥姥舀了一碗飯給大舅母說:“快吃吧,要不都涼了。”
大舅母沒有接,說:“娘,你先吃,我再舀。”
姥姥說:“你吃吧,我上那屋看看。”
大舅母這才開始吃飯,剛吃了兩口,姥姥回來了,把桌上孩子們剩在碗里的飯放到一個碗里,拿起來開始吃了。這讓大舅母知道,這就是娘。
吃完早飯,大舅和二舅去上班了,三舅和我母親上學了,四姨和老姨還小,吃完飯,四姨看著老姨在炕上玩。
姥爺吃完飯,出去了,到村子里找人聊天。五十多歲的姥爺,在當時可以稱得上老頭兒了。留著小胡子的姥爺,更顯得老了。
冬月、臘月的天短,三四點鐘太陽就落山了。姥姥飯前就把豬、雞都喂完了,特別是雞架門,黃鼠狼是有空兒就鉆,惹不起,只能防。可是關雞架門的時間,就是太陽落山的那一陣,只有日落了,雞才全進架。早了,把雞關外頭了;晚了,黃鼠狼就可能趁這個機會進去。雞架的小窗戶,每天都是堵完還要再看看。好在這幾天有婚禮剩下的飯菜,十八印的大鍋,下面燉,上面蒸,一鍋就出來了。雖然姥姥不讓大舅母干活兒,可大舅母覺得不好,還是出來幫著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放桌子、撿碗、拿筷子這些活兒,大舅母都干得麻利。
吃完飯,姥姥收拾完外屋的,就趕緊上炕,開始做衣服。過年一定要讓孩子們穿上新衣服,姥姥這些年一直堅持的。今年,又多了一個大舅母。姥姥會裁衣服,但不是像城里成衣鋪那樣用尺量,而是必須找一件舊衣服,比著剪。大點、小點,全憑感覺。做出的衣服,沒有不合適的。村子里一些人家也都來找姥姥給裁衣服,雖然都是幫忙的事兒,也是一份人情,姥姥在村子里,就有了一個好人緣。
夕陽,一晃不見了,人們都說太陽是早上騎馬,晌午騎牛,晚上騎個葫蘆頭。等天全黑了下來,大舅把中間屋子擋上窗簾,在里面又加上一層用牛皮紙做的簾,這樣在外面就看不見屋里的燈光了。一切都擋好了,大舅用100瓦的燈泡換下15瓦的燈泡,屋子里一下子就亮了起來。姥姥開始做針線活兒了,大舅母幫姥姥納鞋底子,三舅他們開始看書寫作業。屋子里一下子安靜了下來,都在利用這光亮,忙著做自己的事。
村子里電費是按燈泡收取的。點多少瓦的燈,交多少錢。有時電工來查,有時左鄰右舍的,見誰家燈亮,就會去當個事兒來說。燈亮就多花錢,家家都是那點錢過日子,鄰里間就是這樣,攀比。
姥姥的針線活兒好,讓大舅母開了眼界。別說她們村子,就是全鄉鎮,也找不出幾個像姥姥這樣做針線活兒的好手了。縫衣服,講究的是針腳。如今大都市還有手工做衣服的店鋪,據說做一件西服,手工要上萬元。姥姥縫的針腳,不僅面上的齊整,就是里面也齊整得如機器加工一樣。特別是做鞋,男人穿的圓口布鞋,那是姥爺出去的臉面和說話的資本。姥姥一邊做,一邊給大舅母講。
“三層鞋底,一定要畫好,一剪子下來。這樣三層才能齊整。沿鞋口,針腳一定要勻,要小,這才能不禿嚕邊。前臉這兩條筋,繰出來一定是圓的,一定要高低一般齊。一雙鞋的好壞,全在這兒。”
大舅母認真地聽著、想著。這些在娘家,也聽娘講過,可是伸手一做,就不是那樣的了。她跟著姥姥,除了納鞋底子,就是往鞋幫上納“卐”字。納上“卐”字的鞋幫,結實,好看。為了好看,每雙鞋幫都是姥姥畫好了“卐”字,大舅母照著樣子往上納就行了。這是給大人做的鞋,給女孩子做的鞋,就要畫上云卷,用上彩線,就是人們常說的繡花鞋。最難做的,是小男孩的虎頭鞋,那虎頭一定浮出來,立體的,浮雕一樣的在鞋前面。這樣的鞋,不僅是穿,有時小孩子受到驚嚇,晚上孩子睡著了后,把鞋扣到枕頭前面,可以起到鎮靜的作用。這是家家都知道的,只是不一定家家有虎頭鞋。
冬日里,天短夜長,做針線活兒的時候,姥姥就邊做活兒邊給他們講故事。《王寶釧守寒窯》《岳母刺字》《天仙配》,姥姥可以講下來全本。前些年,村子里經常有來說書的,姥姥便拿上鞋底子,邊納邊聽。村里要是來演電影的,姥姥會早早地把飯做好,吃了飯,拿上小板凳,提前去占座。不管是姥姥看過的、聽過的,一遍她就能全記住。講起來,那懸念總是吊人胃口,讓人想聽出個結果來。
姥姥天天晚上往出趕活兒,就為了過年都能穿上新衣裳。到了臘月二十九的晚上,姥姥會把所有人的舊衣裳都換下來,把新衣裳擺好,讓全家早上起來,全都穿上新衣裳。換下來的舊衣裳,一定要洗了,放起來。干凈。臟東西絕不能留到過了年,亮亮堂堂地過年。
大舅母三天回門,姥姥早就把東西給準備好了。臉面。
三天回門,因為路不遠,四五里路,走著去,也就一個小時。可是姥姥還是給大舅借了輛自行車。東西掛在車把子上,后座上載著大舅母。比起趕著毛驢回娘家,進步了。可是讓人看著是那么的相像。
回門的東西,除了煙酒,就是魚了。查干湖產魚,這誰都知道,可要是說什么魚好,那還是查干湖人能說得明白。最上講的,就是三花五羅了。三花是:鰲花、鳊花、鯽花。五羅是:哲羅、法羅、雅羅、胡羅、銅羅。
三花中,除了鰲花最大的長到十來斤,另兩種都是一斤左右,拿不出手。五羅中,也只有哲羅,大的長到三四十斤,法羅有八九斤的,可是太少。雅羅一斤多重,一條兩條的沒法拿,胡羅,一兩左右,銅羅也是,都不能當禮品,面子不好。回娘家,去老丈人家串門,首當是紅毛鯉子。好看,喜性。再就是花白鰱,其中花鰱,也叫胖頭,學名是鳙魚。再就是草魚、青魚,十幾斤一條,掛在自行車上,一進村子,打眼。就為了這個打眼,姥姥給準備了一條八斤左右的鰲花、十五斤的哲羅、十五六斤的草魚、二十斤的胖頭。四條大魚往自行車上一掛,一路上,大舅也沒敢騎,他怕摔倒了。大舅母先是跟著走,快到村口的時候,大舅讓大舅母坐后座上,他推著。多少年后,大舅母說,三天回門,真是露了臉了,至今她們村子也沒人回門超過她的禮物。
一到路上,大舅母就跟大舅說,到了娘家改口,叫爸,叫媽。大舅說:“走時娘說了,頭一件事就是改口。改了口,只要是說話,就得叫。禮多人不怪。”
大舅母說:“還是娘想的周全。”
大舅說:“那是。兜里還有糖塊,娘說,小姨子、小舅子,都是近親,拿點糖,對你這個姐夫就親了。”
“那爹沒說點啥?”
“我爹說,別啥事都聽你娘的,咋說也是后媽。可我不,親媽后媽,就看對你咋樣。娘比親媽還親。”大舅心眼實,凡事認準的理,誰說了也沒用。
“讓誰也看不出是后媽,對我更好。娘家媽也沒這樣,手把手地教,一句一句地告訴。親閨女也就這樣了唄。”大舅母這幾天就感覺到了,姥姥是對她真心的好。
三
大舅母是在結婚過了年懷孕的,到了秋天,生下了一個女孩。
孩子一生下來,姥姥就覺得不對,孩子手會動,兩腿不會動,腰上還有個包。雖然明知道孩子有毛病,可是姥姥想,過一陣子或許會好的。大舅母坐月子是姥姥伺候的,滿月了,除了喂奶,都是姥姥給照看孩子。
因為是女孩子,姥爺給起了個名,叫帶弟。意思是帶出男孩子來。
帶弟一周歲多了,兩條腿還是不會動,只能用手拉住東西往前爬。腿不好使,嘴卻巧得讓人心疼,她只要一說話,那聰明勁兒便顯露出來。似乎是為了討人喜歡,她的每一句話都是那么得體,讓人舒服、高興。快到兩歲的時候,基本上話都學全了。見奶奶干活兒,她就會說:“奶奶,你歇會兒,我這腿也不爭氣,等我腿好了,我幫你干。”
“爺爺你抽煙往我這邊點,我給你點火。等我腿好了,我在園子里全種上你愛抽的煙。除了睡覺,咱就抽煙。”
吃飯的時候,她總是說:“你們先吃吧,我又干不了活兒,剩下啥,吃一口就行了。”
那時只有老姨沒上學,比帶弟大幾歲,平時就由老姨看著帶弟。有時老姨一生氣,帶弟就說:“老姑,你去玩吧,我又跑不了,不用看了。”話是這樣說,可是她的小手卻抓住老姨不放開,兩只眼睛水汪汪地看著老姨。多少年之后,老姨提起帶弟,眼淚還在眼圈里轉。
就在帶弟三歲那一年的秋天,姥姥突然就病了。病到第二天,人就脫相了。請來大夫看,大夫說不行了。姥姥自己也知道不行了,就拉著大舅母的手說:“媳婦,我這幾個孩子就交給你了。看在……”話沒說完,姥姥就咽氣了。仿佛就在轉眼之間,姥姥就在大舅母的面前過世了。
大舅母原本就對這些弟弟妹妹們好,可是當時有姥姥在,外人看不出來。當姥姥沒了之后,這一切便顯現了出來。姥姥沒了那年,三舅十二歲,母親十歲,四姨八歲,老姨六歲,帶弟三歲多。三舅領著母親、四姨上小學,家中就只有老姨看帶弟。帶弟雖然聰明,時時想取悅老姨,可是老姨總想去外面玩,便常常扔下帶弟,自己偷偷跑出去玩。這事兒,大舅母也知道,可是她從不說老姨一句。在她的腦子里,沒媽的孩子,要格外地去愛,哪怕是做錯了什么,也不能去責怪。孩子小,不懂事,等大了,就好了。大舅母常說的話:“可秧長。”
仿佛家中的孩子和大小事與姥爺無關似的。對孩子,他說:“是人不用管,管死不成人。”
大舅在漁場趕大車,那是個不錯的工作。除了工資外,到縣城還有補助。雖然補助一天只有兩角錢,可那也是個錢。只是從早到晚不在家,家里的一切都是大舅母一人操持。大舅有時買回好吃的,總是平分給母親和帶弟他們。母親一直對我們說的話是:“你大舅不護小頭。”
大舅母總有干不完的活兒,特別是晚上,大舅母總能變出活兒來。特別是進入冬天,搓苞米,那是每個月都要干上幾晚的。這苞米都是大舅母在院子周邊種的,秋天收回來,曬干了,放在外面糟損,可是又不能像生產隊一樣到場院里打成米粒,只能搓。搓好了,裝進麻袋,拉到加工廠加工成苞米面、苞米 子。搓苞米,磨手,又枯燥,大舅母就開始講故事了。大舅母的故事中,最精彩的,就是塔虎城的故事。
大舅母說,塔虎城,老百姓都叫塌乎城。那是金兵從江東出河店過來,圍困塔虎城,一圍就是一年多,可是城里的遼王照樣地吃喝,守城的士兵也是有吃有喝。圍城的金兵也不知道城里哪來的那么些糧食,可是想硬打吧,塔虎城的城墻又高又厚,上面能跑馬車。攻不進去,沒法子,只有圍住,啥時城里沒吃的,就自然地投降了。城外人不明白,城里人也不明白,咋就有吃不完的糧食呢?一天遼王的女兒實在忍不住了,晚上就去問她爹:“爹,城里的糧食都存在哪兒了?咋天天吃,天天有呢?”
遼王讓左右的人退去了,說:“女兒,爹有一匹白馬,每天晚上往回馱糧食,運一個晚上,就夠咱全城人吃一天的。”
“一匹馬能馱多少哇,哪能夠全城人吃的呢?”遼王女兒有些不信。
“那是一匹神馬,一回能馱幾大車的糧食。”遼王說。
“那天天這樣馱,不得累死嗎?”遼王女兒說。
大舅母說,就這一個死字,犯了忌了。白馬累死了。
帶弟說:“爺爺說過,說話要忌口,不能啥都說的。特別是過年,更不能說不好聽的話。去年過年,我腿疼得要啥了,我就是不說那個字。這不也過來了嗎?娘,我也想去看看塔虎城。”
大舅母說:“等暖和了,讓你爹拉你去看看塔虎城。城墻老高老厚了,站在上面,就能看到咱們青山。”
帶弟說:“娘,白馬那個(死)了,塔虎城咋樣了?”
“白馬一沒,城也就塌了,大遼國就讓大金國給滅了。說錯一句話,一個國就沒了。”大舅母講到這兒,嘆了一口氣。
“娘,我不說那個字,咱們都長命百歲。”帶弟邊說邊看著大舅母的臉。
大舅母把臉在帶弟的頭上蹭了一下,接著搓苞米,往下講著村子里流傳的故事。
春天來了,大舅母做完早飯,就要種園子。那是有三畝地大的園子,大舅把壟打完,余下的活兒,就要大舅母去做了。在靠近院子的地方,有一口土井,井邊上,大舅母種上小白菜、香菜、臭菜、水蘿卜,這些菜三兩天就要澆一次水。略遠點的地方,種苞米、豆角,還有甜稈、高粱、葵花,靠近墻邊的地方,種上窩瓜、絲瓜。一個春天,大舅母有時間就在園子里忙。那是一夏天全家人的菜。
出事的那一天,早上起來,帶弟就說腦袋難受,身子也難受。可是帶弟的身體一直是這樣的,大舅母也就沒當回事。那天大舅母在園子里種香瓜。瓜喜肥,大舅母就在每一顆瓜秧下都放上半锨豬糞,然后澆上水,等水沉下去,再把瓜籽種上。來回打水的時候,大舅母看到帶弟在窗前,手在玻璃上比畫著,大舅母也招招手,可是忙于種瓜,也沒回屋里去看。她出來的時候,跟老姨說了,照看侄女,老姨也答應了。大舅母一直種到快晌午的時候,要做飯了,她才在井臺上洗了手,進屋了。到了外屋,她喊了一聲:“帶弟。”里屋沒回聲,她急忙進了里屋,見帶弟趴在窗臺上,老姨不見了。
“帶弟,不能趴窗臺睡覺,要受風的。”大舅母邊說邊上了炕,想抱帶弟下來。可是當她拉住帶弟的胳膊,帶弟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她扳過帶弟的臉,帶弟眼睛睜得圓圓的,沒氣了。大舅母一把抱起孩子,下了地,就往場衛生所跑。衛生所的大夫正要下班,見大舅母抱孩子沖進來,忙讓大舅母把孩子放在床上。可是當大夫看完之后,聽診器都沒用,說:“孩子沒氣了。”
大舅母給大夫跪下了。
“不是現在沒氣的,是有一段時間了。咋才送來?”大夫說著把大舅母扶起來。
大舅母再次撲向帶弟:“帶弟啊,是媽對不起你呀。就為了種幾個瓜,我咋這么饞呢!”說著大舅母抽打著自己的嘴巴。
聽到信的人們都來了,村子里就是這樣,誰家有事,大伙都過來幫忙。更何況大舅母人緣好,姥爺一家在村子里人性好。幾個婦女上去把大舅母抱住了,幾個上點歲數的老太太過來,把帶弟亂亂的衣服和頭發整理好。大家都在等著姥爺和大舅的到來,由他們決定下一步。
就在這時,姥爺進來了。他看看孫女,又看看大舅母,朝那幾位婦女說:“你們幫著把她媽送回家去吧。”說完,他朝身邊的人說:“李二狗子在村子里嗎?”
姥爺的話音沒落,就聽人群外有人說:“我在。大叔,你家的事呀,我聽到信兒就來了。你說。”
姥爺說:“二,把孩子埋了吧。捆上谷草,青山上,找個陽面高坡,別讓土壓著臉。我這兒有十塊錢,拿著去吧。”
李二狗子邊說話,邊把錢接了過來:“咱爺兒倆還用這個嗎?我這馬上就去,我一個人就行。”說著他把錢放好,抱起了帶弟,出了衛生所。
守在衛生所沒走的大舅母一把拉住出來的李二狗子說:“二哥,抱好了帶弟,她腿不好。”
李二狗子說:“放心吧。”
“埋她奶奶能看到的地方,帶弟膽小。有她奶奶照應著,她不害怕。”大舅母還是不松開李二狗子。
“一定的。一定。我知道,發送老太太的時候,我跟著去了。我辦事,你就放心吧。”李二狗子說著便往前走。
“一定找個陽坡,背風的地方。”大舅母還是不松開李二狗子。
“我知道,我知道。老太太就在陽坡。”李二狗子說著一使勁兒,掙開了大舅母的手,抱著帶弟,朝青山走去。
大舅母在后面追了幾步,讓人給拉住了,她大聲地朝李二狗子走的方向喊:“帶弟,別怕,有奶奶。媽媽晚上去陪你。有啥事跟奶奶說,給媽托夢……”
帶弟的事,就這么快的處理完了。等大舅晚上出車回來,聽到信兒急忙地趕回家,大舅母正在那兒整理著帶弟的衣服和用過的東西。原本就瘦弱的大舅母,仿佛一下子又瘦了一圈,衣服顯得那樣的不合體。抽泣的身體,帶動著衣裳一抖一抖的。她把帶弟的衣裳理平,放在一個藍花布的包裹皮中,最后是帶弟最喜歡的、一直沒有穿的繡花鞋,那還是姥姥親自繡的。這雙鞋,帶弟一直放在身邊,并告訴奶奶:“等我的腿好了,穿上奶奶做的鞋,幫奶奶干活兒,給奶奶做好吃的。”
大舅原本就話少,這時更沒話了,只是一袋接一袋地抽煙。一袋抽完了,在鞋底上把煙袋磕干凈,又裝上一袋。在炕角上坐著的老姨,她也知道錯了。剛剛被母親和四姨給打了幾下,就讓大舅母給拉開了。大舅母是從心里不怪老姨的,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怎么擔得起這么重的事。全怪自己太粗心了。
上燈后,大舅說:“別想了,多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吧。”
這個孩子能不能像帶弟一樣?這誰也說不準的事。可是大舅母就是放不下帶弟,有時她會坐那兒想,一個殘疾女孩子,到了那面咋辦?一想到這兒,她就會想到姥姥,這一老一小的,咋過?等到雞叫了,天亮了,又到了起來做飯的時候了。
大舅母起來,大舅也起來了。大舅母說:“你上山,把帶弟的衣裳給燒了吧,都是帶弟喜歡的。”
大舅點點頭,進屋取出了大舅母包好的衣物,上青山了。
我的大表哥就是在這樣的時候降生的。大表哥生下時一聲響亮的哭,全家人都高興了。大舅母第一件事就是摸大表哥的腿,那是蹬得有力的一雙腿。直到這時,大舅母的心才算平靜了下來。
六歲的老姨這回看起孩子來,不錯眼珠地看。有時老姨對母親說:“三姐,我眼睛看得有點疼。”
母親說:“你虎哇,不能看一會兒,閉一會兒眼睛。”
老姨說:“不敢。”
多少年之后,母親對我說:“沒媽的孩子,懂事早。”
大舅母的月子是大姨和大舅母娘家嫂子來伺候的。一個月后,都走了,日子還得大舅母一個人扛。
自從有了大表哥,母親她們多了一個名詞:“我大侄。”放學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大侄,抱大侄。姥爺更是有點好吃的,便想著他大孫子。大表哥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
四
春天,最先光顧的,是青山。家東面的青山,草叢中鉆出來的婆婆丁、苦麻菜、苣荬菜,是家家都愛吃的野菜。大舅母天一放亮,就挎著筐,拿一把鐮刀頭,上山了。家離山近,沒走幾步就上山了,山坡上的野菜,剛鉆出來,嫩綠,遠遠地就看見了。站在青山頂上,往北,是湖面。湖北岸,有一條鐵路,雖然看不見鐵路,但能看到火車冒煙,那道煙像是在水中移動。每次上山,大舅母都要朝北看上一眼,接著便抓緊挖菜。不管挖多少,做飯前是一定要回去的,一大家子的早飯都等她做呢。
早飯后,上班的、上學的都走了,姥爺也去村里找人嘮嗑去了。大舅母收拾完屋里,把孩子放在炕里,讓老姨照看著,便開始喂豬,喂雞,剁鴨子吃的菜。為了一年的油水,也為了一年的零花錢,姥家年年都是養兩口豬,殺一口,賣一口。喂豬的桶,是用膠皮做的,大舅母一次只能拎大半桶,裝滿了,拎不動。兩口豬,小的時候還好喂,一桶兩桶的,可是到了冬天,喂一頓就得來回跑四趟。那時三舅已是大小伙子了,可是大舅母從沒讓他幫一次。雞鴨食都是用野菜剁成碎碎的,拌上糠。把這一切活兒干完了,她進屋看一下孩子,就到了做中午飯的時候了。中午飯后,大舅母又挎上筐,上青山去挖野菜了。每次上到山上,大舅母都要往北望一眼,碰到過火車的時候,能看到火車冒煙,大多的時候是不過火車的,那就煙都看不到。看不到火車,大舅母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失落感,心里空蕩蕩的。每次她都想多站一會兒,等火車過來。可是家里一堆活兒等著,由不得她。多少次,她就是這樣戀戀不舍地下了青山。
一天,大舅回來得早,大舅母見大舅沒什么事,在那兒抽煙,就問:“北面的鐵路離咱這兒有多遠?”
大舅說:“你問這兒干啥?”
“不干啥,就是問問。我上青山挖菜,能看見那兒的火車冒煙,可是看不清火車長成啥樣的?”
“直走不遠,二三十里地兒。要是從路上走,得繞上個大彎子,從塔虎城那兒繞過去,七八十里路。”
“火車是啥樣的?咋冒那么多煙?那得燒多少火才能冒那么大的煙?”
“火車是啥樣的?長長的,好多節,有火車頭拉著。火車頭上燒火,一節有咱們房子這么長。我也沒到過跟前,也是在路上看到的。等有時間了,我拉你去看看。”
“火車上燒啥?是木頭嗎?”
“燒煤,大塊煤。專有一個燒爐子的,爐子里裝的水,把水燒開了,就帶著車走了。一邊走一邊從兩邊往出噴白氣。等有時間了,我拉你去看看就知道啦。”大舅能知道的,也就是這么多。
“哪有時間?我就是好奇,總能看著冒煙,就是不知道啥樣。要是有時間了,真想去看看。”大舅母聽到大舅拉她去看,心里特別高興。有大舅這句話,她就知足了。她也不是真的非看不可,看不看能咋的,不當吃不當喝的。可大舅說了,那就是一份恩愛。后來,大舅母把這話說給我母親,說她這一輩子,知足了。大舅心里有她,等有時間了,一定跟著去看看火車。
大舅母把我母親她們當成自己的親妹妹,有什么話都愛說給她們聽。親。
到了夏天,各種野菜都下來了。特別是水邊的堿蓬草長了起來,只要用刀割就行。割回來,放到大缸里一泡,發酵了,就能喂豬了。雞鴨也都可以放出去找食吃了。豬、雞是省事了,可園子里的草也瘋了似的長,一眼沒照顧到,草就把苗給蓋住了。大舅母一有時間,就要進園子鋤草。她一邊鋤草,一邊還要聽著屋里的動靜。帶弟的事讓她心總是懸著,有時鋤了一會兒,耳邊就像響起了孩子的呼喊聲,她扔下鋤頭就往屋里跑。自從帶弟沒了,大舅母就沒擦過帶弟拍過的那塊玻璃。她最怕的,就是兒子到那玻璃前。每次她都對老姨說:“老妹子,別讓你侄兒去窗臺那兒。”
“我知道了大嫂。”老姨自從帶弟的事兒之后,仿佛一下子長大了。
姥家的園子里自從出了帶弟的事兒,就再也沒種過香瓜。大舅母也從不買香瓜。后來全家人都不提香瓜,因為一提香瓜,大舅母就會掉眼淚。那是大舅母一生中心里的陰影,直到彌留之際,也沒能走出來。
家里的活兒,總是沒有干完的時候。姥爺是真正的老爺子,有時候,他從外面回來,見豬從圈里跑出來,進了園子吃菜。他會走到屋里,對正在做飯的大舅母說:“豬進園子了。”說完,鞋一脫,上炕躺下了。
大舅母就得趕緊放下手中的活兒,進園子里把豬趕出來,而不會讓姥爺去趕豬。在大舅母的眼里,老人就是老人,永遠是對的。哪怕是錯了,也不能說。兒女是不能說老人不對的,這是大舅母從小的家教。
秋天,是大舅母最喜歡上青山的時候。秋高氣爽,天高云淡,這時站在山上,可以看到火車如一條黑線在行走,火車頭上冒著煙也看得清楚了許多。看過之后,她便加緊干活兒。有的時候,看完了,她會責怪自己,看什么呀,不頂吃不頂喝的。可是每次來到山上,她都是忍不住要往北多看上幾眼。要是這個時候沒有火車經過,她會覺得心里空落落的。仿佛是白上來一趟似的。
家里的錢都是大舅管,大舅母只是用錢的時候跟大舅說一聲。有時大舅說:“沒錢了。”大舅母就會說:“那下月放工資時再說吧。”她從不問大舅的錢干什么花了。她覺得大舅花了,一定有花的道理。
有時大舅說:“再放工資你管吧。”
大舅母說:“我可管不好。再說了,女人管錢,說出去你多沒面子。你沒聽說過騾子駕轅馬拉套,老娘們兒當家瞎胡鬧嗎?還是你管吧。”
就這樣,家里的錢,一直是大舅管著。除了每個月的工資,就是賣豬、雞、鴨的錢,大舅母都交給大舅管。
家里用錢最多的,是三舅。三舅在鄉里念了初中之后,考進了縣里的高中。高中就住校了。那時在學校吃飯,家里要往學校交糧。按學校的要求,大舅每月都是早早地就送去。大舅母每月都要做上幾罐魚肉醬,用罐頭瓶子裝好,同糧食一起給三舅捎去。學費錢都是大舅按時給,大舅母從沒問過,可她知道,從三舅上了高中,家中的錢更緊了。到了冬月了,大舅還沒把花布買回來,大舅母有些急了,就問:“花布啥時能買回來?過年了,別人不做新衣裳,他三個姑姑總得做一件花襖吧。”這時大舅母用的他,是指大表哥,三個姑姑就是母親她們姐三個。
“沒錢了。都給老三交學費了。”大舅說。
大舅母看看大舅說:“你別急,我想想法子。過年,小閨女都想有件新衣裳,要不都沒法出門。咱家又不比別人家。”
“我也急。可是急也急不出錢來。”大舅說。
大舅母怕大舅急,怕大舅上火,就說:“我想法,咋的也讓他三個姑姑過年穿上花衣服。”
就是那一年,大舅母用她結婚的花被面,給母親她們姐兒仨做了花衣裳。母親后來跟我說,那是她一生中穿得最好看的花衣裳。還有紅紅的大綾子,扎在頭上,扎成了蝴蝶結。一跑起來,紅紅的綾子扎成的蝴蝶結在頭上晃動著,像飛起來一樣。俊。
五
多年的和尚修成佛,多年的媳婦熬成婆。
大表哥十八歲那年,大舅母熬成了婆。
大表哥結婚的時候,家中有姥爺、大舅、大舅母和大哥、二哥、姐和老弟。母親他們兄妹四人都結婚了。三舅結婚在縣里,也沒和大舅分家,等于是凈身出戶。
大舅母喜歡大兒子,用姥爺的話說:“家有長子,國有大臣。”可以說是傾其所有,為大兒子辦婚事。雖然如此,那長長的彩禮單子上,還是有幾樣沒能買到。一是煙臺產的掛鐘,因為沒有票,沒買到。那時物資是計劃供應,全漁場那年也沒給一張鐘票。二是十四尺青趟絨,那是供銷社沒有,布票也沒有了。還有些東西,那是實在沒辦法,這些都由媒人跑了幾回,并用面子擔保,結婚后一定給補上。這叫欠彩禮,也叫欠下了人情。這在當時,是普遍的現象。
大表嫂家的村子,是鄉政府駐地,比一般的村子要大一些,比漁場要大上幾倍。大表嫂的家是種地農民,雖然彩禮欠下些,可大表哥在漁場上班,也算是高攀了,至少不算是下嫁。
大表嫂姓蘇,一米七五的個頭,一百五六十斤的重量,有兩個大舅母重。我們都叫她蘇大個子,沒人去問她的名字了。大舅同意這門親事,因為大表嫂長得大,不像大舅母,瘦小。用大舅的話說:“發實。”但是,從當年姥姥一個比一個高的標準來看,接下來的兩個兒媳婦得多高?事到臨頭,也就顧不得那么多了。
大舅家,應說是姥爺家,三間房,姥爺占了一間,廚房一間,大舅實際上只有一間。一間房住大舅一家子,只有南北炕了。大舅和孩子住南炕,大表嫂和大表哥住北炕,兩炕之間,掛上幔子。這在大布蘇草原是普遍的居住現象,所以,彩禮中,幔子是必在其中。
我們所有的人都在想大舅母的身體怎么扛過兒子結婚的勞累,可是大舅母始終是精神兒地忙著。是的,家中離不開大舅母,就是來幫忙的人也感到如此。
“剪子?剪子在哪兒?”
“斧子?斧子在哪兒?”
“線板子?紅線?”
“紅包,壓車的紅包在誰那兒?”
……
家中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在問,只有大舅母能回答上來。雖然忙得喘不過氣來,可大舅母臉上一直笑,是發自心底的,在每一道深深的皺紋之中。結婚正日子的早上大舅母換上的新衣服,到了中午,那衣服像是穿了一年似的。她是奮不顧身地干著活兒,怕出現一點點的紕漏。可是她從沒有支使別人的習慣,看到了活兒,便伸手去做。這樣的結果,是她那身新衣裳,當成了工作服。有人找她問事,問完了,她想去做下一件事,可腿像灌了鉛似的沉,必得扶上一把才能動起來。身體疲憊,可眼睛亮亮的,興奮。
大表哥結婚的第二天早上,第一個起來的,是大舅母。她把昨天宴席上剩下的飯菜熱一下,端到桌子上來,然后才喊大表哥兩口子起來吃飯。雖然大舅母累得腿軟、眼花,可是高興,兒子娶上媳婦了,這是天大的事。盡管她強挺著起來,可是她還是得起來。她希望大兒媳婦能起來,哪怕是幫她燒一把火,她心里也高興。再說了,到現在,她也沒和兒媳婦聊過幾句。她還記得,她結婚的時候,也是這樣,婆婆像親娘一樣幫著她。她也要對兒媳婦像親閨女一樣,她要把家中的大小事物都交代一下,可是大兒媳婦沒有起來。
“大兒子,起來吃飯了。”大舅母站在幔子外面小聲地叫著。
“你們先吃吧。”大表哥在幔子里迷迷糊糊地說。
“起來一塊兒吃吧,大兒子。一會兒就涼了。”大舅母小聲地說。
“嗯。起來了。”是大表嫂的聲音。
大舅母聽兒媳婦說話了,回身到外屋去了。
姥爺在外屋聽到了里屋的說話,在外屋說:“傻吃苶睡呀,真的是傻吃苶睡呀。也不知道早上起來幫你媽干點活兒。”
在大表哥對面炕上的二表哥接過話說:“心寬體胖,一看就是傻吃苶睡。”
大表嫂在北炕一把將幔子拉開,大聲地喝道:“你說誰?你說誰呢?誰傻吃苶睡了?心寬體胖也不是吃你家糧長大的。”
“誰傻吃苶睡誰知道!”二表哥說。
“爺爺說可以,你說就不行。你是干啥吃的管我,我嫁給你哥了,沒嫁給你。你憑啥說我?”大表嫂衣服沒穿好就下了地了,樣子像斗架的公雞。
大表嫂身材高大,二表哥瘦小,兩人站在一起,顯然不成比例。可是二表表哥不怕,跳著腳說:“尊老愛幼,你們老師沒給你講過呀。為啥早上不起來做飯?”
大舅母在外屋聽屋里吵起來了,忙進屋,她先指著二表哥說:“怎么跟你嫂子說話呢!沒大沒小的。我不是給你們講過老嫂比母的故事嗎?再不能和你大嫂這么說話了。你那幾個姑姑哪個這樣跟我說話了?越大越沒規矩了。”說完,回過頭來跟大表嫂說:“他小,不懂事。別跟他一樣的。洗洗臉,吃飯。”
大表嫂看看大舅母那一臉的憔悴,沒再說什么,出去洗了臉,回來吃飯了。吃完飯,大表嫂回到北炕,把幔子拉上一半兒,斜躺在行李上了。
大舅母看了,跟過去說:“咋啦?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去衛生所看看?咱衛生所的小大夫看病還行。”
“沒事。躺一會兒就好了。胃里窩了口氣。”大表嫂躺在行李上說。
“那我去給你拿點面起子來。”大舅母也不管大表嫂是啥態度,到外屋拿來半勺子面起子。遞給大表嫂說:“我要是胃里窩住氣了,吃上就好。”
大表嫂沒法子,接過了面起子說:“放這兒吧,我一會兒吃了。”說完把臉轉到了里面。
大舅母看看,沒再說什么,到外面干活兒去了。她想,可能是兒媳婦想家了。都是從新媳婦過來的,都想家。
第二天,大表嫂還是吃完飯就躺下。
第三天,回娘家。這是當地的習俗,稱三天回門。因道兒近,三天回門是不能在娘家住的,要天黑前回來。如果道遠,就得七天回門,在娘家住上一個晚上才能回來。那天大舅母早早地就把回門的禮給備好了,吃了早飯,大舅母就讓大表哥領大表嫂回娘家了。
大表哥和大表嫂三天回門,晚上早早地就回來了。當天晚上,大表嫂對大舅母說:“我想分家。”
大舅母當時端了半簸箕生瓜子,正要去炒,聽了這話,半簸箕生瓜子全撒地上了。如果不是在鍋臺邊上,她扶著鍋臺,就摔倒了。可是緊接著,大舅母馬上說:“咋了?”
“樹大分枝。”大嫂說。
“你們兩口子商量了?”大舅母問。
“是他讓我說的。”大表嫂說。
大舅母沒再說什么,把撒在地上的瓜子收起來,開始炒瓜子了。一邊炒,一邊淚水滴到鍋里,發出嗞啦嗞啦的聲響。
分家,在村里不算小事。
按照村里的老理兒,分家一定要找舅舅。親娘舅,娘親舅大。為了把家分好,大舅母除了自己的娘家哥哥,還把大表嫂的親舅舅找來了。大表嫂的舅舅是村里書記,用大舅母的話說,是個明白人。另外,還找來了村小學的葛鳳江老師,寫分家單。這不是誰都能寫明白的。
大舅和大舅母把這些事想好了,大舅母突然想到,這事最好別讓老爺子在場,分家終是件上火的事。大舅想想說:“送爹上大姐那住兩天去。前幾天大姐還說了,讓老爺子去住幾天。”大舅的大姐就是我大姨,嫁到了青山東鄉政府的村子。分家前,大舅把姥爺送去了。
舅舅來了,雙方的舅舅,坐在炕桌的兩頭。大表嫂的舅舅坐在炕頭,這表示高看一眼。在我們村子,最尊貴的地方,就是炕頭。另外還有一層意思,大表嫂的舅舅是他們村的書記。大家都叫他潘書記。凡是到過農村的都知道,村書記就是一村中的人尖子。精。
潘書記既然坐了炕頭,自然就得由他先說正題了:“親家,這事,讓我咋說呢?可是沒法子,樹大分枝。可也要分得兒子還是兒子,媳婦還是媳婦。都說分家三年生,那就是沒分明白。”
大舅點點頭,大表哥的舅舅也跟著點點頭。誰也沒接話,親家說的是理兒,就由著親家往下說。
“你這家我也看了,分家另過,第一件事,是得有房子,不能讓孩子去溜房檐。可是現蓋,那是來不及了,只有買。他們也打聽了,這村子有一家賣,三間房,八百元。雖然是土平房,價不高。咱們就合計一下,這八百塊錢咋辦?放在誰家,都不是個小數。”潘書記說。
八百元。大舅母在外屋一聽,險些沒把手中的勺子掉地上。
大舅聽了,說:“八百,一下子拿八百?就是借,也借不到那么多呀。”
潘書記說:“八百,咋說也不是個小數。可這也是置一份家業。就是借,說到哪兒去,也不是個丟人的事。這也不是買餑餑餅子,吃了就沒了,這是家業。井里沒水四下淘嘛。別人不說,我這個當舅舅的,也算上一份,有多幫多,沒多幫少,總不能看熱鬧就是了。咱們先說下行不行?”
大舅說:“行。給孩子買房子,那是正事,咋能不行呢。”
大表哥舅舅,我們也叫他老竇大舅,他說:“正事。親家說得對。我這個舅舅也算上一份,有多少幫多少。”
大舅想想說:“那這三間房要是都給了老大,我這還有老二、老三呢。他們咋辦?”
潘書記說:“親家,這事,我在村子也經過。既然是分家,就得分個明白,別留下麻煩。這里面有這么幾條道,你們看:一是三間房兄弟三人一人一間。二是老大要這三間,他拿出兩間的錢,三間全歸他。”
老竇大舅看看坐在身后的大外甥和大外甥媳婦,說:“你們兩口子合計一下,兩條道,自己選。”
大表嫂說:“三間房我們都要,那兩間的房錢我們給。彩禮欠下的錢,我想用這錢頂。頂剩下的,我們寫條欠著,有錢了就還。”
彩禮欠下的錢,是大伙都知道的。這個賬大伙都認。既然這樣,那就算算賬吧。大表嫂早就把彩禮單子準備好了,拿到桌上一算,兩百三十多元。這樣一頂,大表嫂再拿出三百元。
大表嫂算完彩禮賬說:“屋里用的,我啥都不要,再去掉一百元。剩下的兩百元,我打欠條。”
如此一來,房子全歸了大表哥,可是八百元現錢還得大舅往出拿。大舅坐在炕沿上,只是抽煙,一句話也沒說。
大舅母在外屋聽得明白,可是她不好進屋去說。這事有大舅在,有哥哥在,有親家在,她一個女人家,進去說個啥。可是一想到兒子要搬出去,盼了這些年的兒媳婦,轉眼間分家另過,和她成了兩家了,大舅母的眼淚就止不住地往出流。
老竇大舅見大舅不說話,就問:“妹夫,你們手里有多少錢?算計一下,還得借多少,這事總得落下來呀。”
“手里哪還有錢了,結婚的錢還欠著兩百多呢。”大舅聲音不大,屋里的人卻都能聽到。大舅說的是實話,在村子里,大舅家的日子過得算是好的。滿村子算起,沒有外債的,沒幾家。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去了領糧買油的,人情往來的,頭疼腦熱的,還能剩下幾個錢?就這幾個錢,還得過年吃頓餃子,春秋換季的衣裳。不欠錢,那就是會過日子的。
潘書記坐在那兒,沒說話,只是看著老竇大舅。
老竇大舅聽了妹夫這話,一拍大腿,說:“那還買啥呀?八百元,不是個小數。”到了這個時候,是親三分相,他肯定要替妹妹一家著想。過日子,背上這么大一筆債,放在誰家都是個大事。
老竇大舅的話音沒落,就聽大表哥身后哇的一聲,大表嫂號啕大哭。
在外屋的大舅母終于忍不住了,她進到了里屋說:“兒媳婦,別哭。媽就是砸鍋賣鐵,也把房子給你買下。”
大表嫂正哭著,聽大舅母這么說,立馬停住了哭聲,喊了一句:“媽!”這是大表嫂自結婚到現在,叫的第一聲媽。
大舅母說著兒媳婦別哭,自己卻淚流滿面,她一邊哭,一邊說:“我不能讓我孩子受委屈,一定給我兒子買房子。”屋里人看到瘦弱的大舅母的雙肩在寬大的衣服里抖動著,都感動了。最先說話的,是潘書記,他說:“我借給你們兩百元,親家,啥時有啥時還。我信著你們了。”
老竇大舅說:“我這兒就有八十元。先借這八十元吧。”
大舅母說:“圈里有三頭豬,都賣了,能賣四五百塊錢。過年不殺豬了,先讓我兒子住上房。”
大表嫂這時又喊了一聲:“媽!”這回顯然是被大舅母給感動了。可是據我所知,這也是大表嫂這一生中,最后叫大舅母“媽”。因為從這之后,她再也沒叫過。后來有了孩子,就改稱“他奶奶”了。
炕燒得熱,潘書記的上衣實在有些穿不住了,只好脫下來。上衣一脫下來,里面的白襯衣就露了出來,那只是一個襯衣領子,下面什么都沒有。如果不脫衣服,誰也看不出來,那只是一個領。這種襯衣領,縣里許多干部都這么穿。因為襯衣實在是貴了點。潘書記把襯衣領子也一起脫了下來。
直到這個時候,坐在邊上的葛老師才說話:“分家單上還有什么要說的,我都寫進去。我這兒先起草一個稿,大家看看,如果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我就開始復寫。一式幾份?”
“兩份吧,爺兒倆一家一份。”潘書記說。
分家單
甲方:章鳳魁
乙方:章樹茂
一、經父子全家協議,分家。
二、新購本村新居產權由章樹茂所有(購房資金由欠彩禮錢二百三十元、家具一百元相抵,另由章樹茂出兩百元)。
三、老宅三間與章樹茂無關。
四、今后父母贍養由兄弟三人共同承擔。
協議人:章鳳魁、章樹茂
見證人:潘天祥、竇慶富、葛鳳江
大家看后,沒啥意見,就由葛老師復寫。大舅母到外屋去炒菜,分家飯是一定要吃的。直到這時,大表嫂才第一次走進廚房,幫著燒了一把火。
六
大表哥分家,大舅母病了一場。病好了,便總是覺得心口悶得慌。悶得嚴重了,她就吃點面起子。這些年,她自己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面起子了。
大舅母病還沒好,姥爺回來,立馬就知道大孫子分家另過了。老兒子大孫子,那是姥爺的命根子。聽說了這件事,姥爺就認為是大舅母的主意,可這話又不好問。那天晚上,找茬把大舅罵了一頓,生著氣就睡覺了。哪承想,第二天早上,姥爺起來,就瘋了。抓住了大舅母,拿炕上的笤帚就打。好在孩子和大舅在家,大伙上去把姥爺拉住了。大舅母雖然挨了打,可是她卻沒生氣,對孩子們和大舅說:“讓他打兩下出出氣就好了。老爺子這是急火攻心,病了,這么些年,沒見他打過人的。”
姥爺的病,時好時壞。犯病了,就瘋,就罵,就打人。好了,跟好人一樣。別人說他打了大舅母,他還不承認。后來看到大舅母被打的傷,他還一再地給大舅母賠不是。可是犯了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姥爺這一有病,家中就熱鬧了。大姨二姨三舅都回來了,母親離得近,隔三岔五地回去一趟。大家回來,都是來勸姥爺的,大家都明知道不怪大舅母。姥爺是明白人,不犯病的時候,咋說都行,犯了病就不是那樣的了。大舅母的身上頭上都讓姥爺給打壞了,可是大舅母總是說:“老爺子這是有病了,打就打兩下。父打子不羞,都怪我,還是我沒能把兒媳婦給攏住。”父打子不羞,這是多少年的老話,誰沒讓父親打過?可又有幾個公公打兒媳婦的呢?
姥爺的病,后來是三舅托人買來了藥,吃上就見效,犯病的間隔漸漸地長了。不犯病的姥爺,見大舅母一天比一天瘦,還是心疼的。
春天里,大舅母上青山挖菜,還是每次都往北面望上幾眼,可是眼睛有些模糊了,看不清了,有時能聽到火車的笛聲。聽到那笛聲,大舅母晚上便跟大舅說:“我上青山,聽到火車的笛聲了。你說這么遠都能聽到,到了近前,還不把人震聾了?”
“瞎扯。都震聾了,誰還敢開火車了?”大 舅說。
大舅母想想,也是。她不再說了,而是想著那火車的笛聲,到了近前能是多大動靜?總得比汽車的響,汽車是讓路上的人讓路,那火車上,讓啥呢?大舅母就這樣地想著。想了一會兒,她又對大舅說:“火車跑得那么慢,一天能跑多遠?”
“火車,快了去了。站在路邊,刷的一下就過去了。風能把人帶倒了,還慢?”大舅有些煩了,咋啥也不懂呢。
“我在青山上,感覺是慢慢地往前爬似的。”大舅母說。
“有時間了,我拉你去看一回就知道了。你咋就跟這火車干上了?鐵路上的事,誰能說得清。等你有時間,我拉你去看一回就知道了。”大舅說。
每每聽到這樣的話,大舅母都會感動好一陣子。男人對她好,就是女人最大的幸福。可幾十里的路,來回要一天的時間,哪有那個時間。雖然如此,她還是感到幸福。每次回到娘家,大舅母總是把幸福感告訴娘家人,娘家村里人也都羨慕大舅母找了個好男人。大舅母回娘家最常說的話,就是:“他不愛說話,可心里有我。總要帶我去北面看火車,可這一天忙的,哪來的時間。把家扔下了,去看火車,不讓人笑話死。”
大舅母心口疼的病越來越重了,有時疼得直不起腰來。可是當二表哥他們說讓她去衛生所看看,她總是笑著說:“吃點面起子就好了。老毛病了,用不著去衛生所。去了就得花錢,沒買幾片藥,就花上好幾塊錢。要多少得給多少,價都不讓講。搞不好,還讓你上縣里大醫院開刀動手術啥的。嚇都嚇死了。”
到了秋天,從山上往下背柴草,大舅母背得少了,進了院子,放下柴草,好一陣子起不來。等到起來,拍拍腿,恨自己,咋說沒用就沒用了呢?這么點柴草,就累成這樣了。姥爺看到了,說:“背不動,少背點,多跑幾趟。”
大舅母一邊摘著灰白頭發上粘的草葉,一邊說:“誰有爹您那個福哇。一趟下來,家里就雞飛狗叫的,到點都餓了。”大舅母邊說著,邊走進了屋里,開始引火做飯。“吃飯點耽誤不得,有學生。”這是大舅母最常說的話。
等吃完了中午飯,姥爺要睡個午覺。大舅母見姥爺的鞋有些塵土,便拿一塊舊布,把土給擦掉。青布鞋,有一點兒泥土就顯現出來,大舅母用指甲蘸點唾沫,把泥點摳掉,再擦凈,然后把鞋放到炕沿下面,斜著立在那兒。
姥爺的衣服、鞋,大舅母不管多忙,天天都要看看干凈不干凈。大舅母說:“老爺子是一家子的臉面,可丟不起這個人。老貓炕頭睡,一輩留一輩。”大舅母的一輩留一輩,那是我看到最直接、最淳樸的身教。什么大道理都沒有大舅母的身教更讓子女們記住。
進了十月,大舅母每天總是感到餓,又有點饞。在此之前,餓是有的,可是她從來不饞。不管多好吃的東西,她從不往嘴里放一口。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她張不開嘴。可是近日,她卻總是聞到香味,就是爆鍋的香味,也讓她饞得不得了。為這個,她打過自己的嘴,可還是控制不住。在家里,只有姥爺看她一天比一天瘦,看她看肉的眼神,知道她真的饞了。一天,孩子們都走了,姥爺說:“給我做兩碗疙瘩湯。多加點油。”
大舅母認真地做著,一共是兩大碗。鍋里就剩下一點點湯,大舅母嘗嘗,香,真香。湯端到桌子上,大舅母要回身的時候,姥爺說:“大份的,給你一碗。特意給你多做一碗。”姥爺稱幾個兒媳都是這樣叫,大份的,二份的,三份的。
大舅母說:“爹,我不餓。”話說著,可眼睛直直地看著那碗湯。
姥爺說:“吃吧。你這些年,虧嘴。”
大舅母沒再說什么,拿來一雙筷子,可是端起碗,她像是做錯了什么事一樣,低著頭,臉幾乎貼在碗上。疙瘩湯香,可是眼淚也伴著出來了。姥爺的湯還沒吃到一半,大舅母的湯就吃完了。
大舅母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大舅說:“去縣里醫院看看吧。”
大舅母說:“都是大夫,衛生所看了,沒啥大毛病。我就是這個體質。從小就沒胖過。”
大舅說:“不一樣。”
大舅母說:“等有時間的再說吧。多買點面起子回來,吃一口,胸口就舒服了。”
大表哥雖然分家另過了,可是大舅母總是不放心,有點時間就過去看看。發現兒子缺啥,就從家里往那兒拿。幾個月過去了,大表嫂懷孕了。大舅母就說:“別自己做了,都上家里來吃吧。”
大表嫂二話沒說,一日三餐都回姥家吃。饞啥東西了,便自己回家做點,自己吃了。這事大舅母知道,可是她從沒有去說。有人和她提起,她會說:“懷著孩子,都這樣。那是孩子饞了。再將就幾個月,生了就好了。”
幾個月后大表嫂生了,小子。
這是一家人最高興的事,不管大家如何地看大表嫂,都喜歡這剛生下來的小子。幾個姑奶都回來了,家里又像辦喜事一樣的熱鬧了。
大伙高興了一陣子之后,便想到給孩子起名字。姥爺說:“他們這輩范的云字。”姥爺這么一說,名就只有一個字了。
大姨說:“爹,你給起個名字,這可是你的重孫子。”
姥爺說:“老了,跟不上了。還是你們起吧。”
二姨說:“大弟,你起,你是爺爺了。”
大舅說:“我可起不好。”
母親說:“我看就叫亮吧。有了這個孫子,都亮堂了。”
三舅說:“我看這個名字行。見著一輩人了,心里就亮堂了。”
就這樣,大表哥的兒子叫章云亮。
大舅母自從有了孫子,便每天都要跑去看上一眼。白天沒有時間,便晚上拉上大舅一起去。家中凡是有一點兒好吃的,都想著給孫子吃。可是家中還有姥爺,還有一大家子人。所以,大舅母就只能偷偷地往大表哥家拿。這事姥爺心里明鏡似的,可就是不點破,他怕大份的下不來臺。可是后來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說:“大份的,兒孫自有兒孫福。你看你都啥樣了,給自己留一口吧。”
大舅母一聽這話,眼淚又出來了,說:“爹心疼我,我知道。可是這心里就是放不下,東西往嘴里一放,就想到孫子的小嘴了。啥好吃的都咽不下了。”
“大份的,不是我說呀,你這樣下去,不行啊。你照鏡子看看,你的頭發,一點兒油腥沒有,比我這頭發都白了。再熬下去,非倒了不可呀。”姥爺說著,嘆了一口氣,回頭走了。那是姥爺為兒媳婦掉淚了。不犯病時的姥爺,明白。
大舅母也知道自己的身體不行了,可是又能咋樣。這一大家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哪個都得管,哪個都扔不下。好在姑娘大了,可以幫她一把了。
大舅的女兒,從小大伙就叫她小姑娘,我們都叫她姑娘姐。姑娘姐像大舅母,從小就知道幫著她娘干活兒。小學念完了,就沒上初中,留在家里幫娘干活兒。姑娘姐心疼娘,看不上大表嫂,便阻止她娘往那拿東西。大舅母也沒辦法,就只好背著女兒,偷偷地把東西往兒子那兒拿。有時家中做點好吃的,姑娘姐便看著她娘把東西吃下去。大舅母就邊吃邊說:“等你有孫子了,也跟我一樣。見著下輩人,就是不一樣。”
姑娘姐也不說啥,就是看著她娘把東西吃了才算完。大舅母也沒辦法。雖然這樣,大舅母的身體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早上下地,要扶著炕沿活動一會兒才能走動。只要是能走動,她就會不停腳地忙一天。對姑娘姐干的每一件活兒,她都要再看一遍。
一天早上起來,大舅母對姑娘姐說:“姑娘,我夢見你大姐帶弟了。”
姑娘姐沒見過帶弟大姐,但她聽說過。她問:“都夢見啥了?”
“夢見你大姐腿好了,在那面照顧你奶奶,照顧得可好了。你大姐會說,你奶奶喜歡得跟眼珠似的。你大姐看到我,問我啥時候去?”大舅母說到這兒,停下不說了。
姑娘姐說:“夢都是反的,那是我大姐不讓你去。你也去不了。”
“你沒見過你大姐,那嘴,真的不知道像誰了,真會說話。啥話到她嘴,就是好聽,能說到人心里去。你那幾個姑姑都喜歡的不得了。那天要不是為了種幾棵瓜,也不能。都怪我,都怪我。”說著大舅母又流出了眼淚。
姑娘姐說:“娘,啥都是命。上午我去買點紙,送點錢去就好了。”
“行。多買點紙。燒的時候,小心山火,把周邊的草都收拾好了。前幾天我上山看了,清明時收拾好的,現在草又長出來了。”大舅母邊說著,邊擦干眼淚,準備下地做飯了。
七
大舅母孫子章云亮一歲多了,就在那年冬月底的一個晴天,大舅母站在門口,朝東面的青山看看,她想上去,看看能不能看到北面的火車。這樣的天,或許能看得清楚一點。可是今年的雪大,山坡上全是雪,沒有了落腳的地兒。她想轉到南面,那兒的坡小點。可是剛到了山坡,腳下一滑,便摔倒了。平日里,雪地上誰沒摔過。可是這回,她想爬起來,腿疼得鉆心,不敢用力,她試了幾回,都沒起來。她想喊人,可又覺得就摔了一下,喊人來,有點丟人。最后還是有過路的村里人看見了,去家里送了信兒,大舅知道了,找來幾個人,把大舅母直接抬到了衛生所。
衛生所的大夫看了,說是腿骨骨折。打上石膏,養。
躺在炕上,大舅母的飯量一天不如一天。人也瘦得只剩下一層皮了。
一天,大舅問:“咋回事兒?咋吃得這么少?”
大舅母說:“肚子里漲,吃了面起子也不管用。”
大舅說:“上縣醫院吧。”
大舅母說:“不去,別浪費那錢。孩子都大了,正等著錢用呢。偏偏這個時候,我腿又摔壞了。”
大舅說:“小姑娘十五了,家里的活兒都能干了,你就養你的病吧。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大舅母說:“我還真想讓小姑娘把書念完,可是她不想念了,那就不念吧。姑娘家的,念到啥時候也得嫁人。”
大舅說:“識個眼前字也就行了。你這腿好了也得三個月,傷筋動骨一百天,不是一兩天能好的。想吃啥,我給你買回來。”
大舅母哭了,說:“我這一輩子,知足,知足了。”
大舅說:“干了一輩子活兒,都沒出過村子,有啥知足的。”
大舅母說:“女人這一輩子,嫁了個不打不罵的丈夫,就算知足了。我娘讓我爹打了一輩子,你一下都沒打過我。我知足了。唯一沒辦到的,就是想走近了看看火車,你說帶我去看,可就是沒有時間。不過有你的話,我就知足了。”
大舅說:“扯淡!打打鬧鬧的,咋過日子?好好養你的病,明天我再問問大夫。等你腿好了,我帶你去看火車。這回家里有小姑娘,也不用惦記了。”
大舅母說:“這幾天我總是夢見帶弟,要不是種那幾棵瓜,帶弟也不會沒。我干啥要種那幾棵瓜呢?”
大舅說:“多少年的事了,想她干啥?是兒不死,是財不散。老話都是這么說,別去想那些沒用的了。”
大舅母說:“咱倆不管誰先沒,都要和帶弟埋在一起,多少有個照應。”
大舅說:“這你放心,一定埋到一起。”
大舅母說:“我真不知道見到帶弟說個啥,我這當娘的,自己的孩子都沒照看好。想想我就后悔。”
大舅說:“上有老,下有小,你這一輩子,沒享啥福。”
大舅母說:“我知足。我這輩子,挺知足的。和村子里那些姐妹比,我不比她們差,雖說沒享啥大福,可也沒受著罪。也沒出田抱壟地下地干活兒。你對我好,爹也對我好,我知足了。”
大舅說:“沒遭啥罪,可也沒享著福。這回好好養養吧。”
大舅母說:“我想梳梳頭,你把臉盆幫我拿來。”大舅母梳頭,總把木梳沾上水,這樣梳出的頭就光,要不頭發總是亂亂的,梳不齊。可是當她拿起木梳,沾上水,胳膊卻舉不到頭頂上了。
大舅說:“我給你梳。”
大舅不會梳頭,也從沒給人梳過頭。可就這一句話,大舅母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她感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不過如此。接下來,大舅母的頭慢慢地靠近了大舅的身子。當大舅感覺大舅母的頭歪到自己的身上不動了,大舅母已咽氣了。
大舅母是帶著幸福走了。這一生除了沒有走近前看火車,她都滿足。雖然沒走近看一眼火車,她也是滿足的,大舅說過多少次,有時間了拉她去看火車。
大舅母走了,大舅這時就想一件事,后悔,咋就沒拉上她去看一次火車。按理說也不遠,也就七八十里路,咋就沒去一趟呢。后來每每提起大舅母,大舅都會說他這輩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沒拉大舅母看一眼火車。
姥爺自從有了重孫子,病也好了,姥爺說:“把我那口壽木抬出來,收拾一下,給大份用吧。”
大舅說:“爹,那怎么行呢,你都備了幾十年了。”
“給她用吧。她這一輩子,不易。”姥爺堅持著。
姥爺的壽木擺在院子里,這是村子里人都知道的壽木,足三五的。厚厚的油漆,不知上了多少遍了。來家吊喪的人看了,知道壽木給大舅母用了,都嘆息一聲:
“好人!”
作者簡介:孫正連,男,1957年生于吉林省乾安縣。1989年進入吉林省作家進修學院學習。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洪荒》《大布蘇草原》《守望大布蘇》《大布蘇淖爾》,長篇小說《大布蘇湖的秘密》《一九四五年大布蘇考》《浴血長城》,散文集《憑吊大布蘇》《走進千古大布蘇》。編著《查干湖鳥類名錄》《查干湖百科》《查干湖漁場志續志》《查干湖開發區續志》,中短篇小說曾轉載于《小說月報》《作家》《滇池》《青春》《春風》《章回小說》《鴨綠江》《北方文學》等。中篇小說《江水燉江魚的日子》發表于《人民文學》2021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