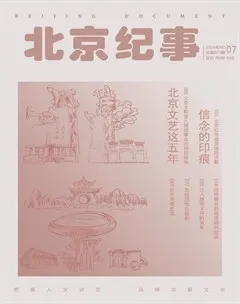敬畏認真,人生有果
高鋒霜
中國美術館2月—4月的開年大展“美在薈萃”,集中展示了國內15家美術館的鎮館之寶,展品琳瑯滿目,大師群星閃耀。三樓湖北美術館收藏的雕漆《春和景明》,令人眼前一亮。三扇中堂掛屏,山巒、關樓、松濤、云海,如詩如夢意境幽遠。兩側對聯“目極湖山八百里、人在水天一色中”,瀟灑飄逸灑脫靈動,觀者無不拍手稱絕。
掛屏作者文乾剛,北京特級工藝美術大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人。2009年北京工藝美術行業協會、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北京玩具協會的專家評審委員會,為文乾剛雕漆譽名“文氏剔紅”。
疫情前即與文老先生相識,近日又欣聞先生的作品集和設計圖集相繼出版,美術館歸來便與先生聯系,到文大師工作室祝賀、拜訪和請益。
在雕漆技藝路上攀登
正值初春,乍暖還寒,位于京郊的文老工作室外幽靜恬淡,室內大師帶領幾位藝徒雕漆制作有序進行。見面后,忙碌的文老先生停下手頭工作接待了我,第一時間面贈了那兩本新作,說道:“《質宗古意文興今情》《鏤象于漆傳之久遠》兩本書,分別精選了近年的雕漆制品和5T電子版雕漆圖樣,記錄了自己在延續雕漆文化的所愛、所念,呈現了自己對傳統工藝和當代文化相融相生的理解。”
翻開兩部作品扉頁,都有對作者簡單的文字介紹。文乾剛老人祖籍遼寧,生于秦皇島,1961年畢業于北京工藝美術學校雕塑班,分配到北京雕漆廠。
83歲高齡的文老先生精神矍鑠待人熱情,談新書、憶當年神采飛揚。他說,進廠后才了解到,雕漆又稱剔紅,始于漆器。五代時期的墓葬出土了銀胎雕漆碟,《髹飾錄》中有宋人雕漆裝飾的記述,明朝開辦官坊、清朝設置造辦,雕漆制作達到高峰,與玉雕、景泰藍、象牙雕刻被譽為京城工藝“四大名旦”,再加上宮毯、京繡、金漆鑲嵌、花絲鑲嵌,合稱“燕京八絕”。
那時中專生稀少,廠領導對他非常重視刻意培養,除了承擔廠里的文字工作,同時安排他學習雕刻和設計。提起當年自己入行的師傅,文先生敬佩之情溢于言表:“雕刻老師周長泰是大明風格,講究飽滿圓潤;汪德亮老師是大清風格,講究精到和變化。我從雕刻的‘上手五大工序‘刺、起、片、鏟、勾學起,再學‘下手錦紋雕刻。那幾年,我起早貪黑苦練基本技能,直到操刀如同寫字,不停筆、不修飾、線條流暢,一刀到位。對一百多種錦紋、三十幾種放射性劈松球等花樣也是得心應手,還跟汪德亮老師學到一手抖動做龍脊刺的絕招,把龍脊刺做得均勻起伏、精致生動。教我學習設計的朱廷仁先生是技術副廠長,他師承于雕漆作坊明古齋,后來被評為北京市二級工藝美術大師;孫彩文先生是廠里的主要設計人員,1956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四位‘雕漆老藝人之一。我向他們學到嚴謹認真的設計理念,也學到他們以靜蘊動、以柔含剛、以平取浮、以簡顯繁的設計風格。”
就這樣,文先生很年輕時就熟練掌握了雕漆的設計、木工、制漆、制胎、髹漆、畫工、雕刻、拋磨、燒藍等各道工序的技藝,相繼擔任了車間主任、設計室主任、創新室主任、總工藝美術師,挑起了工廠生產技術的大梁。
讓雕漆成為獨立的藝術品
人們日常見到的雕漆都是盤盤罐罐,雕漆藝術本身的魅力被器皿的功能所覆蓋。文先生立志沖破和擯棄雕漆的“器皿情結”,讓雕漆獨立登上民族藝術的輝煌殿堂。
首先,精彩傳神的三彩馬使他產生了創作靈感。經過縝密思索、多方咨詢和無數次現場臨摹,他設計開發出“雕漆馬”。米白馬身、硬木底座,嵌銀飾、掛藍釉,造型靈動華彩畢現,作為廠里的主打產品熱銷了20多年,海量訂單使員工得到了實惠,成為國家主要工藝出口項目之一。
其次,創新發展了龍馬負河圖。伏羲七天七夜降服龍馬,以馬背河圖定人倫、創八卦、點造書契,“龍馬負河圖”的傳說和藝術制品早已流傳于世。文先生把其引入雕漆,重新設計馬匹的頭、頸、身、腿與龍形相應部分重合,龍馬通體紅艷威猛神武,背上帛圖鑲嵌綠寶石和青金石,星光閃爍精美絕倫。
改革開放以后原工廠不復存在,文先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三十年來,他的團隊不斷摸索創新,雕漆藝術得以大幅度提高。文先生帶我進入他的精品展覽室,觀賞先生近年的杰作,使我大開眼界:
迎面映入眼簾的是亭亭玉立雕漆梅瓶,大朵的梅花在瓶面通體綻放,光彩奪目。文先生介紹說:“宋代經瓶、明朝梅瓶,都是以瓶體‘開光形式作畫,圖案集中在瓶體的框框里,藝術想象和視野受到很大局限。我的梅瓶繪畫,是讓嬌艷的梅花如同碧野精靈,狂放不羈地從修長瓶體‘跳將出來,表現出空前的感官沖擊力,也契合了我們雕漆人壓抑已久、亟待釋放的藝術熱情。”
尤為引人矚目的,是屏風《剔紅維摩詰演教》。主圖是象征辯論和探索的維摩詰坐于錦榻高談大論,諸多菩薩、神將、神女或凝思、或感悟、或嘆服,表情各具其妙。令人稱奇的是人物的眼神,始終對觀賞者緊追不舍、暗覷于人,神秘莫測玄妙無窮。文先生笑言:“傳統雕漆人物的眼睛是寫實的球體,缺少流轉和變化,形同死眼。我用鏤刻的手法,將雕刀作畫筆,雕刻出油畫效果的高光,讓人物的眼睛充滿靈動的魅力。”
展示中除少數桌椅床榻等雕漆家具,大都是富麗堂皇的雕漆屏風,文先生解釋說,屏風可繪畫題詩,融實用性、欣賞性于一體,雅俗共賞喜聞樂見,是裝飾高檔客廳、大廳、會議室的首選,與古典家具呈現出和諧寧靜之美。因此,我把這種價值連城的帝王家物,確定為雕漆制品的市場方向。
成功不負有心人,文大師創作的一對三米高的牡丹、石榴雕漆瓶,陳列進中央軍委接見廳。《剔紅居庸疊翠》《剔紅五岳長春寶座》等大型屏風獲得市級、國家級金獎,分別被北京市政府、市非遺博物館等單位收藏。湖北博物館收藏并在中國美術館“美在薈萃”參展的《春和景明》,引領了當代雕漆藝術的發展趨勢和潮流。
光鮮后面的艱辛和汗水
和諸多成功人士一樣,文先生為雕漆藝術的巨大付出可以想象。雕刻和設計的基礎是繪畫,漆雕創作必須高水平地掌握人物、山水、花鳥、龍鳳、動物等幾乎傳統繪畫的所有技能。文先生說,自己幼年時就醉心于畫畫,因生逢戰亂,沒有像樣的紙張和顏色,墻面、地板就成了他的畫板。他收集香煙盒上的畫片,臨摹武俠小說里的文臣武將、神仙湖怪,上世紀五十年代考進北京工藝美術學校,才得到初步的專業培訓。如今的繪畫和書法成就,更多地來自刻苦和勤奮。
創作仿唐剔紅馬時,文先生一次次到歷史博物館觀摩研究,還先后去東風農場、紅星農場、靈山高原馬場去寫生。面對各種動態的馬群,一畫就是半天,回來后再一遍遍默寫。
創作和設計,必須具有深厚的文史知識。因此他擠時間背誦唐詩、宋詞、元曲,研讀四大名著、《古文觀止》等古典文學著作。同時學習世界美術史,力求在創作中融匯中西,使濃郁的民族特色與世界文化藝術接軌。
目有所察才能心有所悟,為了觀摩北京的名勝古跡,他靠騎車和徒步走遍城郊各處景觀,一邊走一邊畫,翻山越嶺、忍饑耐寒。飽覽自然的神奇、天地的造化,使他的創作多姿多彩永葆勃勃生機。
工作室的同仁們談及文大師,說他的生命都在緊張工作中度過。為了保證下一步工序的進度,他往往抓緊別人休息的日子,搶時間、趕進度。大家敬佩他不吸煙不喝酒不打牌,幾乎沒有任何娛樂活動,平日研習書畫、遠足攝影,都是為雕漆藝術服務。還說他最大特點是善于接受新事物,近年學會了開車、學會了熟練地使用計算機設計畫圖,進入了雕漆藝術創作的自由園地。
文老先生不忍提及全身心投入雕漆而對家庭、父母、子女的虧歉和內疚,閱盡人間滄桑之后更顯豁達。他說自己最高的精神追求和享受,是“敬畏認真、人生有果,不能碌碌而過”。無疑,“文氏剔紅”是文乾剛大師敬畏認真的人生之果。更難能可貴的,雖已耄耋之年,仍表示還要帶領藝徒們,在雕漆傳統技藝基礎上,做更多的嘗試、更多的探索、更多的突破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