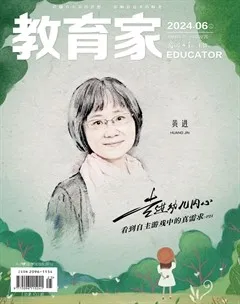叩問新時代幼兒園勞動教育的境界
郭良菁
追問1:勞動與游戲、生活的關系為何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我國并非新議題。作為國民教育體系基礎階段的幼兒園,有必要基于對普通學校教育與生產勞動為什么在特定時代相互分離、為什么隨著時代發展又被倡議重新結合的理解,并結合對3-6歲兒童身心發展水平的認知,審慎規劃勞動教育。
幼兒園勞動教育必須考慮時代背景和年齡分工
在人類的早期階段以及現在仍保持著簡單生產生活方式的群體中,教育與生產和生活中的勞動是融合在一起的,不需要專門議論“勞動教育”。兒童甚至在能獨立移動之前,就自然而然地被成年人帶入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活動,模仿并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從一個片段到完整的過程,日復一日地在應對勞動過程給自己的體力和腦力帶來的挑戰中進行著學習,也自然而然地體驗到勞動成果對自己生存的意義,意識到勞動讓自己作為人的本質力量逐漸展現。
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人類社會分工和勞動分工均愈發細致,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工逐漸固化,簡單勞動日益被機器取代。越來越多的兒童被送進專門的教育機構,為或遲或早地“成為”不同的勞動者做準備。近代以來,鑒于童工現象造成了兒童片面畸形發展的嚴重后果,工業化國家還通過法律要求教育機構承擔起保護兒童不受雇傭勞動摧殘的職責,使他們在體力和腦力上全面蓄能,以應對未來生產勞動及分工不斷變革的挑戰。所有這些都促使身處教育機構中的兒童日益遠離社會生產勞動,越是年幼的兒童,越是被賦予課業學習的“正業”。為了讓兒童把更多精力花在學業上,很多家庭也把他們隔離在家務勞動之外。
然而,這種“普通教育”機構并不直接為專門職業做準備而將兒童隔離在生產勞動之外、由成年人的勞動成果來供養兒童的“社會共識”,卻給兒童理解學習和勞動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如果幼兒已有行動能力卻無須做任何事,其生存所需都唾手可得,連照料自己都被理解為“別人的事”,那么這種依賴心發展下去很可能變成不勞而獲的習慣,影響兒童主體感和自主性的形成,責任心的養成必定落空。雖然有些幼兒出于渴望“成為大人”的心理,在假想的角色游戲中模仿自己所觀察到的成人勞動的言行片段,但這些游戲畢竟不能如真實的勞動那樣讓他們體驗到勞動成果的效益。一旦假想的情境結束回到真實生活中,他們又只能“做個閑人”,那些能取得實利的勞動成果與他們自身的力量無關。
在這種隔離下,幼兒與勞動這種活動無法建立情感聯結,無法認識到“勞動創造美好生活”,更談不上認識其他勞動者創造的勞動價值及對自己的重要意義。一旦身邊有成年人貶低特定勞動的意義及對應的勞動者,這種蔑視態度很容易被幼兒習得。
在一個反對不勞而獲的社會中,新生成員持有蔑視勞動的觀念當然是危險的,一些兒童成年后試圖輕松賺快錢、騙取或剝削他人勞動所得的行為,危害著家庭甚至社會,日益引發教育者的擔憂。在這種背景下持續倡議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改變將兒童與勞動相隔離的做法,當然不是為了把未成年人當成勞動力直接承擔社會分工、為社會創造價值,也不是為了將他們固定在某種勞動分工上提前訓練特定的勞動技能,而是為了給他們機會,使之在親身體驗勞動過程的基礎上,認識勞動與自己衣食住行的關系、社會所有人合理分工協作進行勞動才能獲得生存所需、自己有能力為獲取勞動成果貢獻力量并有權利與其他勞動者一起共享勞動果實、在努力取得勞動成果的過程中感受自己的體力和腦力都在不斷發展。有此認識,他們才能為或遲或早承擔的社會分工做好準備。
賦予幼兒勞動的機會并精心規劃勞動過程
來到世上不久的幼兒,因語言、識字能力有限,很難依賴“聽講”“看書”來學習,而要通過在自己的生存環境中開展各種活動,包括游戲、交往交流、勞動、探索等,進行非正式的學習,獲取直接經驗,為后續的正式學習打基礎。不同類型的活動滿足著幼兒不同的學習需求。那么,具體有哪些活動算得上是勞動呢?
與人類其他實踐活動相比,勞動的獨特性在于能對個體或群體的生存產生價值,這類活動的成果要么直接滿足人的生存必需,要么可用勞動報酬交換生活資料。這也是勞動與游戲的最大區別,游戲大多不追求實利。在幼兒園或家庭這兩個幼兒主要的活動場所中,凡與幼兒安全健康地生活有關的事務,都是勞動,如飲食起居、灑掃整理、修繕維護等。不應讓幼兒與這些絕緣,或僅僅為了完成“勞動教育”的任務而走個過場,應在整體規劃幼兒園三年課程和家園共育時,便審慎地將勞動教育滲透其中。
首先,遵循幼兒動作發展和包括自主性在內的社會性發展的順序,使勞動從生活自理開始慢慢擴展范圍。生活自理是幼兒承擔的合理社會勞動分工,也創造著價值——減輕成年人花費在照料上的勞動量,且飲食起居等事務與幼兒切身需求有最直接的聯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應該成為小年齡兒童最主要的勞動教育內容。教師和家長應該在這些勞動中將自己的作用定位為“指導員”,讓幼兒意識到這些是他們“自己的事”,耐心鼓勵幼兒發揮能力,并引導他們發現自己力量的不斷增長。
隨著幼兒活動范圍的擴大和能力的增長,幼兒園可以引導幼兒調查社區周邊生活服務人員、幼兒園教職員工、自己的家庭成員所承擔的社會分工以及他們各自的勞動成果,從中挑選與幼兒獲取所需的生活資料和服務有密切關聯的職業,如菜市場商販、快遞員、司機、園丁、廚師、保安、清潔工等,引導幼兒通過參觀和訪談深入了解甚至體驗部分力所能及的環節,對這些勞動的意義以及勞動者要具備的本領形成更清晰的認識,感受人們不同的勞動分工和彼此服務,進而在幼兒園一些復雜勞動項目中探討合理分工問題并做嘗試。
其次,成年人需要時常反思自己的勞動觀念和對待特定勞動的態度,謹防把自己有關勞動和幼兒勞動能力的錯誤認知滲透到勞動教育的設計中。如假設人都喜歡玩不喜歡勞動、懷疑兒童沒有能力承擔有一定挑戰性的勞動或克服勞動中存在的困難,于是自行切割勞動過程,把“簡單環節”派給幼兒淺嘗輒止,而絕大多數需要動手動腦的環節則包辦代替,剝奪了幼兒在多個勞動環節間變換去獲取豐富體驗、最終品嘗依靠自己的力量或分工協作取得成果的愉悅感的機會。
成年人還需要對活動目的性以及幼兒肢體能力和認知能力水平有充分的理解。相較于不限定目標和成果的游戲、與他人輕松交往和情感溝通、自由探究和認識周遭事物、做自己喜歡的事等其他活動,幼兒可能在特定時刻對特定勞動表現出缺乏興趣,如當勞動過程相對單調、時間較長、需要的體力和腦力也超出幼兒當下能力范圍時,幼兒很可能會有“怕苦怕累”的逃避表現。教師要防止以成人之心給幼兒貼上“拈輕怕重”“不愛勞動”的道德標簽,而要思考如何增加勞動過程本身的愉悅感。
最后,把勞動過程轉化為內容豐富、展現體腦潛力、交流互助的有趣味的過程,可以從諸多智慧的勞動者那里獲得啟發。比如,允許幼兒以自己的意愿和節奏穩步邁向勞動成果,動靜結合、勞逸結合;支持幼兒把看似復雜的勞動過程轉化成可承擔的小任務,通過借助或改造勞動工具、學習小竅門讓勞動變得更省力;還可以探討如何緩解勞動帶來的疲憊感,尋找調劑方法如唱歌、休息等,使勞動成為一個不乏理智和情感的過程。再比如,當幼兒經歷了較長的勞動過程才取得成果,或者只承擔了勞動過程中看似與最終成果不相干的某一個小環節時,絕不能忽略幼兒對勞動成果的慶祝和享用過程,有必要把每個幼兒貢獻的力量都直觀地呈現出來,特別鼓勵挑戰自己原有能力的表現,讓幼兒感受到他人的認可。這些早期體驗才是新時代勞動教育應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