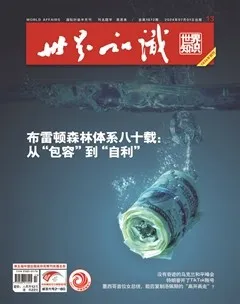破除日美話語體系、錨定東亞和平發展的“琉球學”
陳剛

當前,亞太安全形勢嚴峻,美國聯合盟友對華多邊打壓,日本強化在琉球群島的軍事部署,制造區域緊張局勢,加劇地區陣營對立。日美之舉嚴重威脅東亞和平安全,嚴重侵害琉球民眾的生存權、發展權、安全權。琉球島內和平反戰運動高漲,向國際社會發出“絕不能讓沖繩(琉球)再次淪為戰場”的呼聲。
今年5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海問題研究中心、日本研究所在京聯合舉辦“東亞和平發展與琉球學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以“琉球學”建設為核心進行研討,達成很多基本共識。
建構自主的琉球知識體系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在迄今的145年間,琉球命運幾經舛變。其間,日美長期掌控琉球歷史話語權,制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顛倒黑白的琉球敘事,誤導了國際社會對琉球問題的基本認知。要構建“琉球學”自主體系首先需要明辨日美的琉球史話語謬誤,確立正確的琉球史觀。
1879年,存在數百年的琉球王國被日本武力吞并,但日本卻將吞并行為詭辯為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國家維新、內政變革,冠以“琉球處分”之名,將其滅人之國、絕人之祀的歷史罪行納入國家統一的歷史敘事。這樣的論說不僅抹殺了琉球王國的主體地位,也掩蓋了日本吞并行為的侵略性和非法性。神奈川大學教授后田多敦指出,琉球王國被日本吞并前已同英國有國書往來,同美國、法國、荷蘭簽訂有修好條約,這些國書和條約書上押蓋的琉球本國制作的“琉球國印”,表明琉球是作為獨立政治主體同西方國家交往的。從國際法角度看,歐美也認可琉球的政治主體地位。最新在法國發現的《琉法條約》原件也再次印證了琉球的獨立王國地位。因此,無論是從主權角度還是王權角度,琉球都是被日本吞并的,只是日本故意在吞并時將權屬搞得模棱兩可,以混淆視聽。但琉球人并不認可這樣的敘事,他們要以自己為主體,從琉球視角解讀這段歷史,以琉球為主體建構歷史。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是戰后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根據兩份文件規定,戰后“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作為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的琉球被剝離出日本主權范圍。但隨著戰后國際關系的變化,美國背棄了盟國的上述規定,轉而與戰敗國、敵國日本暗相勾結,不斷破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所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更改盟國所確立的日琉間地理分界,從而衍生出“琉球地位問題”“釣魚島主權問題”等本不存在的爭議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劉丹老師指出,日美的上述行動是違反國際法的。同時還指出,日本為排除中國對琉球的影響,將琉球稱謂從戰前通用的基于漢語發音的“Liuqiu/Liuchiu Islands”改為基于日語發音的“Ryukyu Islands”。1950年4月,日本又制造出以日本為中心的所謂“南西諸島”概念,替換已在國際上通用數百年的“琉球群島”概念,其目的便是試圖消除“琉球群島”這一國際公認稱謂的影響,尤其是避免受到“琉球”這一中國發音的影響。
1972年,美日私相授受,通過簽訂《琉球與大東群島地位協定》,將琉球行政權移交給日本。日本再行偷梁換柱伎倆,將本就非法的“行政權移交”置于“沖繩復歸祖國”的敘事下不斷宣傳,將《琉球與大東群島地位協定》也改稱為《沖繩返還協定》。而飽受美國“刺刀加推土機”壓迫之苦的琉球人也曾天真地以為,“復歸日本”會帶來希望,部分人基于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立場,支持所謂的“復歸”。但美日在此后的對琉政策卻暴露了“復歸”話語背后的掠奪本質。1972年后,美日把原本部署在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紛紛轉移到琉球,琉球美軍基地面積占比激增至76%,“基地負擔”成為琉球難以承受之痛。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還無視琉球人的意愿,通過修訂《駐日美軍用地特別措施法》,剝奪了琉球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審查權,使美軍可以肆無忌憚地征用琉球土地用以軍事基地建設,日本政府充當起美國對琉壓迫的“急先鋒”。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認為,所謂1972年“沖繩返還”,實際上是日本對琉球的又一次吞并,此后,琉球陷于日美的雙重殖民統治之中。
可見,在不同歷史時期,日美都建構起了有利于其統治的琉球話語體系,因此建構我國的“琉球學”知識體系便需要對這些話語、概念進行辨析,形成以琉球為主體,以法理為基礎,以道義為前提的琉球史敘事。
疏解琉球安全發展困境
以弱肉強食、實力至上為原則的強權主義,是日美統治琉球的基本理念。強權之下,弱小的琉球因無抵抗之力而淪為犧牲對象。在日美交替統治琉球的145年間,琉球民眾的生存權、安全權、發展權不斷受到侵害,這是“琉球學”建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來自日本本土的侵略者紛紛涌入琉球,以武力和強權為依恃,對琉球大肆掠奪。1932年,時任《琉球新報》社社長的太田朝敷在回顧日本殖民統治琉球50余年的歷史時指出,“置縣后琉球的政治權力和社會中心逐漸轉移……本縣人基本被排除在新的政治權力之外,在如今官權壓力無所不及的時代,本縣人雖然生活在屬于自己故鄉的土地,但卻淪落到宛如食客的地步”。
1972年,同樣的歷史在所謂“沖繩復歸”后重演。“復歸”后日本資本宛如潮水般涌入琉球群島,導致島上的中小微企業紛紛倒閉,許多琉球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資、重勞動、非正規就業等不穩定的雇傭形態。而投資于琉球的日本資本卻將利潤回流到本土。直到今天,沖繩縣仍然是日本國內人均收入最低的地方,兒童貧困率是日本本土的兩倍,屬日本最貧困地區。松島泰勝認為,當今琉球仍處于殖民地經濟狀態,陷于美日雙重殖民壓迫之中。
近年來,琉球的生存權再次面臨嚴重威脅。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以冷戰思維對中國進行多邊打壓,而作為美國重要盟友的日本,不僅沒有嘗試在中美兩國間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反而火上澆油,跳到美國對華遏制打壓的最前沿。2022年12月,日本推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要構建“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徹底拋棄“專守防衛”原則,背棄“和平國家”理念,加速推動國家戰略的安全化轉型。日本政客也不斷鼓吹所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持續渲染“中國威脅論”,不斷激化兩岸對立,慫恿“臺獨”“以武拒統”,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加劇東海緊張局勢。
在錯誤政策引導下,日美兩國不斷強化在琉球群島的軍事部署,加速琉球群島“軍事要塞化”建設。日美兩國的軍事行動,不能不讓人想起1945年的“沖繩島戰役”。在這場戰爭中,日本把琉球當作防衛本土的“棋子”,超過15萬的琉球人在戰爭中喪生。如今,日美兩國再次將琉球推向軍事對抗前沿,琉球民眾不得不面臨再次陷于戰火的巨大風險。為此,琉球各界持續向國際社會發出“絕不能讓沖繩再次淪為戰場”的呼喊,在聯合國等國際舞臺控訴日美兩國對琉球的“殖民壓迫”。
推動東亞和平發展
日美兩國對琉球的壓迫政策和“戰略犧牲”,不能不讓人發出“弱小民族何以在強權時代自立求生”的拷問。
回顧歷史,琉球也并非沒有高光時刻。明清時期,中原王朝秉持“懷柔遠人”“恤佑外藩”等原則,積極支持琉球發展。政治上,賜予琉球“閩人三十六姓”;經濟上,給予琉球“朝貢不時”“下賜海舟”等優待;文化上,積極向琉球傳播儒家文化,接納琉球留學生進入國子監學習。500余年間,中琉之間雖然實力差距懸殊,但卻長期保持友好往來關系,在經濟貿易、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天文歷法、生產技術等各領域保持密切交流。中國的對琉優待政策也使琉球從偏居一隅的“東海島國”成長為連接東亞的“萬國津梁”,開啟了琉球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中國古代的周邊外交理念不同于西方“弱肉強食、實力至上”的叢林法則,不追求自我優先的利益至上原則,而是著眼于同周邊大家庭的人文相通、命運與共。長期以來,中國在同周邊鄰國交往時,始終秉持親仁善鄰、講信修睦、以誠相待、守望相助、互惠互利、合作共贏、包容互鑒、求同存異等基本理念。這樣的理念既根植于中華民族“合和共生”的文明基因,也形成于中國與周邊國家具體的地緣格局和政治關系。

2024年1月10日,日本沖繩縣名護市民眾舉行示威活動,抗議日本政府為駐日美軍新基地工程施工做準備。
從歷史經驗看,中琉之間友好交往、民心相同,是東亞和平發展的重要支撐,而美日對琉以鄰為壑、戰略利用,是威脅東亞和平發展的重要禍源;從未來遠景看,琉球的發展不可能永遠局限于“殖民地經濟”,其獨特的歷史地位、海洋資源、漁業物產、文旅資源理應得到更為積極的利用。
當前,中國繼續將“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作為處理與周邊關系的基本方針,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亞洲區域一體化”等建設,將中國和平發展成果惠及于周邊各國。作為曾經是東亞地區“萬國津梁”的琉球,也必將在基于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東亞文化交流、文明互鑒與經濟合作中再次發揮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東海之大,足以容得下中日兩國的共同發展,也理應為琉球和平發展留一片安定空間。如何弭兵于文,止戰于合,是“琉球學”建設的時代使命。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