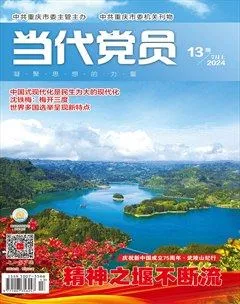梅開三度


事件
1989年1月21日,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huì)發(fā)來喜報(bào),沈鐵梅憑借《三祭江》《鳳儀亭》《闔宮歡慶》榮獲第六屆中國戲劇梅花獎(jiǎng),這也是重慶首次獲得這一中國戲劇表演最高獎(jiǎng)項(xiàng)。
人物
沈鐵梅,女,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重慶市文聯(lián)主席、重慶市川劇院院長(zhǎng),第二批國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川劇代表性傳承人,國家一級(jí)演員,曾三次獲得中國戲劇梅花獎(jiǎng),兩次獲文華大獎(jiǎng),代表作品川劇《金子》《李亞仙》《江姐》等。
“這簡(jiǎn)直是給我們川劇從業(yè)者吃了一顆‘定心丸’!”近段時(shí)間,盡管行程密集,工作繁忙,但重慶市川劇院院長(zhǎng)沈鐵梅臉上未見倦容,反而振奮不已。
原來,川渝人大再度攜手,準(zhǔn)備采用協(xié)同立法形式推進(jìn)川劇保護(hù)傳承立法工作,已形成《重慶市川劇保護(hù)傳承條例(草案)》,其中就川渝兩地建立合作機(jī)制、合作內(nèi)容、人才培養(yǎng)、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規(guī)定。
自幼學(xué)戲的沈鐵梅,眼神格外靈動(dòng),談到川劇立法時(shí),她的眼里更是閃爍起期盼的光。“入行以來,我一直在保護(hù)傳承川劇中堅(jiān)守,帶領(lǐng)團(tuán)隊(duì)耕耘探索、不斷前行。”沈鐵梅動(dòng)情地說。
作為傳統(tǒng)川劇藝術(shù)的繼承者和現(xiàn)代川劇藝術(shù)的開拓者,沈鐵梅一以貫之用自己的方式守護(hù)著川劇這枚巴蜀大地璀璨的非遺明珠。
摘梅之路
沈鐵梅的名字里有一個(gè)梅字,似乎生來就和中國戲劇梅花獎(jiǎng)有著不解之緣。
1988年,沈鐵梅與父母一起坐上重慶駛往北京的火車,汽笛聲悠長(zhǎng),列車滿載希望,也載著她的期待與忐忑。
彼時(shí),年僅22歲的沈鐵梅,雖然已在川渝地區(qū)收獲各個(gè)獎(jiǎng)項(xiàng),但眼看就要參加首屆中國戲劇節(jié),站到首都的舞臺(tái)上進(jìn)行專場(chǎng)演出,難免感到壓力巨大。
壓力,不僅來源于對(duì)自己資歷尚淺的憂慮,也來自各位老師慧眼識(shí)珠寄予的厚望。
1985年10月,重慶舉辦了首屆霧季藝術(shù)節(jié),曹禺、劉厚生、張瑞芳等文化藝術(shù)界名家都出席觀看。這次藝術(shù)節(jié)上,沈鐵梅作為青年演員帶來了川劇折子戲《鳳儀亭》的表演。
第二天,沈鐵梅如往常一般在川劇院內(nèi)練功,突然有人喊:“鐵梅!快到對(duì)面藝術(shù)館去,老藝術(shù)家們想要看看你!”
沈鐵梅馬上放下行頭,一路小跑去藝術(shù)館。“老藝術(shù)家們給了我高度的肯定。”沈鐵梅自豪地說,“劉厚生老師還建議我去參加梅花獎(jiǎng)的評(píng)選。”
這是剛從戲校畢業(yè)不久的沈鐵梅第一次聽說梅花獎(jiǎng),她暗暗將其記在了心頭。
這一年,川劇院成立了青年集訓(xùn)隊(duì),沈鐵梅成為集訓(xùn)隊(duì)員之一。
時(shí)間一晃到了1988年,恰逢中國首屆戲劇節(jié)在北京召開,梅花獎(jiǎng)評(píng)選在即。整個(gè)四川省團(tuán)名額有限,原本只計(jì)劃讓沈鐵梅帶一部作品加入省團(tuán)的演出。但是,要用折子戲參賽,就必須至少連演三出戲形成專場(chǎng)。“我能闖出去,真心感謝重慶劇協(xié)、四川劇協(xié)老師的愛才之心。”一方面,沈鐵梅努力多方爭(zhēng)取,另一方面各位前輩推波助瀾,寶貴的參演名額終于落到了重慶川劇院,這是重慶時(shí)隔多年后再一次獨(dú)立參賽。
“院里將我的恩師競(jìng)?cè)A先生以及其他老師請(qǐng)來專門再次打磨這幾出戲,我們則緊鑼密鼓地學(xué)習(xí)排練。”沈鐵梅說,師傅競(jìng)?cè)A是一位對(duì)自己有著深遠(yuǎn)影響的川劇名家,既會(huì)編曲,又能作曲,她請(qǐng)師傅競(jìng)?cè)A到家中住下,每日探討川劇伴奏音樂的提升、聲腔練習(xí)等。
秣馬厲兵,數(shù)月后,帶著一聲聲囑托和爛熟于心的《三祭江》《鳳儀亭》《闔宮歡慶》三出折子戲,沈鐵梅就這樣第一次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鐵梅,你要放松,自己要有把握,放松了演,你絕對(duì)會(huì)很優(yōu)秀。”沈鐵梅的父親,著名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沈福存在車上安撫她。
“為了備演,我們都沒有在北京游覽。”沈鐵梅說,那時(shí)條件也很艱苦,一家三口住在北京燈市口一家賓館的地下室,每天房費(fèi)15元。
演出當(dāng)天,再多艱辛壓力,在沈鐵梅站上舞臺(tái)時(shí),都煙消云散,川劇在這個(gè)年輕女孩的身上釋放出巨大能量,打動(dòng)了現(xiàn)場(chǎng)所有人。她也憑此在1989年1月摘得第六屆中國戲劇梅花獎(jiǎng),這也是重慶首次獲得這一中國戲劇表演最高獎(jiǎng)項(xiàng)。
大部分戲劇表演者畢生難得一次梅花獎(jiǎng),但沈鐵梅捧回“一度梅”后,2000年,其改編自曹禺作品的川劇現(xiàn)代戲《金子》,讓她二度摘“梅”;2011年,被譽(yù)為川劇版“茶花女”的《李亞仙》,又讓沈鐵梅“梅開三度”。
川劇革新
在今天所有人都在為“川劇女皇”沈鐵梅精湛的表演叫絕時(shí),很難想象她也曾完全不喜歡川劇。
“從小,我在重慶京劇團(tuán)長(zhǎng)大,父親用京劇的‘搖籃曲’培養(yǎng)我,我從三歲就開始唱戲了。”京劇的優(yōu)美聲腔、嚴(yán)謹(jǐn)程式深深吸引了沈鐵梅。
“一開始,我是拒絕學(xué)習(xí)川劇的。我的母親當(dāng)時(shí)是群眾川劇團(tuán)挑大梁的旦角主演,我經(jīng)常去看她們的戲。當(dāng)時(shí),我覺得川劇和京劇的區(qū)別就在于川劇太隨意了,幫腔、打擊樂震耳欲聾,幫唱基本以吼為主。”沈鐵梅說。
沈鐵梅報(bào)考戲校時(shí),正逢當(dāng)時(shí)戲校不招收京劇專業(yè),為了繼續(xù)在藝術(shù)的道路上前行,在父親的鼓勵(lì)下,沈鐵梅萬般無奈只得轉(zhuǎn)考川劇。天資聰穎的沈鐵梅,臨時(shí)跟母親學(xué)了一段川劇《雙拜月》,就一舉考上了四川省川劇學(xué)校的重慶班。
盡管不喜歡粗獷的川劇,但父親告訴她,只要選擇了川劇就要定心學(xué)習(xí),不能三心二意。沈鐵梅便在學(xué)校勤學(xué)苦練,每天清晨六點(diǎn)半起床練功,練身段、練舞蹈、練唱腔、練圓場(chǎng)……“一天沒有練功,便會(huì)覺得自己在退步。”沈鐵梅說。
父親是京劇大家,也是“戲迷”,“他三句話不離戲,幾乎隨時(shí)都在琢磨戲”,父親這種執(zhí)著磨戲的精神影響了沈鐵梅。早在學(xué)習(xí)階段,沈鐵梅就展現(xiàn)了守正創(chuàng)新的能力。“我覺得川劇以前的唱腔發(fā)聲不好聽,我告訴自己要把川劇唱美,讓觀眾入耳,但是又保留川劇唱法本身的味道。”沈鐵梅說,學(xué)校老師們對(duì)她的唱法予以認(rèn)可,她也成為班里第一個(gè)登臺(tái)演出的學(xué)生。
在沈鐵梅40余年的演藝生涯中,方向至關(guān)重要,有了明確的目標(biāo),才能創(chuàng)造更好的機(jī)遇。
在選擇川劇這條道路后,沈鐵梅就全身心投入進(jìn)去,變不喜歡為熱愛,在全新的領(lǐng)域掌握最專業(yè)的技術(shù)、搏出最亮眼的風(fēng)采。問及沈鐵梅第一次沖擊梅花獎(jiǎng)在北京演出緊不緊張時(shí),她答:“我打的不是沒準(zhǔn)備的仗,掌握了這個(gè)戲的各方面表現(xiàn)的能力,在技術(shù)上就不會(huì)緊張。”
如今,成為重慶川劇事業(yè)的“掌舵人”后,沈鐵梅仍然秉持著“把握好方向和坐標(biāo),在川劇的正道上行穩(wěn)致遠(yuǎn)”的理念,帶領(lǐng)團(tuán)隊(duì)對(duì)川劇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不懈探索。
現(xiàn)代川劇如何發(fā)展,這是沈鐵梅近年來一直探索的課題。川劇是昆曲、高腔、胡琴、彈戲、燈調(diào)“五腔共和”形成的藝術(shù),但其中樂器伴奏方式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所以沈鐵梅一直帶著團(tuán)隊(duì)研究,希望尋找最契合的樂器,優(yōu)化彈戲、胡琴的伴奏方式,提升音樂性和劇場(chǎng)效果。而在現(xiàn)代戲的創(chuàng)作上,讓沈鐵梅第二次獲得梅花獎(jiǎng)的《金子》,則是他們對(duì)現(xiàn)代戲“戲曲化”創(chuàng)作的探索。在《金子》中,變臉、藏刀、踢袍等川劇絕活的加入,是為了更進(jìn)一步表達(dá)人物狀態(tài),讓演出更具生命力;手絹的使用,則是替代傳統(tǒng)舞臺(tái)的水袖,形成戲曲節(jié)奏。
美美與共
1988年,當(dāng)《鳳儀亭》在北京被唱響時(shí),悅耳的唱腔博得滿堂彩。
2004年,《鳳儀亭》的唱詞“漢室王業(yè)豈偏安……”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響起,沈鐵梅帶著川劇與西方交響樂融合的《鳳儀亭》征服了海外觀眾。這不僅是川劇的跨界融合實(shí)踐,也是推動(dò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我就是要抓住一切機(jī)會(huì),把川劇通過不同方式推廣到世界去,讓大家了解川劇的魅力。”把川劇推向世界,讓海外觀眾走近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沈鐵梅畢生所求。
德國、美國、英國……一場(chǎng)場(chǎng)演出接連不停,沈鐵梅更加理解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我們需要建立文化自信,不要去擔(dān)心別人聽不懂、不接受。”沈鐵梅說,“你能從他們的眼睛里看到對(duì)中國文化的熱情。”
長(zhǎng)期以來,沈鐵梅都在深耕川劇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賦予傳統(tǒng)川劇在現(xiàn)代背景下新的生命和意義,讓其得到更好的保護(hù)、傳承、發(fā)展、壯大。談及今年9月,又有一批學(xué)生即將進(jìn)入重慶川劇院學(xué)習(xí)時(shí),沈鐵梅很是欣慰。
對(duì)沈鐵梅而言,川劇事業(yè)承載了父親的啟迪、恩師的教誨,更承載了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一代代戲劇人的傳承堅(jiān)守、推陳出新,才讓川劇這一巴渝文化的符號(hào)為重慶文化史寫下濃墨重彩的注解,讓傳統(tǒng)文化得以煥發(fā)新生。
已故著名劇作家魏明倫曾對(duì)重慶川劇良好的發(fā)展勢(shì)頭點(diǎn)贊:“重慶的川劇現(xiàn)在是發(fā)展壯大了,而且越來越好,一部《金子》就囊括了那么多大獎(jiǎng),了不起!我認(rèn)為重慶川劇真的崛起了……”
數(shù)讀
新中國成立以來,重慶推出了一大批具有重慶辨識(shí)度的渝派文藝精品。羅廣斌、楊益言創(chuàng)作的長(zhǎng)篇小說《紅巖》自1961年出版以來,發(fā)行量逾1000萬冊(cè)。黨的十八大以來,重慶文藝事業(yè)更加欣欣向榮,全市130余件作品榮獲國家級(jí)重要文藝獎(jiǎng)項(xiàng),雕塑《烈焰青春》榮獲全國美展雕塑金獎(jiǎng),詩集《檸檬葉子》《無限事》《賀拉斯詩全集》、小說《山前該有一棵樹》連續(xù)四屆獲得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川劇《江姐》斬獲文華大獎(jiǎng),為新時(shí)代文化強(qiáng)市建設(shè)貢獻(xiàn)強(qiáng)大文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