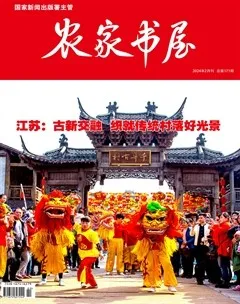《重新發(fā)現(xiàn)〈詩經(jīng)〉》: 從《詩經(jīng)》中找尋真實歷史
宋晨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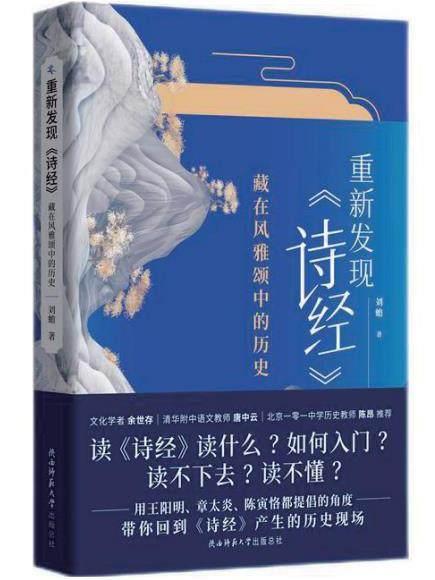
記得小時候,我爺爺曾跟我說,他們幼年念私塾,都知道一句話,叫“學(xué)了《詩經(jīng)》會說話,學(xué)了《周易》會算卦”。千百年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詩經(jīng)》都是當作文學(xué)范本而被大眾認知的。
這也不怪人們的認知,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已給《詩經(jīng)》奠定基調(diào):“不學(xué)《詩》,無以言。”(《論語·季氏》)所謂“無以言”,朱熹注曰:“言之無物,言之無據(jù)。”此外,孔子還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總之,千百年來,人們都將《詩經(jīng)》當作抒發(fā)個人情感、學(xué)習作詩的經(jīng)典教材。
然而,這種評價卻忽略了《詩經(jīng)》的另一個價值——史料價值。正如學(xué)者李樹軍在《〈詩經(jīng)〉與周代社會交往》中所言:“西周和春秋時期,詩歌不只具有抒發(fā)情志的功能,還有重要的社會政治功能,詩歌是其禮樂制度和禮樂文化的重要構(gòu)成內(nèi)容,詩歌是儀式的組成部分,詩歌還可以觀察不同地域的風俗習慣,借以了解朝廷和諸侯國施政的效果。”作為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里面保留了大量最原始的史料,蘊含了當時人們對當政者的態(tài)度。
如果我們把《詩經(jīng)》當作史料來讀,必定會讀出不一樣的維度。劉蟾《重新發(fā)現(xiàn)〈詩經(jīng)〉》一書,正是用通俗的語言,以《詩經(jīng)》作為史料,同時參考最新的出土文獻以及學(xué)術(shù)成果,來為我們重建了商朝建立到春秋末年的真實景象。
本書開篇,作者即以《商頌》追溯商朝的歷史,按照王國維的研究,“《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觀堂集林》),因此,與后出史料相比,《商頌》所載更為可信。作者在書中根據(jù)當代學(xué)者所做的考證和地下出土材料,更正了人們一直以來對商紂王時期“酒池肉林”和“炮烙之刑”的認知。
所謂“酒池肉林”,其實是上古時期人們聚眾“群飲”風俗的遺留,而“炮烙之刑”也并非把人綁在燒得通紅的銅柱子上。作者根據(jù)上博簡(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中《容成氏》的記載,認為“炮烙”實為“炮格”,是由人修建一座高臺,在臺下放上銅盂和木炭,再為臺上架一根圓木,讓人從上面走過,若中途掉下則會被燒死。
書的第二部分,作者則從“雅”中還原西周的興起與滅亡。作者選取了《生民》《公劉》《黃矣》《大明》等幾篇作為證據(jù)。根據(jù)李山教授考證,這幾篇其實都是西周中期的祭文(見《〈詩經(jīng)〉創(chuàng)制的歷程》)。祭祀最主要的是心誠,因此,這些祭文中所講述的一些事跡是可以作為史實依據(jù)的。當然,同時也要注意,其中必然也有周天子粉飾自己的統(tǒng)治之詞。比如,周人的祖先姜嫄感而受孕等,這些本不可信,實為統(tǒng)治者強調(diào)“權(quán)自天授”之言。但《生民》里說,姜嫄所生之子后稷推行科學(xué)合理的農(nóng)作物耕種,則可以從側(cè)面反映周代早期部落農(nóng)耕技術(shù)的發(fā)展。
此外,還有對“烽火戲諸侯”的考證。雖然很多學(xué)者已從不同角度考證“烽火戲諸侯”并不存在,但是作者獨具慧眼,從《小雅·菀柳》中發(fā)現(xiàn)依據(jù)。根據(jù)李山研究,該詩應(yīng)出現(xiàn)在西周后期東周之初。若真有“烽火戲諸侯”,肯定不會不寫,但其中未見相關(guān)記載,從另一個側(cè)面也間接證明了此事子虛烏有。
作者花費最大的篇幅,是注重運用《詩經(jīng)》中“風”的相關(guān)記載以還原幾個春秋諸侯國的真實事件。“相比《頌》《雅》而言,《風》的爭議最小”,因為“風”都是“王官采詩”,即官方到民間采集的歌謠,因此更加原汁原味,最能反映當時的政治事件、社會風俗等。
作者運用“風”中的相關(guān)篇章,讓我們了解到當時人們對這些肉食者的鄙視,同時表達出同情弱者,尤其是很多作為政治犧牲品的悲慘命運。比如,當鄭莊公的母親和她小兒子打算密謀篡奪君位,當時的人就借用女子與情郎幽會的故事,諷刺鄭莊公的陰險狡詐:他之所以忍讓弟弟叔段,其實是想讓他主動造反,進而有借口除掉他,自己還得個仁愛的美名。
讀完這本書,你就會深刻發(fā)現(xiàn),百姓內(nèi)心的喜怒哀樂,都蘊藏在彼此傳唱的歌謠中。即使歷史如何被篡改,那些最真實的聲音,始終不會被掩蓋!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