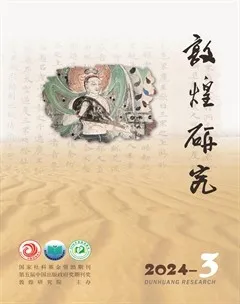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92窟“祇園記圖”考釋
趙燕林



內容摘要: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92窟前室西壁的未知名故事畫,根據遺存畫面、榜題等內容來看,應為依《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繪制的“祇園記圖”。此圖較為完整地表現了《須達起精舍品》所載“須達起精舍”“降魔”和“佛陀說法”三部分內容。是目前可知莫高窟同類題材中時代最早、內容最全、構圖形式最復雜的一鋪。該壁畫的識讀,不僅為該題材相關研究補充了重要原始圖像素材,而且對全面認識和研究后世降魔變文、勞度差斗圣變等內容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莫高窟第292窟;祇園記圖;勞度差斗圣變
中圖分類號:K87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3-0075-12
Textual Research on the“Illustration of Jetavanavihār”
in Sui Dynasty Cave 292 in the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ZHAO Yanl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736200, Gansu)
Abstract:The untitled sutra illustration painting on the west wall in the antechamber of Mogao cave 292 from the Sui dynasty can be concluded to be a depiction of Jetavanavihār that was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scenes of The Sutra of the Wise and Foolish: Chapter Concerning Sudatta Having aVihara Built. The painting presents a relatively complete depiction of the three main scenes of the sutra, namely “Sudatta having a vihara built,” “Defeating Mara” and “The Buddhas sermon.” This painting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is the earliest and most complete image of this theme found to date, and because the compositional form of the mural is among the most complex among paintings of its kind at Mogao. Identifying this painti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primary research material useful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theme of Jetavanavihār, and corrects the previous view that there was no such sutra illustration in the caves of the Sui dynasty at Dunhuang. In addition, the content of the painting is also highly relevant to studies on the content development of two later documents, Xiangmo Bianwen降魔變文(Transformation Text on Subduing Demons) and Laoducha Dousheng Bian勞度差斗圣變(Transformation Text about Raudraksas Battle with Sariputra).
Keywords:Mogao cave 292; Jetavanavihār illustration; Raudraksas Battle with Sariputr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莫高窟第292窟位于莫高窟南區中段第二層,開鑿時代“大致應在隋開皇九年(589)至大業九年(613)略后的這段時間里”[1]。此窟為隋代最大的兩個中心柱窟(第292、427窟)之一,前室寬 ?6.2米,進深殘長3.6米,高3.6米;甬道長1.6米,寬2.2米,高2.8米;主室長10.4米,寬6.9米,四壁高4.65—6.05米。是隋代為數不多的大型洞窟。
對照《敦煌石窟內容總錄》來看,此窟前室頂西披盛唐畫千佛(存部分),五代補畫部分;西壁門上存五代愿文榜題一方,兩側畫趺坐佛各二身;門南塑金剛力士一身,表層五代畫千手眼觀音一鋪,底層隋畫故事畫;門北塑金剛力士一身,表層五代畫已殘,底層隋代畫故事畫[2]。但底層隋畫故事畫的內容學界尚無討論,本文擬對此做出嘗試性解讀。
一 敦煌石窟中的“祇園記圖”及
勞度差斗圣變相關研究問題
祇園記圖又稱勞度差斗圣變,主要依據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涼州沙門慧覺(一作曇覺)等譯《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繪制而成,主要包含“祇園因由記”和“牢度差斗圣”兩部分內容[3]。一般認為,敦煌壁畫中存在三種形式的勞度差斗圣變:一為橫幅連環畫形式,僅有西千佛洞第12窟{1};二為佛龕里對坐斗法形式,僅有莫高窟初唐第335窟;與此相似的還有窟門兩側對坐斗法的形式,莫高窟第6、72窟皆屬于此類;三為整幅通繪起精舍及斗法形式,如莫高窟第9、196等窟;與此相似的還有上部大部畫變相,下部畫屏風畫供養人像的形式,如莫高窟第85、146、53、55、98、454、25等窟。如果撇開洞窟建筑形式對繪畫構圖的影響,按其主體內容劃分,又可分為“橫幅連環畫形式”和“對坐斗法形式”二類。其中第一類屬早期形式,且僅有西千佛洞第12窟;第二類為初唐及之后的普遍流行形式{2}。
此外,敦煌遺書中亦存多份依據《賢愚經》改編的講唱文《祇園因由記》(P.2344、P.3784)《降魔變文》(S.5511+胡適藏本、S.4398v、P.4615、傅斯年圖書館藏第188107號,俄羅斯藏Dx.4019+
4021、Dx.11182RV、Dx.3676)等。如:敦煌藏經洞出土勞度差斗圣變畫稿1份(P.tib.1293;按:有學者將 P.4524也列為畫稿,但因其屬于宣講者使用的本子,應歸于變相)、勞度差斗圣變榜題底稿2份(S.4257v、P.3304v)、變相2鋪(P.4524、S.P.62)[4]。但時代都較晚,幾乎全部為晚唐及其以后所成,不能作為討論隋代相關畫作的文本。
《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大致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創建佛教圣地祇園的故事: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名叫“須達”的大臣,因樂善好施故又號“給孤獨”。須達欲為子納妻,當得知王舍城巨富護彌有一女,即前往王舍城為子求妻。須達在護彌家得聞佛僧名及其功德,便向佛陀進獻貢物,并在佛陀的教誨下成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須達欲請佛陀前往舍衛城說法,但佛陀需有精舍才可前往。于是,佛陀遣舍利弗隨同須達一道至舍衛國選址修建精舍。最終,選中祇陀太子園,欲購買修建精舍。祇陀太子要以黃金布地的價格方可相與并反悔時,佛陀護法首陀會天化作一人前來評理,并以“太子法,不應妄語”為由促成交易。隨后,須達即遣人以大象負金前往祇陀園,黃金略有不足,祇陀太子便與須達共立精舍。這時,二人共建精舍之事被外道六師所知,六師欲阻在舍衛國建立佛陀精舍,于是建議國王讓其與沙門弟子角力,以角力輸贏定奪是否修建佛陀精舍。舍利弗同意角力,國王即宣布七日后在城外寬闊處六師與沙門弟子角力。
故事第二部分講述舍利弗與六師之勞度差斗法之事。首先是舍衛國民擊鼓會眾,一切人民前往觀戰。同時人民為國王及六師設高座,須達為舍利弗設高座準備角力。先是善知幻術的勞度差化作一大樹,而舍利弗以風吹拔樹并將其碎為微塵取勝;然后勞度差又化作一七寶水池,而舍利弗則化作一六牙白象吸干池水取勝;勞度差又化作一高山,而舍利弗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破之;勞度差又化作一十頭毒龍,而舍利弗化作一金翅鳥擘裂食之;勞度差又變為一頭健碩的大牛,而舍利弗則化作獅子王分裂食之;勞度差又化作夜叉鬼吐火進攻,而舍利弗化作毗沙門天王阻之取勝。最后,舍利弗身升虛空并現四威儀恢復原形入座,為大眾說法,六師及大眾隨舍利弗出家學道。
故事第三部分講須達借舍利弗道眼入六欲天見過去六佛,同時精舍建成并請佛說法之事。舍利弗戰勝勞度差之后,須達與舍利弗各牽繩一頭前往祇陀太子園共經精舍。在這過程中,舍利弗含笑并借其道眼,須達得以悉見六欲天嚴凈宮殿及過去六佛,并知悉自己分別為過去六佛修建精舍之事。隨后,精舍建成,須達建議國王遣使請佛臨覆舍衛國說法。于是,佛陀降臨舍衛國說法,解救苦難,并將此園賜號為“太子祇樹給孤獨園”,以流傳后世[5]。
根據莫高窟隋代第292窟前室西壁相關畫面內容來看,此可能為依《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而成的“祇園記圖”,我們據此對這一內容進行識讀討論。
二 第292窟前室西壁“祇園記圖”解讀
莫高窟隋代第292窟前室西壁有上下兩層壁畫,表層為五代繪制,底層為隋畫。底層隋畫除部分畫面被門南、門北中央塑一大型金剛力士塑像所遮擋,門上及南、北兩側部分畫面因后代重修、重繪遮擋損毀不知為何內容外,其余大部分內容可識。此畫南北通長6.2米,高3.6米。面積約22.3平方米,屬于一鋪大型故事壁畫。另,此圖現存榜題30余方,大部分漫漶,少數可釋讀,為識讀該畫提供了重要依據。
對照《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及畫面內容來看,第292窟前室西壁故事畫為隔門連環畫構圖形式(圖1)。甬道門南、門北兩側均以“S”形黑色山巒為界,巧妙地經營了《須達起精舍品》的不同情節,門北側為“須達起精舍”和“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大部分內容(圖2);門南側為部分“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及“佛陀至祇陀園精舍說法”(圖3)。目前,全圖可辨認者共3部分9組32個畫面。
(一)第1部分 須達起精舍
繪于門北側,主要包括“須達為子求妻得見世尊”“須達購祇陀園時”“須達與舍利弗共建精舍時”等3組11個畫面(見圖2)。
1. 第1組(畫面1—3) 須達為子求妻得見世尊
位于北側畫面下部,主要內容為“須達樂善好施”“護彌女施食婆羅門”“首陀會天示禮拜供養之法”3個畫面。
畫面1:須達樂善好施
塑像北側下部畫一蓮池。蓮池內上畫一宮殿,殿門正對一橋,橋下流水潺潺。殿內席地坐一白衣長者,長者右手撫于膝面,左手上指。殿外左側有一人侍立,右側一人一手伸出,似在做施舍狀,前方有多人做接受狀;左側一人侍立在外。
榜題:位于做施舍狀人和受施人中央上部,文字模糊。
解讀:根據畫面內容及后續其他畫面來看,此畫面可能表現須達“居家巨富,財寶無限,好喜布施,賑濟貧乏及諸孤老”[5]418。
畫面2:護彌女施食婆羅門
位于畫面1上方南側,宮殿內一亭亭玉立的白衣女子伸手施物于前方一微屈膝的黑衣男子。
榜題:宮殿南側前方一黑色榜題,文字極為模糊,僅可見其中一“婆”和最后一“詣”字。
解讀:根據畫面內容及榜題來看,前部畫面可能表現:“須達為子求妻,即語諸婆羅門:‘誰有好女相貌備足,當為我兒往求索之。”于是“諸婆羅門,便為推覓,展轉行乞,到王舍城”“王舍城中,有一大臣,名曰護彌,財富無量,信敬三寶。時婆羅門,到家從乞。國法施人,要令童女,持物布施。護彌長者,時有一女,威容端正,顏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羅門”的相關內容[5]418。后方榜題及畫面待查。
畫面3:首陀會天示禮拜供養之法
一宮殿內畫身穿白色寬袍大袖的老者,右手上舉,席地坐其間。殿外右側臺階上一黑衣男子站立向外,右手伸出作比劃狀,殿外臺階下多人跪拜作揖。殿外后方一頭戴籠冠的白衣男子作行禮狀。
榜題:此處共有二方榜題,一方位于殿外男子和婆羅門中央,上書:“……護彌……”一方位于殿外后側白衣男子前方,文字模糊不明。
解讀:此當為護彌女施食婆羅門后,須達得見世尊,并欲敬禮世尊。但當首陀會天見其不知禮拜供養之法,遂化作四人“到世尊所,接足作禮,長跪問訊,起居輕利”示范如何禮拜世尊的畫面。同時,須達欲請佛陀前往舍衛城說法,但佛陀需有精舍才可前往。于是,須達“即于道次,二十里,作一客舍,計校功作,出錢雇之,安止使人,飲食敷具,悉皆令足”。結果,“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共舍利弗,按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按行周遍,無可意處”的畫面[5]419。
2. 第2組(畫面4—6):須達購祇陀園時
畫面4:須達共舍利弗欲購太子園時
中央畫一宮殿,宮殿外北部上空一飛天俯沖而下,殿外北側下方有二人(一著白衣、一著黑衣)面向宮殿下跪行禮。
榜題:宮殿北墻下方有一黑底榜題,上隱約可見“……祇陀太子……”等字。
解讀:當須達和舍利弗一同從王舍城至舍衛國“按行周遍,無可意處”修建精舍的場地時,發現“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平正,其樹郁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5]419。于是,須達到太子所請求購置太子園,以為世尊起立精舍的畫面。殿外北側下方二行禮人物當為舍利弗和須達。
畫面5:祇陀太子將園與須達時
中央宮殿內畫一頭戴王冠身穿深衣,盤踞而坐、身體前傾右手上舉作思維狀的王者。殿外南側一黑衣男子身體前傾,雙手微微上舉,似正指向殿前身穿白衣雙手作揖的男子。
榜題:宮殿南側二人間有黑底榜題,上書“□(祇)□(陀)太子□(將)園與須達時”。
解讀:此為須達到太子所求購太子園時,太子要求須達“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愿“聽隨其價”購之。而后,太子又以“我戲語耳” 為由反悔時,須達與之辯論的畫面[5]419。其中殿內王者人物當為祇陀太子,殿外黑衣男子當為須達,殿前作揖男子當為首陀會天。
畫面6:首陀會天下為評詳時
位于“祇陀太子將園與須達時”畫面的殿外南側上方。畫一體型較大,肩有四臂,上身赤裸下身著短裙似婆羅門形的人物。
榜題:宮殿上方有一黑底榜題,上部部分被五代壁畫覆蓋,內容漫漶不明。
解讀:當須達愿以黃金布地之資購買祇陀園,太子又欲反悔時,暗中相助須達的首陀會天即化作一人,下為“評詳”,說“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中悔”后,祇陀太子“遂斷與之”的畫面[5]419。
需要說明的是,四臂婆羅門形象的人物為何是首陀會天?據《賢愚經》《不空■索咒經》《入大乘論·卷下》等多部佛經記載:首陀會天,號“凈身”[5]410,又稱“凈居天”[6]或“大自在天”[7]。《入大乘論·卷下》載:“摩醯首羅者,即是凈居自在。”[8]又《百論》注:摩醯首羅天“秦言大自在”[9]。因此,首陀會天有時會以其主神摩醯首羅的形象出現。如:在榆林窟五代第36窟千手千眼觀音變主尊左側上方的摩醯首羅天,即為一面四臂,上半身赤裸、下著短裙、腰束獸皮,以游戲坐坐姿坐于一青牛背上[10]。此圖中的首陀會天雖無坐騎青牛,但與一面四臂、上半身赤裸、下著短裙、腰束獸皮的形象卻極為一致,故應當為首陀會天。
3. 第3組(畫面7—11):須達與舍利弗共建精舍
主要位于第2組畫面下部,中央為一宮殿,分別畫“置金自滿”“象負金出”“象負金時”“黃金鋪地”“須達與舍利弗共經精舍”等5個畫面。
畫面7:置金自滿
方形白色布袋,內滿置方孔錢幣。錢幣兩側各跪一人,北側一人似作數錢狀。
榜題:銅錢和大樹中央存一黑色榜題框,隱約可見“……樹……金……”等字。
解讀:對照經文來看,此當為祇陀太子欲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之價將祇陀園賣與須達時,“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足。”祇陀太子問須達:是否“嫌貴置之?”而須達答:“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耳。”祇陀太子見須達如此決心,便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的畫面[5]419。
畫面8:象負金時
位于塑像頭左側后部,兩人牽一白象,大象身負布袋緩慢行進。
榜題:北側前方一黑色榜題,隱約可見“□(象)負金時”。
解讀:對照經文來看,此當為祇陀太子“遂斷與之”祇陀園時,“須達歡喜,便敕使人:‘象負金出。”的情節[5]419。
畫面9:象負金出
位于畫面南側最上部,與下部“象負金時”的大象同向而行,此頭大象背負數量不菲的方孔錢幣亦向北而行。
榜題:不明。
解讀:按照故事情節來看,此畫面應為“象負金時”的連續畫面。但畫者卻將兩處本應連續的畫面有意分開,這應是畫者根據構圖需要而有意調整的。如果將兩頭體型較大的大象放置在相近畫面位置,不僅構圖較為困難,而且很難表現出將要負金和正在負金的故事情節。同時,這里畫者將佛經所謂的“黃金”畫成了古代中國特有的方孔錢,用方孔錢代表黃金,這不能不說是畫者利用中國元素表現佛經內容的又一例證。
畫面10:黃金布地
位于“置金自滿”畫面北側,一大樹下一人,雙手正在持長形工具以黃金鋪地。
榜題:施工人的正前方存一黑色榜題框,隱約可見“……金……”字。
解讀:對照經文來看,此當為須達欲買祇陀園時,祇陀太子謂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時的相關畫面[5]419。
畫面11:須達與舍利弗共經精舍
位于北側北上角,上部畫群山及樹林,下部南側一樓閣,頭戴王冠、身穿深衣腰懸玉佩側身向后的青年男子轉身看一身穿白色袈裟的僧侶,兩人各牽繩之一端前行,四周遍開蓮花。
榜題:中央一黑底榜題,榜題上書“須達……祇陀園”等字。
解讀:此畫面當為舍利弗戰勝勞度差之后,“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欲往請佛說法之情節[5]420。其中,深衣男子當為須達,白色袈裟僧人當為舍利弗。
(二)第2部分 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時
繪于北側塑像上側南后部及南側上部。自北向南依次畫“國王待舍利弗與六師角力時”“六師待與舍利弗角力時”“諸沙門并須達待舍利弗與六師角力時”,甬道南側畫“須達請舍利弗與六師角力”等4個畫面。南側上部主要圍繞“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展開。可分為兩組畫面,北側以勞度差及六師率眾斗法,南側以舍利弗率眾人迎戰為主要內容展開。主要包括“勞度差咒作十頭毒龍,舍利弗化作金翅鳥王啖之”“勞度差咒作一樹,舍利弗以旋風摧之”“勞度差咒作一池,舍利弗化作六牙白象吸之”“勞度差咒作一山,舍利弗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擊之”“勞度差咒作一牛,舍利弗化作獅子分裂食之”“勞度差咒作夜叉鬼,舍利弗化作毗沙門天王以火滅之”等3組18個畫面(見圖2—3)。
1. 第1組(畫面1—4):國王待六師與舍利弗角力時
畫面1:國王待六師與舍利弗角力時
位于塑像頭南后部山巒形分割線下部,與“須達欲買祇陀園”位于同一平面上,自南向北一黑衣人物跪于山前做祈禱狀,北側樓臺上似坐一人,樓臺前多人環繞。
榜題:黑衣人與樓臺間有一黑色榜題,上書文字依稀可見“……國王……”等字。
解讀:對照經文及畫面來看,此當為須達用黃金鋪地的代價購買祇園時,六師又要求與六師角力以輸贏決定祇園的歸屬。舍利弗決定與六師角力后,“是時人民,悉為國王及其六師,敷施高座”“爾時須達,為舍利弗而施高座”[5]420。山巒下的樓臺當為人民為國王及六師敷施的高座;南側樹下一人,當為舍利弗。下部樓臺當為須達為舍利弗而施之高座。
畫面2:六師待與舍利弗角力時
山巒南側上部群山,下側前部一人,似坐于一高臺之上;后部六人,有佩劍者、擎華蓋者、持幡者,其中外側身形較小者身懸大鼓,似正在擊鼓。
榜題:前部高座后部、眾人前部各有一方黑底榜題,上書文字不明。
解讀:根據經文及畫面內容來看,此當為舍利弗與六師弟子勞度叉決計角力后,“舍衛國中,十八億人,時彼國法,擊鼓會眾”之畫面[5]420。其中,前部似坐于高臺上的人當為國王,后部佩劍者、擎華蓋者、持幡者六人當為“六師”,旁邊懸鼓者當為“擊鼓會眾”者。整個畫面是講國王及人民觀戰,六師等待與舍利弗角力。
畫面3:須達待舍利弗與六師角力時
位于畫面“六師待與舍利弗角力時”下方,前部大部分毀,后部一大樹,大樹下有沙門多人。
榜題:不明。
解讀:根據經文及畫面內容來看,此當為沙門并須達等眾人等待舍利弗與六師角力。
畫面4:須達請舍利弗與六師角力時
位于南側塑像上部北上方,門上畫面南側。畫面中央為竹林,兩側各有一組人物。竹林北側畫大蓮花狀華蓋,華蓋下設高座,高座上坐一有頭光的黑衣比丘狀人物;身后隱約可見侍從或弟子數人,其中現存一身有頭光,其他因畫面損毀具體不明;前部竹林下有一人向坐者下跪行禮。竹林南側上部畫華蓋,華蓋下設高座,高座上坐有頭光白衣比丘狀人物;身后侍立兩身侍從,均有頭光。
榜題:竹林中央存一白底榜題框,上書文字兩行,南側上部可見“舍利□(弗)……”等字,其他漫漶不清。北側坐者和跪者之間上部中央亦存一白底榜題框,文字不明。
解讀:對照經文及畫面來看,此當為六師要求與沙門角力以定祇園歸屬時,舍利弗迎戰前在樹下入定的內容。北側為佛經所載:“時舍利弗,在一樹下,寂然入定,諸根寂默,游諸禪定,通達無礙。”據此可知,北側高座上著黑衣有頭光僧人當為舍利弗,大樹下所坐之人亦當為舍利弗;而跪者當為須達,此即經文所謂:“是時須達,至舍利弗所,長跪白言:‘大德!大眾已集,愿來詣會。”的相關畫面[5]420。南側三人則為以勞度差為代表的六師外道。
2. 第2組(畫面5—10):勞度差幻化時
畫面5:勞度差咒作十頭毒龍
繪于“須達請舍利弗與六師角力時”南側,上側畫一多頭多身毒龍向南俯沖而來,下側繪多人向南行進。
榜題:不明
解讀:此應為勞度差“復作一龍,身有十頭,于虛空中,雨種種寶,雷電振地,驚動大眾”的畫面[5]420。
畫面6:勞度差咒作夜叉鬼
毒龍正前方繪一體型高大、面目猙獰、身穿短裙、張牙舞爪似人非人的怪獸。
榜題:不明
解讀:此應為勞度差“作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燃,目赤如血,四牙長利,口自出火,騰躍奔赴”的形象描繪[5]420。
畫面7:勞度差咒作一牛
夜叉鬼正前方是頭長兩尖角、四肢粗壯、匍匐在地、張口大吼的大牛。
榜題:不明
解讀:此應為勞度差化為一“身體高大、肥壯多力、粗腳利角、爮地大吼”的大牛[5]420。
畫面8:勞度差咒作一樹
位于整個斗法畫面的正中央及中央上部,中央一形似芭蕉樹的樹木,樹葉向兩側緩緩展開。上部是郁郁蔥蔥的樹林。
榜題:不明
解讀:此應為表現勞度差“于大眾前,咒作一樹,自然長大,蔭覆眾會,枝葉郁茂,花果各異”的畫面[5]420。
畫面9:勞度差咒作一山
位于“勞度差咒作一樹”畫面的上部,畫巍峨高山,上有樹木花果。
榜題:不明
解讀:此應表現勞度差“復作一山,七寶莊嚴,泉池樹木,花果茂盛”的相關畫面[5]420。
畫面10:勞度差咒作一池
位于“勞度差咒作一山”畫面南側,畫一圓形寶池。
榜題:不明
解讀:此應表現勞度叉“又復咒作一池,其池四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花”的相關畫面[5]420。
3. 第3組(畫面11—18):舍利弗應戰時
位于勞度差幻化畫面南側,由北至南分別畫:舍利弗以旋風摧樹、舍利弗化作毗沙門天王以火燒夜叉鬼、舍利弗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擊山、舍利弗化作金翅鳥王啖十頭毒龍、舍利弗化作獅子裂食大牛、舍利弗化作六牙白象吸干池水等內容。
畫面11:舍利弗以旋風摧樹
繪于舍利弗率眾人迎戰畫面的下方,一棵大樹根部向上、樹干向下而倒。
榜題:不明
解讀:當勞度差咒作一樹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根,倒著于地,碎為微塵”[5]420,此當表現舍利弗以旋風摧樹的畫面。
畫面12:舍利弗化作毗沙門天王火燒夜叉鬼
舍利弗以旋風摧樹畫面上部,一頭戴武冠、左手托塔、身穿皂袍、腳踩一怪物的神人面南而立。
榜題:不明
解讀:此為勞度差咒作夜叉鬼時,舍利弗則“自化其身,作毗沙門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哀脫命。辱心已生,火即還滅”的畫面[5]420。
畫面13:舍利弗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擊山
與毗沙門天王并列繪一頭戴武冠、手執金剛杵、身穿皂袍的人物面南而立。其下前方大山開裂,下部亂石崩下等內容。
榜題:不明。
解讀:此當表現勞度差咒作一山時,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遙用指之,山即破壞,無有遺余”的畫面[5]420。
畫面14:舍利弗化作金翅鳥王啖十頭毒龍
毗沙門下部一向南飛翔的金翅鳥,周圍畫面漫漶不明。
榜題:不明。
解讀:此當表現勞度差化作十頭毒龍時,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鳥王,擘裂啖之”的畫面[5]420。
畫面15:舍利弗化作獅子裂食大牛
位于“勞度差咒作大牛”畫面的北側,一張開大口威風凜凜的獅子與大牛似作搏斗狀(圖4)。
榜題:不明
解讀:此應表現勞度差咒作大牛后,舍利弗隨即“化作師(獅)子王,分裂食之”的畫面[5]420。
畫面16:舍利弗化作六牙白象吸干池水
位于塑像北側下部,以黑色山巒為界,山巒南側為“國王遣使請世尊為一切大眾說法”;北側近甬道部分毀,上部一水池,水池上部飄蕩著不知名花卉等。水池北側為茂密的樹林。近甬道處有多人(部分毀)立于樹下緩緩向南行進;南側及上部群山環繞,下部一似為黑色地毯上立一白色大象,象鼻伸向水池作吸水狀(圖5)。
榜題:不明
解讀:經文中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的第二回合,先是勞度差咒作一池,“其池四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華”欲以此贏舍利弗,舍利弗見此,遂“化作一大六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蓮花,一一花上有七玉女,其象徐庠,往詣池邊,并含其水,池即時滅”[5]420。
畫面17:舍利弗現四威儀
繪于毗沙門天王上部,一體型威猛、身穿短裙、張牙舞爪、口吐火焰的似人非人的怪獸凌空而來(圖6)。
榜題:不明
解讀:此為舍利弗與勞度差大戰六個回合戰勝勞度差后,“時舍利弗,身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東沒西踴,西沒東踴,北沒南踴,南沒北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還合為一身;于虛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的諸般神通形象[5]420。
畫面18:舍利弗還攝神足會大眾
繪于舍利弗現四威儀下部,毗沙門天王及力士南側。中央一榜題框。緊鄰中央榜題框北側上部畫一比丘狀人物,雙手合十,向南行進。南側亦畫一隊穿長袍狀人物,皆雙手合十,向北行進。
榜題:中央設白底榜題框,內書文字兩行,文字模糊不明。
解讀:北側向南行進雙手合十比丘狀人物當為舍利弗及諸沙門,南側向北行進雙手合十穿長袍狀人物當為被降服后的六師徒眾。此當為舍利弗“時會大眾,見其神力,咸懷歡喜。時舍利弗,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跡,或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六師徒眾,三億弟子,于舍利弗所,出家學道”的畫面[5]420。
(三)第3部分 佛陀至祇園精舍說法
繪于南側南上角及南側下部,主要為“須達與祇陀太子共立太子祇樹給孤獨園”“須達借道眼悉見六欲天中嚴凈宮殿”及“國王遣使請世尊為一切大眾說法”等3組畫面。
1. 第1組(畫面1):須達與祇陀太子共立“太子祇樹給孤獨園”
位于南側南上角,上部有竹林及其他樹木,下部為一三廡間宮殿,中央一間內有二人相對席坐其間,交談正歡。兩側房內畫面模糊,內容不明。
榜題:畫面模糊,榜題文字內容不明。
解讀:此畫面與北側北上角“須達與舍利弗各牽繩一頭共經精舍”(第1部分畫面11)相呼應,表現了“須達與舍利弗共經精舍”之后,世尊“與諸四眾,前后圍繞,放大光明震動大地,至舍衛國”說法時,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樹給孤獨園,名字流布,傳示后世” 的內容[5]421。
2. 第2組(畫面2) 須達觀六欲天中嚴凈宮殿
位于須達與祇陀太子共立“太子祇樹給孤獨園”畫面下部,部分被南側塑像遮擋,下部大部漫漶不明。但依然可以看出,此處為眾多層層疊疊的宮殿院落,儼然一派人間宮殿建筑群。
榜題:每處宮殿院落幾乎都有榜題,但因部分被塑像遮擋及其畫面漫漶等原因,致使榜題文字不明。
解讀:當須達與舍利弗各捉繩一頭共經精舍時,不知何故舍利弗卻“欣然含笑”,須達問其緣由,舍利弗答言:“汝始于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舍利弗“即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凈宮殿”。須達又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驕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這時,須達答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上”時,只見第四天宮殿湛然,其余宮殿全部消失不見。于是,二人又“復更從繩”,舍利弗“慘然憂色”并說出了在過去六佛時,須達皆為過去六佛起立精舍的因果。說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犍椎”并欲請佛[5]421。畫面中層層疊疊的宮殿建筑當為須達在過去六佛世時分別為佛修建的精舍,亦即須達所見“六欲天中嚴凈宮殿”。其他內容可惜為塑像所遮擋,甚為遺憾。
此外,在南側塑像南側下部,茂密的竹林及一樓閣,樓閣中央有一方榻,方榻南側有二少女,方榻之上及北側內容漫漶不明。我們推測,這一內容可能表現的是舍利弗所謂“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驕逸自恣”的相關畫面及內容[5]421。
3. 第3組(畫面3) 國王遣使請世尊為一切大眾說法
位于甬道南側塑像北部中間位置,畫面南側及上部為山巒,中央為國王及眾大臣,形式似初唐第220窟維摩詰經變中的中原帝王出行圖。國王頭戴冕冠在前,眾大臣緊隨其后。下部前方以白色山巒為界,另畫一眾人等,但形象、體量小于上部的帝王及眾大臣。
榜題:位于國王出行圖上方,白底墨書“□□□□□□舍衛國□□”等字。
解讀:當精舍已成,須達請求國王“遣使請佛”。國王即遣使者詣王舍城,請佛及僧臨覆舍衛國。于是世尊至舍衛國為一切大眾說法。有意思的是,經文中并沒有國王迎接世尊說法的內容,而壁畫中卻創意性地繪制出了中原帝王率眾觀戰及聽法的畫面,尤其是其中戴冠冕的帝王像,顯然是被刻意畫為中原帝王的形象,這也使得這一畫作更具中國化特色。
至此,須達起精舍的故事內容全部結束。值得關注的是,最后三組畫面與北側北上角的“須達共舍利弗各牽繩一頭共經精舍”畫面相呼應,共同圍繞眾多宮殿展開,整體表現了須達與祇陀太子共立“太子祇樹給孤獨園”的主旨內容。這一做法不僅精簡了畫面,而且使兩處故事中的人物相互穿插、互相呼應,使整體畫面更為生動,更具故事性。
四 余 論
莫高窟第292窟前室西壁底層隋代壁畫,由于五代壁畫覆蓋后重新揭取之故,致使畫面多殘破模糊,一直以來并不為學界所知。但據前文梳理,大多內容基本可辨,較為完整地表現了《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的全部內容。比照佛經來看,此圖北側畫《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第1部分“須達起精舍”,大致可分為3組11個畫面;北側南段上部及南側畫第2部分“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及第3部分“佛陀至祇陀園精舍說法”等內容,第2部分大致可分為3組18個畫面,第3部分大致可分為3組3個畫面,共32個故事情節,屬同期大型敘事性故事畫。
根據前賢研究成果,與此相似的內容遺跡在印度和中國新疆地區也有分布。印度現存3處:1. 建于公元前3世紀前后的印度桑奇大塔1號大塔北門左柱正面第2格內的浮雕圖;2. 建于公元前250—前200年之間的中印度巴爾胡特大塔欄楯的浮雕圖;3. 建于公元前100—前50年之間的印度北方比哈爾邦的菩提伽耶寺的浮雕圖。在中國新疆地區存2鋪:1. 開鑿年代約為4世紀前后的森木塞姆石窟第44窟中主室券頂右側原有的“祇園布施”圖;2. 開鑿年代約為5—8世紀的庫木吐喇第23窟主室右壁的“祗園布施”圖[11]。以上“祇園圖”主要內容幾乎全部為“祇園布施”的“黃金鋪地”。尤其是新疆地區的祇園布施圖既有源自印度的傳統風格,亦具有濃烈的漢化特色[12]。從這一點來講,印度和中國新疆地區現存的“祇園布施”圖之間存在諸多借鑒或傳承關系。同時,北朝敦煌石窟中的“祇園記圖”與此也具有一定的承續關系,尤其是其線性敘事的繪畫形式,更有可能起源于印度佛教藝術[13]。而綜合來看,新識讀的莫高窟隋代第292窟“祇園記圖”雖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但與其他“祇園記圖”存在的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仍然值得關注。
敦煌石窟中最早的“降魔”故事出現在西千佛洞北周第12窟主室窟門西側,整體畫面不大,采用簡單的構圖,主要繪制了“須達起精舍”和“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兩部分內容。此畫整體呈倒“U”形線性構圖,上下兩部分共12個故事情節。上部自左向右繪“須達辭佛回國”“須達與舍利弗四處選地”“選定太子花園”“黃金鋪地”4個情節,下部繪六回合斗法、外道皈依、舍利弗說法等8個場景。與印度和中國新疆地區的“祇園布施”圖相比,這一內容在敦煌石窟中形式顯得更為復雜、故事情節更為豐富,應是這一題材逐漸發展、完善,抑或被有意改造的結果。
長期以來,學界多認為敦煌隋代石窟中并無“祇園記圖”的相關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于這一內容全面、準確的認識。一般認為,莫高窟最早的為初唐第335窟西壁的《勞度差斗圣變》以及稍后年代比定為8—9世紀的P.4524《降魔變文》{1}。而此兩畫完全省略了故事的第一部分,沒有任何表現須達尋找祇園的畫面,所有情節都取自舍利弗與勞度差的斗法,故此畫只能以“降魔”“勞度差斗圣變”稱之,這也是此類壁畫在唐宋文獻中所使用的名稱[14]。在此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敦煌石窟中再也沒有相關內容出現。直至唐咸通三年至八年(862—867)營建的翟法榮窟(莫高窟第85窟)中才再次出現了延續初唐做法的勞度差斗圣變,并一度成為熱門題材,目前至少有19幅唐宋之際該內容的壁畫保存下來。其中雖然也有表現“須達起精舍”,但圖畫形式卻依然延續了初唐第335窟舍利弗與勞度差對坐斗法的基本構圖,其他并無大的改變。
如果說西千佛洞第12窟考古分期時代無疑,則本文所論莫高窟隋第292窟“祇園記圖”當為敦煌石窟中出現的第2鋪,且無論構圖形式還是內容方面都顯示出不同尋常的改變。據研究,敦煌石窟壁畫中的這一畫作構圖因時代而有所差異,但整體上都以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內容展開[15]。而新發現的第292窟“祇園記圖”則顯得更為復雜,既有連環畫構圖形式的因素,也有隔門分繪不同內容的特點。最為突出的是,此畫中畫家巧妙地使用了多個故事情節共用一組畫面的構圖技法。如:此窟北側北上角的“須達與舍利弗各牽繩一頭共經精舍”這一畫面,經文中在斗法之后,而此畫卻出現在須達購買祇園之后,如果按照一般連環畫的敘事方式理解,無論如何都是令人費解的。但是如果聯系前后經文,這一形式卻巧妙地利用了同一個畫面,既表達了須達購買祇園并以黃金鋪地修建精舍,又表現了舍利弗與勞度差斗法取勝之后,舍利弗與須達牽繩量地共同前往祇園修建精舍的曲折故事。還有,此畫南側上部,畫家以并列不同內容的構圖方法將勞度差幻化的不同形象以及舍利弗與勞度差分別斗法的情節并列表現出來。這一構圖方式較好地表達了經文所述勞度差幻化的不同情形以及幻化之后與舍利弗斗法的漸次過程,使這一畫面更具一種時空感。可以說,多種構圖方法在這一畫作中的巧妙使用,或與當時畫家重視“經營位置”的理論要求不無關系。
總的來看,莫高窟隋第292窟“祇園記圖”完整地表現了《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的全部內容,是目前可知同類題材中內容最豐富、表現形式最復雜的,是敦煌石窟中同類題材的早期形式。根據前文梳理研究,我們認為,這一內容的識讀,不僅為該題材相關研究補充了重要的圖像原始資料,而且補寫了隋代敦煌石窟無此經變的空白,為準確認識這一內容在印度、中國新疆以及其他地區的傳播、發展以及佛教藝術中國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更為全面認識后世降魔變文、勞度差斗圣變等內容的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啟示。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元林研究館員、王惠民研究館員的悉心指導及呂文旭副研究館員、喬兆福館員的大力幫助。在此,對以上諸先生的指導、幫助謹表謝忱。
參考文獻:
[1]樊錦詩,關友惠,劉玉權. 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M]//敦煌文物研究所. 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2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84.
[2]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內容總錄[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19.
[3]金維諾.敦煌壁畫祇園記圖考[J]. 文物參考資料,1958(10):13.
[4]魏迎春,李小玲. 莫高窟第72窟勞度差斗圣變解說[J]. 敦煌學輯刊,2022(3):73.
[5]佚名. 賢愚經:卷10:須達起精舍品[M]//慧覺,等,譯.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冊.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418-421.
[6]龍樹菩薩. 大智度論:釋天主品[M]//鳩摩羅什,譯.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5冊. 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5:443.
[7]佚名. 不空■索咒經:須達起精舍品[M]//阇那崛多,譯. 高楠須次郎,渡邊海旭.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 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8:399.
[8]堅意菩薩. 入大乘論:卷下[M]//道泰,等,譯.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2冊.東京:大一切經刊行會,1925:46.
[9]提婆菩薩. 百論:舍罪福品[M]//婆藪開士,釋. 鳩摩羅什,譯.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0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168.
[10]張元林. 敦煌、和闐所見摩醯首羅天圖像及相關問題[J]. 敦煌研究,2013(6):1-12.
[11]趙莉. 西域美術全集:10:龜茲卷:庫木吐喇石窟壁畫[M]. 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42.
[12]邢逸菲. 印度早期祇園布施圖像研究[J]. 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21(1):139.
[13]巫鴻. 空間的敦煌:走進莫高窟[M]. 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245.
[14]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M]. 人民出版社,1963:76,149.
[15]李永寧,蔡偉堂. 降魔變文與敦煌壁畫中的勞度叉斗圣變[C]//敦煌研究院. 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編:上.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165-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