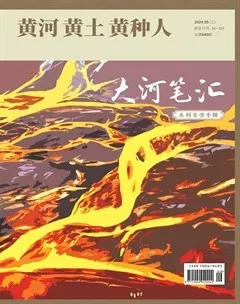長在骨髓里的老屋
胡金華
稻草人
在石板路和田埂的交叉口
我扎了個稻草人
一把爛蒲扇驚起貪吃的麻雀
老師發在獎狀上的紅五星
壓彎我年幼的腰和田地金黃的稻穗
當鬢毛和鄉音漂染著雜質
溫馨的螢火蟲爬上了冰冷的電桿
田埂還是田埂,交叉路口還在
道路寬了還鋪了黑油
斑馬線閃著城市的光芒
一個氣沖空皮囊的假交警格外醒目
一招一式全像稻草人
夜歸的鄉下人嚇成了麻雀
老屋
左邊是地灶鐵鍋干柴
右邊是裝得七八擔水的瓦缸
中間娘陪嫁的紅漆碗柜格外耀眼
盡管里面只有幾個窯碗
母親和我常抬到河里洗了又曬
一大家人和鄰居社員在堂屋穿梭
木梁上蜘蛛結網扯出止血止淚的土藥
拾級而上唯一的祖屋
樹兜床底的土窖冬暖夏涼
那是我們躲貓貓的游樂園
平時存滿紅薯蘿卜
祖母常說躲日本兵時藏過祖輩
三年饑餓時救過全家
夢回故園
塵封已久的記憶頓時猶新
生怕夢醒,不想驚跑老屋里的故人
屋檐下躲雨的燕雀
鄉下人的算計與生俱來
一年到頭圍著頭頂的那片天
天要破損就會漏雨
防漏是一門必備的生存術
從夏天就要準備
扮禾后的稻草要捆均勻和曬干
變成鄉音里的稈
當茅草被寒風卷起
父母和我在木梯上爬成上樹的螞蟻
父親把新稈插入舊稈中
像細作土地般
用身體碾壓成一排排梯田
日子略好買得起瓦片了
我們又復述一遍把稈換成瓦
只能恰好一片瓦搭著另一片的邊
只能更加小心翼翼
結果是一半黃的茅草一半黑的瓦屋
暴雨來了
茅屋這邊麻雀彈琴地上落草落灰
瓦屋那邊泉水叮咚地上冒泡
父親在屋內用竹竿東戳西戳
母親用盆和桶接住一個個音符
一家人是屋檐下躲雨的燕雀
各自尋找干燥的天地
哦,可惜老屋如我的頭發沒有了頂
父親也去了陰間撿瓦
我在陽間,關于老家的夢
總爬不出那片青黃不接的天與那道殘墻
茅草搖曳著我童年少年溫馨的記憶
放牛娃
我到中年才知有奢侈品一說
童年如果有,傘一定是
一把傘可抵當時鄉間一茅屋
鄉下人的頭頂
只有天空和竹編的尖笠斗笠
躲雨是鄉里娃的必備
看牛娃管不了天氣管在牛尾巴上掛笠
毛毛細雨落在山丘
我在桐葉楓葉和葉一樣的竹笠下
站成現代畫家筆下的牧童
電閃雷鳴
我在石壁凹陷處東躲西藏
應該像當今游客眼中的一只猴
一次平地和傾盆大雨突遇
我只好鉆入牛的肚皮下
重回母乳間尋找溫暖
躲成揮之不去的印記
年底生產隊殺我的老牛
我撕心裂肺和牛一起流淚
若是現在那牛還在
肚底也裝不下我這一身肥肉
門前有棵苦楝樹
門前地坪,有棵苦楝樹
比茅屋高大許多
枝繁葉茂,開著好看的紫白色的花朵
樹尖有喜鵲在筑窩
有陽光與和風的時候
一村人在樹下憩蔭扯談磨生產隊的洋工
滿村的煙火粗魯的笑聲在空氣中飄蕩
我用苦楝籽作彈弓彈打過大人和小鳥
和小伙伴爬到頂尖淘過喜鵲窩
喜鵲驚叫樹下卻毫無波瀾
我邊翻字典邊讀報紙引來夸獎
比人高的秤掛在樹枝上
我站上凳子稱豬屎牛糞
挑擔人說小學生的我算術好字很漂亮
苦楝樹全身都苦苦入胸膛
果子汁涂上可以治凍瘡
挖根熬水可以殺死蛔蟲
我喝過,先暈后屙蟲最后全身輕松
苦楝花香十里銘心刻骨
旁邊的老屋和村莊啊
就是一棵苦楝樹
現在,鄉下很少見到苦楝樹
后院的背簍
背簍就掛在后院天井的墻上
有大有小,都可裝下我的年輪
背簍下的磨刀石旁插著砍刀鐮刀
柴火豬草牛草
什么都往家里背
那時山上野地刨得精光
累計還是背回了一座大山
駝了我年幼的腰背
換取了翻山越嶺的力氣和學費
背簍的圓筐圈進幾十年光陰
重回生命的圓點我才發現
背上的竹簍竟是一個打水的竹籃
兒時的月亮
窮之極的夜晚
聽風聽大人談古論今
口水流進銅錢兌油炸粑粑的故事里
大人在地上畫著的銅錢像月亮
我看著木箱抽屜上的手柄扣發光
眼盯著門鎖墊發綠
夢里只想把月亮也戳一個孔
變成個大銅錢
還盼望月色未跑的大清早
能有一個挑擔的外地佬
用一串刀片甩打出清脆的吆喝
將牙膏皮干雞屯子
換成一枚一枚的小月亮
如今,誰還擁有那一分兩分五分的銀月
誰還擁有那種尋找月亮的一絲一毫快樂
殺魚草
門前是娘經管的池塘
回娘家的姐一口氣釣了四條草魚
魚兒身材修長絕對是女人的夢想
我提起來笑道
喝礦泉水長大
岸上有草,以后要養能飛的魚
精瘦的魚喚醒我精瘦的童年少年
同病相憐逼我第二天大清早去割草
兒時背簍的沉重和辛酸
換成了輕松與愉悅
久違的汗泉井噴
像當年踩在打稻機上呼風喚雨
八十多歲的母親聲聲喚我回家
一邊替我擦汗一邊嘮叨
殺一次草只能喂飽一餐
農村人家里還是要多生兒孫
寂寞的小路
在這條小路走出
一個倔強的男孩
是四處爬行尋找結果的野藤
秋風起藤葉枯
返回這條小路一身殘疾
遠方送給的果是一簍苦瓜
到了需要執棍看景的殘余
風啊,還是那樣冷熱不定的風
吹走了那個看牛娃的竹笠和頭發
雨水直接灌進了胸腔
漲成一片思念的海
淹沒了父親叔叔舅舅
和他們的那個時代
雨停了
路邊全是寂寞的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