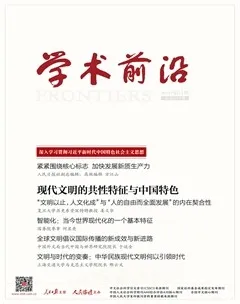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的解析、批判與超越
陳寶勝 李學敏
【摘要】政治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特定政治文明結構與發展水平的系統性呈現。作為政治文明核心的政治權力是理解政治文明形態的鑰匙。權力來源、授權形式、權力結構和運行方式是政治權力系統的基本話語構成,以此為視角,社會契約、選舉授權、分權制衡與資本主義民主法治的“契約型”話語邏輯構成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基本理論敘事。理論上的契約權遮蔽事實上的資本權、周期性選舉積弊、分權制衡治理低效、資本主義民主法治內生缺陷等,導致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實踐面臨諸多困境。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話語邏輯的理論敘事是建構技術權、雙向授權與整合性權力相統一的話語邏輯。
【關鍵詞】政治文明形態? 話語邏輯? 權力系統? 契約型
【中圖分類號】D621?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1.012
政治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特定政治文明發展水平的系統性呈現。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是政治文明形態的理論敘事。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極具理論系統性、發展相對成熟的政治文明形態之一,以致福山形成了“意識形態終結”的幻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是必須面對的“競爭性”話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一個核心任務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系統解析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及其局限性,探尋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建構中國特色政治文明形態自主知識體系的可能路徑,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價值。
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的“權力系統”理論框架
解析政治文明形態,需要明確分析政治文明形態的“尺度”,即剖析政治文明在內在規定性和外部影響雙重作用下,表現出的某種具有同一性、有機性和時空特征的存在狀態。[1]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2],將國家權力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米爾斯認為,“一切政治都是權力之爭”[3]。王滬寧認為,政治最根本的問題是權力,國家本身是一定權力的表現形態。[4]政治文明理論研究常常圍繞政治權力而展開,國家權力的形成及以權力為核心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政治運行機制是政治文明形態比較研究的重要議題。[5]馬克思在《關于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計劃草稿》中圍繞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權力形式、權力機構、權力與法、權力授予方式等列舉了研究提綱。[6]綜合政治哲學理論譜系,借鑒現有政治權力理論分析成果,權力來源、授權形式、權力結構及權力運行方式構成政治權力系統的四個基本要素,這四個方面的理論敘事構成了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的系統表達。
權力來源。權力來源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根源,是社會承認并服從國家權力的理由。權力來源是對政治權力本質的解讀與闡釋,回答的是政治權力“是什么”“從哪里來”的本體論問題。“關于國家(政府)權力來源的學說,是政治理論的核心,它既是現實政治活動的理論觀念反映,又是現實政治運作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7]權力來源話語邏輯影響著授權形式、權力結構、權力運行的話語邏輯與制度安排,在政治系統理論與實踐中處于基礎性地位。“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并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8]政治權力總要構建權力來源理論為其統治提供合法性(合理性)支撐。表面上看,合法性信仰指向合法律性,即構筑政治統治的法律認同;從深層次看,合法性信仰指向合理性,即構筑政治統治的社會承認基礎,實踐中主要表現為政治權力來源話語邏輯的理論敘事。客觀而言,人民主權是權力來源的本質意蘊,但不同政治文明形態對權力來源有不同的話語表達,考察特定政治文明形態對權力來源的話語敘事,是理解其權力觀念、權力價值、權力行為話語邏輯與實踐制度安排的基礎。
授權形式。授權形式指特定政治文明形態內部權力行使者獲得權力的方式,是政治權力行使者獲得權力主體資格的程序性規定。特定政治文明形態,其內部權力機構、權力行使者如何被授權,是其權力運行的實踐起點。經濟人理性決定了實踐中的權力行使者通常優先對權力授予者負責。“誰給我權力我就對誰負責”,這是通常的權力使用邏輯,授權形式因而是決定權力行使者施政行為與權力倫理的關鍵變量,指向權力行為邏輯的規律性認識,回答的是“權力行使者何以產生”“為什么是我”“我會對誰負責”的認識論問題。在權力授予形式方面,暴力有時被作為權力授予形式或者說權力獲取形式的終極保障,但以暴力作為權力授予形式的話語邏輯,則極易導致政治權力更迭淪為“叢林法則”暴力循環,[9]不利于政治社會秩序的穩定,且權力授予、獲取更迭的社會成本太高,理論與實踐都不應也不會過于強調暴力的權力授予形式,文明的政治文明形態通常都要建構符合文明發展要求的權力授予形式理論敘事和制度安排以維護穩定的政治社會秩序。
權力結構。權力結構指權力機構設置、權力分配及權力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是以權力為核心,權力主體間關系為紐帶、體現權力價值目標的權力配置結構。[10]權力結構是橫向權力結構和縱向權力結構的統一。橫向權力結構是同層級權力的專業化分工及相互監督制約的政治關系,縱向權力結構是指權力從高到低各層次的縱向配置及其相互關系,亦即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配置關系。其明確了權力來源、完成權力授權,形成了體現特定政治文明形態政治理念、價值目標的權力結構話語,建構了兼具原則性、穩定性、靈活性、有效性的權力結構及其運行規則,回答的是權力監督、制約、運行結構設置的方法論問題。理論而言,權力結構是承載體現特定政治文明形態基本理念、價值目標、話語邏輯的功能性設置,權力結構話語邏輯和實踐制度安排與權力來源、授權形式的話語邏輯應有邏輯一致性,但實踐并非總是如此,權力結構實踐制度安排與理論敘事之間沒有必然一致性。“結構決定功能”,權力結構實踐制度安排才是真正體現和承載特定政治文明形態真實話語邏輯的載體,考察特定政治文明形態權力結構的話語邏輯,需要同時考察其理論敘事與實踐制度安排。
權力運行方式。權力運行方式指權力主體行使權力作用于權力客體、實現其權力影響力的方式。權力運行方式指向權力行使或作用于權力對象、實現權力影響力的過程、依據和方法,體現權力運行的規范性和文明程度,回答的是權力如何運行的方法論問題。常見權力運行方式主要有人治的方式、法治的方式或德治的方式。人治的方式指權力主體在權力行使過程中依據個人或少數人的理性和能力作出決定、作用于權力客體的權力運行方式。法治的方式指權力主體在權力行使過程中依據法律制度、規定程序、專業知識等作出決定、作用于權力客體的權力運行方式。德治的方式指權力主體在權力行使過程中以道德為軸心,將道德與法治相統一,依據道德和法律作用于權力客體的權力運行方式。[11]權力運行方式作為貫徹權力作用的實踐環節,意味著將權力界定在什么邊界內、以怎樣的程序實現決策、執行、監督、協調、控制等的作用方式。政治文明擺脫憑借個人主觀控制的權力邊界、依據個人好惡確定法律規范、極具不確定性的人治型權力運行形態,形成“制度籠子”約束、依據既定法律行使權力、更具確定性的權力運行形態,這意味著政治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話語邏輯
以批判神權政治及其話語邏輯為旨趣,資本主義政治哲學家通過“社會契約論”構建了政治理論體系,設計了公開選舉的授權形式,形成了“權力惡”為假設的分權制衡式權力結構和以民主法治為原則的權力運行方式,確立了系統的“契約型”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
社會契約: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權力來源話語敘事。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誕生之前的歐洲,是“君權神授”、神權與王權共同宰制社會的格局。為了在理論上摧毀封建統治的根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作出巨大努力,社會契約論正是這種努力的成果。早在古希臘時期,伊壁鳩魯就提出基于約定正義的社會契約說,認為國家是人們為了獲得安全而達成互不傷害的“默示的契約”的結果。[12]霍布斯繼承、發展了這一思想,認為自然狀態是“彼此互相離異、易于互相侵犯摧毀”的叢林狀態,為了獲得自我保護,人們因而訂立信約并讓渡自己全部的權利給國家。[13]洛克認為人們在自然狀態下是沒有約束的和諧狀態,訂立契約是為了更便利地“謀求他們彼此間舒適、安全和和平的生活”,而且這種權利的讓渡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主權者的權力因而也不是至高無上的,是應該受到契約限制的權力。[14]盧梭完善了社會契約論,將人天性善良作為前提假設,提出人們訂立社會契約是為了克服自然狀態中不利于人類生存的障礙;人們讓渡的權利不是授權某個個人或組織,而是反映共同意識的共同體,即資產階級“理性王國”。他指出,人們向共同體讓渡權利的目的是“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15]。社會契約為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提供了“國家‘原理即它的‘存在理由”[16],構成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敘事的邏輯起點。
選舉授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授權形式話語敘事。社會契約論為資本主義政治選舉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哈林頓是早期系統闡述設計選舉制度的代表人物,他認為一個平等共和國的官職應由人民投票選舉、平等地輪流執政。[17]洛克認為,政治社會的政治權力應由選舉產生,選舉是現代政府權力產生的唯一合法形式,“只要人民按照公正的和真正平等的辦法來選舉他們的代表,毫無疑問,那就充分體現了政治社會的意志”[18]。其后,潘恩[19]、密爾[20]等論證了代議制政府對人民主權原則實現的必要性,認為只有公開選舉才能真正實現人民主權。熊彼特提出民主“本身不能是目的”,而是“一種政治方法”,是“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的制度安排[21],亨廷頓認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果其強有力的決策者中多數是通過公平、誠實、定期的選舉產生的,并且實際上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那么這個國家就有了民主政體”[22]。隨著選舉制度理論與實踐的不斷完善,選舉不應受財產資格、性別限制,遵循普選、平等、公開[23],“自由進行,不受威嚇”[24]等原則,成為資產階級政治文明的基本話語內核。
分權制衡: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權力結構話語敘事。通過選舉完成權力授權之后,權力如何設置、如何保障權力“利維坦”不會背離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而侵蝕公民的自由權利,是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家思考的又一重要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構成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三權分立”、以權力制約權力的理論敘事和制度安排。社會契約論以權力“惡”為核心假設,認為權力天然具有“惡”的傾向,以致霍布斯就將“利維坦”這一個怪物的名字作為其著作的題名。孟德斯鳩認為,權力之“惡”會導致“所有擁有權力的人,都傾向于濫用權力”,“為了防止濫用權力,必須通過事物的統籌協調,以權力制止權力”,因而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主張。[25]分權制衡的主張有其思想傳統。亞里士多德就將城邦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審判。[26]斯巴達政體就存在制衡結構:公民參政防止君主專制、君主牽制元老院、元老院對公民大會形成制衡。布丹把國家主權歸納為立法權、戰爭與和約權、任命官吏權、最高裁判權、赦免權、效忠服從權、鑄幣權、度量衡選定權、課稅權等九項。[27]洛克提出將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28]權力制衡理論成為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政體的基本框架、組織原則和運行機制,也是迄今西方民主制度建構遵循的原則。杰斐遜、麥迪遜和漢密爾頓分別提出縱向分權、三權均衡、司法獨立等理論,推動了權力分立與制衡理論進一步完善,形成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縱橫兩個方向的權力結構設計理論敘事。
民主法治: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權力運行話語敘事。“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孟德斯鳩用《論法的精神》為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與法治奠定了邏輯基礎。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保障權力有效運行、防止權力濫用的方法是為權力設置邊界,這種權力邊界的設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分權制衡式的權力結構,二是民主法治的運行方式。民主法治理論都源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9]。斯賓諾莎突出強調法治對維持國家治理和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性,認為“政體法制是國家的生命,所以,只要政體法制保持完整有效,國家必然能夠維持不墜”[30]。在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話語中,資本主義法治內含規則、限權、良法以及未來預期確定性的內在邏輯,但資本主義法治必須與資本主義民主相依存,孟德斯鳩就將資本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相聯系。資本主義民主為資本主義法治提供了實質性的支持,而資本主義法治則為資本主義民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兩者決定著資本主義政治權力的基本運行規則,共同維系著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形成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話語邏輯的基石。
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的缺陷與斷裂
社會契約、民主選舉、分權制衡、資本主義民主法治的“契約型”話語敘事構成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基本話語邏輯,其社會契約的權力來源理論敘事闡發并遵循了人民主權原則,為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提供了合法性支撐,又對公開選舉的授權形式提出了必然性要求,而“權力惡”的理論假設決定了要保障人民主權就必須采取分權制衡的權力結構和民主法治的運行方式。至此,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成了較為精巧自洽的話語邏輯,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和斷裂。
虛偽民主:理論上的契約權遮蔽了事實上的資本權。公共權力來自人民,這是現代政治理論的共識,但實踐中的公共權力來源與理論上的“應然”常常相悖。圍繞社會契約進行的資本主義國家建構以資本創造政治的形式完成,資本才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31],以“人民主權”為原則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生活在其中“自由得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只能出售勞動力以獲得維持生存的條件。[32]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以“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超階級”的詞匯使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似乎以民主的形式復歸了人的自然權利,把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剝削工具的國家美化為“理想的”共和政體,事實上“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33],以政治權力支持下的“經濟強制”剝奪了無產者的人權,把無產者推向民主領域之外,掩飾了自身的階級性質與階級統治的實質,[34]形成了虛假的民主政治。
迎合政治:周期性選舉導致諸多積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把競爭性選舉作為民主標準,將選舉從實現人民主權的手段變成了目的,背離了民主的本真含義。選舉授權強調選票,這使得資產階級政客在周期性選舉中常常傾向于迎合選民,并因此導致諸多政治積弊。首先,為了在選舉中獲得多數選票,政黨及其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傾向于作出迎合選民愿望的政策承諾甚至用金錢購買選票,但勝選后其往往難以兌現,使選民逐步對選舉失望而走向政治冷漠。其次,周期性選舉促使競選者為了獲得多數選票而迎合特定社會群體,無法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容易引發利益被忽略甚至受損群體的不滿情緒。部分競選者還會通過強調社會分歧和指責特定群體來獲取選民支持,事實上加劇了社會沖突,容易引發抗議、示威或其他形式的反對當局的社會運動,增加社會分裂和政治動蕩的風險。最后,對選票的渴求導致無論是選舉過程中還是當選后的政客與政黨在表面上需要注重“民意”,引致所謂“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傾向,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則會控制媒體、引導輿論以攻擊對手、美化自身,導致極端情緒化和極端政治,引發社會動蕩。
政黨分贓:分權失靈與治理低效。分權制衡的權力結構設計,初衷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但在資本主義政治實踐中,政黨立場漸趨極端化,贏得選舉的政客上臺后傾向于任命本黨人士與親信擔任政府機構重要職位,傳統三權分立的分權制衡被“黨派分權”取代,出現“政黨分贓”,破壞分權制衡權力結構設計。首先,資本主義國家選舉制度催生的政黨分贓直接影響司法獨立,使之成為政黨爭斗的工具。美國總統任命的大法官及司法官員往往基于黨派忠誠而非法律專業性或公正無私的原則,這就削弱了司法權作為政府權力制衡的關鍵機制。其次,黨派斗爭使立法機構變成黨派利益代言人,成為“破碎的部門”[35],弱化了其立法與監督制約功能。再次,分權制衡的權力結構被破壞,行政權不斷擴張,不僅減弱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也使其易受特殊政治利益集團或富有階層的影響,加劇政治不平等。最后,政黨分贓使決策和執行被黨派利益綁架,黨派、政府、議會之間“互相拆臺”,合作少、制約多,決策僵局和政策執行滯后成為常態。特別是面對危機事件時,理論上的高效決策、高效資源調配常受黨派利益鉗制、機構制衡影響、層級權限束縛,導致政府危機應對反應能力和行政效率低下。
運行限度:資本主義民主法治存在天然缺陷。首先,資本主義民主實際上是資本控制的金錢政治,資本主義民主法治天生就是資產階級階級統治和剝削的工具,當選民“不把選舉權用于公共的理由,而是為金錢而出賣選票,或者按照控制著自己的人或出于私人原因希望謀求其好感的人的意思投票時,代議制度就沒有多大價值,并可能成為苛政或陰謀的單純工具”[36]。其次,資本主義法治天然具有滯后性。法治是對權力運行的規范性要求,但國家治理應兼具規范性與靈活性。在分權制衡的權力結構下,一項政策制度、法律規范的出臺或修改意味著復雜的程序和利益博弈過程,社會、政治或經濟制度中發生的變化或創新往往很難迅速反映在作為治理依據的法律規范和政策條款之上,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天然的滯后性和低效率性。再次,周期性選舉帶來的周期性權力更迭會導致頻繁的政策調整,利于長遠利益的戰略往往被擱置,強調短期利益的政策則更容易被施行,權力集團通過金錢操縱選舉、媒體、司法和行政,會破壞民主法治的公平性、實效性。最后,資本主義民主的天然缺陷帶來的“多數暴政”可能侵犯少數群體的權利,“依靠普選權來治理國家就像繞道合恩角時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樣:他們不研究風向、氣候和使用六分儀,卻用投票來選擇方向”[37],其結果往往是“武斷、嚴厲而且具有破壞性”[38]的“多數人暴政”。
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的路徑
從社會契約的權力來源,到公開選舉的權力授權,再到分權制衡的權力結構與資本主義民主法治的運行方式,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個層面構建了精巧自洽的知識體系,為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實踐提供了系統務實的話語邏輯支撐,但這一話語邏輯具有內生缺陷,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斷裂。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與實踐制度安排并非“歷史的終結”,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話語邏輯,建構更具文明性、進步性的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與實踐制度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超越社會契約。伴隨著政治文明的發展,“一切公共權力來源于人民”已經成為歷史的共識,然而,人民主權的真理性、客觀性、本質性,并不必然表現為實踐性。人民是抽象集合的群體性概念,權力是客觀實在的影響力,人民主權的抽象原則要轉化成公共權力的實踐影響力,需要經邏輯轉換才能實現。雖然“社會契約”只是資產階級為其政治統治塑造的“關于自己本身、關于自己是何物或應當成為何物的種種虛假觀念”[39],但其闡釋了“人民主權”轉換成“國家權力”、產生實際政治影響力的轉化形式,對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創造新的政治文明形態有重要理論價值。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話語邏輯和政治實踐,需要超越“社會契約”闡釋與轉化人民主權的話語邏輯,重構人民主權轉化為國家公共權力影響力的理論敘事。綜觀人類政治文明史,從神權政治時代的“帝王心術”“統治術”到契約政治時代的法治理論與實踐、系統性現代管理方法,都是作為軟科學的治理技術在支撐與實現公共權力的影響力。當前,新興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應用于國家治理、強化公共權力影響力的實踐場景不斷深入,治理技術與科學技術形成的技術權日益顯現。進而言之,“神權”“契約權”與“統治術”都是治理技術的體現,是技術治理的初級形式,堅持程序合理性與實踐合理性相統一,以科學合理的民主程序和機制保障人民主權的實現成為超越資本主義“契約權”話語邏輯的有效路徑。
超越選舉授權。根據權力授予方向,人類迄今所創造的政治文明形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自上而下的權力授予(權力剝奪也是一種逆向的授予),另一類是自下而上的權力授予。自上而下的權力授予指權力來自上級,由于權力是自上而來,權力行使者會努力對授予其權力的上級負責,更多地考慮上級的意愿和要求,而不太注重社會或下級的心聲,這種政治文明形態,權力行使效率高但公平性、回應性不足。自下而上的權力授予指權力來自社會,由于權力是自下而來,權力行使者會努力對授予其權力的社會負責,更多地考慮下級的意愿和要求,而不太注重上級的意愿和想法,這種政治文明形態,權力行使的公平性、回應性高但效率不足。理想的政治文明形態應該是自上而下的授權與自下而上的授權相結合,使權力行使者既對上負責又對下負責。在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話語邏輯與制度安排中,自下而上的選舉授權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權力對下負責,提高了權力行使的科學性、公平性、透明性、回應性,但低效且難以應對危機情境的諸多問題,甚至會使其背離其宣揚的所謂自由、民主、公平的價值觀,并導致民粹主義。要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話語邏輯與實踐制度,就需要借鑒自上而下的授權優勢,將授權與去權相分離,在自下而上的選舉授權外,引入自上而下的授權方式,采用社會選舉、政黨罷免,或政黨任命、社會罷免雙向聯動的授權方式。
超越分權制衡。“根據國家中每一個人授權,他就能運用付托給他的權力與力量,通過其威懾組織大家的意志,對內謀求和平,對外互相幫助抗御外敵。國家的本質就存在于他身上。用一個定義來說,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訂立信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40]根據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公共權力的原初功能是對內謀求和平、對外抗御外敵,然而公共權力的功能與價值決不應僅限于此。除維持內部秩序與抗御外敵之外,公共權力的價值與力量還在于它可以實現“自然的叢林狀態”下無法實現的功能,而統合社會資源、多元力量以達成共同體的公共目標,正是這種力量與價值的重要體現。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分權制衡的權力結構雖然達到了使權力機構之間互相制約、防止權力濫用的目的,卻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公共權力統合資源、防止內耗的能力。與此同時,“三權分立”只是資產階級“階級統治的行政形式和議會形式之間所進行的無謂的斗爭”,“議會形式只是用行政權用以騙人的附屬物而已”,現代國家權力結構“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監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41]因此,要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形態的話語邏輯與實踐制度安排,就需要創新權力結構設計,實現分權制衡與資源整合的有機統一,一個可能路徑是在其分權制衡的權力結構之外,設置一個可以統合“三權”的力量,使新的權力結構既可以保持分權制衡的獨立性,又可統合三權、裁決分歧、“集中資源辦大事”。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系浙江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重大項目“政治文明新形態”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ZT22WT13)
注釋
[1]黑格爾:《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58~359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頁。
[3]米爾斯:《權力精英》,王崑、許榮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3頁。
[4]王滬寧:《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頁。
[5]參見M.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1984, 25(2); H. Soifer. "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8, 43(43); L. Weiss and E. Thurbon. "Power Paradox: How the Extension of US Infrastructural Power Abroad Diminishes State Capacity at Ho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8, 25(6).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頁。
[7]胡承槐:《關于國家權力來源的三種政治哲學的比較分析》,《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8]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39頁。
[9]埃爾曼·塞維斯:《國家與文明的起源》,龔辛、郭璐莎、陳力子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7頁。
[10]陳國權、黃振威:《論權力結構的轉型:從集權到制約》,《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年第3期。
[11]張康之:《公共管理倫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8頁。
[12]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卷,鄧正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4~175頁。
[13]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5、131~132頁。
[14]洛克:《政府論》下篇,瞿菊農、葉啟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9頁。
[15]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9頁。
[16]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范進、楊君游、柯錦華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212頁。
[17]哈林頓:《大洋國》,何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6~37頁。
[18][28]洛克:《政府論》,劉曉根譯,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31、124~126頁。
[19]參見潘恩:《人的權利》,田飛龍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
[20][23]參見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21]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95~396頁。
[22]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6頁。
[24]讓–馬里·科特雷、克洛德·埃梅里:《選舉制度》,張新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3頁。
[25]《孟德斯鳩文集》第1卷,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200~217頁。
[26][29]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67~168頁。
[27]田芝健:《論國家權力的現代歸屬和依法運行》,《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
[30]斯賓諾莎:《政治論》,馮炳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42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頁。
[32]馮旺舟:《艾倫·伍德“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總體批判探析——基于〈共產黨宣言〉的文本學解讀》,《國外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33]《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1頁。
[34]孫帥:《西方民主合法化“自我”與非法化“他者”的政治陷阱批判》,《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0期。
[35]T. Mann, N. Ornstein, 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36]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0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05頁。
[38]查爾斯·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觀》,何希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08頁。
[3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頁。
[40]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2頁。
[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222頁。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