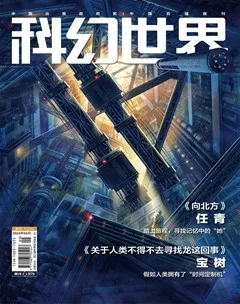韓國科幻關鍵詞:從不毛之地到黃金時代(下)
在上篇中,我們將重心放在韓國科幻領域中最為核心的科幻文學上,從“Science Fiction”的譯法談起,延伸至科幻小說的引入與本土化,以及科幻文學獎與新生代作家的互相成就。以科幻文學為中心發散開來,韓國科幻的其他領域也同樣不斷發展壯大著,一同邁向黃金時代。
幻迷活動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PC通信”(即“網絡論壇”,Computerized Bulletin Board System)流行的網絡環境下,除了以Djuna為代表的韓國科幻本土化創作風格的確立,還同時帶動了韓國幻迷活動的快速發展。眾多幻迷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網絡空間里盡情表達自己的喜好,并以這種共同喜好為基礎,在當時的“四大論壇”HiTEL、Chollian、Nownuri、Unitel成立了各種線上幻迷組織,比如Chollian的“美麗新世界”、HiTEL的“科幻小說同好會”與“SF電影研究會”、Nownuri的“SF2019”、Unitel的“SF Odyssey”等。
其中,成立于1989年的“美麗新世界”是韓國最早的論壇幻迷組織,“SF電影研究會”則是“2010果川國際科幻電影節”的前身。這些幻迷組織不僅主導著科幻讀者的活動,還會上傳一些原創科幻小說,其中人氣較高的作品則會推進線下紙質出版。同時,為了滿足眾多幻迷閱讀和收藏經典科幻作品的需求,他們發起了“直指工程”①,致力于復原那些已經絕版的科幻經典,“科幻小說自發出版團”則主要負責翻譯國外作品。
后來,這種自發的志愿活動擴大到了實體出版領域:幻迷們指責盜版科幻圖書的翻譯錯誤,通過網絡分享絕版科幻小說的內容,羅列有必要重新出版的科幻作品目錄,強烈要求出版社推進出版。在科幻作品出版之后,他們還經常對作品水準、翻譯質量等進行評判,給當時的作者和譯者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壓力。
韓國幻迷的組織內部,自然也難以避免“粉絲”(fans)群體常見的各種弊端。以科幻知識、閱讀量、活動范圍等為標準,幻迷們被劃分為“至尊”“骨灰”“中級”“入門”等,這種等級制度引發了嚴重的論爭,而且愈演愈烈,甚至波及了科幻翻譯和出版界。
科幻漫畫與動畫

看過電影《獨行月球》(2022年)的觀眾應該都會了解,本片改編自2021年引進中國的韓國同名科幻漫畫(原名Moon You)。
說到韓國科幻漫畫,由上篇提到的出版于1952年的《亨德爾博士》開始算起,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與科幻小說一樣,其發展歷程同樣受到了鄰國日本的影響。曾有學者指出,韓國科幻漫畫的主人公多數是“動作英雄”和“超級機器人”,正是被早期引進的《鐵臂阿童木》(1952年)、《鐵人28號》(1958年)、《魔神Z》(1972年)、《高達》(1979年)等日本作品帶偏。此外,美國原子彈(1945年)與美蘇太空競爭(1955年—1975年)帶來的災難恐慌,也是引導韓國科幻漫畫創作方向的時代元素之一。
奇怪的一點是,比起地球末日之類的反烏托邦(Dystopia),當時的韓國科幻漫畫似乎更加熱衷于將戰后韓國經歷的“災難恐慌”看作殖民地解放或者停戰的救援武器,并轉化為樂觀的前景展望。比如,韓國首部科幻系列漫畫《正義使者雷非》(Emissary of Justice RAYPHIE,1959年)中,最終走向滅亡的只是外來入侵者,地球人則成功克服了戰爭危機。其故事走向可謂是彼時“富國強兵”的大眾文化心理的投影。
與韓國科幻小說相比,韓國科幻漫畫至今依然未能得到學術界的眷顧,研究資料甚少,受關注程度遠不及純情漫畫等其他類型。與此相比,科幻動畫或許更加“幸運”,恰逢20世紀70年代的“動畫片時代”,韓國推出了《機器人跆拳V》(1976年)、《黃金之翼 123》(1978年)等經典之作,至今仍是一些中年人回憶童年的必選。


科幻電影與科幻文學影像化
縱觀韓國科幻電影,早年已有奉俊昊導演的《雪國列車》(改編自法國同名漫畫)享譽世界。近年來,韓國推出的原創科幻電影作品愈發增多,題材也日漸多樣化,比如太空(《勝利號》,2021年)、登月(《寂靜之海》,2021年)、永生人(《徐福》,2021年)、外星人(《外星+人》,2022年)等。
在如今技術發展與觀眾基礎已經充分具備的業界,科幻快速成長為搶手題材,尤其又有各大流媒體平臺的加持,投資人、創作者必然躍躍欲試。2020年,韓國八位電影導演聯合拍攝的科幻作品集《SF8》,在網絡平臺公開導演版本之后,又在MBC電視臺播出,實現了流媒體與傳統媒體受眾的合流。



2022年5月,韓國娛樂界巨頭CJ ENM與韓國首家創作者代理公司“盛開創意”(BLOSSOM CREATIVE)合作發起影視化IP發掘項目“未知原創”(Untold Originals),首批確定參與的四位作家中的三位(裴明勛、千先藍、金草葉)為專職科幻小說家。同時,第六屆韓國科幻文學獎(2022年)、第三屆文允成科幻文學獎(2023年)均在參賽說明中添加了與著名影視制作公司“探討影視化改編”的字句。科幻文學影像化,顯然已是業界運營常態。
盡管如此,迄今為止的業績似乎并不盡如人意。以2023年上映的備受期待之作《月球》為例,制作費高達二百八十億韓元,觀影人數卻僅為五十一萬,未及損益臨界點(六百萬人)的十分之一。此前的《外星+人》和《徐福》的觀影人次也僅有一百五十三萬和三十八萬,而這些電影由于科幻片的類型特性,制作費均在兩百億韓元以上①。對此,評論認為韓國科幻電影為了視覺效果而犧牲了電影最本質的元素——故事。
金泰勇導演的《夢境》(Wonderland)、金寶拉導演的《光譜》(改編自金草葉同名小說)、元新淵導演的《尋王》(Seeking the King)……待上映片單的持續更新,是韓國電影人依然在科幻領域不斷嘗試與挑戰的最直接表現,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中韓科幻交流前景展望
上篇提到,早在2019年,第五屆中國(成都)國際科幻大會便特別策劃了“韓國科幻文學的現在與未來”專場,邀請尹汝敬、張康明、金周永、金善民四位韓國科幻作家與中國科幻迷們面對面交流,全慧珍的短篇小說《巴蜀三萬里》還獲得了“100年后的成都”全球科幻作品征集活動“特別獎”。

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首次在中國成都順利召開,韓國科幻小說家金寶英、全慧珍、金草葉等出席了現場活動,其中以全慧珍的演講《中國古典〈三國志〉對日韓科幻的影響》最為火爆,此后演講全文刊發在《零重力報》。在大會期間進行的第34屆銀河獎頒獎典禮上,金草葉憑借短篇集《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行》獲得“最受歡迎外國作家獎”,尹汝敬獲得“中國(成都)國際科幻大會·中國科幻國際交流功勛勛章”。值得一提的是,《科幻世界》策劃的“日韓幻想文學專輯”將在近期刊發金寶英、金草葉的中短篇小說。
今年是Djuna出道三十周年,筆者在此借用他在媒體采訪中的發言結束本文:“過了三十年,世界已經完全大變樣。以前用韓文展現科幻想象力的創作既罕見又生疏,現在‘我們’已經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韓國科幻已經發展出自己的譜系,不再是小眾文學,如今創作科幻小說也不是什么‘特別’的挑戰。”或許我們可以期待,韓國科幻的其他領域也會迎來這一天。
①此名稱的靈感源于“古騰堡工程”,“直指”則取自韓國佛典古籍《佛祖直指心體要節》,簡稱《直指》。“直指工程”網站至今仍免費開放,可以閱讀幻迷們復原的各種科幻作品,詳情參見:https://sf.jikji.org/。
①《勝利號》240億,《寂靜之海》300億,《外星+人》300億,《貞伊》200億,貨幣單位皆為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