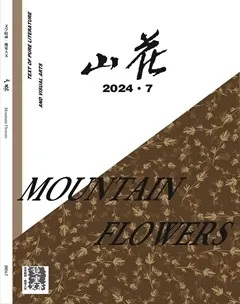熟悉而陌生的詩人
耶胡達·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舉世公認的以色列當代最偉大的詩人和20世紀最為重要的國際詩人之一,生前以母語希伯來語相繼出版了《眼下,以及別的日子》(1955)、《兩個希望之遙》(1958)、《1948—1962年詩選》(1963)、《而今在喧囂中:1963—1968年詩選》(1968)、《不是為了記憶》(1971)、《這一切后面隱藏著某種偉大的幸福》(1976)、《時間》(1978)、《偉大的安詳:紛紜的問與答》(1980)、《恩典時刻》(1983)、《你從人而來,也將歸于人》(1985)、《拳頭也曾是張開的手和手指》(1989)、《開,閉,開》(1998)等十余部詩集,此外,還創作有《并非此時,并非此地》等兩部長篇小說,以及若干短篇小說集、戲劇與兒童文學作品等。除以希伯來語寫作外,阿米亥還偶爾親力親為將作品翻譯為英文,如與著名詩人特德·休斯合譯的《阿門》(Amen)等詩集。
也正是因為特德·休斯的慧眼識珠和力薦,阿米亥得以被國際詩壇快速接納,并獲得近乎明星般的禮遇。1965年出版的《現代譯詩》第一期,特德·休斯將阿米亥的詩歌和波帕、赫伯特和沃茲涅先斯基等人的作品同期推出,并立即在英語詩壇獲得極大的關注。此后,1966年,阿米亥受邀參加當時最時髦的國際藝術節——意大利的斯波萊托國際藝術節(Spoleto Festival),這也是阿米亥首次在國際舞臺上亮相,并和奧登、龐德、金斯堡、翁加雷蒂、赫伯特以及特德·休斯等國際一流大詩人同臺朗誦詩歌。次年,阿米亥再次受邀前往倫敦,與帕斯、奧登、龐德、沃茲涅先斯基、聶魯達共同參加國際詩歌節。
耶胡達·阿米亥之于國內的讀者和詩壇,可謂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詩人。
說他“熟悉”,是因為早在三十年前,傅浩、鐘志清等人就從英語和希伯來語介紹翻譯過他的作品。這些譯作,甫一照面,皆無一例外地引起一片驚艷之聲,后續亦不乏譯者自覺參與到這一驟然間變得熱火朝天的譯介之中。
迄今為止,就成規模的譯作而言,以傅浩的翻譯數量最多,先后出版過三本阿米亥譯詩選:《耶路撒冷之歌:耶胡達·阿米亥詩選》(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耶胡達·阿米亥詩選(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噪音使整個世界靜默:阿米亥詩選》(作家出版社,2016)。此外,尚有黃福海翻譯的阿米亥的蓋棺之作,也是唯一在國內出版的單行本《開·閉·開》(Open Closed Open,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還有澳大利亞華裔詩人歐陽昱依據美國學者、翻譯家羅伯特·阿爾特(Robert Alter)編選的英譯本《耶胡達·阿米亥詩選》(The Poetry of Yehuda Amichai,2015)轉譯的作品,該譯本可謂集合了英語世界14位譯者之努力與心血,中譯本命名為《如果我忘了你,耶路撒冷:阿米亥詩集》(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但所譯并不完整,如《圖德拉最后一位便雅憫的游記》(The Travels of the Last Benjamin of Tudela)、《阿赫濟夫之詩》(Poems of Akhziv)和《阿赫濟夫》(Akhziv)等三首長詩并未收錄。
本人所依據的譯本同樣來自上述羅伯特·阿爾特所編選的英譯本《耶胡達·阿米亥詩選》。該英譯本共分11輯,從1955年的《眼下,以及別的日子》到1998年的《開,閉,開》,時間橫跨三十余年。考慮到英譯本體量龐大,為照顧中文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承受力,此次中譯本僅選譯了部分內容,約占原譯本容量的一半略多。
除成規模的譯本之外,尚有層出不窮的詩歌類或泛文學類刊物上刊載的或豐或簡的阿米亥譯作選輯,以及好事者在網絡世界拼湊的“混裝版”譯作選。
說阿米亥“陌生”,意在說明這一事實:雖然有如上逾三十年之功,數十位譯者前赴后繼地譯介,阿米亥的作品實際并未在漢語世界擺脫觀光性的欣賞層次,除了對其詩歌作品的艷羨和贊嘆之外,我們對其理解似乎未能再前進半步,更遑論其作品對當代中國詩人寫作的借鑒意義和實質性影響。對阿米亥作品普遍的熱烈反響和無力轉換之間,呈現出某種醒目的尷尬和矛盾。
這一方面自然與譯作的參差不齊和不盡如人意有關,事實上,不僅漢語世界的譯者,即便是從希伯來語直接入手翻譯的英譯者的譯作水平也同樣參差不齊。我本人則尤為鐘愛查納·布洛克(Chana Bloch)的譯筆,鐘愛其譯作的鮮活、細膩、微妙、含蓄和體貼。她先后和斯蒂芬·米切爾(Stephen Mitchell)合譯過《耶胡達·阿米亥詩選》(1996, 2013),和查納·克龍費爾德(Chana Kronfeld)合譯過阿米亥的蓋棺之作《開,閉,開》(2006)。
另一方面,則是我們通過現有漢語譯作,深入剖析阿米亥獨特的詩歌魅力和貢獻,及其對當下中國詩人寫作的啟發,不僅力有不逮,甚或理解乏力。就個人有限的翻譯經驗和對阿米亥英文譯作的理解而言,阿米亥之于中國當代詩歌界的借鑒意義尤為重大和迫切,這一意義相較20世紀80年代之后國內詩人曾熱烈追捧過的里爾克、聶魯達、希尼、奧登、布羅茨基、史蒂文斯和策蘭等詩人不僅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并非因為后面幾位不夠偉大,而是阿米亥的詩歌作品所體現出的置身于東、西文明之間,古、今傳統之間,新、舊語言之間,神圣與世俗之間的獨特處境,與當代漢語詩人的身份處境更為肖似,更讓人感同身受,并已毫無爭議地樹立起一座相似語境下的現代詩歌豐碑。
阿米亥之令人難忘,端在于其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既大開大合而又清新自然的風格,奇崛而迅忽的想象力,豐富、徹骨的比喻,深刻的思想氣質和悲憫平等的人道品質。其體驗,仿佛你讀完第一首,就迫不及待地期待第二首,讀完一部作品,就按捺不住地渴望讀完全部作品。這一沖動之不可遏止和經久不息,似乎只有青春期少男少女間魂牽夢繞的情書堪與媲美。偉大的詩作從來就不缺乏,但阿米亥的撩人之處卻獨擅勝場,即便面對任何熟視無睹的日常經驗,阿米亥也總能發現其中直擊心靈的神圣或不朽成分。在詩中,此類轉換和點金之術比比皆是,輕松自如,信手拈來,其過目不忘和震撼如同我們第一次聽說人類和果蠅的基因相似度高達61%時的那種驚愕、不可思議而又久久難以忘懷的心情。
下面,本人將根據自己對阿米亥英文譯作的有限的閱讀和翻譯,試圖指出阿米亥及其詩歌中的特異之處,以及有可能帶給當代中國詩人與詩歌愛好者的價值和啟發。
一、東西之間的心靈競賽
據說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之初,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大學生一接到參戰通知,就開始整備行囊,里面除了衣物、一把來復槍,就是一本耶胡達·阿米亥的詩集了。這一場景想必對今天的讀者而言極為陌生和罕見,因為古往今來的戰爭,從未出現過戰場上的士兵們成規模地將詩歌視作戰火中的慰藉的情況,況且,阿米亥的詩作也并非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的政府配給品。而詩中的文字,并未理直氣壯地叫囂著要殺死敵人,甚至從不會為殺戮與死亡提供哪怕最簡單的鎮靜劑。
要解釋這一令人倍感驚奇的場景,恐怕要訴諸阿米亥作品中對于在東西之間流浪千年、無以為家的猶太人普遍心路歷程的刻骨銘心的表白。阿米亥曾借12世紀的猶太詩人耶胡達·哈勒維之口說起猶太人在上千年的漂泊流亡中心靈和身份之間永恒的撕扯:
“我的心在東方,卻居于極西之地”
那是猶太人的歷程,那是猶太人在東西間的心靈競賽,
自我與心靈之間,往與來之間,往而不來,來而不往,
逃亡者和無罪的流浪者之間。一場無盡的旅途,
……在身與心,在
心與心之間徘徊,死就死在兩者之間。
——《猶太人的歷程:變化即上帝,死亡乃先知》
詩人假借耶胡達·哈勒維的心靈嘆息和悲泣,剖白出猶太人在東西文明之間、身心之間獨一無二的疏離感,而且這一疏離感并不會因死亡而壽終正寢,相反,他們的死不過是這一疏離感的小小的路標,供后來者的靈魂在更加浩茫的疏離的荒漠中辨認漫無目的的前程。
歷史上,從公元70年第二圣殿——猶太人的信仰搖籃——被羅馬軍隊搗毀,到公元135年,猶太人被迫開始大規模地海外流散,從此,這一亞伯拉罕系三大宗教最早的源頭——猶太教的子民們,這一地處西亞、被近代的歐洲中心主義者稱為“近東”的民族和宗教同一的特殊群體開始了近兩千年的漂泊和苦難之旅,其客居之地以歐洲為主,但在歐洲土地上的幾乎所有王朝、國家、時代,猶太人總是因其異質性的文化和信仰身份而備受歧視與迫害,直至“二戰”時期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形式將其推向極致的絕境:
他們的心在東方
他們的身體在西方的盡頭。他們的身體在西方,他們的
心在東方,
就像候鳥一樣,失去了夏天和冬天,
失去了起點和終點,他們飛來飛去
日復一日,直至傷痕累累。
——《這片土地懂得》
與在地理上的東西間備受流離之苦平行展開的,則是在身份認同的東西之間備受摧折撕扯的心靈之痛。即便像阿米亥這樣,出生在“二戰”時的德國,青年時期(1936年)返回巴勒斯坦參加英軍的猶太人支隊,后參加以色列獨立建國,從表面上來看,似乎要比他的父輩以及過去兩千年的先祖們幸運得多,但這一幸運,也僅僅限于表面。就地緣政治層面而言,建國后的猶太人似乎擁有了合法獨立的國際政治地位,但是他們內心卻早已結出一個碩大無朋的疤,這一疤痕由歷經兩千年的漂泊流亡累積而成,即便他們的身體停止了流浪,但他們的心仍在隱隱作痛,就像風停時,掛在籬笆上的空蕩蕩的塑料袋,因為風還會再起,永無止息,雖然那風是從過去吹來的:
耶路撒冷滿是用舊的猶太人,因歷史而疲憊不堪,
猶太人,二手,有輕微破損,議價出售。
并且世世代代眼望錫安。所有生者和死者
的眼睛全都像雞蛋一樣被磕破在
這只碗的邊緣,
……
耶路撒冷會需要什么呢?它不需要一位市長,
它需要一位馬戲團的馴獸師,手持長鞭,
能夠馴服預言,訓練先知急速奔跑
在一個圈子里繞啊繞,教會全城的石頭排成隊
以一種大膽、冒險的形式結束最后的宏偉樂章。
稍后他們會跳回原地
迎著掌聲和戰爭的吵嚷。
然后眼望錫安,哭泣。
——《耶路撒冷滿是用舊的猶太人》
因此之故,阿米亥將現代的猶太人,即他自己親自參與建立的以色列國的猶太人,稱為亞伯拉罕的第三個“虛構”的兒子以弗吉(Yivkeh,“神哭泣”之意)的后裔:
亞伯拉罕有三個兒子,不僅僅是兩個,
亞伯拉罕有三個兒子:以實瑪利、以撒和以弗吉。
以實瑪利第一個出生,是為“神聽見”,
以撒接踵而來,是為“神歡喜”,
以弗吉最后出生,是為“神哭泣”。
沒人聽說過以弗吉,因他最年幼,
是天父最鐘愛的兒子,
是在摩利亞山上被獻祭的兒子。
以實瑪利被母親夏甲所救,
以撒被天使所救,
但卻無人向以弗吉伸出援手。
……
《妥拉》上說是公羊,其實是以弗吉。
——《〈圣經〉與你 ,〈圣經〉與你及經文別解》
按照猶太人《圣經》的記載,“以實瑪利”系亞伯拉罕和婢女夏甲所生,乃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撒乃亞伯拉罕的嫡子,為猶太人的祖先;以弗吉作為虛構者,實則以《圣經》中“以撒獻祭”中的公羊為原型,因這公羊代人受罪,沉默不語,任人宰割,活脫脫近兩千年來備受流亡迫害之苦的猶太人的形象,與《圣經》中所記載的為耶和華所寵愛的猶太人,即以撒的后裔的形象大相徑庭。但是,阿米亥卻執意要為這沉默的替罪“公羊”翻案,為沉默者獻上贊歌,在共謀者——上帝、天使、亞伯拉罕、以撒——全都離場的空空如也的歷史舞臺上,他的詩作乃備受侮辱者的沉默的遺照:
《以撒的捆綁》中真正的英雄是公羊,
他對他人的共謀一無所知。
他是心甘情愿代替以撒去受死。
……
我想留下最后一幀鏡頭
猶如登在某個優雅的時尚雜志上的照片:
皮膚棕褐,養尊處優的年輕人,身穿花哨的套裝,
近旁是天使,身著出席正式招待會的盛裝,
……
在他們身后,那只公羊,猶如一道彩色的背景,
身陷屠宰前的灌木叢中,
灌木叢是他最后的朋友。
天使回家了。
以撒回家了。
亞伯拉罕和上帝早已沒了蹤影。
但是,《以撒的捆綁》中真正的英雄
是那只公羊。
——《真正的英雄》
二、時間,拯救的藝術
阿米亥將時間視為其詩歌創作中最重要的維度。如果說,在古代世界當中,無論東西,時間是圓形的,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那么,在基督教中,時間則是線性的,有著明確的起點、高潮和終點。而阿米亥的時間,則是既相對,又彼此關聯和相互指涉的,他稱之為“比較時間”,即一種“相對”的時間,譬如過去的時間相對于現在或未來的時間,個人的時間與公共的時間,譬如圓形時間之于方形時間等,它們互為對照,如影隨形,卻又彼此獨立,相互見證:
圓形時間和方形時間
以同樣的速度行進,
但它們經過時的聲音是不同的。
——《證據》
這一流淌在阿米亥作品血液中的時間源于猶太人特有的時間感,源于猶太教的圣書傳統。猶太《圣經》曾謂:《圣經》中的一切無所謂先后。事實上,這也是某種上帝(耶和華)視角的時間,一切的時間,無論過去、未來,皆為現在,皆匯聚于當下,因而也是永在的。
那位名聞遐邇的法國國王說過:洪水,去我身后!
義人挪亞說過:洪水,走上前來!
當他離開方舟時,他宣布道:洪水在我身后。
但我卻要說,我置身洪水中央,
我是方舟與活物,既潔凈又不潔凈,
我是一個物種的兩面,既雄既雌,
我是記憶的活物,又是遺忘的活物,
……
——《〈圣經〉與你 ,〈圣經〉與你及經文別解》
基于這一猶如置身洪水中央的時間感,阿米亥作品中的時間便成了同時經受著過去與未來,身前與身后沖刷的時間,是在記憶和遺忘的旋渦中起伏的時間,是多聲部、多維度、平行、復合,可隨意組合,即時拼貼的時間。用阿米亥自己的話說,他能夠撿拾出“生命中的任何一刻并幾乎身臨其境”:
哈馬迪亞,快樂的記憶。四十年代
和打谷場上的愛情。時至今日
秕糠甚至還令我刺癢不已,盡管我的身體
反復清洗,我的衣服
換了一茬又一茬,而姑娘還是在
五十年代離去,在六十年代消失,在七十年代
徹底銷聲匿跡——時至今日
秕糠甚至還令我刺癢不已,
我的喉嚨因不厭其煩的吶喊而嘶啞:
請你再次回到我的身邊
回到我身邊,回來吧,時光,回來吧,枇杷樹!
——《哈馬迪亞》
正如阿米亥所言,在希伯來《圣經》中,將來時甚至被用來描述過去的時間,這一點同樣在上述所引述的片段中有所體現:“我的衣服/換了一茬又一茬,而姑娘還是在/五十年代離去,在六十年代消失,在七十年代/徹底銷聲匿跡”。
通過作品中對于時間的重構,阿米亥詩歌緊緊抓住了所有失去的事物,詩歌因此為不可逆的過去賦予了通向未來的可能。就此而言,詩歌乃事關拯救的藝術:
好吧,別再蓋房子,別再修路了!
就讓我們造一座疊在內心的房子,
修一條繞在靈魂深處線軸上的路。
這樣我們就不會死,永遠不會。
……
在孤獨的盲目中,他們在兩腿間,
在白晝和黑夜的交替中相互觸摸。
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時間,
沒有別的處所,而先知們
早已壽終正寢。
——《時間:1》
經由詩歌,自我和記憶盡管被歲月反復淘洗,但仍能自由穿梭,抵擋時間的碾壓,從而獲得拯救:
我生于1924年。當我想起人類,
我只明白和我一樣的同齡人,
他們的媽媽和我的媽媽一同分娩
無論是在醫院,還是在暗室。
……
但愿你能發現持久的安寧,
活人在活著的世界里,死人
在死去的世界里。
誰對童年的記憶最真切
誰就是贏家,
倘若真有什么贏家。
——《1924》
詩歌賦予了記憶減輕時間重壓的緩釋閥的功能,同時,它也是流逝而無常的歲月中的標志物,猶如打撈沉船之地水面上的浮標。在記憶的航道上,詩人即便會因超載而遭受沉船的危險,但作為詞語之船的船長,他卻不會中途跳船而遁,注定與沉船同歸于盡:
在我停止生長之后,
我的大腦便不再生長,而記憶
就在身體里擱淺了
我不得不設想它們現在在我的腹部、
我的大腿和小腿上。一部活動檔案、
有序的無序,一個壓沉超載船只的
貨艙。
……
詞語已開始離棄我
就像老鼠離棄一艘沉船。
最后的詞語是船長。
——《最后的詞語是船長》
如果說記憶是有待閉合的敞開,那么,遺忘則是有待敞開的閉合。在遺忘的膠囊的中心,記憶借助詩歌的文字之光得以永存。只有經歷過萬劫不復的痛苦的人,才會以這種方式保存記憶,被遺忘拱衛的記憶:
而誰還會記得?你又用什么來保存記憶?
你如何保存這世上的一切?
你用鹽保存,用糖、高溫和深度冷凍
真空封口機、脫水、制成木乃伊來保存。
但是,保存記憶的最好方式是將它存放在遺忘中
這樣,甚至一絲一毫的記憶都不會滲入
打擾記憶永恒的安息。
——《而誰將紀念紀念者?》
三、神圣和世俗交戰的語言
阿米亥的詩歌系現代希伯來語詩歌的第三代,即詩人在以色列建國前后進入成年階段,參加過獨立戰爭,他們又被稱為“獨立戰爭的一代”或“解放一代”,代表詩人有阿米亥、拿單·扎赫(1930- )、大衛·阿維丹(1934-1995)等,多以現代希伯來語為母語進行寫作,且更加注重口語的運用和表達,其詩歌寫作技巧和風格更多受到英美現當代詩歌的影響。與前兩代詩人相比,他們不再乞靈于猶太教法典文體的傳統典雅風格,并且免除了“兩個祖國”所帶來的文化撕裂,他們的觀察經驗和表達興趣更多地來自對日常生活的反思。作為一門新生的語言,現代希伯來語,尤其是現代希伯來口語,可供阿米亥進行創作的資源并不豐富,但卻給予了他拓展全新的、未知疆域的自由。一方面,他不得不,但又是自覺地從希伯來《圣經》等古典文本,這些作為傳家寶的語言地毯上拆下絲線,以便二次使用。脫離了舊有的紋路、編織圖案的羈絆的語言絲線,經過詩人的巧妙編織,煥發出新鮮的、奇幻般的、耳目一新的,同時又與舊有的使用痕跡形成鮮明張力的特征。另一方面,阿米亥又在尚未展現出封閉地平線的現代希伯來口語的廣袤之地上,閃展騰挪,別出心裁地創造出諸多前所未有的新詞——如根據“海平面”仿造的新詞“臉平面”(face level):“我就像一個站在/約旦沙漠里的人,盯著某個標志:/‘海平面。’/他看不見大海,但他知道。//因此,無論在哪兒,我都會記得你的臉/根據你的‘臉平面’。”(《曾經的摯愛》);如根據“狂犬病”所仿造的新詞“狂海病”(seabies):“在瀕臨大海的地方破碎。/挽歌,我的巢穴之歌。/巖礁嘴唇上的泡沫。/大海有狂犬病,/它有狂海病。”(《阿赫濟夫之詩:1》)。諸如此類的別出心裁,完全印證了他的自我評價:“我幾乎從一開始寫詩起就是后現代式的。”
與作為正統、保守而虔誠的猶太教徒的父輩不同,阿米亥生活在一個相對富裕、物質主義、世俗化的社會中,在很多時候,他是以一個世俗主義者,甚至是無神論者的身份在寫作,因此,與前輩或者正統派的猶太教徒相比,存在之于阿米亥,并無源自傳統信仰層面的現成答案,他必得在詩歌中重新尋找答案,或通過詩歌為生存尋求新的基礎。在此意義上,他所面臨的存在的意義問題,和萊奧帕爾迪、歐洲頹廢派、蒙塔萊、現代英美詩人并無不同。
然而,經由我胸前的傷口
上帝向宇宙張望。
我是通向
他公寓的門
——《伊本·蓋比魯勒》
但是,另一方面,詩人和上帝的關系又是復雜的,他需要上帝作為不負責任的代言人為世界的不幸、猶太人的苦難買單,“詩人無法將現實世界不可預測的暴力、不道德和不確定(如先知和拉比所做的)歸咎于人類的邪惡以及未能創造一個以真理和正義為基礎的社會,也無法擺脫他全能的童年上帝。也許正是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讓詩人的信仰支離破碎,而上帝就像一個木偶,潛逃在外,漠不關心,心懷愧疚,他不愿相信上帝,但也無法完全擺脫上帝。詩人通過這個微不足道的上帝,就像模仿先知的腹語一樣,抒發自己的苦悶和痛苦”。為此,他在面對上帝時,就像當初摩西面對上帝時一樣,不失時機地向上帝高聲抗辯,或者將上帝視作置身事外的無能為力者:
在不相信的情況下喊著“上帝”
即使我相信他
我也不會告訴他戰爭的事
就像人們不給孩子講大人的恐怖故事。
——《我在戰爭中學會了》
也的確有評論者認為,阿米亥的詩歌是“與全能者的一次不朽的爭論”(約翰·科恩語)。唯有借助這種爭論,阿米亥才能表達自己對于母語、祖先的宗教和苦難、紛爭那種基于反諷、悖論風格的復雜情感:
現在就用這疲倦的語言說吧,
一門從圣經的睡夢中撕裂的語言:眩暈著,
從一張嘴晃到另一張嘴……
——《民族思想》
事實上,給猶太人和世人設計命運的上帝,乃同一個設計師——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但更多的時候,上帝卻并沒有讓詩人感到內心愉悅,而是加重了記憶的負累,撕扯著詩人的心靈:
猶太人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
像兩塊碾子,將我碾磨,有時
碾成齏粉
——《我不是六百萬分之一:我壽命幾何?開、閉、開》
因此,在屢屢感覺陷入絕境的詩人那里,上帝其實是退場和消隱的,猶如他一貫的袖手旁觀,因此救贖需要自己發明宗教,而對詩人來說,這唯一的宗教乃是詩歌,它讓非對象化的、真正的宗教性得以在文字中現身,一種無信仰對象的宗教,一種超越世界的世界觀:
一位阿拉伯牧羊人正在錫安山上尋找他的山羊,
而在對面的山上,我正尋找
我的小兒子。
一位阿拉伯牧羊人和一位猶太父親
雙雙陷入暫時的潰敗。
……
之后,我們在灌木叢中找到了他們
我們的聲音又回到了我們的體內,又是笑,又是哭。
尋找山羊或兒子
一直以來都是這群山中
某種新宗教的開端。
——《一位阿拉伯牧羊人正在錫安山上尋找他的山羊》
四、戰爭的毀滅與愛的悲憫
阿米亥的詩歌中充滿著大量的愛情詩,特德·休斯干脆認為這恐怕是阿米亥詩歌最重要的題材:“幾乎他所有的詩作都是披著這樣或那樣偽裝的愛情詩……在以戰爭、政治和宗教的詞語寫他最隱私的愛情苦痛的同時,他不可避免地要以他最隱私的愛情苦痛的詞語寫戰爭、政治和宗教。”
的確,阿米亥的詩歌中,有相當的比例在寫愛情的苦悶、婚姻、單相思、對女性之美的艷羨。但如果僅僅以愛情一言以蔽之,則過于狹隘了,毋寧說,他是以愛情來象征愛的極致狀態,因此,特德·休斯才不無機敏地指出,他的愛情詩乃是“偽裝”的,因為愛情展現了陌生的兩性之間最迷人的吸引,因此它也成為了對現實當中戰爭、爭斗、混亂、殺戮的反向抗議。如果說戰爭是被禁止的愛,是毀滅的藝術,那么,愛則是生命力最充沛的張揚,是和平的藝術,孕育生命可能的藝術。
被禁止的愛
和戰斗,有時,就是雙雙這樣結束的。
但最重要的是,我學會了偽裝的智慧
——《在戰爭中我學會了》
從以色列建國開始,巴以沖突便成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經久不息的不幸的底色。戰爭和沖突成了現實無孔不入的裂縫,有時,這裂縫是隱蔽的,不易覺察,善于偽裝,它往往以和平的外觀、“愛的禮物”的假象出現。愛和毀滅像是一把雙刃劍的兩個刃口,愛與傷害、傷害與愛相互假借助對方的嗓子發出聲音,咫尺相對:
兩廂廝守時
我們就像一把稱手的剪刀。
待我們一拍兩散,重又
化作兩把利刃
扎進世界的肉里
各就各位。
——《愛與痛苦之歌》
這種“兩廂廝守”的兩性間的愛,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變幻莫測的愛,有時也是以色列人和比鄰而居的巴勒斯坦人之間愛恨情仇的隱喻,并且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提心吊膽的、家常便飯般的組成部分:
耶路撒冷是一座晃動著我的搖籃城。
每當我在正午時分醒來,就會有事發生在我的身上,
對有的人來說,就像最后一次從他心愛之人屋子的
樓梯上走下,而雙眼依然緊閉。
然而,我的日子迫使我睜大眼睛
記住每一個擦肩而過的人:或許
他會愛我,或許他會埋下一個炸彈
裹以漂亮的包裝,像一件愛的禮物。
——《時間:52》
戰爭狀態即無處不在的“恨”,“恨”讓“愛”受傷,因此,若要懷揣著愛的希望安然長存,則需要為愛建立某種保護機制,猶如戰場上為搶救傷員所預備的止血帶、藥棉、消毒器具等:
他們用可怕的戰爭智慧告訴我,要我
把急救繃帶纏在心上
纏在那顆仍然愛著她的愚蠢的心上
纏在那顆健忘的聰明的心上。
——《如他們昔日所言,歷史之翼的沙沙聲》
所有的悲悼都來自愛的失去,這愛不僅僅為戀人或情人所專有,也包括那些在戰爭和殺戮中犧牲和毀滅的至親骨肉:
我們的悲悼該是什么樣子?大衛如是悲悼掃羅和約拿單:
“迅捷敏于鷹隼,強健勝于雄獅,”我們的悲悼
該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們真的比鷹隼更迅捷
他們該翱翔于戰爭的上空
免于受到傷害。從下方,我們該會
看到他們
說:“那里有老鷹飛過!那是我的兒子,我的丈夫,
我的兄弟。”
如果他們確實比獅子還強健
他們就會像獅子一樣活著,而不會像人類一般死去。
他們該會從我們手上進食,
我們會撫摸他們金色的鬃毛,
我們會在家里馴養他們,用愛:
我的兒子,我的丈夫,我的兄弟,我的丈夫,我的兒子。
——《而誰將紀念紀念者?》
當傷害成為歷史的負擔,成為日常,成為生活的定義的一部分的時候,愛就被賦予了特別的含義,它必得被強化為某種宗教、某種信念、某個定律,如同自然律和良知一般,只有毫無顧忌、不知羞恥、勇敢而無畏地喊出愛的定律,詩歌才能免于蒼白,詩人才能鼓勵世人和自己一樣獲得自我拯救:
因為愛必須言明,而非耳語,這樣才能讓人
親眼所見,親耳所聽。它必須除去偽裝,
顯眼、咋呼,如同聒噪的笑聲。
它必須是“多結果子,生養眾多”的媚俗廣告:
神氣活現、令人驚艷的“多結果子”,鋒芒畢露、受盡折磨的“生養眾多”之于人類
這個物種——不過是涂在苦澀生活表面的糖霜。
愛是文字和花朵,是勾引著昆蟲和蝴蝶的
田野里的花朵,也是女人衣裙上的碎花圖案。
大腿內側柔嫩的肌膚,靈魂
最私密的內衣,張揚到天上的風衣,是公共關系,
將地球上的人類拽向大地,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
和神性輕浮的定律。哈利路亞。
——《秋日,愛,商業廣告》
五、結語
縱觀整個20世紀,將東方的智慧、傳統、文明和西方現代詩歌的語言技巧和形式完美地融為一體的典范,除了泰戈爾,恐怕就數耶胡達·阿米亥了,而從對人類現代經驗更為嫻熟、全面、深刻的介入和揭示而言,阿米亥無疑更勝一籌。
從觸及人性的深度和智慧來看,阿米亥的詩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被稱為現代人的“圣經”,只不過這是一種無神論式的對至高存在的沉思,是對愛歇斯底里的、悲憫而反諷的謳歌,是擁抱此世的末世論,是卑微地和普通人的悲喜經驗短兵相接、生死與共的糾纏。他憑一己之力將生命的本質上升到悖論的高度,就此而言,仍在東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古代詩歌經典和現代白話文創作之間、世俗與超越之間苦苦掙扎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的中國詩人,除了阿米亥,實在沒有更近在咫尺的反躬自省的尺度和楷模。
最后,謹以此譯本送給我的二女兒小愚。她的出生,讓我明白“意外”如何豐富著生命以及我們對生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