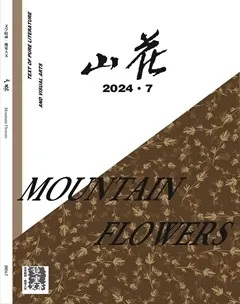關于從貴州土紙開始的藝術探索
造紙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自東漢蔡倫發明至今已逾千載,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承載了中國文化審美精神。隨著科技的發展,時代的進步,造紙工藝也隨之不斷改變。值得一提的是,貴州安順牛蹄關村的土紙至今仍完好保存著古法造紙作坊和工序,在徐悲鴻、傅抱石等藝術大家的親身實踐并極力推崇下,貴州土紙為越來越多的人了解與青睞,如今已被外界譽為東方文明古法造紙的“活化石”。
為緬懷和紀念徐悲鴻先生在中國美術發展進程中作出的積極貢獻,回顧其藝術風采,進一步挖掘貴州土紙對新時期藝術拓展的價值,讓這一貴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用藝術賦能鄉村振興,徐悲鴻紀念館、中國美術館、中國國家畫院、貴州省文化和旅游廳聯合主辦,貴州美術館承辦的2023年度國家藝術基金支持項目,從“徐悲鴻的貴州土紙”開始的一系列展覽活動于2023年8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啟幕,經南京、重慶進行巡回展覽,于2024年5月在貴州美術館完滿結束。
此次展覽的作品載體均是來自安順牛蹄關村的土紙。土紙以其獨特的材質和制作工藝,引起了大眾的關注和喜愛。它不僅有著貴州山區自然的質感和色彩,被賦予了山區獨特的韻味,還有當地濃郁的文化氣息,體現出貴州人民對傳統工藝的執著,也展示了他們精湛的技藝。《天工開物》中曾記載了造皮紙的工藝:“凡紙質用楮樹(一名轂樹)皮與桑穰、芙蓉膜等諸物者為皮紙”。[1]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蜀人以麻、閩人以嫩竹……楚人以楮為紙”。楮樹又稱構樹,是當地一種樹的品種,其樹皮平滑,韌性極強,不易裂開,材質潔白,非常適合作為造紙的原材料。而且楮樹在貴州境內廣泛分布,生長快,適應性強。古法造紙工藝相對復雜,從原材料采集到制作成白皮紙,大致要經過十七道工序流程,原材料和工具均就地取材,基本以家庭式作業為主。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古法造紙在技術上得到了進一步優化,但其工藝一直傳承延續至今。
如今,貴州土紙再次與藝術碰撞,不僅是傳承非遺技藝,也為藝術創作賦予了更多可能。為了更好地呈現貴州土紙在形式、內涵、審美等各個方面的豐富表現力和包容性,展現貴州土紙的特色及多樣性,探索土紙藝術的多種可能性,此次展覽先后特別邀請了來自國畫、油畫、版畫、雕塑、綜合材料等不同專業的美術名家二百六十余位,走進安順牛蹄關村的土紙制作現場,近距離體驗土紙制作工藝及流程。貴州土紙品種很多,其傳承與江南傳統古紙不同,更原始粗放、更生態多姿。正如徐悲鴻所贊,此紙“吸墨力強,堅韌綿扎,細膩白澤,折不起皺紋,畫與紙相得益彰”。徐悲鴻當年充分挖掘貴州土紙的特性,不但“適于重筆的揮灑暈染,而且受墨蒼潤沈著,能夠獲得宣紙繪畫所不能獲得的卓異效果”,他三次在貴陽舉辦大型個人畫展,用貴州土紙畫了很多水墨作品,僅贈送貴陽友人就有五十多件,并對自己學生宗其香用貴州土紙作畫取得的藝術突破大加推重:“宗其香用貴州土紙,用中國畫筆墨作重慶夜景燈光明滅……突破古人的表現方法,此為中國畫的一大創舉。”
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上,我們看到了徐悲鴻在貴州繪畫時的原作,其作品內容極其豐富,涵蓋了人物、山水、花鳥等題材,可見他對貴州土紙青睞有加。其妻子廖靜文曾言:“此后,先生若畫一百匹馬,有九十九匹馬是從貴州土紙上奔出的。”徐悲鴻、傅抱石等藝術大師用貴州土紙作畫,是他們當年從美術媒材角度對藝術創作的勇敢嘗試和創新。
一些當代藝術家受徐悲鴻貴州土紙的創作影響,以貴州土紙為載體進行創作。他們將貴州土紙作為藝術創作的基礎,其實踐形態多種多樣,作品不再滿足于對紙媒承載作品的單一表達,而是嘗試重塑貴州土紙的社會價值與當代生活及藝術的表達,引發藝術界對于傳統手工藝如何面對材料表征和邊界、如何平衡技術與藝術的關系、如何貼近時代審美與功能的深度思考,從而打破對貴州土紙的傳統認知與思維定式。
其中,石向東作品《貴州山水》就以三維立體的藝術形式呈現出來。藝術家們可以從做紙開始,涵蓋廣泛的材料和工藝進行創作,將其塑造為二維或三維的藝術表現形式。在制作貴州土紙的過程中,可將自然植物如棉、麻、棕、草、果實和葉子等放入藝術創作中,這些具有可辨識度的植物形態,可以傳達藝術家不同的思想和情感,也能賦予藝術作品獨特的觸感和質感。正如中國美協民族美術藝術委員會副主任、貴州省美協原主席諶宏微介紹的:“貴州土紙,或者說我們安順牛蹄關的土紙,也就是徐悲鴻的貴州土紙,它其實和我們繪畫里面經常用到的中國宣紙不一樣,更粗獷,更‘草根’,但恰恰對于一個藝術家的創造性來說,它是一個新的元素,新的可擴展的一個空間。這次活動通過所有的藝術家,全國的和貴州知名美術家的體驗,來達到一種中國美術所倡導的創新精神,來挖掘一些新的貴州土紙的藝術表現力。”
讓藝術家們體驗古法造紙,與非遺繼承人交流、互動、合作,借助古法紙漿原料、輔料的藝術延展可能性,用新思考、新理念闡釋并激活這一古老的、有豐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傳承,使其內在精神在紙媒介的外在形態上不斷外延和創新。一方面他們展現了傳統語境通過貴州土紙,在作品中的延續與多樣表達,體現出了藝術家從對自然萬物的豐富表達到對個人藝術面貌當代轉換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由他們通過對不同媒介材料與藝術形式、樣式,包括平面、立體、多維空間樣態表達的探索,呈現紙媒材藝術多樣性探索的邊界和可能性。這也是徐悲鴻先生倡導從貴州土紙開始中國畫創新的藝術理念在當代的延伸。此次活動或許可以看作是古法造紙與當代藝術表現的一次碰撞融合,也是貴州土紙這一具有豐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傳承與時代精神的一次對話交流。
另外,此次活動吸引了全國不同專業的創作者,包括“紙媒藝術家”,形成了一批貴州土紙的創作群體。他們的作品不僅呈現了徐悲鴻倡導的通過貴州土紙在藝術上的探索和創新,也展示出當代藝術家筆下生動的貴州印象、貴州特色、貴州故事,還包含了當代藝術家們對貴州傳統造紙技藝的參與和支持,彰顯了藝術家們共同推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共同助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振興的時代擔當。
注釋:
[1]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