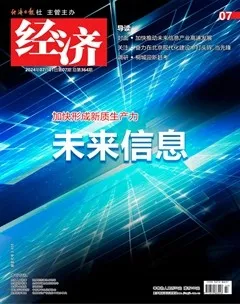亞洲金融危機與美國次貸危機比較分析
金融危機具有隱藏性、廣泛性、傳播性和爆發性,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了解歷次風險的機制和規律,從中總結經驗教訓,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固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通過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比較研究,分析了經濟危機形成的深層次成因,并以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為例,分析了金融機構在風險中的角色,對我國應對全球化風險的方略進行了探討。
兩次金融危機的相同點
一是金融危機的形成歸咎于實際的經濟狀態。這種狀態的變化會對資源配置造成影響,并使得各種資源錯配,進而導致各種資源的耗費。無論亞洲金融危機還是美國政府次級債務危機,它們都源于這一狀態,即實際的經濟效率降低,產業的變革落后,沒有足夠的新的收入來源。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結構、技術水準、政策環境的差距導致的,這些因素使得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國際貿易、投資、技術、政治等領域的不對稱愈加明顯,進而引發了亞洲區域性的金融動蕩。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是美聯儲的放松貨幣政策,這種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日益增長的消費與投資欲望,進而引發了債務的迅速增長,同時,由于金融機構的過度創新,信貸資產被證券化,層層嵌套轉移金融衍生品的風險,引發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經濟衰退。
二是宏觀經濟政策失誤。亞洲金融危機是在東南亞國家經濟較快發展的表象下爆發的,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國際資本的迅速大量流入,東南亞國家為了吸引外資,在固定匯率制的同時,擴大了外匯市場的過度投機,金融炒家短期大規模的外幣兌換引起了東南亞多個國家匯率無法維持與美元掛鉤匯率機制,引起危機的爆發。美國次貸危機主要是由于2000年互聯網泡沫崩潰造成的,美聯儲在之后一直實行低利率政策,但在2004年,由于美國的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通脹明顯,美聯儲決定再次啟用新一輪的低利率政策。這一輪的低利率政策的實施導致了流動性的過剩,以及更寬松的監管措施,這些因素導致大量的投資者涌入股票市場和住宅投資領域,進而導致股價和住宅投資的增長,并造成了資產泡沫的形成。當信貸膨脹超出預期,資產價格暴漲,加劇家庭、企業以及其他行動主體的融資壓力,從而降低了他們的收入,導致信用失衡,引起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如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波動、債務違約等,這些因素共同構建了一個復雜的、持續的、災難性的金融和實體經濟的惡性循環。
三是經濟發展模式存在缺陷。亞洲金融危機很多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體制不完善、資本未充分競爭的情況下,過度開放外匯市場,在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下,東南亞多數國家存在貿易剪刀差,導致了國際收支不平衡,經濟增速往往依靠外債來支撐,透支性經濟增長模式加上不良資產的擴張,成為爆發經濟危機的主因,而國際游資的炒作成為了巨大誘因。美國經濟危機實質也是一種負債式經濟發展模式,次級債的大量發行,使經濟狀況一般的負債人無法在經濟下行時抵御資產貶值的沖擊,最終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進而影響信用體系的崩塌。
四是以風險交叉共振為主要特征。亞洲金融危機是國際游資在外匯市場不斷沖擊泰銖,導致引起泰國本國貨幣擠兌進而蔓延至整個亞洲,這體現出金融市場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交叉共振的特征。美國金融危機是房地產市場繁榮的情況下,金融機構通過ABS等資產證券化轉化成金融衍生品將風險傳導給資本市場,本質上也是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交叉共振的特征。
兩次金融危機的不同點
一是兩次金融危機的性質不同。亞洲金融危機是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擠兌,東南亞國家采取的外匯政策是固定制匯率下的自由外匯投機,外匯投機者在市場上以做空形式套利,加之監管的不完善,出現了擠兌風險,在外匯儲備不足的情況下,本國貨幣遭受重大沖擊,從而引起了匯率的貶值,造成了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金融危機是信貸政策導致的連環交叉風險傳導,而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機構充當了風險傳導的中樞,通過過度的金融衍生品創新,將風險傳導至資本市場,導致了美國金融市場大量金融機構破產。
二是兩次金融危機波及范圍不同。亞洲金融危機是對亞洲開放的市場環境和金融市場漏洞產生的沖擊,具有隨機性和可控性。美國次貸危機范圍則波及全球實體經濟,是金融系統性風險造成的實體經濟的沖擊和倒退,隨之帶來的政治經濟問題,影響深遠。
三是兩次金融危機傳播方式有所差異。亞洲金融危機傳播途徑主要依靠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即將低端的農副產品轉換成發達國家工業產品,從而實現國民經濟增長,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的國民經濟結構的失調,使整個地區國民經濟萎縮。由于國際游資炒作、監管缺失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而美國次貸危機本質是國際資本流動作為傳播渠道,經濟危機的爆發往往伴隨著過度活躍的創新,美國在資本市場的投資組合創新,將信貸市場風險分散至資本市場,通過國際資本流動波及全球,對“大而不倒”的經濟體過度依賴,間接造成了全球經濟的衰退。
四是兩次金融危機應對措施不同。一些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采取了多種有效的防范手段,例如日本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利用公共資源來幫助日本企業處理債務。在美國經歷過次貸危機之后,美國不僅繼續實行傳統的聯邦基金利率和再融資利率下限,而且也采取了多項全面的金融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對金融市場的改革,例如實行更加靈活的融資模式。
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中的重要作用
2004年到2006年,是美國次貸危機泡沫形成期。美國早期的債務周期使得債務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大量的債務被轉移到實體經濟,從而推動了美國經濟的迅猛發展。經濟增速達到3%至4%,失業率低于長期平均水平,達到4%至5%。聯邦政府的利率從2004年的1%大幅上升至2006年的5%,而標普500指數的回報率達到了35%,與盈利增長率接近,表明經濟保持穩定,資產價格的波動性也極小。
這3年之間,房屋價格上漲了30%,相比2000年上漲了80%。次貸群體的債務比率迅速攀升,2005年的房屋貸款與房地產投資總量超過5000億美元,相較于1998年的數量翻倍,這一數字也使美國的GDP總量提升至300%。隨著貸款利率的降低,房地產市場的波動也會更大。由于投機客的大量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漲幅迅猛。
在這段時期,美國經濟出現了泡沫化特征,存款利率持續下降,大量海外投資者涌入美國。美國制造業的就業率也隨之下降,導致美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上失去了很多份額。然而,房地產行業的泡沫化也導致了一輪經濟景氣周期的到來。隨著建筑行業的就業機會增多,出口的衰退也得到了緩解。海外資金的涌入也促進了消費的加杠桿,但是,過度的借貸卻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收入增長。當債務到期時,出現現金流問題。“影子銀行”肆無忌憚地打包次貸產品進行衍生品創新,以此來分散風險,但這也最終引發了一系列危機。
可見,促使泡沫形成的不僅是低利率水平,還有寬松的信貸政策、缺乏監管、過度的金融創新等因素。金融機構充當放款人角色,借款人和放款人存在資產債務錯配,在下行周期中,矛盾就會凸顯出來。同時,資產證券化將風險隱藏并轉移至二級市場,此時影子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將住房按揭打包成多種金融創新產品,如抵押貸款證券(MBS)、債務擔保證券(CDO)、信用違約互換(CDS)等。影子銀行承擔了與商業銀行相似的金融功能,如保險公司(AIG)和投資銀行(雷曼兄弟、貝爾斯登),由于缺乏監管和透明度,導致整個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2007年,五大市場的波動性較低,投資銀行過去幾年創造的大量金融創新產品CDS、CMO等帶來了巨大的風險。由于短端利率水平上升,導致持有短周期的資產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而持有長周期的資產吸引力變小,資金撤出金融資產導致價值下降。資產價格的回落帶來財富效應的負面反饋。2007年9月18日,美聯儲降息0.5%,超出市場預期的0.25%,此時,整個標普500距離歷史高點只有2%的差距。但風險較大的貸款已大量流入社會。投行將貸款者的產品重新包裝、分層,疊加風險已不能簡單剝離,并形成了一個傳導鏈。2008年9月,美國財政部被迫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2008年9月,曾是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的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同日美林被美國銀行收購。2008年9月,美國接管美國國際集團,并向其緊急貸款850億美元。影子銀行為衍生產品精心設計的復雜信用鏈條,最終“蝴蝶效應”使次貸危機向全球性國際金融危機演變。
由此可見,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抵御外部沖擊是防范系統性風險的重要保證。亞洲金融危機所揭示的高負債率、期限錯配、不良資產、過度炒匯等問題,都是系統性風險的誘發因素,在外匯市場上,金融機構充當了炒匯中間人的角色,國際游資通過外匯衍生工具進行投資,使得原本脆弱的本國匯率機制崩潰,一旦出現本幣貶值、資本外逃,就會造成擠兌,引發政府信用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揭示了銀行信貸的介入推動金融資產膨脹,進而通過資本約束和政策變化使資產市場出現危機,資產通過資產負債表效應和流動性枯竭引發內生性的商業銀行危機——信貸緊縮,從而使實體經濟陷入較長時間的衰退。金融資產價格上漲與銀行信貸擴張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促使金融資產膨脹并最終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這提醒我們,金融的國際化需要與一國金融體系的競爭力相匹配,需要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穩健調控,以應對國際金融機構的資產調整,以及國際游資對本國金融體系的沖擊。同時,必須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和運行安全監測制度,保持金融市場總體穩定。
夯實實體經濟基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防范金融危機是治本之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都是由于世界經濟體系薄弱環節斷裂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動蕩,都是對制度模式、經濟失衡和國際貨幣體系的一種調整,金融危機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首先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出現經濟衰退,進而危及民生,激化國內矛盾,引發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金融是虛擬經濟發展的產物,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風險防范的治本之策,如何讓金融市場在切實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保持穩定,仍是需要破解的重要課題。
提升全球共治力度穩步擴大對外開放,構建與國際經濟格局相適應的治理模式,是維護金融市場抗風險能力的必由之路。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固定匯率制難以發揮匯率市場的調節作用,國際熱錢和市場投機行為會造成貨幣體系的崩潰,應逐步構建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區域化”貨幣體系,逐步推動人民幣作為結算、投資和儲備貨幣在周邊國家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落地,探索數字化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堅實基礎,提高跨境資金流動性逆周期調控能力,有效抵御外部沖擊。
綜上,通過對兩次金融危機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發展和安全要動態平衡、相得益彰。為此,我們必須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全力維護國家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