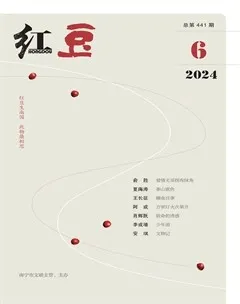少年游
玉輪懸空,銀漢無(wú)聲,整個(gè)槐樹(shù)灣沉浸在幽靜的睡夢(mèng)中。高高低低的農(nóng)舍參差錯(cuò)落,我在屋脊上奔走如飛,腳步輕勝貍貓。從一個(gè)房頂跳躍到另一個(gè)房頂,其間一丈余寬的間隔根本阻擋不住我,更遠(yuǎn)的距離我就借助旁邊的樹(shù)冠或柴垛。我躍上枝頭,不等枝葉擺動(dòng),已騰空而起。起起落落之間,我已在槐樹(shù)灣所有的房頂上游走了一遍。我看到有的院子里垛著白天割來(lái)的青草,草汁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有的院子里晾衣繩上掛滿滴水的衣服,如同被滿月的銀輝浸濕。最后,我來(lái)到小東北家年久失修的房頂上,伴隨著碎瓦墜地的聲音,躍上村口那兩棵高大的古槐。沒(méi)想到這兩頂遒枝雜錯(cuò)的樹(shù)冠竟是如此之大,里面棲息的鳥(niǎo)兒竟是如此之多。黑色的烏鴉,灰色的布谷,花白的喜鵲,墨綠的斑鳩……它們被我驚醒,紛紛振翅而起,五彩羽毛悠悠飄落。我站在一根粗壯的樹(shù)干上,仰望它們扶搖直上,空氣被震動(dòng)得嗡嗡作響……
我?guī)е唤z隱痛睜開(kāi)睡眼,痛感越來(lái)越清晰越來(lái)越真實(shí),來(lái)自左腳的拇趾。摸起床頭的手電筒,借著暗淡的橘光,我看到趾甲折裂,有一絲殷紅。一定是夢(mèng)中踢到墻上了。我回想起剛才的夢(mèng),似乎是飛上了村口的槐樹(shù),一群鳥(niǎo)被驚起,我想跟隨它們一起騰空直上,卻一腳絆在叢生的樹(shù)枝上。
待疼痛減輕,我趿拉著涼鞋走出房門(mén)。院子里遍灑滿月的銀輝,令我手中的光亮仿若秋螢之光。于是,我關(guān)掉手電筒,隨手把手電筒放在門(mén)口旁的雞窩上,走到院墻根的榆樹(shù)下撒尿。樹(shù)上垂下一條條細(xì)絲,懸掛著一個(gè)個(gè)蜷作一團(tuán)的“吊死鬼”,我小心地躲避著它們。頭頂?shù)脑铝料褚粋€(gè)巨大的白玉盤(pán),映襯得天空愈發(fā)湛藍(lán)。墻角的磚縫里有蟋蟀在彈奏《月光曲》,曲調(diào)清脆;牛欄里的黃牛在睡夢(mèng)中反芻,聲調(diào)沉緩;雞窩里,不時(shí)傳出一陣嘰嘰咕咕的夢(mèng)囈聲,喑啞低短;遙遠(yuǎn)的地方,似有狗吠之聲,細(xì)聽(tīng)又不真切。我站在樹(shù)下,又一次回想起剛才的夢(mèng),那種輕盈如飛的感覺(jué)令我心里泛起一陣微瀾,便收攏雙腿,跳了幾下,身體依舊沉重如石,落地又加劇了腳趾剛剛平復(fù)下來(lái)的痛感。
電視里飛檐走壁的大俠們都是夜間出行,我踮著腳往院門(mén)走,剛走出兩步,忽覺(jué)墻頭上似有黑影一閃而過(guò),就趕緊轉(zhuǎn)身回屋了。
吃完早飯,走出家門(mén),燕飛已在老棗樹(shù)下等我。他是從犁城來(lái)姥姥家過(guò)暑假的,他姥姥家跟我家僅一墻之隔,所以每年這個(gè)時(shí)候我們都是最好的朋友。此時(shí)他正仰望著樹(shù)葉間青綠色的棗子,見(jiàn)我過(guò)來(lái)就問(wèn)我這棗子啥時(shí)候能熟。我說(shuō)早著呢,得等到中秋。“七月十五棗紅圈,八月十五棗落竿。”我顯擺了一句從作文書(shū)上看過(guò)的諺語(yǔ)。他說(shuō):“那我吃不著了。”我說(shuō):“一個(gè)破棗兒有什么好吃的?”“你不是說(shuō)很甜嗎?”他問(wèn)我。我說(shuō):“你還稀罕這,你在城里啥好吃的沒(méi)有?”他搖搖頭說(shuō):“那不一樣。”
我挎著籃子,提著鐮刀,和燕飛順著我家西墻根往村后走。正是盛夏時(shí)節(jié),雖然早上的陽(yáng)光還沒(méi)有發(fā)威,樹(shù)上的蟬卻已經(jīng)開(kāi)始了一天的鳴唱。路邊青草細(xì)長(zhǎng)的綠葉上還滾動(dòng)著夜間的露珠,牽牛花擎著一個(gè)個(gè)小喇叭,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仿佛準(zhǔn)備隨時(shí)吹奏一曲天籟。螞蟻們也開(kāi)始了一天的忙碌,有的單獨(dú)行動(dòng),有的成群結(jié)隊(duì)。我揮舞著手中的鐮刀,眼前浮現(xiàn)著電視里那些持劍打斗的畫(huà)面,但我只會(huì)左右比畫(huà),幾下便沒(méi)有了興致。
我們走進(jìn)那片開(kāi)闊的荒草地,高高的蒿草沒(méi)過(guò)膝頭。我把籃子和鐮刀扔到草叢里,和燕飛爬上一道半人多高的土堤。土堤的頂部只有一拃來(lái)寬,土質(zhì)干松,全都是旁邊田里泛起鹽堿之時(shí)人們用鐵锨鏟起的薄薄的一層浮土,長(zhǎng)年累月堆積而成。我們一前一后在土堤上奔走,練習(xí)飛檐走壁的本領(lǐng),碎土在我們腳下簌簌滑落,騰起陣陣黃塵。這是燕飛想出的主意,他說(shuō)這兒的土這么松軟,我們?cè)谶@上面練習(xí)就會(huì)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想方設(shè)法減輕自身的重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我們已經(jīng)練了半月有余,卻沒(méi)見(jiàn)任何效果。
我們都迷戀而且夢(mèng)寐以求地想練成在武俠劇里看到的武功,包括拳腳和劍術(shù),甚至輕功。別說(shuō)小小的槐樹(shù)灣,方圓十幾里的村莊里從沒(méi)聽(tīng)說(shuō)哪個(gè)人會(huì)一招半式,我們想找人指點(diǎn)也無(wú)人可找,只能自己去琢磨。好在燕飛說(shuō)他會(huì)一套拳法,是學(xué)校里體育老師教他們的。他打了一遍給我看,一招一式,緩慢而不連貫,也沒(méi)有電視里那種打出來(lái)呼呼掛風(fēng)的效果,但我還是非常羨慕他。我們槐樹(shù)灣只有一個(gè)老師,除了語(yǔ)文和數(shù)學(xué)這兩門(mén)課,我都不知道還有體育課這一說(shuō)。除了拳法,燕飛還有一個(gè)讓我震驚的本領(lǐng),他會(huì)鯉魚(yú)打挺,他說(shuō)這是他一個(gè)在武校的小伙伴教他的。武校,這又是一個(gè)新鮮的名詞。那一刻,我真恨自己為什么沒(méi)像燕飛一樣也出生在城里。我問(wèn)燕飛武校是什么,他說(shuō)是專(zhuān)門(mén)學(xué)武的地方。我問(wèn)他在哪兒,他只說(shuō)了兩個(gè)字——很遠(yuǎn)。我又問(wèn)他怎么不去學(xué),他說(shuō)他爸媽說(shuō)知識(shí)比武功更重要。我們都覺(jué)得這種說(shuō)法可笑至極。燕飛說(shuō)他的這兩項(xiàng)本領(lǐng)都可以傳授給我,條件是我要和他一起練習(xí)飛檐走壁。
“飛檐走壁我當(dāng)然更愿意練。相對(duì)于拳腳,這是更上乘的武功,可是沒(méi)有人教咱們啊。”我說(shuō)。
“咱們自己練。所有的武功不都是人琢磨出來(lái)的?”燕飛很有把握地說(shuō)。我同意他的說(shuō)法,可心里卻沒(méi)有底。
我們?cè)谕恋躺吓芰藥讉€(gè)來(lái)回,累得氣喘吁吁,大汗淋漓,卻依舊沒(méi)有絲毫進(jìn)步。堤上布滿了我們的腳印,還有一個(gè)個(gè)犬牙交錯(cuò)的豁口。
“還是不行啊。”我說(shuō)。“咱這才練了幾天啊。”燕飛毫不氣餒地說(shuō),“等啥時(shí)候咱把這土堤踏平了就差不多了。”
他這話讓我不禁想起電視里的俠客為了練功踢呀踢,踢斷樹(shù)干的畫(huà)面。
“你還是先教我鯉魚(yú)打挺吧。”我平復(fù)了一下呼吸,說(shuō)。“那套拳你會(huì)了嗎?”“會(huì)了。我打給你看看啊。”
我一招一式地練起來(lái)。由于不熟練,一邊練一邊回憶燕飛教給我的動(dòng)作。
“不對(duì)。”燕飛打斷我的動(dòng)作說(shuō),“你腳下的動(dòng)作配合得不對(duì)。”他說(shuō)完又給我演示了一遍,然后讓我照著做,直到我跟他做得一樣了才罷休。
“這下可以教我鯉魚(yú)打挺了吧?”我用近乎哀求的語(yǔ)氣說(shuō)。
可燕飛還是拒絕了我。他扯下一根狗尾巴草,一邊擺動(dòng)一邊說(shuō):“鯉魚(yú)打挺不難學(xué),現(xiàn)在我們要先練成飛檐走壁。”
我很失望。“那你再練一下讓我看看?”我簡(jiǎn)直要為自己這種卑下的口吻感到害羞了,同時(shí)又生怕他拒絕。我的算盤(pán)是先把他的動(dòng)作記住,然后去偷練。在飛檐走壁練成之前,這是他壓箱底的功夫了,當(dāng)然不能輕易教人,電視里的高手不都是這樣的嗎?
或許燕飛也不敢得罪我吧,他點(diǎn)點(diǎn)頭,把狗尾巴草扔到地上,走到草地上躺下——蚱蜢驚散。之后兩臂抬起,雙手放在頭兩側(cè),然后抬起雙腿,直抬到屁股離地,最后腿猛地往下一擺——驚起更多的蚱蜢。但是這一次,他的身子剛起來(lái)就往后倒退了兩步,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又是一片雨點(diǎn)般的蚱蜢驚惶飛逃。
不知道為什么,我心里竟隱隱有些高興。“可能是剛才練得太累了。”我驚異于自己的卑鄙心思,趕忙安慰他說(shuō)。話一出口臉上又爬過(guò)一絲熱辣,于是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燕飛臉色絳紅,沒(méi)有注意到我的慌亂。他又一次躺倒在地,又一次重復(fù)了一遍剛才的動(dòng)作,大叫一聲,從地上站了起來(lái)。我動(dòng)作夸張地給他鼓掌。燕飛的臉色漸漸恢復(fù)了正常,呼吸卻好長(zhǎng)時(shí)間平復(fù)不下來(lái)。
太陽(yáng)當(dāng)空,曬得我后背火辣辣地疼。
“真熱。”燕飛擦掉額頭上的汗水說(shuō)。
“你先回去吧。”我對(duì)他說(shuō),“我還得去拔菜,等會(huì)兒我去找你。”
燕飛手搭涼棚望了望太陽(yáng),點(diǎn)點(diǎn)頭,踩著厚厚的野草回家了。
陽(yáng)光下,青草的葉子反射著銀色的光,陣陣濃郁的花香暖烘烘地從簇?fù)碇?jìng)相開(kāi)放的野花上襲來(lái),吸引著一群蜜蜂嚶嚶嗡嗡,還有幾只白色的飛蛾翩躚飛舞。在過(guò)往的夏天里,這片草地曾是我的樂(lè)園,我在這里捉過(guò)螞蚱、蜘蛛、青蛙,還有一只剛剛睜開(kāi)眼的野兔崽兒。但是今天,我不打算在這里停留,只想趕快找個(gè)隱蔽又涼爽的地方去練習(xí)鯉魚(yú)打挺。我撿起地上的籃子和鐮刀,翻過(guò)土堤,穿過(guò)一片玉米地,來(lái)到一棵大樹(shù)下。樹(shù)蔭下清涼,我精神一振。我把人們?nèi)釉诘仡^的半干的雜草收起來(lái),鋪到樹(shù)下,開(kāi)始偷偷地練習(xí),但是一連做了十幾次都沒(méi)有成功。我坐在地上,呼呼喘著氣,腿和腰都在隱隱作痛,心里面懊惱至極。一只鬼鬼祟祟的蜥蜴翹著半個(gè)身子嗖的一聲從我面前躥過(guò)去,我抓起一旁的鐮刀追了上去。
夜深了,我卻無(wú)法入睡,滿腦子想著鯉魚(yú)打挺。我躺在床上,回憶著白天里燕飛的動(dòng)作,又做了幾個(gè),依然沒(méi)有成功。小床吱嘎作響,似要散架,我不敢再做,四仰八叉地望著漆黑的房頂出神。
突然,我聽(tīng)見(jiàn)燕飛在窗口叫我,轉(zhuǎn)頭一看,只見(jiàn)他倒掛在我小屋的窗戶上。
“快出來(lái)。”他壓低聲音對(duì)我說(shuō)。
我一躍而起,從床頭跳到窗臺(tái)。“我還要練鯉魚(yú)打挺呢。”我悄聲說(shuō)。
“咱先出去飛一圈,完了我教你。”他特意用了“飛”這個(gè)字,臉上洋溢著得意的微笑。
我鉆出窗口,雙手搭在瓦上,輕輕一躍,躍上房頂。頭頂圓月高懸,地上亮如白晝,連瓦片上的裂痕都看得一清二楚。“咱倆比賽。”燕飛站在我家坑坑洼洼的屋脊上,抬手畫(huà)了一個(gè)圓,說(shuō),“圍著槐樹(shù)灣跑一圈,不能落地。甭管誰(shuí)輸誰(shuí)贏我都會(huì)教你鯉魚(yú)打挺的,說(shuō)話算數(shù)。”
我答應(yīng)了。
我們?cè)谀{(lán)的夜色里穿行,越過(guò)寬寬窄窄的胡同,高高低低的磚墻、土墻、籬笆墻,腳下聲息皆無(wú)。月色溶溶,一排排瓦片就像魚(yú)的鱗片,有又細(xì)又高的野草從縫隙間鉆出,在水一樣的光里一動(dòng)不動(dòng)。人們都沉在睡夢(mèng)里,整個(gè)村莊闃寂無(wú)聲,瓦縫間夏蟲(chóng)的振翅聲清晰入耳。房頂?shù)臒焽琛⒔邮针娨曅盘?hào)的天線桿在我們身邊閃過(guò)。村莊外,樹(shù)影沉沉,大片的莊稼地望上去一片漆黑,而坡下灣里的水卻平滑如鏡。借著電線,我來(lái)到同桌小黎家的房脊,他的院子里停著新買(mǎi)的拖拉機(jī),車(chē)輪旁睡著他的大黑狗。起夜的小黎提著短褲,看見(jiàn)房頂上的我們?nèi)绻眵乳W過(guò),驚訝得咽下打到一半的哈欠卻合不上口。我得意至極,腳下用力躍上兩米開(kāi)外的另一個(gè)房頂……頃刻之間,我們到了村子的另一頭,一戶人家的墻頭悄立著一只偷雞的狐貍,狐貍皮毛火紅,尾巴碩大,轉(zhuǎn)動(dòng)的眼珠如鬼火閃爍。“抓住它。”我和燕飛異口同聲叫道。與此同時(shí),警惕的狐貍也發(fā)現(xiàn)了我們,身子一扭,跳下墻頭,向著村外箭一般竄去,我和燕飛緊隨其后。荒草萋萋,狐貍在草間潛行,身影忽隱忽現(xiàn)。草叢中掩藏著干結(jié)的牛糞,還有地鼠掏洞拱起的土堆。我們踏草而飛,始終緊追不舍,一直追到一片墳塋邊,狐貍消失不見(jiàn)。我們站立在兩棵高立的紅荊樹(shù)的枝條上。這種農(nóng)人用來(lái)編筐的枝條質(zhì)地柔韌,在我們腳下一起一伏,細(xì)密的針狀葉子散發(fā)出濃郁的澀香。聳起的墳頭間茂密的雜草兀立不動(dòng),壓墳紙卻颯颯作響。我和燕飛對(duì)望一眼,都看出了對(duì)方心里的畏怯,轉(zhuǎn)身向著村子的方向跑去。
回到家門(mén)口分手的時(shí)候,燕飛對(duì)我說(shuō):“其實(shí)鯉魚(yú)打挺很簡(jiǎn)單。”他告訴了我其中的要領(lǐng),讓我先練習(xí)仰臥起坐,以增強(qiáng)腰腹肌肉的力量。“我當(dāng)時(shí)就是這樣練的。”他對(duì)我說(shuō)。
回到家我就躺在床上練習(xí),直到腰膝酸軟,才倒頭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覺(jué)得全身骨骼酸痛,耳朵嗡嗡直響,咬牙勉強(qiáng)起了床。母親摸了摸我的額頭,說(shuō)我發(fā)燒了,找出之前的退燒藥讓我服下。
院外,燕飛在叫我。
“我發(fā)燒了。”我對(duì)他說(shuō),“今天不能去練了。”
燕飛難掩滿臉的失望之色。
“我去,也只能看著你練。”我心中不忍,又補(bǔ)充了一句,“要是我感覺(jué)好點(diǎn)了就和你一起練。”
“好。”燕飛喜笑顏開(kāi)地說(shuō),“今天練完了我就教你鯉魚(yú)打挺。”
“你已經(jīng)教過(guò)我了。”
“啥?”燕飛疑惑地看著我,走過(guò)來(lái)伸手摸摸我的額頭說(shuō),“你真發(fā)燒了。”
那天上午我一直看著燕飛在土堤上來(lái)回奔走。他奓著雙臂,身子歪歪斜斜,腳步跌跌撞撞,完全沒(méi)有昨天夜里的輕盈。我看著他的身影,只覺(jué)得天旋地轉(zhuǎn),只好躺在草地上。天空萬(wàn)里無(wú)云,藍(lán)得仿佛拿筆尖一蘸就能寫(xiě)出字來(lái)。燕飛幾次叫我上去,我都對(duì)他擺擺手。
“還不行嗎?”他從土堤上跑下來(lái)。
“頭暈。”我說(shuō)。
“現(xiàn)在我教你鯉魚(yú)打挺吧。你先看我做一遍。”
我緩慢地坐起來(lái)。
燕飛躺在地上,一邊做動(dòng)作一邊講解,毫無(wú)保留,就跟他昨天晚上對(duì)我說(shuō)過(guò)的一樣。“要加強(qiáng)腰腹的力量,練仰臥起坐最管用了,我當(dāng)初就是這樣練的。”他最后對(duì)我說(shuō)。我一時(shí)分不清正在發(fā)生的到底是夢(mèng)境還是現(xiàn)實(shí),恍惚之間竟然沒(méi)有聽(tīng)清他到底說(shuō)了什么。
夏日漫漫,燠熱似乎永無(wú)盡頭。我用了差不多一個(gè)星期的時(shí)間終于學(xué)會(huì)了鯉魚(yú)打挺,雖然不能做到每次都利索地站起來(lái),但十次里面還是能夠成功多半的。而飛檐走壁依舊絲毫不見(jiàn)長(zhǎng)進(jìn),我漸漸地感覺(jué)到心灰意懶。每天正午時(shí)分,驕陽(yáng)如火,我躺在鋪在院門(mén)下的涼席上,聽(tīng)著焦躁的蟬鳴聲,看著門(mén)前不遠(yuǎn)處在池塘中央戲水的小伙伴,對(duì)他們的召喚充耳不聞。燕飛躺在我的旁邊。時(shí)間一天天過(guò)去,他對(duì)練功的熱情絲毫不減,總是抱怨時(shí)間過(guò)得太快,而早上涼爽的時(shí)間又太短,因?yàn)榛氐匠抢锼驼也坏竭@種練功的土堤了。一進(jìn)八月,田里的玉米秀出細(xì)細(xì)的棒槌兒,棉花結(jié)出豆粒大的棉桃,燕飛就被他的母親接走了,說(shuō)還有很多作業(yè)需要做。與燕飛相比,這是我唯一一個(gè)可以驕傲的地方,我們槐樹(shù)灣的孩子永遠(yuǎn)不用擔(dān)心假期的作業(yè)。臨走之前,燕飛囑托我還要多加練習(xí)鯉魚(yú)打挺,并約定明年再一起練飛檐走壁。說(shuō)到飛檐走壁,土堤在我們腳下坍塌得七零八落,再加上幾場(chǎng)大雨的沖刷,似乎比原來(lái)矮了整整一頭,可我們的功夫卻還是在原地踏步。我們只有在夜晚的月色里閃轉(zhuǎn)騰挪,在各自的夢(mèng)里相遇。白天,我們回味著身輕如燕的感覺(jué),共同研究著夜里的動(dòng)作,卻始終不得要領(lǐng)。
燕飛的離開(kāi)讓我若有所失,也在突然間感覺(jué)到夏日其實(shí)所剩無(wú)幾,天空的顏色與穿過(guò)樹(shù)葉的風(fēng)不知從哪一天起似乎悄然起了某種變化。在這一個(gè)月的時(shí)間里,我天天和燕飛膩在一起,企圖成為人人艷羨的武林高手,而冷落了昔日的伙伴。等到我再想回到他們中間時(shí),卻感到一種若有若無(wú)的疏遠(yuǎn)與排斥。
有一天,我獨(dú)自一人在土堤上跑了幾個(gè)來(lái)回,感覺(jué)索然無(wú)味。旁邊玉米地里的莊稼已經(jīng)有一人多高,我提著籃子鉆了進(jìn)去,里面密不透風(fēng),花粉撒落在身上,融進(jìn)汗水里,密密麻麻地刺癢。后來(lái),我提著滿滿一籃野菜往回走,在打麥場(chǎng)上被小武攔住。不知道為什么,我和小武天生不對(duì)付,一見(jiàn)面用不了三言兩語(yǔ)就會(huì)掐起來(lái)。在教室里,他坐在我的后面,經(jīng)常在我起身時(shí)用腳把我的凳子鉤到他的桌下,讓我在毫無(wú)防備的情況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惹得全班同學(xué)哈哈大笑,而他更是拍著手笑得肆無(wú)忌憚。因?yàn)檫@事我們兩個(gè)更是不知打了多少架。
小武二話不說(shuō),沖著我就要撞過(guò)來(lái)。我早有防備,看他的樣子是又要打架了,這也正合我心意,正好試試燕飛教我的拳法。
但是還沒(méi)等我放下菜籃、擺出架勢(shì),小武一下就抱住了我的腰,我急欲甩開(kāi)他好施展拳法,可用盡了力氣也擺脫不開(kāi),反倒被他一下摔在了地上。菜籃滾到一邊,野菜撒了滿地。打麥場(chǎng)的地面雖說(shuō)不上堅(jiān)硬卻仍令我后腦嗡嗡響。此時(shí)我早已忘記了剛剛學(xué)會(huì)的鯉魚(yú)打挺,即使想起來(lái)也根本來(lái)不及施展,因?yàn)閷?duì)手隨即就坐在了我的身上。
一群在麥秸垛邊玩耍的孩子見(jiàn)我們打起來(lái),都嗷嗷叫著跑過(guò)來(lái)看熱鬧,小武的哥哥小文也在里面。但我的兄弟不在場(chǎng),即使在場(chǎng)他也不會(huì)出手,這是槐樹(shù)灣孩子打架的規(guī)矩。看到小武坐在我的身上,小文就放心了,大聲叫著:“揍他,壓住他,可別讓他起來(lái)。”其他孩子也跟著起哄。
小武真的在我頭上揍了兩拳,讓我眼冒金星。我急了,不管不顧伸手去抓他的臉,指甲在他臉上劃過(guò),留下血痕。
“抓人臉,娘們兒打仗才抓人臉!”小文在旁邊嚷道。其他孩子都跟著附和。
大概是因?yàn)槊娌砍酝矗∥淞庖凰桑晃曳韷涸诹松硐隆N乙舱蘸J畫(huà)瓢還了他兩拳,他情急之下?lián)狭宋业哪槨_@下小文沒(méi)有叫嚷,但有別的孩子打抱不平:“咋都學(xué)娘們兒啊?站起來(lái)打。”
我又揍了他兩拳,起身讓他站起來(lái)。
小武氣咻咻地爬起來(lái),剛想往我身上沖,就被幾個(gè)大孩子攔住了。“好了,好了,打平了,誰(shuí)也沒(méi)吃虧,就這樣算了。”他們把小武推到小文身旁。
小文沒(méi)理他弟,只是看著我笑,一臉譏諷之色。
“你給我等著。”小武指著我跳著腳叫道。
“等著就等著,我還怕你?”我也毫不示弱。
往家走的路上,我越想心中越懊惱,不是因?yàn)樯蟻?lái)就落了下風(fēng),也不是因?yàn)樽约郝氏仁褂昧藷o(wú)賴(lài)的招數(shù),而是因?yàn)闊o(wú)論我怎么琢磨,似乎都無(wú)法用燕飛教我的拳法擋開(kāi)小武撲過(guò)來(lái)的身體,那我練它還有什么用呢?
八月過(guò)半,暑熱漸退,雖然樹(shù)上的蟬聲依然聒噪,但我已收拾起書(shū)包進(jìn)入學(xué)校了。在課堂上,我時(shí)常想起燕飛。農(nóng)村的孩子因?yàn)檫€有秋假,所以暑假比城里的短,燕飛一定正在家里做他的作業(yè),不知道他會(huì)不會(huì)想起我。我又和小武打了幾架,卻依舊沒(méi)有使用上從燕飛那里學(xué)來(lái)的一招半式。好幾次,我想起燕飛說(shuō)過(guò)的武校,明年我一定要問(wèn)清楚到底在什么地方,那里的武功一定可以把小武打倒在地。
年少的我從沒(méi)出過(guò)遠(yuǎn)門(mén),連去犁城的次數(shù)也屈指可數(shù)。遠(yuǎn)方,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既是一種美好的誘惑,也是一種未知的恐懼。趁家中無(wú)人,我從炕席下摸出一卷零錢(qián)塞進(jìn)褲兜,偷偷摸摸地出了門(mén)。玉米、高粱夾峙的田間小路上空無(wú)一人,我順著小路走上碎石鋪就的鄉(xiāng)間公路,路過(guò)幾個(gè)村莊,行不到五里就到了鄉(xiāng)里。街道兩邊排列著供銷(xiāo)社、郵局、糧所、飯館、雜貨鋪,門(mén)前全都冷冷清清。循著叮叮當(dāng)當(dāng)?shù)那脫袈暎襾?lái)到一家鐵匠鋪,店前同樣門(mén)可羅雀。以前我跟著祖父趕集來(lái)買(mǎi)鐵鍬、鐮刀到過(guò)店里,我記得店主是個(gè)粗壯的中年男人,但這回卻換成了一個(gè)須發(fā)皆白的老人,門(mén)口擺的、墻上掛的也不是粗糙的農(nóng)具,而是一把把精心打制的刀劍。我暗自納罕,心里想或許可以買(mǎi)把劍帶上,就不由自主地走到老人跟前。問(wèn)完了價(jià)錢(qián),我才知道自己連最便宜的都買(mǎi)不起。老人看看我,問(wèn)了幾句話之后,點(diǎn)點(diǎn)頭道:“好啊,那我就送你一把劍。”
我驚奇地望著老人。他慈祥地笑了,說(shuō):“我小時(shí)候也有一個(gè)遠(yuǎn)方的夢(mèng),可是沒(méi)有膽量出走。等你哪天回來(lái)給我講講,就算是這把劍的價(jià)錢(qián)了。”
我把劍扛在肩上,向著前方大步流星走去。天蒼蒼,野茫茫。微風(fēng)輕拂,路兩邊的莊稼奏出輕快的樂(lè)曲,我心中更是輕快得都要飛起來(lái)了,二十公里的路程一閃而過(guò)。
遠(yuǎn)遠(yuǎn)地,“犁城車(chē)站”四個(gè)大字沖著我招手,我走進(jìn)車(chē)站,里面空蕩蕩的。燕飛曾告訴我,有個(gè)窗口上寫(xiě)著“售票”兩個(gè)字,就在那兒買(mǎi)票。我走近窗口,女售票員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問(wèn)我去哪兒。
“武校。”我壓抑著心中的自豪與激動(dòng)說(shuō)。
“哪里?”售票員又提高聲音問(wèn)。
“武校。”我又說(shuō)了一遍。
“什么武校?我問(wèn)你到哪一站!”售票員白了我一眼,高聲叫道,“喂,這是誰(shuí)家的小孩?買(mǎi)票要大人來(lái)哈!”
“我家的,我家的。”一個(gè)中年男人不知從哪兒一下子冒出來(lái),不由分說(shuō)就抓住我的手。
“不是,我不認(rèn)識(shí)你!”我大叫一聲,伸手去摸掛在腰間的劍擎在手中,卻發(fā)現(xiàn)竟是一根開(kāi)了叉的高粱稈。
“跟我走吧,你這孩子!”中年人獰笑著。
“不!”我驚叫著從夢(mèng)中醒來(lái),額頭冷汗涔涔,心口突突直跳。
秋風(fēng)漸涼,學(xué)業(yè)也一天天緊了起來(lái),我沒(méi)有時(shí)間再去那道長(zhǎng)長(zhǎng)的土堤上練習(xí)飛檐走壁。偶爾,月夜之下,我依舊奔跑在槐樹(shù)灣的房頂上,翻墻越戶,只有我孤零零一個(gè)人,在第二天早上起床時(shí)疲憊不堪。等到大雪紛飛之時(shí),我就縮在冰冷的被窩里,抱著母親給我裝滿熱水的燙瓶,再也不想出門(mén)了。
第二年暑假,燕飛依約前來(lái),在最初的生分過(guò)后,他對(duì)我說(shuō):“咱去釣魚(yú)吧,我?guī)Я酸烎~(yú)竿來(lái)。”
他給我看了他的釣魚(yú)竿。那是我見(jiàn)過(guò)的最漂亮的釣魚(yú)竿。
我偷拿了兩角錢(qián)去小賣(mài)部買(mǎi)了魚(yú)鉤和魚(yú)線,用鵝毛做了魚(yú)漂。每天我和燕飛扛著釣魚(yú)竿提著小桶——我還挎著籃子——去村后的河邊釣魚(yú)。樹(shù)蔭下,清風(fēng)徐徐,水面波光粼粼,我們一邊盯著水中的魚(yú)漂一邊說(shuō)說(shuō)笑笑。
遠(yuǎn)處的荒草地里,那條長(zhǎng)長(zhǎng)的土堤已被人修補(bǔ)好了,并添了春天新鏟下的生滿鹽堿的泥土,看上去比去年更高了。在陽(yáng)光熾烈的幻影中,兩個(gè)少年在土堤上行走如飛,腳下飄起股股黃塵……
“哎……”我剛想重提飛檐走壁的話題。
“嘿,來(lái)了。”燕飛歡呼一聲。一條鯽魚(yú)閃著點(diǎn)點(diǎn)白光劃出一道優(yōu)美的弧線,落在身后的空地上,蹦蹦跳跳……
【作者簡(jiǎn)介】李成墻,作品散見(jiàn)于《清明》《春風(fēng)文藝》《文藝報(bào)》等刊物。
責(zé)任編輯 梁樂(lè)欣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