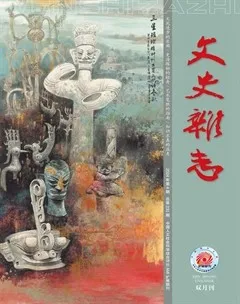巴蜀山水之畫 萬卷天府之畫
摘 要:管苠棢著《巴蜀山水畫敘論》是一部知名畫家從文獻學角度研究美術史的力作。其以實物證文獻,以文獻明實物,史料豐富,考評嚴謹,既源于舊學,更有創新,從而為巴蜀山水畫的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關鍵詞:生活;史料;足跡;新知
巴蜀大地,人文薈萃,源遠流長。易學在蜀,菩薩在蜀,道學在蜀,天數在蜀,文宗在蜀,自古詩人皆入蜀,入蜀方知畫意濃,先賢的話語無不昭示著巴蜀文化在中國文化史的地位,對于山水畫也是如此。對管苠棡先生的《巴蜀山水畫敘論》(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版),初略一覽,便覺堪稱巴蜀山水之畫,或呼萬卷天府之畫,是巴蜀美術考古之力作。拜讀之余,感慨如下:
一、源于自然,水到渠成。巴蜀地區對山神的崇拜,源于巴蜀地區的崇山峻嶺既為巴蜀人提供了生息的場所,又隨時威脅著巴蜀人的生命,尤其是岷山山系多發的地震帶對生靈帶來巨大的毀滅性。同時,這里的山川還孕育了生命,是生靈萬物歸藏之所,使古蜀人產生強烈的敬畏心理。而崇山峻嶺,交通不便,使出行困難。古蜀山區的人自古就渴望飛越高山峽谷,在地質災害發生時可以飛騰逃離。這種飛越和飛騰只有傳說中的神可以做到。也許,這些心理狀態便是仙道文化產生的心理基礎。《敘論》通過嚴密的分析論證,自然而然地回答了為什么在古巴蜀最早產生“崇山仙道”。而這種“崇山仙道”也就必然成為中國山水畫最原始的心理動因和山水畫文化的源頭,祭山圖自然成為山水畫萌芽的雛形。源于生活,來于生活,方有藝術的產生,方有足以影響后世之藝術的產生。
二、源于史料,論證嚴密。自唐五代以來,巴蜀地區就是人們遠離戰亂、追求安定生活的樂園,文人匯聚,財貨匯聚,到北宋時達到頂峰。而宋代則為中國文化之高峰,已成為學界之共識。最早的地方官辦學校——文翁石室(漢代)出現于成都;最早的宋版佛經《開寶藏》編纂、印制于成都(歷時12年,有13萬多片雕版);第一部書法薈萃之作《淳化閣帖》也由巴蜀人王著編撰,成都刻印;最全的儒學十三經石刻也完成于成都(從五代到南宋,歷經二百余年,共2300塊石刻);第一個宮廷畫院——翰林畫院,第一個畫派——黃筌畫派,均誕生于五代孟蜀之成都。天時地利人和諸多條件具備,才有變革創新的可能。所以山水畫的第一次變革出現于巴蜀,出現于唐宋,也是理所當然的。這與宋史學界所提出的“唐宋變革論”亦相吻合。管先生爬梳史料,收集到34位入蜀寓居以及本土畫家的資料,從創新的角度,分析了唐宋山水畫派的流變,填補了其研究的空白。而第二次變革出現于民國年間,也與巴蜀作為抗戰大后方,人才匯聚,流派匯聚相關。流風所及,余音不斷;創新所至,佳作迭出。故兩次變革之說,斯為同理。
三、源于足跡,腳踏實地。好山好水在巴蜀,好人好事在巴蜀。管先生積數十年之心血,尋物尋人,足跡遍布巴蜀名山大川,街路小巷,以實物證文獻,以文獻明實物。北行川陜之路,西走川藏之線,美景美色,納入書中,擇其要者,條分屢析。
四、源于舊學,又加新知。傳統的美術史研究,是作品本身加上文獻記載,而作品本身則是重中之重,文獻只是佐證。管先生在舊學的基礎上,又加新知。如對金沙博物館“山云禾田圖”(金沙石鉞)的分析,獨具新意。其徘徊于歷史文獻之中,考古文獻之中,學人研究成果之中,口述文獻之中,鉤沉稽古,發微抉隱。我們從每卷末的注釋可以看出,第一卷有270條,第二卷有157條,第三卷雖為“當代實踐思考與未來展望”,但也有注釋20條。全書共有參考文獻181部,參照圖目28種,洋洋大觀,為其新觀點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略顯不足的是,因該書引用史料眾多,而其注釋置于每章之末,不便閱讀。希望下次再版時能放在當頁腳注,則更為完備。
管先生的《巴蜀山水畫敘論》圖文并茂,相得益彰。這厚重的三大冊,印制精美的三大冊,必將在巴蜀山水畫研究方面留下歷史的足跡,占有一席之地。
最感到更高興的是,管先生作為一個知名畫家,卻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研究美術史,巴蜀山水畫的研究或許由此從另一個角度打開新的窗戶。當然,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書畫理論家和畫家都來關注巴蜀山水之研究,巴蜀山水畫之研究。
作者:四川大學古籍所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