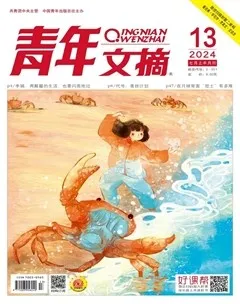混在男生群里的那個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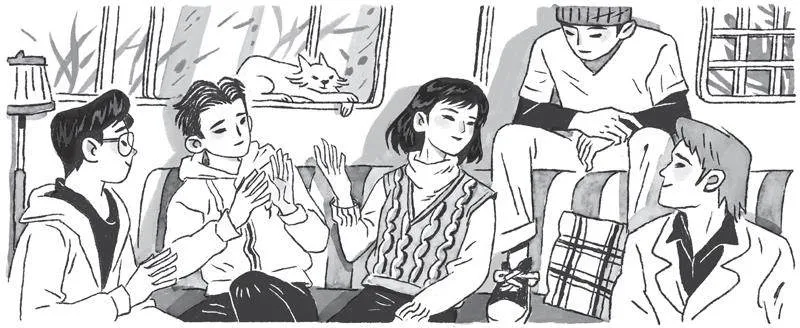
我二十歲左右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留學時,不希望男生把我當成女孩對待,我希望他們把我當成“兄弟”,只有這樣,和他們在一起時,我才感到自在。
在綠園的某一棟小樓里,住著我的幾位商學院男同學,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和我的關系尤其好,是真的“兄弟”。
除了我這個總是“開小差”去搞文學的學生,當年這幾位商學院同學大概是所有留學生里面表現得最躊躇滿志的一群吧,大家仿佛覺得那些頂級投資銀行的大門已經向自己敞開,自己一畢業就會衣冠楚楚地走進去,成為影響著金融界、企業界的才俊之一。這樣的小野心也許在我那些男同學的言談舉止上都有所表露。但我知道他們為人其實都比較直爽、熱情,并沒覺得他們這種“自以為了不起”算什么大不了的問題。
他們住的那棟樓是我在綠園期間唯一常去的男生住處,我至今仍對一走進去就看到的“荒涼”景象記憶尤深:樓下的客廳因為是公共地盤,顯然沒有任何人照顧它,窗戶全部洞開(我后來發現外面的流浪貓喜歡從窗戶那兒跳進跳出),沙發前面的茶幾上、地板上到處都是被風吹得散亂的報紙。當我對此提出異議,他們聲稱,這樣的隨意正是男人的居所所追求的效果,我覺得好笑,深知這不過是男生的懶惰和不良衛生習慣所造成的“效果”。但他們任由小貓出入客廳、從不打它的溫和,我是很贊同的,因為我知道有些男生粗暴地對待流浪貓。
他們住在樓上,我們在其中的一個房間里小聚。因為他們把我當成他們中的一員或者看成一個幼稚的“小兄弟”,所以我并不介意坐在床上和他們一起聊天。我們隨便聊著一些事不關己的話題,譬如,哪位教授有才華哪位根本就是瞎混,某位學姐或學長就業后發生的變化,還有綠園里近期的八卦……我漸漸發現當我和男生們在一起說話時,我仿佛有一種“變換角色”的能力,不僅是我盤腿坐在臟兮兮的床上的假小子一般的姿勢,還有說話的語氣,甚至連我的感覺也有點傾向于男性化。
我后來意識到,我在寫作時也常常有這么一個隨時“換位”的能力,我可以自然而然地從男性的角度去敘述。
我可以對一個男性的遭遇感同身受,同時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女性主義者。從小到大,我都極度討厭大男子主義,厭惡對女性的任何貶低和忽視,我也喜歡女性更為仁慈、感性、敏感的特質,從不覺得自己需要像男人一樣粗枝大葉地生活。在我的“女性主義”觀念里,女性并不需要變得和男人一樣,她需要的是和男人同等的權利和尊重。
我們聊天的時候,窗戶洞開,風在屋子里穿來穿去。突然,他們會問我:“說說你自己吧,你最近又在讀什么有趣的書啊?”碰到這種時候,就像自己的秘密被別人當場揭發出來一樣,我總是支支吾吾地搪塞過去:“沒有呀,沒看什么新書。”我不愿意談我看的書,因為我知道這對他們來說過于陌生、沒有意義。有時,我也會和他們一起去看電影、吃飯。
有時候,人們問我,為什么在小說里能把男性寫得那么真實。我想,這可能和我與男性朋友的相處方式有關。首先,你得確定能相互尊重、平等視之,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性別界限才不至于成為干擾或困擾。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無論是對于女性還是男性,我最大的興趣是觀察、了解他們,而非評判,否則我就不可能了解到他們的真實想法。作為男生群里的女生,我一般不會過于敏感、計較,我相信我的朋友們在我面前也會覺得沒有過多的顧忌和拘束。譬如,我不計較男生們大大咧咧的舉止,不計較他們抽煙喝酒、罵幾句并不過分的粗話,就像我不計較他們貓兒來往的荒涼客廳和不那么宜居的房間一樣;如果他們談論女生,我也不反對,但不同意的話,我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
每當我的朋友們煞有介事地談論著屬于男性的“大話題”時,我看著他們那故作嚴肅的表情就暗暗覺得好笑。偶爾,我會掃興,表示這個話題非常無聊,但大部分時間,我會在一邊聽著,那些談話的內容或者立即變成我的耳旁風,或者被我在心里沉默地思索一番。有時候,想到身為男性在這個社會上需要承擔的“義務”,需要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強硬角色),我絲毫不羨慕他們。要知道在一個會批判“女人不像女人”的社會,肯定也會批評“男人不像男人”。男性有“特權”,同樣也有社會加之于他們的規訓和桎梏。因此,在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就想,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肯定會支持女性擺脫社會規訓,因為這也是解放我自身啊。
(摘自“奴隸社會”微信公眾號,本刊有刪節,八方留白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