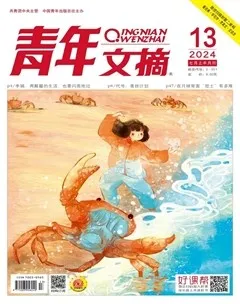宏偉的《三國演義》,細致的《水滸傳》

一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是寫打打殺殺,寫英雄好漢。
《三國演義》里有五虎將,《水滸傳》里也有五虎將。《三國演義》里的五虎將是關羽、張飛、趙云、馬超、黃忠,《水滸傳》中的五虎將是關勝、林沖、秦明、董平、呼延灼。關勝是關羽的后代,不但長得像,也使一口青龍偃月刀。林沖是“豹頭環眼”,手使丈八蛇矛,也像極了張飛。董平和趙云都是年輕英俊,馬超和秦明都很勇猛,呼延灼和黃忠也有類似的地方(在一些版本的故事里,呼延灼晚年因抗擊金兵陣亡)。《三國演義》里有諸葛亮,《水滸傳》里有吳用和公孫勝。《三國演義》里有劉備,《水滸傳》里有宋江,二人都是以仁義出名,動不動就哭,可是大家就喜歡跟著他。
但是,你可能已經注意到:這兩部書里對人物的稱呼不太一樣:《三國演義》里,習慣稱為“英雄”。《水滸傳》里,習慣稱為“好漢”。當然也可以調換過來,你把梁山一百零八將稱為“英雄”沒什么問題,可是要把諸葛亮、郭嘉、龐統,甚至周瑜、魯肅稱為“好漢”,是不是有些怪怪的?
問題出在哪里呢?我們先看一些表面的不同:
第一,三國英雄的武器比較單調,絕大多數是刀和槍。關羽的刀,張飛的矛,趙云的槍,你可能比較熟悉了,但突然問你東吳大將韓當使什么兵器,好像很陌生。其實韓當出場的時候,書里明明寫著“使一口大刀”。誰知十七年后赤壁之戰時,韓當和焦觸交鋒,“手起一槍,刺死焦觸”。難道是韓當玩刀玩膩了,這時居然又使起槍來了?但你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合適——事實上你根本不會注意他用什么兵器。所以《三國演義》注重的,是這個人在戰爭中的作用,而不是上戰場的武功。
但《水滸傳》的兵器五花八門。光五虎將的兵器,就是刀、矛、槍、狼牙棒和鐵鞭,竟然不重樣!此外,武松的戒刀,魯智深的禪杖,李逵的板斧,解珍、解寶的鋼叉,項充、李袞的藤牌,燕青的小弩,扈三娘的套索,出身農戶的九尾龜陶宗旺的兵器竟是一把鐵锨。區別水滸好漢,兵器是很重要的標志。兵器可以代表人物性格,而且從不更換。
第二,三國英雄的本領比較單一,武將就是在馬上打仗,文官就是坐在營寨里出謀劃策。但是水滸好漢的本領五花八門,除了五虎將這樣專職打仗的武將,還有打探消息的戴宗,縫軍旗戰袍的侯健,寫文書的蕭讓,刻印章的金大堅,殺牛宰羊的曹正,飛檐走壁的時遷……
第三,三國戰爭的規模大,水滸戰爭的規模小。三國里打仗,動輒就是“精兵數萬”,甚至“八十三萬人馬”。可梁山最開始只不過“五七百小嘍啰”,鼎盛時期也不過一萬多人。所以,梁山好漢總要親自上陣,帶頭拼殺。
二
看完這些表面的不同外,我們就可以找一找深層次的不同。水滸好漢和三國英雄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們的出身不一樣。
大多數三國英雄,不是豪強大族,就是文人名士。曹操的父親曹嵩當過太尉;袁紹家族“四世三公”,一直是朝廷重臣(相當于蔡京);孫堅父子都是太守級別的官員,董卓、馬騰、劉表、劉璋、公孫瓚等不是皇親國戚,就是地方軍閥。
“好漢”這個詞,宋代之后,一般是稱呼底層社會的英雄的。所以三國英雄里最像水滸好漢的,是劉備、關羽和張飛。即便如此,劉備恨不得把“劉皇叔”三個字寫在臉上,讓所有人知道他的貴族血統。諸葛亮說自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其實那是他謙虛。諸葛亮的叔叔諸葛玄可是豫章太守,諸葛亮自幼跟隨叔叔生活。沒有諸葛玄的支持,諸葛亮怎么可能一邊“躬耕隴畝”,一邊卻對天下大勢了解得如此透徹?周瑜是江東名士,精通音樂,“曲有誤,周郎顧”。而梁山上精通音樂的鐵叫子樂和,只是一個民間歌手,在登州監獄當獄卒;善于吹笛的馬麟,只是個閑漢。
所以,三國是貴族、高官、豪強、名士的游戲場,沒有普通百姓什么事。但水滸好漢出身都是底層社會。宋江是縣里的小吏,吳用是教書先生,公孫勝是游方道士。梁山主要戰將,除了呼延灼官職稍高之外,關勝是巡檢,林沖是禁軍教頭(普通武術教練,雖然“八十萬”很唬人),魯智深是提轄,都是低級軍官。再往下,三阮是漁民,劉唐是流浪漢,李逵是獄卒,張青、孫二娘是小酒店老板,王英是趕車的,郭盛是賣水銀的,石秀是販牛馬的,湯隆是鐵匠……即便有錢的如晁蓋、盧俊義、李應、穆弘,也只是土財主,而絕不是權貴。
用一句話概括,梁山好漢的主體是市民階層。因為來自底層,所以他們沒有制式的兵器,兵器都是揀自己順手的用。因為來自底層,他們引人注目的刻印、裁縫、打鐵、獸醫等技能,都是謀生的本領。因為來自底層,擺在他們面前的首要問題就是生存。魯智深趕路,想的是如何找碗粥喝;林沖在草料場,想的是如何打酒暖身子;武松在柴進莊上,想的是下一個地方去投奔誰。而不是像曹操和劉備,坐在花園里,青梅煮酒論英雄。三國英雄早已不需要為吃飽穿暖發愁,他們想的事情更宏大、更長遠。
三
但是,這樣說來,《水滸傳》就比不上《三國演義》嗎?不是的,對底層社會的描寫和關注恰恰是《水滸傳》的優秀之處。這就反映了更深層的不同:兩部書的重點不一樣。
即便是在《三國演義》里,打仗也需要軍旗戰袍,調兵遣將也需要寫文書、刻印章,武將們打完仗也得吃喝,這些基礎工作總得有人做。可《三國演義》是不管這些的。刺探軍情,只要一個“探子來報”就可以,然后高層就開始商議軍機大事了。至于這個探子在敵前吃了多少辛苦,擔了多少風險,姓什么叫什么,《三國演義》是不關心的。
你看到三國英雄叱咤風云,可曾想過:他們的戰馬病了誰來治?他們的盔甲壞了誰來修?可曾好奇過:廖化當年是如何落草的?甘寧早年為什么做水賊?張角兄弟經歷了什么,一定要造反?
《三國演義》寫押運糧草,幾句話就到了前線。你可曾想過:這些運糧的士兵,如果趕上酷暑怎么辦?他們辛苦不辛苦,想不想家?《三國演義》里,幾句話就打下一座城,你可曾想過:城里小販的生意還能不能做?晚上居民能不能出來閑逛?會不會有人趁火打劫?
每個小人物的經歷和情感,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們的價值甚至比英雄們的龍爭虎斗更寶貴。但這是粗線條的《三國演義》不能告訴我們的(當然,這也不是它的任務)。它只關心打下了哪座城,占領了哪座關。即使是頂級英雄如劉關張、諸葛亮,也不過是天下大局棋盤上的一顆顆棋子。
《三國演義》沒告訴你運糧的士兵的處境,但《水滸傳》細細地告訴你了:楊志押送生辰綱,熱得嘴里冒火;《三國演義》沒告訴你亂兵進城時老百姓的遭遇,但《水滸傳》細細地告訴你了:“剿匪”的官兵下到三阮村子里,就要大吃大搶,老百姓不堪其擾。《水滸傳》沒寫皇帝和大臣是怎樣商議大事的,但告訴你社會的底層是什么樣的,官府小吏如何敲詐勒索,街頭潑皮如何橫行霸道。
所以,《三國演義》宏偉,《水滸傳》細致。《三國演義》放眼的是天下大事,《水滸傳》著重的是個人經歷。《三國演義》是“鳥瞰”,《水滸傳》是“特寫”。因此,你會發現,《水滸傳》寫千軍萬馬打仗,反倒沒那么好看。《水滸傳》最擅長的,就是給你講一個個好漢的故事,你跟著他們的視角,和他們一同悲喜,一同去看更大的世界。
(摘自《為孩子解讀〈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佟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