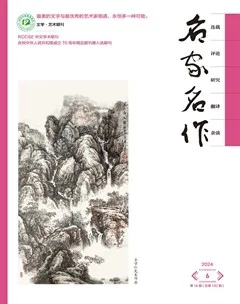張載《正蒙》對先秦儒家“氣論”的繼承與發展
[摘 要] 中國傳統哲學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進程,先秦時期產生的“氣論”亦是如此。在先秦儒家傳統哲學中,普遍認為氣與天、人性有所關聯。“天含有氣”揭示了天是萬物的本原,“氣中有性”表明氣是構成萬物的材質。“氣論”指“氣性論”,也指“性中含氣”的人性理論形態。先秦“氣論”完成了將“氣”從字詞演變為哲學本原的過程,這離不開先秦儒家的思想積累。被世人稱為橫渠先生的張載,在繼承先秦儒家“氣論”的同時,將“氣論”思想發展到了巔峰。張載在《正蒙》中提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的理論,正是“氣論”哲學思想的充分表達。通過對先秦儒家“氣論”的產生進行追根溯源,闡述“氣論”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挖掘張載《正蒙》中的哲學思想。在張載“氣論”的理論架構中,探索其對先秦儒家“氣論”的繼承與發展。
[關 鍵 詞] 張載《正蒙》; 先秦儒家; “氣論”思想
一、“氣論”的演變歷程
所謂“氣”,從一個單字的簡單概念逐漸發展為蘊含豐富內涵的哲學范疇,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歷程。“氣”這一字源,最早見于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氣的解釋。“氣,云氣也,象形。”許慎從宇宙論的角度出發,用天地之氣來解釋氣,即氣是指天地中有形有狀的云氣。甲骨文、金文中也有“氣”這一字體,于省吾指出“氣”存在三方面含義:一方面氣指云雨之氣;一方面“氣至”同“迄至”;一方面氣有終、盡之意。[1]366于省吾為“氣”增加了多種表意形式。《國語》中記載:“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2]伯陽父從天地中陰陽二氣的升降變化、相互作用來說明地震發生的原因。他從邏輯意義上用氣來解釋《周易》中卦爻的變化消長,從認識論的角度用氣來表明天地有其自身秩序。伯陽父陰陽二氣理論的產生,回答了氣生成萬物這一問題。陰陽二氣說與儒家的“氣論”思想有密切聯系,這深刻影響了之后張載的哲學思想。除此之外,由陰陽二氣衍生的六氣也成為重要的哲學概念。陰陽風雨明晦都是氣,其是進一步將陰陽二氣具體化的結果。宇宙天地充滿氣,人作為其中的一分子,同樣離不開氣。血氣作為人體中的自然之氣,用血氣來形容人的有關性格和性情,血氣說對中國哲學的影響尤為深刻。氣字上升為哲學范疇,血氣的哲學視角普遍趨于倫理道德性,更多地將“氣”作為世間萬物的本源。血氣說開啟了中國哲學關于“氣說”,這一精神性解釋的先河。[1]378“氣論”是中國古代的自然觀,它將陰陽二氣的動靜變化、人性中蘊含的血氣等進行描繪,展現出別有風格的“氣性論”。先秦儒家中的“氣論”思想,從宇宙論角度出發指向人性精神。如孔子從人的血氣出發提出要戒氣養身;孟子從人的心性出發提出要養成浩然之氣;荀子提出人的治氣養心離不開禮的結合。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這些表述里,用氣來解釋人作為生命物質的存在,氣很明顯被賦予了生理性的意義。在中國哲學概念中,與西方本源概念相接近的有“本、本根”等,均指向宇宙萬物生成的本源。這種本根,均指宇宙萬物生成之根源。王充和張載等儒家思想中的本根則指“氣”。[3]氣作為一種生命物質的本源存在,不同時期的儒家對“氣論”思想都有著不同的詮釋。“氣論”作為本根、本源的思想,儒家吸收“氣論”思想并與人的仁義道德結合,因此有了孔子作《十翼》與荀子的天人觀。由此可見,“氣論”對儒家人性論思想的影響是很大的。
二、“以氣論性”
“氣論”作為中國天人之學的基本結構,屬于“天”的一部分。儒家將“氣論”引入人性,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春秋時期,孔子揭示了仁學與“氣論”并興于世,開創了“性與天道”來構建儒家的宇宙觀。孔子對《易》的態度重在“觀其德義”,他在《易傳》中將氣的概念發展為“精氣”。“精氣為物,與天地相似”,陰陽二氣在孔子的影響下已經不再簡單的用于卜篩,而是作為孕育天地萬物、養成君子仁德的依據。孔子從天人關系的視角來回答人的生命來源。在孔子看來,人的“性”與“生”息息相關。“性相近,習相遠”,這里的相近指人先天的本性相近。每個人生而含有氣,這種氣秉承的是天地之氣。不僅如此,孔子還將人的德性來源歸結為天地之氣。《論語·述而》中有言:“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4]99他認為人的德性和氣有關,即人的德性也是天所賦予的。《論語·季氏》中有言:“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即衰,戒之在得。’”[4]173孔子一方面指出人生命中的血氣要經歷從盛轉衰的過程,另一方面指出要通過“戒”來養成君子之德。孔子認為,人的生命要經歷從年少、成年再到老年三個階段,而血氣也會隨人的生命變化而具有不同的表現。年少時期的血氣處于未定型時期,人的身體筋骨尚未發育成熟,因此要戒掉誘惑以養成健全之身;成年時期的血氣處于充滿活力時期,人的身體已經發育成形,要戒掉爭斗以理性來約束自己;老年時期的血氣處于衰弱時期,人的身體逐漸衰退,要戒掉患得患失以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認為“逾矩”的發生與血氣有關,因此通過“戒”來調理人的血氣。
孟子也將氣視為人性的根源。《孟子·公孫丑上》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踐行。”[4]368孟子“養氣說”是對先秦“氣論”的新發展。他結合孔子的思想,以“氣”來論證人性本善,使氣從邏輯上不再依存于人的生理需要,而是從道德層面出發,將人的意志與氣相融合。《孟子·公孫丑上》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4]233孟子言氣,主要探討氣與志的關系。他提出了“持志,無暴其氣”的修養功夫,氣是人體中的重要內容,志與氣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心中有志才能領導和調動意氣。因此,孟子強調保持志與氣的專一性。孟子的浩然之氣是指通過不斷收集和積累義氣所得,它的特征是集義所生、具有道德性質的氣,是一種逐漸由內在的吾善養轉向充塞天地的生命之氣。孟子認為心性論與“氣論”的融合是構成人性論的關鍵,“以志養氣”使儒家的人性道德與氣融合,闡述了養成浩然之氣就是要養成大義、至剛之氣。孟子認為心性論與養氣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在儒家“氣論”思想史上,孟子的獨特貢獻是關于浩然之氣的思想以及提出了養氣方法。[5]
荀子作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從天人觀的基本立場出發,提出天以氣化生萬物,陰陽二氣相結合是構成萬事萬物變化的根源。《荀子·禮記》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6]190荀子認為天地間的萬物都來源于天地結合,陰陽二氣不斷推動著事物的變化。荀子第一次明確了“天”是客觀的自然界,強調天地之氣與陰陽二氣,這種氣的產生和存在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荀子·正名》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6]255荀子人性論的核心是“性樸”論,“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這一命題使人生而有的天性與陰陽二氣相聯系,也就是在人性中便蘊含著氣的存在。荀子認為人性是天所賦予的,肯定了人的天性是氣的產物。人的天性是由陰陽二氣和合感應而產生的,天性中所表現的情感就叫情。荀子揭示了氣與心的關系,人的憂慮是因為人心的欲望導致的,人的氣志反過來也會影響人的性情。荀子在《荀子·修身》中提到了“治氣養心”的方法:“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6]24血氣剛強需要用柔氣進行調和;當人的思慮過于深沉時,要調和血氣達到平易溫良。荀子主張以柔氣與平易之氣調和人的性情,通過禮這一路徑來達成“治氣養心”。
先秦儒家都繼承了人性是由天地陰陽二氣所生,在“氣論”的基礎上進行關于人性的研究與探討。關于“以氣論性”的思想,孔子首次提倡并將其發揚,經過孟子與荀子對人的血氣與心志相結合,使“氣論”思想的內涵不斷豐富起來。
三、張子《正蒙》“太虛即氣”理論建構
張載在《正蒙》中將陰陽二氣與儒家“氣論”思想進行融合,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張載借《周易》闡述自己的氣本論思想,其哲學思想對中國哲學的理論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氣性論”首先承接先秦儒家的“重氣”思想,在宇宙論中將道德價值貫穿整個理論體系。張載儒家思想中的本根直指向“氣”,張載在《正蒙》開篇《太和》中已經提出了“氣本體”論:“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于太虛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氣自足也,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為之損益。”“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7]49太和所謂道,大道化于無形之中,太和是指自然、萬物在內的氣之全體而言,在這種本體場所中,氣的轉化是一個整體的變化過程。正如《黃帝內經》中的“恒先之初,迥同太虛。虛同為一,恒一而止”。太虛即氣的“無無”,“氣”這種無形狀的存在,并不是什么都沒有,而是將二者合為一體而談。氣作為一種無形無狀但依舊存在的客形,就表明氣自身處于一種周而不盈的自足狀態。氣的自足性承接孔、孟、荀子的思想,相當于氣是一種自然而然生成的結果。張載的“太虛即氣”,將氣作為本原的存在。氣猶如冰的凝結、水的稀釋一樣,氣有著冷與熱的矛盾,熱的具體表現形式為稀散,冷的具體表現形式為凝聚,氣通過稀散與凝聚形成不同的存在,并且以不同的變化形式做矛盾運動。正是由于冷與熱的矛盾對立作用,萬物得以化生。張載在《正蒙》中說的“太虛即氣”突破了空間內涵,在形而上學中確立了“太虛即氣”的本體論。太虛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絕對空間的,類似于一aTQvdnzmoFRqSwJwOjBucQ==種空曠的房間一樣,氣可以包含世間萬物和承載萬物,氣在太虛的空間中不斷發展,氣的聚散不會隨著變化而改變,正如冰稀釋成為水一樣,這只是氣的客體形態。張載從“太虛即氣”的理論建構中,形成一種以氣為本的宇宙萬物生成論,在哲學理論上使“氣論”達到了思想巔峰的高度。《乾稱篇》上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7]158《乾稱篇》下曰:“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爾。”[7]162氣會進行動與靜的矛盾運動變化,是因為其自身在一體的狀態下,氣與性其實是一體的。張載也談“以氣論性”,“言吾之形色,與父母無二,即與天地無二也”,將人性歸結為天地之性,乾卦和坤卦作為陰陽兩卦代表了天地的具體的象,而用父與母來比喻這種天地之象。他將氣作為宇宙本源的同時,也將家族宗法、民胞吾與的這種仁愛統一起來。張載的人性論,認為天地之性同氣本體一樣,都是一種生生不已的自發狀態。 《誠明篇》曰:“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誠者,神之實體,氣之實用。”天“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7]83在張載看來,人性與天道、氣體是相通的,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因為誠;人之所以長久之道,也是因為誠。儒家的誠者,在人身上表現出人性的道德。誠即是人類精神的實體,也是氣的實際應用。張載在談太虛即氣的理論建構時,將人所存在的精神與天所賦予的道氣結合,“以氣鑄誠”,也就是在氣的規定下,重新解釋性與天道二者之間的關系。張載的“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不僅僅是從形而上的本體論來談氣與天的關系,也是從形而下的認識論來談氣與人性的關聯。張載對先秦時期儒家“氣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實現了將“氣”闡釋到本體論這一層面。不僅如此,張載“橫渠四句”的使命,就是為如何成為圣人尋找一個形而上的根據。張載通過《正蒙》闡述自己的思想,用自身的實踐行動做到了繼承先圣之心、發展儒學思想。
參考文獻:
[1]吾淳.中國哲學的起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66-378.
[2]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曾振宇.中國氣論哲學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99-368
[5]趙法生.氣論視域下的孟子性善論[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4(4):1-10.
[6]安小蘭,譯注.荀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6:24-255.
[7] 張載,撰.王夫之,注.湯勤福,導讀.張子正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49-166.
作者單位:寶雞文理學院政法學院